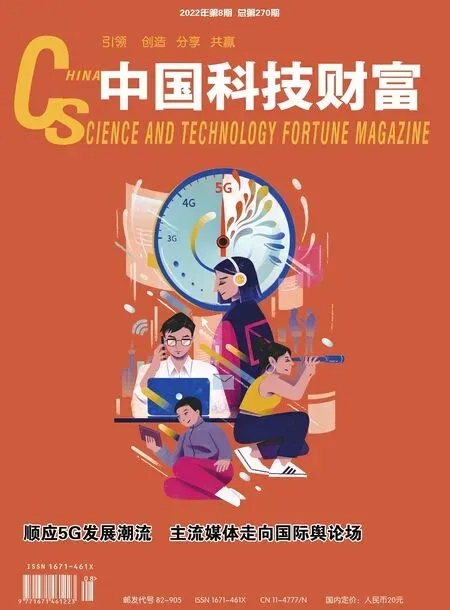生物合成技術釋放綠色潛能
文/本刊記者 畢文婷

提到生物合成,你會想到什么?是生活在實驗室中的微生物,還是出現在科幻電影中的“復制人”?其實,生物合成沒有那么遙遠,它能夠合成淀粉、合成肉制品,具備服務于工業生產與農業轉型的巨大潛力,甚至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降低資源消耗等方面,也能發揮獨特優勢。
在“雙碳”目標的指引下,低碳生物合成正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將如何發揮創新優勢進一步實現產業化應用?日前召開的香山科學會議上,與會專家就上述話題開展了討論。
變革經濟增長方式的重大需求
以二氧化碳、生物質、有機廢棄物等可再生資源為原料,利用工業菌種、工業酶等生物體為工具進行物質合成的生物技術,是低碳生物合成的核心內涵。
中國科學院天津工業技術研究所所長馬延和告訴記者:“低碳生物合成由于原料低碳可再生,且在生產過程中利用生物體系,將傳統高溫高壓的化工生產變革為常溫常壓的生物制造,不但可以實現工業生物碳匯與低碳循環工業,而且降低了物質制造過程中的碳排放,減少了碳足跡,已經成為引領化工、材料、能源、食品、醫藥等化學品生產的工業制造新模式。”
世界自然基金會報告預測,到2030年,包括食品農業、生物燃料、生物基材料與化學品在內的低碳生物合成產品有望每年減少20.7億—26.0億噸的碳排放,對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據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測算,2020年我國排放二氧化碳約112億噸,需要在經濟社會的各領域各環節發展綠色低碳技術。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學校長譚天偉認為,低碳生物合成是變革經濟增長方式的重大需求,是實現工業制造綠色、創新發展的重要突破口。
生物技術原始創新能力有待提升
“綠色生物制造已展現出巨大潛力。”譚天偉說道。2021年發布的《美國生物基產品行業經濟影響分析》指出,生物基產品每年可替代約940萬桶石油,相當于每年減少1270萬噸二氧化碳排放,相關產業還為美國創造了460萬個就業崗位。
我國擁有充足的生物質資源,年可利用量約7億噸,譚天偉說,若能合理利用這些資源,集中替代有限類別產品,將具有解決千萬噸級化工產品的能力及潛力。“要實現這一目標,還需要加強科技創新,解決產品結構、關鍵技術及核心裝備等問題。”
從當前的發展情況來看,絕大部分生物合成路線還無法與傳統的石化和農業路線競爭,技術研發鏈條長、核心技術供給不足、對生物體的認識遠低于化學催化劑等,是擺在低碳生物合成面前的巨大挑戰。
馬延和說,我國需要加強基礎、應用基礎與前沿技術研究布局,加快原料、工具、過程與裝備等領域的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推進實施“低碳生物合成”方向的科技專項,以全球化視野統籌創新資源和要素,圍繞二氧化碳等碳資源轉化利用與物質低碳合成的生物路線,突破一批顛覆性生物合成技術和產業核心關鍵技術,提升我國生物技術原始創新能力,為我國生物產業發展提供引導和支撐,為生物經濟發展提供新引擎。
完善生物安全監管勢在必行
需要引起關注的是,生物合成技術的快速發展帶來了監管模式和治理體系的新挑戰。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分子植物科學卓越中心研究員趙國屏建議,應重點做好與現有政策、法規間的銜接,同時梳理現有監管政策中存在的問題、漏洞及空白,開展長期的監管與政策研究。
澳門大學助理教授杜立提出從三個方面入手創新法律規范機制,“首先,采取以科學為基礎的立法方式促進科研創新;其次,基于技術風險明確分類監管的標準;最后,在政策制定和立法環節引入公眾參與,讓合成生物科技商業化更具有社會許可性。”
與會專家認為,加強低碳生物合成技術自主創新,形成綠色生物工業核心技術能力,是保障我國生物產業安全、掌握生物經濟發展戰略主動權的關鍵。同時,我國也應建立科學和高效的管理體系,加強生物安全和倫理風險評估與監管,建設全社會參與的科學傳播平臺,培養具備跨學科研發創新和多領域綜合創業能力的人才隊伍,以進一步發揮低碳生物合成技術在經濟社會全面綠色低碳轉型中的引領帶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