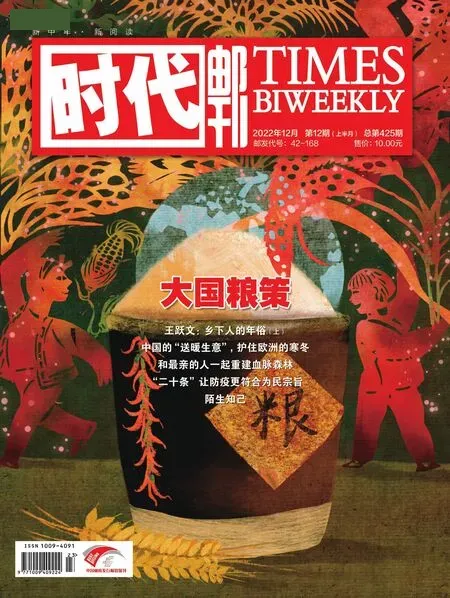退休之后,他們開始追夢
● 王霜霜
對于退休之后的生活,人們通常有很多想象——可能是忙碌的,從職場這個戰場退下來之后轉戰家庭,照顧兒孫;也可能是閑逸的,每天睡到自然醒,有打不完的麻將和跳不完的廣場舞;又或許,會有一種被時代拋下的落寞感。
然而,也有一些老年人在退休之后滿懷熱情與憧憬,去追求那些曾經的夢想。

逐夢影視圈
付頎今年66歲,從銀行退休后,做了一名群眾演員。他臉型圓潤,額頭平整,花白而稀疏的頭發齊整地梳向一邊,平常出演的多是領導干部和行業精英。
年輕時,付頎忙忙碌碌。退休后,他也沒有閑下來。疫情前,他飛去全國各地拍戲,最南去過昆明,最北去過海拉爾,一周只有兩三天在家。他說,這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興趣。
今年夏天,付頎接了一部金融題材的戲,取景就在他曾經工作過的銀行營業廳內。他扮演的是一個被詐騙的老人,不顧銀行工作人員的勸說,非要把大半輩子積蓄轉給騙子。
進入表演狀態,他站在自動匯款機前,用銀行卡指著柜員,破口大罵,情緒非常到位。表演結束,導演夸贊付頎:“您的戲是有生活的。”
臨走前,負責安保的工作人員認出了他,從銀行的監控室走出來問:“您是不是付行長?”
這樣的場景,付頎再熟悉不過,他曾當過8年的支行行長,見過許多要給騙子轉錢的老年人,工作人員勸他,他還罵人,甚至有的還要動手揍人。
付頎成為演員最初是“曲線救國”。年輕時,他喜歡寫作,寫過詩歌、劇本。在金融圈摸爬滾打幾十年,他經歷了很多。有些事,比電視劇還驚險。退休后,他就把這些事寫成了故事。《影子行長》是他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來自他的親身經歷,一個關于銀行巨額資產丟失的故事。他還寫了一本父子關系的小說,叫《父與子的戰爭》。
他想把自己的小說拍成影視劇,但沒有合適的機會。有人給他出主意,“你長得像領導干部,要不先去做群眾演員,進影視圈認識一些人。”
有一次,他聽說,一個劇組正在招能演高級干部的演員,便特意穿了西服打了領帶趕過去。剛到那兒,副導演就把他叫住,讓攝影師給他拍了張照,“你被選上了,就是你了。”工作人員對他說。
到了劇組,付頎才知道他出演的是馮小剛導演的電影《我不是潘金蓮》。那是一場領導開會的戲,一群被選中當干部的演員站成一排,付頎本來在最邊上,后來,副導演看他派頭像大領導,讓他去坐主席臺的最前面,扮演一位副省長。
副導演問他:“這開會的戲,您能拍嗎?”
“我這輩子沒干別的,就開會。開會是我的本專業,我知道什么時候該笑,什么時候該皺眉,什么時候該點頭。”他開玩笑似的說。
大燈一開,三臺攝像機架著,幾十人圍著,有舉著錄音桿的,有拿著燈的,在主席臺上就座的付頎表情松弛,絲毫不怯場。
當退休焦慮到來
退休前,付頎幾乎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每天六點半起床忙著去上班,晚上七八點鐘才能到家。當支行行長時,一個月要值七八天的夜班,大年三十都在單位值班,從沒在家里看過春晚。因為平時經常要出差,孩子的家長會也沒參與過。而那些個人愛好,也全置之腦后了。
92歲的盛瑞玲出生于戰亂年代,年輕時忙于工作,也同樣顧不上照顧孩子,更別提什么個人愛好。盛瑞玲祖籍山東,退休前,在中國礦業大學做校醫。1962年,她和丈夫響應國家號召,一起去援藏,成為西藏那曲人民醫院的醫生。2歲的兒子被安排在成都的幼兒園,由當地政府負責照顧。
醫院放探親假時,盛瑞玲帶著兩包糖去幼兒園看兒子,一進園,兒子喊她“阿姨”。她的眼睛立刻濕潤了,覺得自己虧欠兒子太多。
58歲時,付頎收到了讓他退居二線的通知。之前,每天一到辦公室,一大堆文件等著他批,“這個事情,一定注意以下幾點……”每天有開不完的會,有時是同事聽他講話,有時是他聽領導講話。
突然有一天,辦公室通知“開會了”,他剛要去,站起來才反應過來,“是人家去開會,沒有我。”有時在辦公室坐一天,一個電話都沒有。“一下子覺得自己被人拋棄了,沒用了,挺失落的。”
忙了一輩子,總盼著能清閑幾天,沒人找、沒會議、沒電話……可突然之間擁有了這一切,又有點無所適從。
51歲的春鳴剛剛退休,她也度過了一兩年的彷徨期,常常整宿整宿睡不著。退休前,她在企業里做管理,負責宣傳工作。即將50歲時,春鳴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是提前轉崗退休,還是再熬5年,等到了法定退休年齡再退。
剛進公司時,春鳴還是個二十出頭的小姑娘,之后結婚、生子,如今孩子上大學了,她依然在這家公司。她說,那個年代的人認為,工作是為了讓老年生活有個保障,所以一家單位要待一輩子,“熬”也要熬到拿退休金。
在公司,春鳴一個人擁有一間辦公室,工資待遇不錯,工作干得順手,壓力也不大,但春鳴還是想逃離,“我喜歡自由地安排時間,不用請假,不用加班,不需要在旅途中做計劃、寫文案。”
年輕時,她有過幾次辭職的沖動,但也僅僅是沖動,那個年代的人思想保守,大家都不敢辭職。“辭職,再去找另外一份工作,感覺有點可怕。”春鳴說。
她的頸椎和腰椎不好,失眠嚴重。退休前的一年,她常覺得暈乎乎的。一份工作做了30年,對每天重復的工作內容,春鳴早已倦怠。年紀越大,越覺得時間不等人,實現自我的渴望越強烈,內心還有股沖動,想嘗試一些新東西。
但家里的經濟壓力不小,兒子將上大學,之后留學、成家立業……需要花錢的地方還很多。再忍5年,意味著家里多一筆收入。單位也不贊成她退休,她向領導提了幾次提前退休,都被勸回了。
50歲生日臨近,春鳴越發焦慮。“你整天哭哭啼啼的,那就別猶豫了,退了吧,明天早上就去向領導提。”丈夫說。于是在生日前一周,春鳴申請了提前退休。
第二次選擇
春鳴從小喜歡朗誦。前兩年在朋友的建議下,她開始做有聲主播。她在家里布置出了一個錄音間,一張桌子被窗簾圍住,上面掛滿了紅紅綠綠的玩偶和枕頭,這樣就可以減少噪聲。桌子上,擺放著一個話筒和一臺電腦。
去年,她還申請了一家機構有聲教學老師的職位。和她一塊應聘的多是科班出身,有播音主持專業的畢業生,也有電臺、電視臺的主持人。
那段時間,春鳴每天中午不吃飯,抓緊一切時間看書,還在網上找各種資料,歸納總結。她試音經驗豐富,更能有針對性地回答學員的問題,在這方面,她知道自己更占優勢,但還是焦慮得四天四夜沒睡好。“我心眼小,做事苛求完美。”好在,考核最終通過。
盛瑞玲退休后則成了一名老年模特,她從小長得就漂亮,上學時,學校組織演出,她演過《昭君出塞》里的王昭君,還演過《牛郎織女》里的織女,以及《紅樓夢》里的襲人。她愛美,鞋子臟了一點就要刷,總被父親批評。
“現在大家都喊‘美女’‘帥哥’,我們年輕時,是不能夸人好看的。”盛瑞玲說,那個年代,大家都不談“美”。但在那個大家都穿黑色、灰色、藍色衣服的年代,盛瑞玲還是買了各式各樣的假領子穿在衣服里,為此,她被調到食堂,負責收飯票。
現在老了,有了皺紋和白發,她反而可以盡情地美了。80多歲時,盛瑞玲文了眉,還會定期做皮膚管理,每3個月燙一次頭發。如果第二天要出門,她當晚洗完澡后,會用4個卷發棒把頭發卷起來,提前給自己做好發型。
成為模特后,盛瑞玲變得更加自律。每天睡到早上6點多自然醒,等太陽一出來,就去公園里遛彎;晚上堅持站立一段時間,預防駝背。飲食方面她也很講究,早餐喝一杯豆漿,吃一顆紅棗,加一個雜糧豆包。中午,吃點魚蝦等高蛋白的食物,晚上則吃得很少。
唯一的“壞習慣”是有點網癮,每天玩手機都要玩到11點,她在短視頻平臺有十幾萬粉絲,大家都叫她“神仙奶奶”。她還拍過300多條廣告,經常在電視上、地鐵站里播放。身邊的很多同齡人都不在了,她說,自己大概是“忙著愛美,忘記老去”。
做行長時,付頎到企業,都是廠長、書記出來接待,眾星捧月。但在影視圈,很多時候群眾演員的聲音沒人聽。
一次,拍一場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戲,劇組發的戲服是夾克,付頎向副導演反映,那年代沒這樣的衣服,結果被罵了一頓,“讓你穿什么你就穿什么,怎么那么多事。”
剛開始,付頎不習慣,覺得不被尊重。后來,他就告訴自己,以前的工作已經翻篇了,既然愿意來拍戲,別的群演怎么干,自己就怎么干。讓蹲在路邊吃盒飯,就別惦記食堂。
出去演戲,他就帶張報紙,往地上一鋪就坐下。起身就把報紙一卷,放回兜里。
疫情前,為了拍戲,付頎總到處飛。他拍一天的戲,報酬有時是300元,有時是1000元。老伴數落他:“掙個仨瓜倆棗的,要病了,一住院成千上萬塊錢就沒了。”
付頎從來沒覺得自己退休了,只是覺得自己換了份工作。人生有很多活法,他不喜歡睜開眼就打麻將,喝點小酒就睡覺的生活,“只有當你在工作,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在創造的時候,才是真正的活著。”
春鳴在社交平臺分享自己退休后的工作,有人評論:“既然退休了,就好好享受生活吧,要不干嗎提前退休。”
春鳴回復:“工作和工作是不一樣的吧?”退休后,春鳴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了,她再也不用被鬧鐘叫醒,心靈和身體都由自己掌握。
在她看來,退休是讓自己再做一次選擇,換一條道路重新開始。現在,春鳴過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每天有點事做,有點閑心,還有一點小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