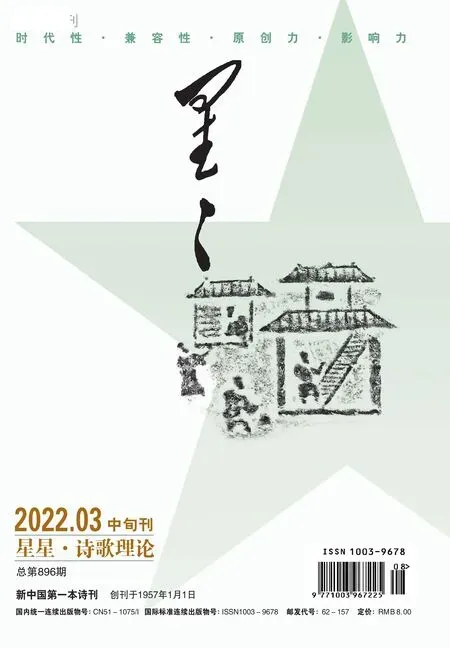試釋西川“終極之問”
范劍鳴
一
當代人在談論杜甫、熱愛杜甫時,離不開對他身世的一個認知:他承擔了離亂時代的種種灰塵。事實上,苦難經歷與詩性人生之間,容易引發一種極具張力的好奇與探問,影響著、吸引著各種階層的讀者,增強俗世社會對詩歌/詩人的敬意。苦難中生發的詩性,是自古而今世所稱道的人性光彩,無論是在信仰基督的國度,還是儒釋道融合的東方之國。
我們幾乎都會以熱愛杜甫的方式,驚訝地目睹著昌耀的人生滄桑:一個重傷歸國的志愿軍戰士,一個自愿投身西部建設的熱血青年,一個土伯特人的女婿……這當然是昌耀一生的世俗身份。作為一名詩人,昌耀又是一個純正藝術的鐘愛者和堅持者。對于人生遭際中的苦難,西川等眾多詩人都曾關注。吳思敬說:“苦難的經歷、獨特的氣質、強悍的內在生命力造就了昌耀。”對于當下從底層冒出來的詩人,昌耀簡直是一則勵志典故。
在昌耀的文學人生中,有一個事實令人頗為好奇但又不大好深究:當苦難加身,詩人對苦難際遇如何認領?詩人的受難意識如何內卷或外溢?人生的苦難經歷與執著的藝術創造之間存在什么關聯?這既涉及到詩人立身的世界觀問題,也涉及到藝術探索的方法論問題。不可忽視的是,苦難經歷和創作取向之間,按照一些知識分子的目光來看,昌耀顯得有些不可思議。我屢屢注意到,不少評論者在談及昌耀詩歌中那些主流意識的詩歌作品時,試圖理解它們對于昌耀本人的意義。
西川曾以“橫空盤硬語”(原指向語言特征,此處兼指文學史影響)來形容昌耀帶給當代中國詩壇的驚嘆。不能忽視的是,西川在《昌耀詩的相反相成和兩次偏離》中,除了對昌耀大加贊賞,還就昌耀的苦難擔當和創作取向,留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終極之問”。1993年8月19日,昌耀寫下一首名為《毛澤東》的詩。西川曾以一個大學者的抱負,直面這首少有人提及的詩作。事實上,要完全揭開昌耀思想底色與創作激情之間的關聯,不能不注意這些“過于主流”的作品。在《昌耀詩的相反相成和兩次偏離》一文中,西川肯定了這首詩,認為是超越了眾多同題之作。而在肯定之后,西川又對創作動機充滿疑惑:昌耀為什么會寫下這樣一首詩?他認為這值得玩味。
西川說,“適其時,跨越整個80年代的中國思想啟蒙運動業已結束,市場經濟剛剛起步。昌耀雖遠居青海,但對國內風起云涌的政治、經濟形勢不可能一無所知。他并不非得寫下這樣一首詩”。“我不清楚昌耀是在怎樣一種心境下寫出的這首詩。是他遇到了不快的事、黑暗的事,感覺有必要重新向毛澤東呼告?還是他面對現實生活,忽然涌起一股懷舊的沖動?還是他撇開了個人榮辱,一頭扎進了大歷史的浩瀚之流?”西川的這個“終極之問”,是順著昌耀主流意識而提出來的。就是說,不但包含“為什么要寫”,還包含“為什么要這樣寫”。他論述說,“在昌耀的作品中,我、土地、人民、歷史這些概念是相通的”,進而他以《我躺著。開拓我吧!》為例得出結論,認為年輕后輩的詩人“大概不會像昌耀在1962年2月的詩歌里這樣寫”。西川認為,“很難理解,寫這首詩時他已身處流放之中了,可個人的榮辱似乎根本阻攔不住昌耀與土地的切近”。
這里的“很難理解”,不只是說年輕一代自覺的創新意識,還包括個性張揚年代對主流意識的理解差異。西川繼而提到昌耀1980年《山旅》一詩的副標題“對于山河、歷史和人民的印象”。西川分析說:“人民是這片山河上的人民,人民是歷史中的人民,我是人民的一分子,我是山河間的一粒塵埃。這都是對的,正確的,要說這里面有什么問題,那就是,這一切都太正確了。”——“太正確了”顯然是一種反語和揶諭,盡管西川認可駱一禾對昌耀的贊語:“民族的大詩人從我們面前走過,可我們卻沒有認出他來!”西川的這種態度,我一直表示理解,又無法完全理解。西川顯然有著學貫中西的知識涵養和通觀世界的鑒賞能力,但對待本土大詩人卻顯得復雜起來。他的“靈魂之問”表明,他尚未完全理解昌耀藝術成就與主流意識之間的關聯。
二
昌耀與主流意識、主流詩壇的關系,一直是評論家們回避不了的話題。要么以“偏離主流”來突出昌耀的獨特性,比如敬文東說,“因為他一直與主流詩壇保持著審慎的距離,在西北高地獨自咀嚼著荒寒與寂寞”。時而又以因其“緊隨主流”而表達某種遺憾和嘆息——當然,這里的“主流”其實是兩個概念,有不同的指向。比如西川說,“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昌耀與新中國成立以來主流文學意識形態的隱隱的關系,這種關系不能用‘好壞’來評價,但它卻標明了昌耀與后來詩人的不同”。無論正反視之,所述之時都難免表現出對意識形態問題的敏感和謹慎。
筆者以為,要徹底解開昌耀思想底色與創作格調之間的關聯,不能不正視那些“追隨主流”的篇什。昌耀在《兇年逸稿》中寫道,“我是土地的兒子”。這樣的宣告不能不讓人想到艾青《我愛這土地》。流寓邊關之時,昌耀固然心心念念以“萬言書”求解放,但同時也為邊關風情所吸引。我不清楚昌耀當年是否經過這樣的反思,但至少我們現在設身處地,這樣的反思仍然是成立的:邊地既然是人類的棲居之地,流放的苦難是否就高于邊地的人民?自身的命運是否需要脫離于邊地的人民?我是人人,人人即我。這是詩人一個特殊的反思視角。正如知青文學既有表現受難的《靈與肉》(張賢亮),也有感恩鄉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史鐵生)。在這里生存棲息,人民,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對應著昌耀的人生曲線和藝術曲線,昌耀詩歌歷程可大體分為三個時期:流放期、旅行期、審思期。早期作品與“主流詩壇”的差異,曾帶給詩壇強烈震撼。一個流放邊地的受難者,在絕境中仍然對生存之所充滿審美的眼光。從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綜合作用的結果來看,個體的人永遠會處在逆境之中,這是一種宿命,因而抱怨命運其實是一種內心不夠強大的表現。我一直不大喜歡流放者對世界、對社會、對國家充滿“正義”的嫉恨心態。我欣賞的態度是,保持人性的堅韌度,活出本真的自己。而昌耀無疑是理想的模式。
用他的話說,“有緣感受這一境界是一種幸福”“喧囂一旦沉寂,泰然處之僅有作人的本分”。此語出于昌耀散文《一個早晨》,副題是“遙致一位為我屢抱不平的朋友”。昌耀的經歷引發眾多人“抱不平”,但昌耀自身卻如此釋然,“由此憶及自己的生活之路,想起自己在這里磨煉了幾十個春秋。我把世代隨雪線升降而棲居在此的族群稱作眾神。生存一度變得如此簡單而質樸:勞動,繁衍生息。享受最具廣度的愛情,而后像發酵的面團松解、揮發、熔融,去無影蹤,不留給本質潔凈的草原一絲痕跡。本然地,也不給后世留一些心理壓力。有緣感受這一境界是一種幸福”。
在那個年代,寫詩是一種精神的自慰,是心靈的自修。難能可貴的是,昌耀不是以詩來抒情、言志、載道,高喊“相信未來”。而是以詩審美,更值得人們敬重。這讓我想起了早年的一次文學講座。有位教授引出賀敬之《桂林山水歌》,認為“在饑饉的年代”唱贊歌,是詩人缺失良心的表現。我卻持反對意見,正面血淋淋的現實,固然是文學的責任,但把那個年代詩人的審美活動,都與“載道”的使命對立起來,也不是正確的文學觀念。
在蒼涼的西部邊地,可以想象昌耀的生存處境會如何艱辛,對于一些人來說,在那樣的處境中仍然吟詠“啊,美的泥土/啊,美的陽光/生活當然不朽”,簡直不可思議。我理解,所謂絕境,坦然處之即為順境,心態簡樸比滿腹悲辛會更好。這也是海子思想苦悶的時期,仍然吟唱“活在這珍貴的人間/泥土高濺/撲打面頰/活在這珍貴的人間/人類和植物一樣幸福/愛情和雨水一樣幸福”。當然,海子詩歌頻繁出現的“痛苦”一詞是哲學意義上的,并不是現世經歷,與昌耀真實的苦難經歷完全不同。
這是苦難意識的“內卷”。并不能說昌耀對苦難毫無意識,僅僅是觀光客對邊地牧童的“文學想象”。事實上,昌耀被流放邊關進而又被判刑,他一直寫“萬言書”試圖解放自己,長詩《大山的囚徒》中就真實表現出受難意識。根本的問題是,面對苦難的心態和事后的反思,是走向沉重的控訴還是命運的自釋,這兩者都是自然而然的表現,但卻有著極為不同的思想底色在支撐。在“生存一度變得如此簡單而質樸:勞動和繁衍生息”的境地,昌耀追求精神的富強,“以詩療饑”的受難者形象,才是真正的詩人形象。
當然,讓他在絕境之中能夠支撐下去的,顯然不只是藝術的安慰,還有內心的飽滿,包括人生觀的適應。“我們遠在雪線那邊放牧的棚戶已經/坍塌,惟有筑在崖畔的豬舍還完好如初。/說泥墻上仍舊嵌滿了我的手掌模印兒/像一排排受難的貝殼/……”,詩人這個時期的創作,就像邊地牧場的“掌模”,強烈烙在了讀者的心中。在我的文化記憶中,“西部二王”(王昌耀、王洛賓)有相似的曲折經歷,也有相似的藝術追求。
三
西川之問,其實就是昌耀藝術創作思想底色的揭曉之處。這首詩真實的寫作動因頗為出乎意料。2020年9月,曾任《西南軍事文學》雜志編輯的王久辛在微信上曬出舊雜志圖片,筆者由此得知,《毛澤東》一詩系昌耀應他之約為該雜志組一期同題詩而誕生。帶著西川的“終極之問”,筆者與王久辛先生進行了深入探討。在跟筆者的交流中,王久辛對應約之事頗為難忘,對昌耀此詩也頗為激賞,言談中頗以故交昌耀為榮。他認為在十余人的同題之作中,昌耀一詩富有深厚的歷史感,思想內涵最為高遠,無疑最具特色。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正義”,我頗以為然。
昌耀寫作這首詩,結尾寫明是詩人自己“一樁心事的了結”。它并不是像西川所觀察的那樣,動機不明。盡管只是應約而寫,詩人并沒有應景而權作應付,反而是頗為珍惜,收入了親手編定的《昌耀詩文總集》。他似乎知道,所有別人為他所做的選集,都不會收錄它。同樣讓人意外的自珍自選之作,還有1959年的小長詩《哈拉庫圖人與鋼鐵》。由此可見,鋼鐵,領袖,這些“過于主流”的元素都是經過他自身思考和觀察得出來的文化符號。
作為讓西川不解的是,“按說他是一個飽受中國社會主義經驗之苦的人”“他似乎是在經歷了‘死去活來’之后對歷史重新表示認同”。西川直接把這種寫作與西方詩人進行了比較,認為“與東歐那些經歷過至少名義上相同的社會主義經驗的詩人來寫(米沃什、赫伯特、申博爾斯卡等等),他們肯定會得出相反的結論”(《昌耀詩的相反相成和兩次偏離》)。這就比較值得玩味。與其說昌耀很不西方,不如說是昌耀對本土文化有更充分的認知和自信。西川注意到詩中“痛快”這個詞,認為昌耀他把神壇上的領袖還原成了魯迅所說的“山大王”的角色,這種理解應該是準確的。作為海子的生前好友和遺著編定者,西川不可能沒有注意到,其實海子有一首跟昌耀極為類似的作品,這首詩叫《秋天的祖國》,副題是“致毛澤東,他說‘一萬年太久’”。
把昌耀和海子的這兩首詩歌進行比較,同樣是一種越超具體歷史和人物的寫法,領袖人物成為別具內涵的文化符號,“他稱我為青春的詩人愛與死的詩人/他要我在金角吹響的秋天走遍祖國和異邦”。這里的“他”,等同于任何歷史上的民族先祖。令人驚嘆的是詩人跟領袖的對話關系,雖然一個是追隨和歸依,一個是受命和呼應,但都是借此表達自己的內心,完全不同于詩經中莊重至極的“頌”。倒是海子詩中的最后一句,“如今只有他 寬恕一度喧囂的眾生/把春天和夏天的血痕從嘴唇上抹掉/大地似乎苦難而豐盛”,跟昌耀一樣包含著對歷史一種極為類似的思辨。
四
西川之問,還有另一個真實的答案。要說那時昌耀心底有什么“不痛快”,確實有。但不是出于個人的際遇,1980年代就開始堵在心里。昌耀在《〈巨靈〉的創作》一文中說,“那些天我是如此苦悶,且懷有幾分火氣。我郁郁不樂,有如害著一場大病,——我反思。我在心底設問。我相信自己無可指責。終于我不能不稱對方為矯情者了,而稱自己不敢矯情,也不敢應矯情之命。我戲稱對方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天外來客——外星人,聲稱對方那種咄咄逼人的聒噪是我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甚耳熟的了。豈止于耳熟?國家、民族為之蒙難。得到實惠的也許僅是矯情者?……”由此可以推知針對昌耀的責問真不少。有一個“對方”跟昌耀進行了對話,進行了交流,進行了規勸。從昌耀的火氣中,這個好心的“外星人”應該是抱有不同文化觀念的朋友。結合當時的1980年代中期,不難推知這個“外星人”是西方文明的使者,是中華文明的否定者。而昌耀《巨靈》一詩的核心意象,卻是詩人對本土文明的抱定。這就不難理解,昌輝在《毛澤東》一詩最后寫道:“一篇頌辭對于我是一樁心意的了卻。/對于世紀是不可能被完成的情告。”此處意思。是如此接近于彼得·漢德克的一句話“要是不這樣表達自己的看法的話,那我的人生中就缺少某些決定性的東西”。
詩人不接受這種規勸,不是由于性格執拗,而是精神世界的自足。昌耀說,“這些感情活動在寫訖的《巨靈》里是不易找到軌跡的了,但詩中自我心底呼出的那一聲獨白——請問這土地誰愛得最深——卻正是這種活動的直接產物。問話并不需要回答,那只是我胸中的一股長氣,一股義憤,也許憋有多年了,今日方得釋然”。這里所說的釋然,就是另一種“痛快”。昌耀進而表明了自己的立場:“我寄情未來,相信未來,我情意無限而纏綿。這魅力源于我對中華民族精神文化、人民創造力、祖國觀念、自然規律、歷史法則——統一被我視為巨靈的實體存在的真誠信仰。”
不知道海子和昌耀的同題詩比較著讀,是否可以再次驗證西方經驗與東方經驗的各自殊異,從而扭轉一批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經驗”問題上慣于類比的習氣。一個曾經的受難者,如果能夠充分地表現人間苦難,本來也是文學的重大貢獻。作為老詩人,昌耀應該有這樣的文學認知。在新時期文學中,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一樣意義重大。作為歸來或復出的詩人,昌耀卻作出了不同的選擇。
1993年前后,是詩人昌耀的行旅期。詩人仿佛如文學史所謂的“回歸派”,結束流放后重歸文化工作崗位,行走在西部大地,感受著時代新氣息,為“新邊塞詩”運動增添異彩。從某個角度說這個時期的昌耀仍然在“以詩療饑”,對詩藝的執著探索,不正是可見他內心充滿“藝術的饑餓”嗎?這時期,昌耀寫作了不少反映主流意識的詩篇,比如《劃呀,劃呀,父親們》,副題為“獻給新時期的船夫”。這首當年被賦予主旋律色彩,充滿“政治抒情”意味的作品,是一首可以超越時代的作品,一首情緒飽滿、造境獨特的文化詩。
而昌耀后期詩歌,是走出了煉獄的智者。就在這個時期,昌耀仍然寫下主流意識明顯的《一個中國詩人在俄羅斯》,一首結合了人類社會理想的反思之作。他對人類精神的生存焦慮和精神困境進行著反省和審思,超現實的詩境,深邃的思悟,成熟自如的語言,爐火純青地表達著他的思想。智性之火錘煉的詩歌語言,順利抵達現代詩的又一個高峰。比照前期作品,不難發現可對昌耀當年的苦難經歷作一種新解:許多時候,人的苦難是一種“被苦難”。流放之苦是事實,但后期走出邊地回到省城西寧,昌耀作為思想者同樣并未擺脫精神的苦難。家庭的不諧,情感的危機,出書的艱難,南歸的夢想,種種俗世的現實問題和都市文明的負面,令昌耀的詩歌出現大量焦慮和憂思。縱觀昌耀各個時期的作品,整體上基調是昂揚明亮的,這顯然與他的思想底色有關。
也許有人會好奇,昌耀為什么沒有像米沃什、布羅茨基他們一樣,陷入人類文明的深度省思。當然,這可以理解為國情不同所致,同時也是個人選擇的結果。昌耀立足本土仍然創造了漢語詩歌的高度,而“過于主流”的作品雖然不是他作品的標高,但卻是結實的基座。觀察昌耀受難意識,明顯能感受到他內卷多于外溢。我們不能不認為,昌耀詩歌中具有深厚的“大地品質”。大地承擔一切,又包容一切消化一切,生生不息,四季輪回。“我是風雨雷電合乎邏輯的選擇”,這個昌耀寫于1999年的自敘文標題,正好也是大地品質的自證。
西川曾在答《青海湖》雜志訪談時說,“昌耀是詩歌里的儒者”。正義,理想,這些思想的基因正是對“儒者”形象的注解。考慮思想底色的因素時,昌耀的詩歌精神與其以“正確”來辯識,不如以“正義”來區分。儒者的定位,自然也是“終極之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