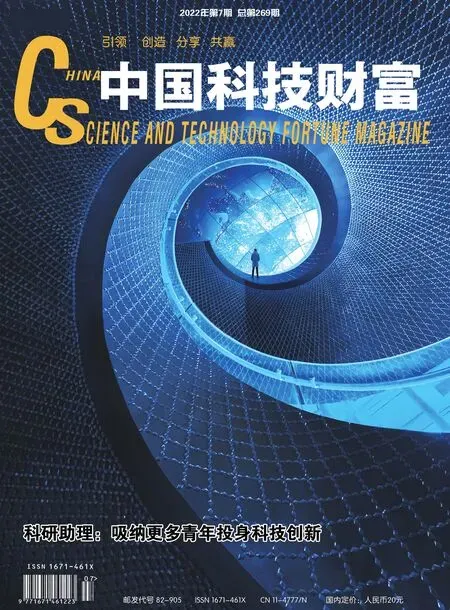3D打印能否實現人類器官移植自由?
文/本刊記者 羅朝淑

近日,美國3D生物療法公司首次在人體試驗中成功植入了來自患者自身細胞的3D打印耳朵。該公司聯合創始人丹尼爾·科恩宣稱,這項組織工程技術在真實世界的應用,對于小耳畸形患者以及更廣泛的再生醫學領域來說,都是一個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這一案例的成功,為下一步目標,包括治療鼻子和脊柱缺損,以及乳腺癌手術后的乳房重建,甚至是器官移植奠定了基礎。”
這一令人激動的消息不免讓人們有了遐想:人類是不是真的快要實現“器官移植自由”了?長生不老或許不再是夢?
支架材料降解速度不易控制
知名耳再造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整形外科醫院外耳整形與再造中心二科主任章慶國在接受科普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臨床對小耳畸形的耳廓再造已經研究了30多年,但目前支架材料和種植細胞兩項技術存在的瓶頸還有待突破。
章慶國介紹,小耳畸形是耳廓的先天性發育不良,臨床上通常表現為耳廓畸形,并常常合并外耳道閉鎖和中耳畸形。目前治療小耳畸形耳廓的方法,主要是利用患者自身的肋軟骨或有機高分子聚合物如多孔聚乙烯作為移植物的支架。但由于聚乙烯是人工合成材料,患者移植后會產生排異反應,可能10年或20年甚至一兩年后,支架就會被排出來。現在用得最多的耳廓支架,是由一種叫聚乙交酯(PGA)的可完全降解高分子生物材料制成,這種材料做成的支架降解后,生長在其表面的軟骨細胞會通過不斷增殖取代其位置,讓移植后的耳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體組織,不會發生排異反應。
“但后者的問題在于,可降解材料的降解速度不易控制。支架降解速度如果大于軟骨生長速度,耳廓就不能獲得比較強的支撐力,可能會慢慢塌陷,最后縮成一團。”章慶國說,“如何讓支架材料的降解速度正好匹配上軟骨細胞的增殖速度,還不能有太明顯的局部早期反應,且能很好接納種植在其上的細胞,是再生醫學亟待克服的材料難題。”
種植細胞生長分化面臨較多難題
“即便很好地解決了支架材料問題,但種植在支架上的軟骨細胞是不是能夠長成性能良好的軟骨,形成的軟骨形態和強度能否達到要求,最后長成的耳朵結構是否均勻,都決定了耳廓再造的成功與否。”章慶國說,這些痛點也是再生醫學發展面臨的關鍵問題。
如今,再生醫學有了3D打印技術的加持,各種先天性遺傳缺陷疾病和各種組織器官損傷的治療是否會變得容易?
章慶國認為,3D打印雖然是一種先進的塑造方法,但在器官移植上卻面臨著更多難題。比如,正常結構的軟骨細胞分化或增殖本來就不太好控制,要在3D打印所需的生物墨水中成長、分化和增殖,軟骨細胞會不會保持穩定?一旦軟骨細胞纖維化變成纖維細胞,那就失去了功能。
我國再生醫學領域的探路者、上海交通大學退休教授曹誼林在接受科普時報記者專訪時也表示:“3D打印技術近年來發展迅速,在打印不具有生命力的材料方面比較成熟,但用它來打印具有生命力的結構,還面臨很多困難,最關鍵的就是要解決支撐材料和活體細胞的結合問題。這是3D打印生命體繞不開的難題。”
曹誼林說,目前這個自體細胞3D打印耳朵最終是否能夠完全長成自體組織,還有待長期觀察。
人類或將步入器官替代新時代
我國是世界上較早進行再生醫學研究的國家。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科學家就開始了對再生醫學的探索。1997年,當時還在哈佛大學醫學院進行博士后研究的曹誼林,在裸鼠背上成功再生人耳廓形態軟骨,首次向人們展示了組織工程技術“再生”人體組織修復缺損的可能性。這只背上長著“人耳朵”的“人耳鼠”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轟動。
但彼時這只耳朵嚴格意義上來說并不是真正的人耳,只是有著人耳形態、由牛的軟骨細胞發育而成的一塊軟骨。考慮到軟骨細胞的來源、如何保持軟骨形態、生物安全性等問題,這項技術一直都沒有投入應用。
2018年,在經過20多年的摸索和探究后,曹誼林利用來自患者的軟骨細胞和復合生物可降解支架,在體外設計了患者特異性耳形軟骨,為5名患有小耳畸形的孩子創造了新的耳朵。在之后幾年的隨訪中,這些新的耳朵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美學效果,且軟骨形成成熟。
業界認為,隨著近年來再生醫學的蓬勃發展,人類或將步入重建、再生、制造、替代組織器官的新時代。在不久的將來,科學家或許能找到修復或替代人類器官的密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