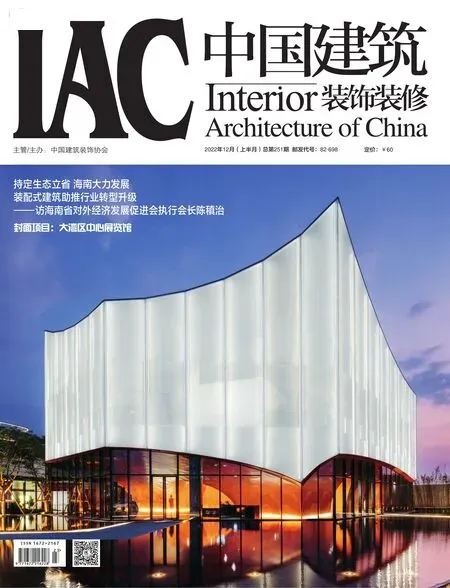從海達·莫理循鏡頭下看清末民初老北京店面設計
劉賀然 莫日根
海達·莫理循是澳大利亞著名攝影家,在中國旅居期間拍攝了五六千張20 世紀30 ~40 年代自然風光和社會風貌的攝影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她更偏愛拍攝中國的民居建筑、街景店鋪和反映民俗風情的傳統工藝照片[1]。本文選取1933 年以后她在北京工作時拍攝的北京街道與鋪面招牌的照片為對象進行研究,從清末民初老北京店面與街道的相互聯系、店面和招幌的呈現形式,分析老北京店面設計中所存在的文化內涵以及對當代商業店面設計的啟示。海達·莫理循的這些攝影作品留存下較多的民俗風貌,為人們留下了很多老北京的鏡像記憶,也為現代店鋪的裝飾設計提供了新思路。
1 老北京店面狀態
從海達·莫理循的鏡頭下可以看出街道與店面聯系緊密,先有街道和胡同的劃分,繼而才有店面和商區的形成。清末民初正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正陽門牌樓”與“大柵欄西門”這些照片傳遞著時代變遷的豐富歷史信息,直觀地反映了老北京的街道文化和風土人情,大到商業街道與鐵藝門頭,小到居民生活的寧靜小巷,都是當時生活的真實寫照。那些正在建設城市的機械設備,是老北京城正在走向近現代的印證。
自古以來,在我國的城市規劃中為了體現中庸的哲學思想,街道的營建都會圍繞著1 條中軸線展開。自元大都起,北京城就開始以1 條貫穿南北的中軸線為基礎布局,規劃人口和商戶的分布,使其在相應的空間上發展形成商業區。老北京的前門大街就具有這樣的特證,兩側的胡同直抵城市內部,其中的商鋪門面為街道增添色彩,二者相輔相成。
明朝建立后,北京城被分為36 坊,坊下分成若干牌,牌下設置若干鋪,鋪管理若干胡同。為了便于管理,在胡同口設置柵欄,早啟晚閉,形制簡單,材料為木質。至清朝,這一制度得到進一步鞏固。乾隆皇帝提出“柵頂仍釘木板,書寫街道胡同各色”,于是各種各樣的胡同門頭出現在大街小巷。清末,大柵欄胡同內的商戶們集資將柵欄改為鐵質,為門頭賦予了更復雜的裝飾和文化內涵。這些鐵藝門頭曾經是為了分隔大街與胡同,方便管理,到后來更多是作為老北京胡同的一大特色,保存和延續了老北京的特色文化,成為了北京的門臉兒[2]。
雖然大柵欄處于商業中心地帶,但具有規模的卻不止大柵欄這一處。據記載,在正陽門的甕城月墻外,東西為荷包巷,(原本東曰帽巷,西曰荷包巷,后統稱荷包巷)本為臨時市集,商民于此支棚架屋,日久遂成為商場。行人輻輳,轂擊肩摩,可以看出前門與大柵欄之間的荷包巷也非常繁榮熱鬧。此外,還有其他連接著北京街道的小地名商鋪與前門大柵欄共同形成清末民初老北京整體的商圈風貌。清末民初老北京街道如圖1 所示。

圖1 清末民初老北京街道(來源:海達·莫理循攝)
2 老北京店面與招幌美學
2.1 店面的呈現形式
清末民初老北京的店面形式多種多樣,《中國建筑藝術圖集》中的《店面簡說》將老北京店面分為牌樓式、拍子式、重樓式和柵欄式4 種類型(圖2),而在海達·莫理循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這些類型的影子[3]。從一些關于市井街區的作品中不難看出,大多數店鋪除了設置牌樓,每家還設有匾額、招幌等元素組合。在老北京,使用最多的就是鋪面牌樓,也稱作門臉兒樓,這種牌樓一般緊貼著商鋪裝修在鋪面外,在裝潢方面風格各異。
(1)牌樓式店面,如圖2(a)所示。參考《北京夢華錄—商號店鋪》可知,這種店面一般都是采用圓木柱,用鐵條將其釘在房檐柱上,再用斗拱托起樓檐。斗拱下是平板枋,斗拱之下、店門之上放上華板,按高度定制華板的層數,按面闊定制華板的塊數,六柱五間重檐十樓的牌樓在當時是最為氣派的。有些小的店面也會修兩柱一樓作為門臉;也有的商鋪只設置柱而沒有樓,這是因為兩柱一樓中的“柱”有財氣沖天、直沖云霄的寓意;還有較次的店面用牌坊而不用牌樓,這樣的牌坊柱中間較為簡陋,沒有斗拱樓檐的遮蓋,也沒有匾額,直接將字號和品名寫在華板上。
(2)拍子式店面,如圖2(b)所示。以海達·莫理循拍攝的一家家具店為例,雖因年久失修有些破舊,但還是可以看出拍子式店面的典型特征。這種店面在店鋪平頂上方豎起欄桿,在欄桿上標出店面的字號,拍子的掛檐板較為出挑,以更加醒目。拍子的柱子是按照店鋪本身的間數分配,柱上為承重枋,承重枋上方安掛檐板。掛檐板起著裝飾作用,上面以雕花覆蓋;一般還會將兩邊安上垂柱,可以使掛檐板向外延伸,垂柱上附有蓮花裝飾。拍子在民居中通常用于宅院的內檐,而店面上的裝飾用于外檐,一般小本生意或風格內斂的商家會使用拍子裝飾店面。
(3)重樓式店面,如圖2(c)所示。以海達·莫理循拍攝的一處已廢棄的店面為例,結合《店面簡說》中的描述,繪制了重樓式店面的大致樣式。顧名思義,重樓式店面從遠處看就好像有層疊的屋頂,相對古典且富有詩意。與拍子大不相同,重樓式的屋頂多用硬山頂,也有的用平頂或歇山頂,上層屋檐用滴水瓦當,通常出現在最繁華地帶的街角,作為胡同或大街的轉角處的“濃墨”存在。
(4)柵欄式店面,如圖2(d)所示。此處以義盛當的招幌為例,結合資料繪制出柵欄式店面樣式。柵欄式的店面一般防御性功能較強,多存在于典當鋪和錢莊,作保衛和防范功能。在店面門前設置1 排木質欄桿,上面有簡單的瓦頂,正門處設置較窄的門樓作為出入口。在一旁會立起1 根柱子,柱子的中上方也會安帶有雕花的上下坊,枋間安置直欞。

圖2 店面的4 種類型(來源:(a)選自《北京夢華錄—商號店鋪》,(b)~(d)為海達·莫理循攝)
2.2 招幌的呈現形式
清末民初時,招幌作為商業性的標志發展得非常成熟。各行各業的招幌都有著自己獨特的形態和風格,按照招幌的設計風格可以分為葫蘆形、銅錢形、帽子形、燈籠形、三角形及菱形等;按照材質可以分為木質、銅質、玻璃、棉絨、絲線及組合材料等;按照呈現形式可以分為實物幌、模型幌、形象幌及文字幌4種形式。按照呈現形式劃分能夠更加完整、清晰地陳述招牌幌子的風格特點,下文將重點分析這4 種形式[4]。
(1)實物幌,如圖3(a)所示。實物幌就是將所售賣的商品實物直接懸掛作為招幌,這種較為粗獷的方式可以讓顧客很直觀地了解店鋪中的商品類別,是一種門檻較低且性價比較高的招幌形式,但并不是所有物品都可以直接懸掛在街市上。例如,一些食品放置時間久了就會失去色澤和風味;還有一些銷售昂貴物品的店鋪也不會直接懸掛,一是以此作為招幌有被盜竊的風險,二是這樣懸掛并不含蓄風雅,過于張揚。
(2)模型幌,如圖3(b)所示。模型幌是將商品實物做成適當大小的模型,具有實物的基本特點卻不具備實物的用途。這種招幌不僅避免了實物幌的弊端,還為街市增添了較強的藝術氛圍。
(3)形象幌,如圖3(c)所示。形象幌為人們提供了另一種相對抽象的招幌形式,有些商品的特征通過形象的隱喻更能讓人心領神會。例如,油布雨傘店的招幌不僅意象地表達出了雨傘的形狀,而且人們可以通過招幌清楚得知所售之物為何。
(4)文字幌,如圖3(d)所示。文字幌是最直白的一類招幌,在我國傳統商業中運用最廣,通常只以1 ~4 個字就可以說明店鋪的營業范疇。例如,琳瑯滿目的糕點鋪招幌如果做成別的形式會比較費力,但做成簡單直白的文字幌則性價比極高,經濟實惠且形式風雅。

圖3 招幌的4 大形式(來源:海達·莫理循攝)
此外,隨著各種各樣的西式文化流傳到我國,街道上偶爾也會豎起西文招幌。這些形形色色的幌子既作為店鋪的行業標志,又在傳承過程中逐漸變成商業文化的物質遺存。它不僅融合了民間美術和市井文化的傳統設計理念,也為近現代商鋪設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啟示。
2.3 店面與招幌的聯系
店面與招幌都是店鋪重要的組成部分,缺一不可。由于店面牌樓的形式與建筑相仿,會讓人誤以為牌樓就是店面本身,但嚴格意義來講,牌樓并不算是店鋪建筑,只是為了裝飾醒目而放置的“大型招牌”。在老北京的店面中,牌樓一般都承載了牌匾的功能,而且商鋪通常將匾額和招幌都設置在牌樓的華板上或直接挑出吊下來,有的商戶為了使自己的店鋪更加醒目,會在店面掛檐板的高度位置挑出一個龍頭型的構件,專門為了懸掛招幌。招幌的形式多姿多態,有較為簡潔直接將商品象征性掛出的;也有稍微復雜些的,在挑頭下懸掛一條橫杠,兩端雕刻著龍頭,杠身也被雕刻覆蓋,然后再懸掛所用的招幌。
清朝時期的北京街市已經非常繁榮,店面與招幌的設計作為一種特定的傳統廣告和民俗語言表達方式,少不了民間手工藝人和工匠的奇思妙想。店面設計經過漫長的智慧凝結形成了4 種店面形式,也代表著不同的文化內涵,牌樓式店面象征大氣,拍子式店面象征內斂,重樓式店面象征繁華,欄桿式店面象征著守衛與防范。招幌的形式隨著不同的商業需要具有不同的功能,人們走在街上不用特意去看店鋪牌樓,通過招幌就可以得知店鋪的經營性質。到了清末民初,工商業在老北京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交通的便利使得各地商品貨物流通廣泛,各樣的商業習俗相互交融,使得招幌的形式更加豐富多彩。
3 老北京店面設計中的文化內涵分析
3.1 中西文化的交融
傳統的招牌幌子傳承千年,經久不衰,不僅具有濃厚的民間特色,而且在時代發展過程中與西方文化交融,逐漸成為我國民俗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過精心設計的造型和挑選的用料,賦予了招幌深刻的意義,無不透露著古老的民俗文化印記。老北京的街道店面設計因很多外來文化的沖擊而變得豐富多彩,除了本地傳統民俗文化特色的鋪面招幌,更多兼具中西風格的店鋪裝飾如雨后春筍般涌出來,這種相互滲透的融合形式逐漸風靡大街小巷。
由于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響,很多店家為迎合人們對于西化建筑語言的追捧,一般都會將店鋪門面裝飾成充滿西式風格的“洋門面”,這其中可見大量的西式山花、帶瓶狀欄桿的外凸陽臺、磚砌平拱券結構的門窗或者西式線腳的運用。“洋門面”的加設形式可分為架空式和嫁接式,前者就是在商店原有立面前加設1 個西式風格的門面;后者則是在原有店鋪上面疊加西式風格的樓層,其所表現出與傳統屋頂的無縫銜接成為當時商鋪店面的一大顯著特點[5]。例如,當時的盛錫福時帽莊,就是嫁接式的中西結合式店面,最底層是中式鋪面,上有牌匾,在2 層加建了西式風格的欄桿陽臺和開窗,頂部還參考了西式教堂的拱形設計。
也有的店鋪外部形式運用的是西式構圖,內在卻是中式比例。例如,老北京的瑞福祥綢緞莊,平面布局為傳統四合院,但臨街建筑卻改為樓房,形成了平房與樓房相結合的新興四合院。
另外,還有一種以鋼結構和磚木結構相結合的構建形式,整體裝飾紋樣偏向巴洛克風格。這種建筑借鑒了西方教堂的建筑形式,但內在結構和比例均為中式,相當于西式外表下的中式本體建筑,也是我國早期中西合璧的商業建筑。這些店面設計中,中西裝飾符號的隨意穿插和混搭,使商店的立面造型變得更加飽滿豐富,同時也顯示了老北京在文化方面的包容性。雖然這些元素與裝飾僅體現在外在形式上,但卻深刻反映了當時西方文化正潛移默化中被東方文化兼收并蓄。
3.2 生活方式的改變
清末民初時,老北京街道的店鋪不僅從外表上開始逐漸轉變,售賣的產品也開始有了新的變化。一些從未進入我國的新鮮玩意兒不斷涌現,使得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小到時裝、金絲邊眼鏡、懷表、化妝品、電話、電風扇和電暖爐等百貨,大到咖啡館、酒吧、電影院以及照相館等休閑娛樂場所,這些新事物通過衣食住行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剛開始,這種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只是星星點點出現在少數貴族中,后來逐漸被大眾所熟知,自然而然就出現了相應的商鋪。當人們密切相關的生活環境發生了變化,也就改變了我國千百年來延續的傳統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6]。學習西方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被迫接受,而是我國在歷史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是進入現代社會的必經之路。雖然外來文化打破了傳統的知識結構,但也逐漸構建出更適合今后發展的文化體系。
3.3 商業民俗的傳承
招幌是我國商業民俗的一大特色,長久以來不僅有實用性意義,更是商業民俗文化的傳承。傳統意義上的招牌和幌子出現于原始社會末期,是社會生產與交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7]。到了清朝,這種商業廣告早已非常成熟,反映出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老北京商業習俗中非常重要的表現形式。傳統的店鋪門臉—招幌成為最普遍的行業標志,不僅用于標明店鋪經營的商品類別或服務項目,還具有促進消費和宣傳的功能。
從宏觀來看,這些招牌和幌子在街區之中起著一定的藝術作用,久而久之形成了濃厚的民間特色,成為街市中美麗的風景,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和傳統文化。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時期,老北京鋪面文化與西方文化互相滲透與交融,使得千百年不變的街道與鋪面都煥發出生機。大多商鋪將新的民族文化內涵應用到門臉設計中,在加入西式裝飾的同時保留了中式設計的底蘊。
4 對當代商業店面設計的啟示
4.1 當代商業店面裝飾存在的問題
傳統的店鋪招幌傳承至今,相當于店鋪的廣告。現如今廣告形式多樣,商家通過各式各樣的手段與媒介給消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卻忽略了傳統意義上的招幌帶給人們的直觀感受。多數商家以博人眼球的設計原則來設計店面與廣告牌,雖然在形式上豐富多彩,但在內涵上卻是千篇一律,導致各個城市的商業街店面裝飾毫無地區差異性、民族差異性及文化差異性。商家只顧及經濟利益,卻忽略了更重要的當地城市街道地域性的體現,文化內涵也被逐漸遺忘[8]。
從海達·莫理循鏡頭下的老北京街道可以看出,傳統的招幌雖然形式簡單,但卻明確地表達出所售商品的內容,并且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內涵。相形之下,當前的一些廣告形式過于奇特復雜,而且很少考慮環境承載力,甚至給整個街區的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設計師們應將傳統招幌的生活氣息和簡潔性特征與現代的商鋪廣告設計結合,進行研究設計。
4.2 當代商業店面裝飾的設計策略
目前,店面設計在靈感方面應多借鑒傳統思想和文化。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傳統文化和地方特色,一個好的店鋪廣告應做到因地制宜。清末民初的店面設計雖然融入很多西式元素,但整體店面的招幌體現了人們對于美好生活和事物的向往。例如,北京地區的招幌大多透漏著深厚的文化底蘊,顏色較為濃烈,儒家思想的“仁、義、禮、智、信”也深刻融入招幌中,同仁堂、義盛當以及海達·莫理循拍攝的老北京街道中關于招幌的照片均有所體現。而江南地區的招幌更偏向于清新淡雅,圖案也較為柔美,各種各樣的民俗元素被用作裝飾圖案和造型。根據不同地域設計具有當地風格的店面,不僅會得到當地消費者的認同,也能從眾多店鋪中脫穎而出。隨著時代的發展,店面裝飾設計應借鑒傳統商業文化的精髓,在傳統文化的內涵下延伸和發展今后的店面裝飾設計。
5 結語
海達·莫理循拍攝的寶貴影像資料可以很具象地幫助人們了解老北京清末民初商業貿易的民俗文化和市井文化,雖然曾經聳立的一幢幢牌樓與店鋪都因時間的推移逐漸被取代,但正是這些店面牌樓支撐起老北京街道胡同的文化底蘊。每種店面招幌的呈現形式都是前人智慧的結晶,與人們的生活和社會發展都有著必不可少的聯系。本文通過探究民間傳統的設計理念和工藝,為現代店面裝飾及其設計提供了良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