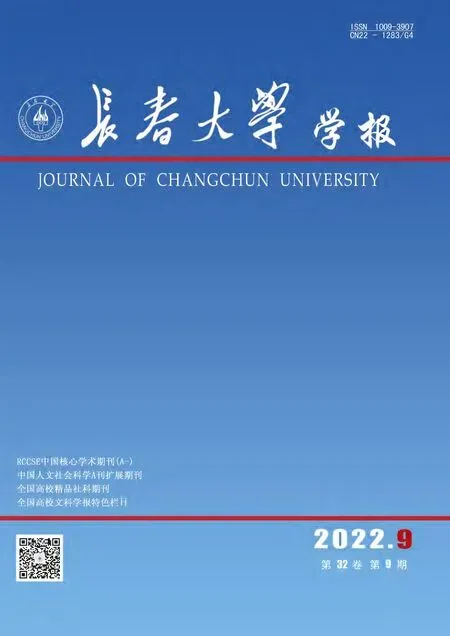嚴譯《原富》中政經類術語使用之得失
張宜民
(安徽農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合肥 230036;安徽大學 歷史學院,合肥 230039)
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有大量的泛政治經濟類專詞。由于晚清西學詞匯匱乏,嚴復翻譯《國富論》時,并無多少現成的譯詞可供使用,只能嘗試自創。前人關于嚴譯《原富》譯詞的研究還有待深入。嚴譯《原富》譯詞數量有多少?異化與歸化方法比重幾何?嚴譯《原富》譯詞使用有哪些得失?給予我們何種啟示?諸如此類的問題需要我們去研究。
依托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嚴譯《原富》[1](上下冊),全面檢索其中斯密亞丹傳、譯事例言、發凡、正文、嚴復按語及腳注,得到1200余條泛政經類譯詞,“音譯詞”類約占55%,“意譯詞與傳統詞”約占38%,“音譯意譯拼合詞”及“音譯+補充解釋”詞約占7%。經過進一步篩選,發現比較嚴格意義上的國民經濟循環(生產、分配、消費、積累)內的經濟類名詞有480余條(意譯詞占77%,音譯詞占19%,音譯意譯拼接詞占4%)。
一、嚴譯《原富》術語中音譯詞的構成及得失
晚清時,大量的西學概念、西方事物在中文中沒有對應的詞匯,音譯法是首選策略。“嚴復是近代第一個大量采用音譯形式介紹外來概念的翻譯家。”[2]238嚴譯《原富》的政經類譯詞以音譯詞類占優勢。嚴復對人名、度量衡單位等各類名稱幾乎都使用音譯法處理。
(一)純音譯詞
嚴復對音譯法的使用,主要是純音譯詞。如用“鎊”[1]20譯pound sterling(英國金本位貨幣單位),用“幾尼”[1]31譯Guineas(最初非洲Guinea之金制造而得名),用“馬克”[1]443譯mark(歐洲古時之重量單位),等等。此種純音譯詞在音譯詞中占大多數。
(二)音譯詞使用之不足
嚴譯《原富》譯詞音譯失誤主要包括不適當地增音、改變讀音,過度使用音譯法等。
(1)增加音素。即增加原詞沒有的讀音。如用“貰勒”[1]785譯ale(注:麥芽酒)。ale讀音[e?l](音近“埃爾”),而“貰勒”讀shì lè。sh音明顯是增加的。
(2)改變讀音。即更改原詞的讀音。嚴譯《原富》音譯詞中,比較明顯改變單詞原本讀音的情況較多。如將denarii(注:名詞denarius [d?'ner?s]的復數,音“第納爾”,便士,古羅馬貨幣)譯為“特那理”[1]556;denarii讀音[d??ner??a?],而音譯詞“特那理”與原詞讀音差別明顯。
(3)過度使用音譯法。嚴譯《原富》中有很多詞語本可以使用意譯法翻譯,卻常常被用音譯法處理。如將capitation(丁稅)譯為“葛必達”[1]750,將gunny cloth(粗麻布)譯為“公尼”[1]111,將jute(黃麻)譯為“優底”[1]111,等等。此類詞語在漢語中并非沒有對應詞或相近表達,本可以意譯或用已有漢語詞套用。嚴氏用音譯法處理,未能直觀表達詞意或性質,不利于理解,并不妥當。
二、嚴譯《原富》術語中意譯詞的構成及得失
除了大量使用音譯詞外,嚴復也很注重意譯法。就《原富》而言,在核心詞領域(國民經濟循環內),還是以意譯詞占優勢。意譯法的使用包括套用漢語已有詞語和自創意譯詞兩大類。
(一)套用傳統用詞來構成譯詞
1.套用詞義一致或相似的漢語詞
英語與漢語有一些詞語的意思是比較一致的。嚴譯《原富》術語中,有些譯詞與英語原文的意思比較一致。如“頭會”[1]325(按人數征稅)與poll-taxes(人頭稅),“關榷”[1]734與custom duty(關稅),“折色之租”[1]27(注:折色,即租稅折算金錢)與money rent(貨幣地租),“泉(幣)”[1]27(注:貨幣的舊稱)與money(貨幣),“泉局”[1]194(注:寶泉局,明清時管理鑄造錢幣的官署)與mint(鑄幣廠),“通功易事”[1]229(分工合作)與division of labour(分工),“懋遷之易中”[1]235(懋遷即交易,易中即中介物)與medium of exchange(交易之媒介),“長僦”[1]339(注:“僦”即租賃)與long lease(即期限很長的租地權),“辜榷”[1]383與monopoly(獨占),等等。
嚴譯《原富》中有一些譯詞與英文單詞在某些方面相似,也可勉強對應。如“太府”[1]581(皇室錢谷的保管出納)與exchequer(舊時英國王室管理歲入的部門),“司農鈔”[1]358(注:司農,職官名,主管錢糧)與exchequer notes(國庫券),等等。
2.加工漢語詞已有詞義
有時,嚴復選取原有漢字某一方面的意思,將其與英語詞語對應。如用“庸錢”[1]70、“力庸”[1]87(注:“庸”有一種含義是“酬勞”)譯wages(工資),用“力役”[1]87(注:“力役”有一種含義是“勞動”)譯labour(勞動),用“力役庸錢”[1]28(注:“庸錢”即“工錢”)譯 money price of labour(勞動力貨幣價格),等等。嚴復摘取了部分詞義,加以利用或改造,創造新意或新詞。
3.運用佛源詞匯
《原富》中有一些譯詞是明顯的佛源詞語。晚清有短暫的佛教熱潮,嚴復本人也信佛,佛源詞語也被他加以利用。如用“無遮通商”[1]119譯free trade(自由貿易),“無遮”為佛教語,謂包容廣大,沒有遮隔;用“頗黎”[1]140譯glass(玻璃),玻璃,又作“頗梨”“頗黎”等,為梵語sphātikā音譯之省音訛變[3]。由于很多佛源詞語早已融入漢語詞匯中,嚴譯《原富》中到底使用了多少佛源詞語,難以統計。
4.套用漢語已有詞語之不足
嚴譯《原富》術語中有一些套用漢語成詞失當的情況。如將bankrupt(破產)譯為“倒帳”[1]256,而“倒賬”是指“欠賬不還”或“收不回來的賬”;將drawing and redrawing(循環劃匯/貸款,接連開具無真實貿易基礎的匯票,向銀行貼現,借新債償舊債)譯為“買空賣空”[1]256(一種商業投機行為,買賣雙方不必交錢交貨,利用市價漲落之間的差價轉手獲利);等等。
(二)意譯詞
套用已有漢語詞語不便之處,嚴氏則用意譯法自主造詞。
1.較為恰當的意譯詞
嚴譯《原富》中不少意譯詞與對應英語單詞的詞義是匹配的。如用“屯棧”[1]404譯warehouse(倉庫/貨棧),用“平價”[1]411譯average price or natural price(平均價格/自然價格),用“合股”[1]597譯joint-stock companies(合股公司/股份公司),用“攤稅”[1]324譯stallage(擺攤稅;攤租),用“落地稅”[1]324譯lastage(市場稅),用“總租”[1]238譯gross rent(毛租金/總租金),用“總殖”[1]239譯gross revenue(毛收入/總收入),用“總贏”[1]91譯gross profit(毛利潤/總收益),等等。
2.自造詞失當
嚴復也有不少自造詞的意思與英語詞語原義不匹配或不夠匹配,或者自造詞本身表意模糊、費解。以嚴復用“國財”[1]62譯national wealth為例。英語中national wealth一詞主要是指“國民財富”,而漢語“國財”一詞主要指“國家財富”。嚴復將national wealth譯為“國財”不妥。
其他自造詞失當的例子還有很多,如用“生利之功”[1]273譯productive lahour(生產性勞動),用“不指之債”[1]759譯unfunded debt(非抵押債務),用“業聯”[1]54譯exclusive privileges of corporation(設立公司之特權),用“交易單”[1]255譯bill of exchange(匯票),用“齊民”[1]316譯freeholder(永久業權),用“過富”[1]95譯overproduction(生產過剩),用“沈債帑項”[1]765譯sinking fund(減債基金),用“環冪”[1]143譯extensive circle(耕種所及之地),用“冠甽”[1]581譯demesne of the crown(即皇室所有之土地),用“借券”[1]255或“諾券”[1]268譯promissory note(期票、本票),用“方便毗勒”[1]257譯circulating bill of exchange(注:循環劃匯/貸款),等等。
3.意譯詞用字古奧生僻
嚴復為人詬病的方面之一就是用詞古奧或詞意生僻,往往帶來不必要的閱讀與理解麻煩。如用“鏨剪摩鋊”[1]183、“鐫镵取鋊”[1]34(注:剝蝕金銀幣中的金銀)譯clipping and wearing(剪切磨損),用“膎膳”[1]200(注:膎即干肉、肉食、熟食)譯butcher’s meat(屠者所售之各種肉),用“罽”[1]9(用毛制成的類似氈子之物)譯woolen coat(羊毛外套),用“毳”[1]207(寒毛、細毛)譯fleece(羊剪毛),用“辟灌之碪捶”[1]232譯forge(鍛造),等等。
4.意譯詞來源不明
嚴復意譯詞中也有來源不明的詞。如嚴復用“蘇荏”[1]737來翻譯spice(香料)。然而,經多方檢索,并未找到“蘇荏”一詞,不知“蘇荏”為何物。
三、嚴譯《原富》術語中音譯意譯拼接詞的構成及得失
有時,嚴復對一些專名作音譯意譯拼接處理。
(一)“專名音譯+通名意譯”拼接處理
此種拼接譯詞分為“音譯+意譯”“意譯+音譯”兩種小類型。
(1)“音譯+意譯”格式。如將Troyes pound(衡量名)譯為“杜雷磅”[1]20,“杜雷”為Troyes之音譯,“磅”為pound之意譯。類似的例子還有:“斯旦稅”[1]585與stamp duty(印花稅),“磅錢”[1]735與poundage duty(對出入口貨物按每磅征稅),“英倫版克鈔”[1]358與bank bills in England(英格蘭銀行之紙幣),擘提生術”[1]164與Pattinson Process(注:帕廷森粗鉛結晶除銀法),等等。
(2)“意譯+音譯”格式。如用“私家泰理”[1]716譯personal taille(注:taille,法國封建時代君主及領主征收的租稅),其中,“私家”為personal之意譯,“泰理”為taille之音譯。此類譯詞的例子還有用“積累版克”[1]249譯savings bank(儲蓄銀行),等等。
(二)“專名音譯+附著說明”處理
有時,專名原詞音譯后,如果不附著說明詞,則可能表意過簡,造成理解障礙,于是不得不采用“專名音譯+附著說明”的方式來處理。如將péages(通行稅)譯為“擘支稅”[1]676/“卑亞稅”[1]741,其中,“擘支”“卑亞”為音譯,“稅”字為附著說明詞。此類譯詞的例子還有將poundage(按貨物每磅重量征收的稅金或手續費)譯為“磅稅”[1]432,等等。
(三)音譯意譯拼接詞之不足
嚴譯《原富》音譯意譯拼接詞處理中存在丟詞等問題。如:將East India Company(東印度公司)譯為“大東公司”[1]115,丟失了India;將Hudson’s Bay Company(哈德遜灣公司)譯為“合遜公司”[1]604,丟失了Bay(灣);等等。
四、嚴譯《原富》政經類譯詞失誤的原因
嚴譯《原富》譯詞的產生與使用,有得有失,情況復雜。嚴譯《原富》中政治經濟類譯詞的處理有不少問題。這些問題的發生,或者是因為原著內容體量大,譯者前后照顧不周,或者是因為譯者本身標準變動的結果,并非是譯者根據語境靈活變化的結果。其失誤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晚清時期術語缺乏規范
清朝長期閉關鎖國,導致晚清時期能表達西學概念的漢語詞匯匱乏。當時,雙語字典少有且粗糙,“直至1908年《英華大辭典》問世,英漢詞典緊缺的情況才得到緩解”[4]。西學涌入,漢語傳統詞匯缺乏對應手段,容受能力有限,乏詞的局面造成一定時期內語詞使用混亂。
晚清政府直到滅亡前才著手術語的規范工作。“科學名詞譯名混亂,是晚清時期影響科學傳播的一個嚴重問題。在救亡與啟蒙的推力下……西方科學知識涌入中國……各類譯詞也被大量創造。存在多種不同譯名所導致的漢語詞匯中新名詞的混亂不一,在1900年前后十年間達到激烈的階段。”[5]直到1909年,清朝學部才設立“審定名詞館”,負責各學科名詞的規范化工作。當其時,嚴復被聘為總纂,曾經手批并編《植物名詞中英對照表》[6]391-638。晚清政府的術語規范工作顯然來得太遲了。
(二)獨力創詞造成譯詞的不夠規范
晚清時期,傳教士以及少量中國人不成系統的譯詞,參考作用不大,嚴復只能自主創造。“嚴復是第一個沒有西方人幫助就能翻譯英文的譯者”[7]163。缺乏必要的詞典,嚴復在一段時間內只能獨力創詞。
亞當·斯密《國富論》內容龐雜,專業性強,大量的詞匯需要處理,這本身就是棘手的難題。缺乏必要的工具書和前人的積累,嚴復獨力創詞,其難度巨大,譯詞出現一些問題不可避免。
嚴復個人的術語規范工作欠缺。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曾咨詢嚴復專門字典的翻譯工作。在一封致張元濟的回信中,嚴復答復:“此事甚難,事煩而益寡。蓋字典義取賅備,故其中多冷字,譯之何益?鄙見不如隨譯隨定,定后為列一表,以后通用,以期一律。”[8]528嚴復認為,翻譯專門字典工作繁瑣而收益小,譯之無大用;嚴復的建議是,按照譯者的方便,在翻譯過程中取舍譯詞,譯后列成清單,供日后翻譯借鑒。在另一封致張元濟的回信中,嚴復道:“又全書翻音不譯義之字,須依來教,作一備檢,方便來學。”[8]537出版《原富》時,應張元濟等人的要求,嚴復才編制了音譯詞表。以嚴氏譯詞很少被后人流傳的事實來看,嚴氏所建議的譯詞“隨譯隨定—列表公布—通用”的方法,實踐效果差。嚴復對譯詞“隨譯隨定”的工作方法,顯然是不夠規范的。此種不規范,造成嚴譯《原富》在前后譯文中對同一事物卻有不同譯詞。如:同一個bye-law(地方規章),時譯“拜勞”[1]598,時譯“約規”[1]124;同一個Corn Law(英國限制農產品輸入之法律),時譯“田約”[1]122,時譯“稼律”[1]122,時譯“谷法”[1]374;同一個carrying trade(海外貿易),時譯“國中與境外貿易”[1]302,時譯“捎業”[1]304;等等。從這些例子來看,同一個術語,可能有不同的音譯變體,可能有音譯拼接意譯變體,可能有不同的意譯變體,處理方法雜亂。
盡管嚴氏譯詞存在雜亂現象,我們也要客觀看待。“……尤其是嚴復,他的音譯詞雖然大部分未能通行,但終究是自佛經譯名以來最大的一次沖擊和試驗,有著其歷史的功績。”[2]245
(三)特定傳播行為造成的譯詞問題
跨文化傳播本身就是復雜的言語行為,尤其要考慮傳播對象與文體風格的選擇。嚴氏在給梁啟超的一封書信中提及閱讀對象的選擇時說:“且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8]516-517晚清時,士人階層的工作語言依然是文言文。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并強調“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9]。嚴復以“多讀中國古書之人”為閱讀對象,譯述時使用“雅馴”的文體,且其譯詞選字常有古奧生僻之處。
(四)日源借詞的影響
借詞(尤其是日源借詞)的沖擊使得嚴氏譯詞的局面變得更加復雜。嚴復刻意創新譯詞,盡量不使用日語來源的譯詞。以bank一詞為例,嚴復將其譯為“版克”[1]393、“鈔商”[1]243,盡管早在1880年代就已廣為流行日源漢字借詞“銀行”[7]260。甲午戰爭后,學習東學、翻譯東學、留學日本成為浪潮,大量的日源借詞或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深深影響了漢語詞匯格局。
五、結語
嚴譯《原富》譯詞是晚清知識精英大規模引入西學詞匯的一個壯舉。嚴譯《原富》譯詞的基本規律是:譯詞總體上以音譯為主,但比較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經濟類譯詞則以意譯為主。跨文化傳播中,嚴復注意會通中英、融匯古今,這對于當下及未來的術語建設依然有指導意義。由于異質文化、思想、語言的接觸與碰撞,嚴氏譯詞也存在諸多問題,其本質是規范性不足。嚴譯《原富》術語使用給予我們的啟示是:跨文化傳播中,既要敢于創新詞匯,尤其要敢于使用音譯詞,又要注意有所取舍,不可過度使用音譯詞;既要合理地繼承傳統用詞,又要注意避免生搬硬套、避免泥古,否則會妨礙術語的傳播效果與接受度;術語的規范化工作尤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