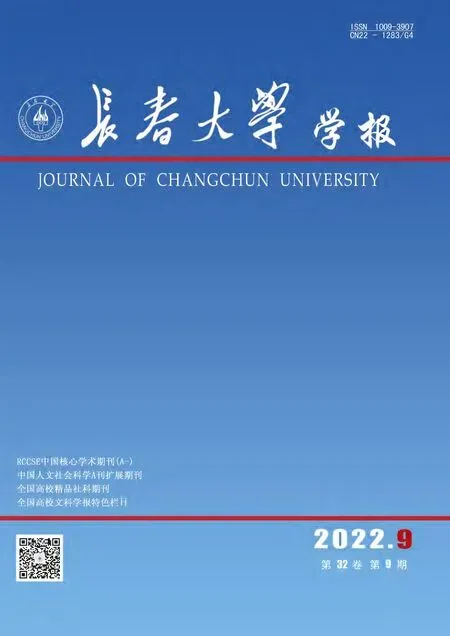論梁啟超的歐西學理詩
寧夏江
(韶關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0)
在清季詩壇,梁啟超算不上大家,但他是個有創新精神和創作個性的詩人。然而學界太多注意的是他的“詩界革命”理論,他貫徹“詩界革命”理論的詩歌創作反而被忽略或忽視了。他沉痛指出詩界革命曾經走入的誤區——“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挦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1]374,認為“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1]376。為推動詩界革命派“舉革命之實”,他創作了許多歐西學理詩——以西方政治學、歷史學和社會學入詩,從思想內容(“精神”)上對詩歌進行革新,克服了維新派新學詩在字面上“挦扯新名詞”的弊端。
一、梁啟超詩歌思想內容的歐西學理特征
梁啟超的詩歌中固然有抒懷、酬酢、品題、應景等舊體詩常見的內容(他晚年的詩歌這方面的內容尤多),但最有特色的是他所創作的歐西學理詩,即抒寫西方政治歷史、人文社會、自然科學等思想學說的詩歌。這類詩歌題材的范圍跳出了中國傳統舊體詩的藩籬,同詩界革命派其他詩人作品中的“新意境”相比,具有明顯的歐西文化的學理性特征,較少關注形而下層面的西方異域之景與風土人情,更多的是抒寫形而上層面的西方社會科學、西方政治制度、西方歷史文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啟蒙先行的新民思想
梁啟超認為,封建專制制度是造成國民道德缺陷和國民性衰弱的罪魁禍首,它使國人淪于奴隸的境地,養成了“奴性”的道德。他因此提出新民思想,通過打破傳統舊思想的束縛,使民智大開,從根源上來醫治國民被腐蝕的靈魂。他認為,一場政治(革命)運動先要有感奮人心的新思想作指導,先行者振臂一呼,民眾廣泛響應,才能取得成功:“新義鑿沌竅,大聲振聾俗。數賢一振臂,萬夫論相屬。人才有風氣,盛衰關全局。”[2]5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就說明了這個道理。“獲實雖今日,播種良遠繇……益信樹人學,收效遠且遒”[2]113,“成功自是人權貴,創業終由道力強”[2]117。這樣的革命運動當然需要卓越的領導者,但最重要的是通過做思想啟蒙工作,把民眾培育成具有新型人格的國民,得到了民眾的支持和參與,“謂是某英雄,只手回橫流。豈識潛勢力,乃在丘民丘。千里河出伏,奔海不能休”[2]113。他高度贊揚了美國獨立運動中民眾所體現出來的戰斗精神,“尋思百廿年前事,穆穆神山不可望。拼死軍前化猿鶴,豈聞閭左有蜩螗”[2]117。他希望通過向國人介紹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民族獨立運動,喚醒和激勵國人向歐美和日本學習,“誓起民權移舊俗”[2]91,“欲向文殊叩法門”[2]63。
(二)舍身變革的志士思想
梁啟超是維新派,但維新變法失敗后,他的思想曾發生轉變,甚至趨向于革命思潮。有論者認為,1899年,梁啟超流亡日本,便和孫中山來往日密,“漸有贊成革命的趨向”[3]119,甚至“與革命黨攜手,共圖大事”[4],并鼓吹欲成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為功”[3]136。1902年,他在日本橫濱創辦《新小說》月刊, “專敘俄羅斯民黨之事實”的《東歐女豪杰》,“將民權大義發揮殆無余蘊”,時人謂:“讀此不啻讀一部《民約論》也。”[5]
梁啟超許多詩篇贊頌了歐美和日本等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革命家,以及為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仁人志士。如《去國行》歌頌了日本倒幕運動中僧月照、南洲翁、高山、蒲生、象山、松蔭等仁人志士:“吁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蔭之間占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2]14《奔勾山戰場懷古》歌頌了北美獨立運動的愛國志士“生命固所愛,不以易自由。國殤鬼亦雄,奴顏生逾羞。當其奮起時,磊落寧他求?公義之所在,赴之無夷猶”。他多次贊揚了盧梭、孟德斯鳩等人思想啟蒙在先,華盛頓、拿破侖等人革命在后,“華拿總余子,盧孟實先河”,意大利的革命杰士瑪志尼“變名憐瑪志,亡邸想藤寅”[2]26。此外,他還頌揚了蘇格拉底(“蘇格拉庾死兮”)[2]92、莎士比亞(“合與莎米為鰈鶼”)[2]92、哥侖布(“蠻長閣龍洲”)[2]27等哲人杰士。他極力抨擊與志士精神相悖逆的奴性:“夫奴性也,愚昧也,為我也,好偽也,怯懦也,無動也,皆天下最可恥之事也”[6]421,“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于世界萬國之間”[6]5931。
(三)優勝劣汰的社會思想
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引發了近代中國思想學術上極大的震撼,激發了有識之士強烈的危機意識。梁啟超高度贊揚嚴復“遠販歐鉛攙亞槧”[2]71,他在《新中國未來記》第三回中說:“因為物競天擇的公理,必要順應著那時勢的,才能夠生存。”在《從軍樂》中,梁啟超描述了世紀之交世界諸國競相并起,強盛弱衰的演變趨勢,“世界上,國并立,競生存”,“弱之肉,強食之,歲靡寧”[2]133。在《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他從生物界的進化談起,“此蟲他蟲相鬩天演界中復幾劫,優勝劣敗吾莫強。主宰造物役物物,莊嚴地土無盡藏”[2]42,再過渡到人類社會,指出人類文明發祥于四大文明古國,后由于“群族內力逾擴張”,地中海文明崛起,取代了四大文明古國;此后“愈競愈劇愈接愈厲”,大西洋文明取代地中海文明而處于人類文明的領先地位。眼下世界格局是“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強,英獅俄鷲東西帝,兩虎不斗群獸殃;后起人種日耳曼,國有馀口無馀糧,欲求尾閭今未得,拚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門羅主義北美合眾國,潛龍起蟄神采揚,西縣古巴東菲島,中有夏威八點煙微茫,太平洋變里湖水,遂取武庫廉奚傷;蕞爾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容商量”[2]43。西方列強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和它們之間的戰爭就是弱肉強食和競爭越來越激烈的體現。他不無憂慮地指出:“我尋風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詳,物競天擇勢必至,不優則劣兮不興則亡”[2]43,“弱肉宜強食,誰尤只自嗟”[2]247,從而喚起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民族危機感。
(四)經世務實的學術思想
梁啟超認識到學術的重要性,認為一個國家的興衰與學術風氣是緊密相關的。他說:“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學術思想焉求之。”[6]561他說:“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6]562近世史中華學術之所以相形見絀,主要是不講經世務實之學,空疏務虛學風泛濫,他在《游日本京都島津制作所,贈所主島津源藏》贊揚中國上古學術“生飭化斂材用昌”,“百物效靈民樂康”,以經世務實為本,便于生民的生產與生活,國力也隨之昌盛。然漢唐以后,學術漸染虛浮空談之風,擯除藝事,空談性理,“后不師古斫大橫,學非所用漢汔唐。俞精俞虛競南宋,及今風氣空言張”。近代西方列強重器物之學,精研入微,“挾技百幻劖造物,一一銖寸基學堂”,國力日益強大,于是中西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我以拙勝與之遇,彼譬則車吾臂螳”。日本學習西方,重器物之學,國力日益強大,“當世若數善述巧,此邦無與抗顏行。日琢群楮亂真葉,盡羿之道孔穿楊。德成而上吾未知,形下惟器信所長”。最后,詩人一針見血地指出,封閉守舊是導致中國百工技藝落后的根本原因,“目力耳力今猶古,原繞原鮮固有常。力不出身貨棄地,厥咎皆坐無紀綱。下傷新步后四國,上悲絕業墜百王”[2]199-200。
二、梁啟超詩歌體制上的歐西特征
梁啟超主張詩界革命“非革其形式”,他的歐西學理詩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用舊的詩歌體式來表現近代西方歷史文化、社會科學思想、自然科學理論,也就是“以舊風格含新意境”,“舊瓶裝新酒”,思想先進但在形式上“文體寄于古”。他詩集中標注甚明的“次原韻”“仍用前韻”“次韻”等詩歌,顯示出梁啟超在詩歌創作中對于傳統詩歌格律聲韻的嚴格遵守。但并不是說他對傳統詩歌的舊形式、舊風格一味地繼承。事實上,他主張對舊體詩在繼承中求新變,對“舊風格”作適當的變通。他說:
彼西人之詩不一樣,吾儕譯其名詞,則皆曰詩而已。若吾中國之騷、之樂、之詞、之曲皆詩屬也,而尋常不名曰詩,于是乎詩之技乃有所限。吾以為若取最狹義,則惟三百篇可謂之詩;若取其最廣義,則凡詞曲之類,皆應謂之詩。數詩才而至詞曲,則古代之屈、宋,豈讓荷馬、但丁?而近世大名鼎鼎之數家,若湯臨川、孔東塘、蔣藏其人者,何嘗不一詩累數萬言也?其才又豈在擺倫、彌兒敦下邪?[7]
這段話精練地體現出他的主張:(1)借鑒西方詩學,以有韻作為詩歌最重要文體特征,“凡有韻的皆是”詩,詩歌不應局限于古體、律體和絕句,騷、樂府、詞、曲、山歌、彈詞等有韻之文,都應屬于詩歌的大家庭;(2)借鑒西方詩學,詩歌的體式可以“不一樣”;(3)借鑒西方詩學,“不受格律的束縛”,解放詩歌體制,詩句可以長短不一,反對傳統詩歌格律嚴苛的限制;(4)借鑒西方詩學,擴大詩歌篇幅,可寫出“數萬言”“十幾萬字”長篇巨制。他把自己的詩學主張貫徹于詩歌創作之中,如《去國行》:
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凌美氣蔥蘢。旁人聞歌豈聞哭,此乃百千志士頭顱血淚回蒼穹。吁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州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陰之間占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2]14-15
這首詩抒寫日本明治維新時,僧月照、西鄉隆盛、高山正之等仁人志士為國圖強奮起拼搏,不懼犧牲,最終使日本國“駕歐凌美氣蔥蘢”,激勵戊戌變法失敗的維新志士,相信中國未來一定會像日本一樣變法成功。詩歌沒有固定的體式,也就沒有受到格律限制。全詩以押韻句子組成,句子長短不一,自由靈活,頗有騷體賦和抒情散文的特色。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是作者有意創作的長篇歌行:
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強。……我尋風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詳。物競天擇勢必至,不優則劣兮不興則亡。水銀鉆地孔乃入,物不自腐蟲焉藏?爾來環球九萬里上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強權強。惟余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肅肅天雨霜,鼾聲如雷臥榻傍。詩靈罷歌鬼罷哭,問天不語徒蒼蒼。(節選)[2]43-44
作者以散文化的筆調寫詩,盡力擴大詩歌容量,表達作者弱肉強食的憂患思想。詩體自由,沒有固定體式,姑且以“歌”標其題;“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強”,“我尋風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詳”,“惟余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毋乃殃”等不僅內容上是新語句,句式上也是新語句。
梁啟超受近代西方軍歌的影響。他認為,軍歌可傳唱全新的時代內容,以軍歌來激發人心,達到啟蒙新民的目的。他自己也創作了許多類似西方軍歌的詩歌作品,如《愛國歌四章》《黃帝歌四章》《結業式四章》《從軍樂十二章》,這些詩歌“格式屬自創,幾乎與整齊押韻的白話詩差不多”[8],“不屑拘拘繩尺間耳”[9]116。如《從軍樂十二章》(選二):
從軍樂,告國民:世界上,國并立,況生存,獻身護國誰無份?好男兒,莫退讓,發愿做軍人。(其一)
從軍樂,初進營。排樂隊,唱萬歲,送我行。爺娘慷慨申嚴命。弧矢懸,四方志,今日慰平生,今日慰平生。(其二)[2]133
這些詩歌句式上松散自由,每句長短不一,韻律靈活多變,節奏明快,文字淺近,可以看作是白話詩的濫觴。詩歌沉郁雄壯,常常以一種重復疊唱的方式來增加情感,強化主題,給讀者造成一種音韻上循環往復的視聽感,起到教育國民的目的[10]78-79。
梁啟超反對維新派新體詩一味“挦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但他并不反對為表達需要而使用新名詞、新語句。在他看來,詩歌要表達“新意境”,如果古典詩歌傳統的語言庫中找不到相應的語詞來表達,就只能自造新語,甚至借用來自歐西、日本的外譯詞,突破古典詩歌語言表達上的桎梏。
梁啟超對新語句、新名詞的使用是很有節制的。他認為新語句必須服從于“新意境”,能少用則盡量少用,刻意使用必反受其害。他在比較黃遵憲與夏曾佑、譚嗣同的詩時曾說:“新語句與古風格常相背馳,公度重風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譚復生,皆善選新語句,其語句則經子生澀語、佛典語、歐洲語雜用,頗錯落可喜,然已不備詩家之資格。”[6]1219他贊賞黃遵憲的詩歌“純以歐洲意境行之”,然用“新名詞”不多;婉批夏曾佑、譚嗣同的詩歌濫用令人費解的新語句、新名詞,“已不備詩家之資格”。
梁啟超詩歌中所用的新詞匯大致可以分為六類:一是國外人名,如拿破侖、華盛頓、伋頓曲、麥塞郞;二是國外地名,如波羅的、西伯利亞、火奴奴等;三是新事物名詞,如輪船、鐵路、電線,海電;四是自然科學名詞,如以太、無機、微生等;五是與進化論相關的名詞,如競爭存、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等;六是政治文化術語,如共和、政體、自由、平等、民權、文明等。前兩類新詞匯由于無法意譯,只能音譯,由其組合成的詩句稍有點生硬。后四類基本上以意譯為主,運用于詩歌中很是得體和巧妙,意境與語句俱新。
三、梁啟超詩歌歐西化的詩學史意義
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列梁啟超為“專造一應大小號炮”的地輔星,并評之曰:“新會(筆者注:指梁啟超)向不能詩,惟嘗與譚瀏陽、黃公度鼓吹詩界革命,著為論說,頗足易一時觀聽。返國以來,從趙堯生、陳石遺問詩法,乃窺唐宋門徑。游臺一集,頗多可采。惟才氣橫厲,不屑拘拘繩尺間耳。”[9]116汪辟疆從傳統詩論家的角度來評價梁啟超的詩歌,著眼點還是1910年前后梁啟超曾向趙堯生、陳石遺詢問詩法而創作的舊體詩。從他舊體詩的成就來看,在詩人林立的清季詩壇排座次,梁啟超確實只能屬地輔星之位。然而如果從他所創作的歐西學理詩對清季詩壇產生的新變和影響,其意義不可低估。由于其特殊的歷史地位,其詩歌具有一種不可取代的文化價值[10]73。
“詩界革命”派從譚嗣同、夏曾佑等人“喜摭拾西籍名詞,入諸韻語”[9]43,到黃遵憲、康有為等人以西方異國風光、民俗人情、近代自然科學知識、新事物、新現象入詩,“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11]。梁啟超認為“所謂歐洲意境語句,多物質上瑣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雖然,即以學界論之,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輸入中國,況于詩界乎?”[6]1219有些“新體詩”雖“驅役(歐西)教典”,卻掩蓋不了“歐學皮與毛”的淺率(《廣詩中八賢歌》)。這是很有見地的觀點——錢鐘書評價黃遵憲就說他“差能說西洋制度名物,掎摭聲光電化諸學,以為點綴;而于西人風雅之妙、性理之微,實少解會。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致,……蓋若輩之言詩界維新,僅指驅使西故,亦猶參軍蠻語作詩,仍是用佛典梵語之結習而已”[12]24。又說嚴復“號西學巨子”,他的詩除少數幾首,“其他偶欲就舊解出新意者……直是韻語格致教科書,羌無微情深理。幾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學亦求卑之無甚高論者”[12]347。
梁啟超強調“詩界革命”重在“革其精神”,他深刻地意識到“當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這樣才能提高“詩界革命”的水平,才具有深遠的意義。其歐西學理詩主要以“真精神,真思想”見長。他的詩歌在“新意境”方面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引“西學”入詩更多的不是從器物層面上,而是從“精神思想”上入手,即“用新理入詩”,達到“洞見政本”的目的。他的詩歌描寫國外自然景物、名勝古跡以及新事物、新現象,比黃遵憲少,比康有為更少。即使是寫歐西新事物、新現象,他也是概述幾句后,馬上轉入感想和議論。如《游日本京都島津制作所,贈所主島津源藏》本來是可花大筆墨描寫制作所器械的新奇精妙,但詩人只輕描淡寫幾句后馬上轉向對歐西之學務實而國強、中國之學務虛而國弱的思考。所以,梁啟超的歐西學理詩很突出的一個特征,就是圍繞歐西政治文化上下議論,闡述借鑒效法西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的詩歌有較深厚的學術背景,蘊蓄著他的學術思想,體現出“新版”學人之詩(1)晚清“新版”學人之詩是指晚清以來受海外異質文化影響的一批“新式”學人創作的詩歌。嚴迪昌先生說他們的詩讀起來“有種以‘新學’入詩,是學人詩新版本的感覺”。見嚴迪昌《清詩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0頁。的特征,歸旨于救國強國之路的探尋[13]。
在他的影響下,20世紀初,新一代學貫中西的學者詩人不僅擺脫了挦扯西典西物、瑣碎務奇的詩風,而且詩歌創作的視野擴展到哲學、美學和文學等領域。如受梁啟超《時務報》影響而放棄舉業、趨向新學的王國維“以西方義理入詩”[12]347,“時時流露西學義諦,庶幾水中之鹽味,而非眼里之金屑。……是治西洋哲學人本色語”[12]24,為“新詩試驗開一康莊”[14]大道。其后,陳寅恪、馬一浮,蕭公權、胡先骕、吳宓、朱光潛等,“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筆者注:指梁啟超)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15],“沒有一個不曾因讀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啟發”[16]。他們自覺“以現代學術入傳統詩詞”[17],“體現出對中西文化的歷史、現狀、未來的感性體悟與學理思考”[18],詩歌的“新意境”更加委婉深沉,“新版”學人之詩達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