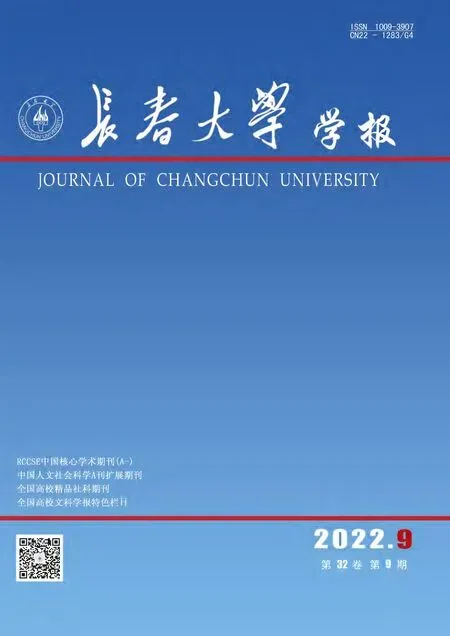英語世界《三國演義》學術史研究
王學功
(內蒙古科技大學包頭醫學院 人文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40)
英語世界不僅是地理概念,還指英、美、加、澳、新等英語國家,更是文化概念,指以英語為媒介構成的迥異于中國文化的學術共同體。英語世界《三國演義》學術史研究,旨在述評英語世界《三國演義》二百年研究史,包括譯者、譯作、研究者、研究論著、學位論文、研究狀況以及內在發展規律。目前,國內學界還沒有對上述成果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分析。英語世界《三國演義》學術史研究可以為國內《三國演義》研究提供鏡鑒,為海外漢學、比較文學等相關學科提供文獻參考。英語世界《三國演義》學術史可分為四個時期:發軔期(1815—1925年),過渡期(1926—1959年),繁榮期(1960—1989年),多元期(1990—2019年)。分期依據有三:其一,文學研究內部各階段所呈現的共同特征和發展規律。例如,發軔期以譯介為主,多元期研究呈現理論、視角、方法多元的態勢。其二,以標志性的全譯本作為分期節點。例如,1925年,《三國演義》鄧羅譯本第一個英語全譯本出版,1991年,第二個全譯本羅慕士譯本出版。其三,與美國漢學分期相一致。例如,1928年,哈佛大學成立燕京學社,標志著專業漢學時期的開始,《三國演義》在三四十年代同步進入學院派研究。上述分期,一方面符合英語世界《三國演義》學術史的發展進程,體現其發生、發展、變化的基本狀貌,另一方面是為了方便行文敘述。但任何分期都不是絕對的,各時期必然存在相交相融之處,類似河流上、中、下游的劃分,都是相對的、宏觀的。
一、發軔期(1815—1925年)
發軔期也可稱之為譯介期。《三國演義》進入英語世界的起點是譯介,該時期共收集一手資料為35種長短不一的譯介,涉及譯者22名,值得討論的問題包括首次譯介、譯者身份、譯介目的和譯介內容。
國內學界一般公認《三國演義》首次英譯是1820年湯姆斯(P.P.Thoms)在《亞洲雜志》發表的《著名丞相董卓之死》。這種觀點源于王麗娜的《中國古典小說名著在國外》(1988),之后的學者黃鳴奮、馬祖毅、鄭錦懷等紛紛引用此說,近30年來幾乎成為定論。2011年,王燕提出《三國演義》英文首譯應歸功于馬禮遜[1],其《華英字典》的“孔明”詞條翻譯了桃園結義和五丈原禳星的相關片段。因此,《三國演義》進入英語世界的起點提前至1815年的《華英字典》,首次英譯的桂冠應該還給馬禮遜。
發軔期的22位譯者,除1人不可考外,其余為英國13人、美國6人、德國2人。根據職業可分為四類:傳教士、外交官、中國官員、其他。傳教士占絕大多數,共10人,外交官4人,中國官員3人。這些譯者大部分僑居中國,翻譯《三國演義》是為了學習漢語、了解中國,編寫漢語教材是鮮明的例證,如衛三畏(S.W.Williams)的《拾級大成》,施約翰( J. Steele)的《舌戰:〈三國演義〉第43回》和艾約瑟(J.Edkins)的《漢語會話:譯自本土作者》。但譯者的傳教士身份決定了他們的譯介目的不僅是為了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更是為了服務他們的傳教事業。
發軔期譯介內容呈現了兩個焦點,一是貂蟬,二是孔明,分別涉及長短不一的6種譯介。“貂蟬”的譯者有湯姆斯、衛三畏、亞歷山大、X.Z.、鄧羅(C.H.Brewitt-Taylor)、卜舫濟(F.L.H.Pott);“孔明”的譯者有馬禮遜、施約翰、美魏茶(W.C.Miline)、司登得(G.C.Stent)、杰米森(C.A.Jamieson)、潘子延(Z. Q. Parker)。發軔期譯者集中譯介貂蟬和孔明,除了原文本的影響外,可能出于兩方面原因:(1)當時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當時有關美人計和諸葛亮的戲劇流傳極廣,普通民眾耳熟能詳,譯者選擇翻譯流行的片段可以吸引更多讀者。(2)無意識的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19世紀的中國形象從18世紀的西方中國熱中跌落,中國人成為陰險、狡詐、愚昧、自私的代名詞,《三國演義》中的精彩片段數不勝數,他們選譯了充滿狡詐、詭計、情色的片段。選擇代表態度。這樣的選擇可能多少反映了他們無意識的西方中心主義,中國始終還是和西方對立的他者。
二、過渡期(1926—1959年)
1925年,《三國演義》鄧羅全譯本的出版標志著發軔期的結束,預示著過渡期的開始。過渡期的《三國演義》研究處于隱而不彰的狀態,研究成果少且不成系統,僅有18種,其中主要成果有3篇書評,3部著作,2篇碩士論文。過渡期最明顯的特征有二:一是鄧羅譯本廣受好評,二是英語世界《三國演義》研究開始從傳教士漢學范疇轉向專業漢學研究范疇。
過渡期的3篇書評都高度評價了鄧羅譯本。包文(A.J.Bowen)稱贊道:“西方受惠于前中國海關官員鄧羅先生,他翻譯了一部非常具有東方色彩的作品。譯者完成了一部非常優秀的作品,是真正的翻譯而不是擴展的概述。以地道的英語再現了原作者的話,尤為可貴的是,英語的行文完好地保留了原作的語氣、精神和節奏。”[2]蒙格(E.Mengel)贊揚鄧羅先生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任務,強調譯文引人入勝,趣味盎然。赫茲佩斯(W.H.Hudspeth)評價鄧羅譯本是才華橫溢的翻譯。
過渡期的3部著作的作者也肯定了鄧羅譯本。費子智(C.P.Fitzgerald)的《中國文化簡史》在討論《三國演義》的章節中大量引用了鄧羅譯文,費在注釋中稱贊道:“不可能有更好的全譯本了。”[3]葉女士(Evangeline Dora Edward)的《龍書》,自1943年至1946年間在美國連續再版4次,盛極一時,書中收錄了鄧羅譯本的9個片段。海陶瑋(J.R.Hightower)的專著《中國文學論題:綱要與書目》中,《三國演義》的題目采用的是鄧羅的翻譯“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海陶瑋的哈佛大學教授身份證明,鄧羅的翻譯已被學術界接受和認可。鑒于鄧羅譯本的深遠影響,把過渡期稱為鄧羅時代應該不過分。
過渡期的2篇碩士學位論文,即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威爾遜(Delaplane Wilson)的《英譯中國小說一覽》(1947年)和哥倫比亞大學李加里(Gary Way Lee) 的《赤壁之戰:〈三國演義〉與〈三國志〉敘述的比較》(1949年),標志著英語世界《三國演義》研究開始從傳教士漢學轉向專業漢學研究范疇。威爾遜的論文考察了中國古代四大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和三部現代小說,試圖回答英語世界為什么忽略中國文學的問題。威爾遜討論了《三國演義》的作者、成書、人物、風格等,論文亮點在于探討了《三國演義》的女性人物,如糜夫人投井保全阿斗,徐母斥責徐庶等,認為三國女性雖是次要人物,卻是忠誠的最好例證。這應該是英語世界最早論及三國女性的論文。李加里的論文逐段對比了《三國演義》第42章至第50章與《三國志》中相同的記敘,旨在廓清小說在多大程度上取材史書、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傳說與作者的想象,同時說明小說的演化和發展方式。李加里的論文是目前發現的第一篇英語世界以《三國演義》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論文的主要貢獻在于,不同于“七實三虛”的模糊概說,而用事實與數據說話,仔細梳理對比小說與史書中赤壁之戰的相關文本,計算出每章史料所占的比重,第一次用量化的方法向我們展示了《三國演義》是小說而不是歷史。2篇碩士論文都是稀見本,為筆者所發現,具有相當的文獻價值。
三、繁榮期(1960—1989年)
繁榮期英語世界《三國演義》研究成果眾多,質量上乘,收集到的一手資料共54種,其中重要成果有3部文學史,9部博士論文,4部里程碑式的著作。這些研究成果顯示的特征有二:一是歷史學視角,從歷史與文學對比的角度研究《三國演義》;二是轉向文學內部研究,關注文體、主題、結構、人物等。繁榮期可以細分為3個階段,每10年一個階段,呈現了明顯的演化特征:60年代文學史獨領風騷,70年代轉向文學研究,80年代敘事學和文獻學研究偏勝,出現了2部集大成的文獻學著作。
20世紀60年代,英語世界集中產生了3部中國文學史:陳綬頤(Show-yi Chen)的《中國文學史述》(1961),賴明(Ming Lai)的《中國文學史》(1964),柳無忌(Wu-chi Liu)的《中國文學概論》(1966)。3部文學史都論及《三國演義》,篇幅長短不等,但呈現了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除作為大學教材使用外,目標讀者都包括普通讀者。陳綬頤在前言中指出,本書的目的是為西方讀者欣賞中國文學提供必需的材料。賴明在出版說明中表明,為了普通讀者,本書簡化了中國姓名的羅馬拼音。柳無忌在前言中指出,他的目的是滿足西方讀者想繼續品讀中國文學作品的需要。
第二,受魯迅、鄭振鐸的影響。受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影響,認為《三國》的來源主要是說書人的話本和宋元戲劇,指出小說與評話的區別在于刪除了因果報應等迷信因素;受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影響,采用賈仲明《錄鬼簿續編》論證作者為羅貫中。
第三,力圖創新,突顯個人特點。陳綬頤《中國文學史述》的特點在于展現中國文學的歷史整體;賴明《中國文學史》突出的特點在于強調社會、經濟因素決定了文學形式的周期性興盛與衰敗,中國文學周期性發展得益于大眾娛樂;柳無忌的《中國文學概論》更注重批評和審美,深刻剖析了《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瑪格麗特·白瑞(M.Berry)比較了柳無忌和陳綬頤兩人的文學史,認為“(陳作)缺少腳注和參考文獻,也沒有涵蓋最近25年的研究,然而提供了統一的、連貫的、有用的參考,沒有被柳無忌不太全面、更富審美導向和學術性的著作完全超越。”[4]白瑞從側面肯定了陳著偏重統一連貫的歷史考察,賴著偏重審美性和學術性。3部文學史都有所側重和創新,具備不同的特點,確定了各自存在的價值。
繁榮期的9部博士論文,除蒂洛瓦尼(M. Dilokwanich)的《Samkok:一部中國小說的泰國改編研究》(1983)以傳播學視角研究外,其他8部均以三國人物為關注焦點。布特(E.I.Boute)的《諸葛亮與蜀漢》(1968)闡明了諸葛亮在蜀漢建國中的歷史作用和真實形象。楊力宇(W.L.Y.Yang)的《以〈三國志〉為〈三國演義〉之源》(1971)選取了劉備、曹操、關羽、張飛、諸葛亮、周瑜等人物,對比了這些人物在《三國志》與《三國演義》中的描寫,研究哪些是史實、哪些是虛構。柯睿(P.W.Kroll)的《曹操的肖像:其人及其虛構的文學研究》(1976)考察了曹操作為官員、詩人、虛構人物和戲劇人物的不同形象。羅斯(G.V.Ross)的《戲劇中的關羽:兩部元雜劇的翻譯與批評》(1976)考察了雜劇中的關羽形象。盧慶濱(A.H.Lo)的《歷史學語境中的〈三國演義〉與〈水滸傳〉》(1981)對三國英雄人物作了反諷解讀,認為他們屬于游俠,是禍亂國家的暴徒。阿曼(G.K.Oman)的《花關索傳研究:1478年韻文敘事研究》(1982)考察了花關索作為西方傳奇英雄的人物形象。馬蘭安(A.E.McLaren)的《明唱詞與早期中國小說》(1983)考察了花關索與《三國演義》版本演化的關系。阿拉斯(J.K.Arase)的《曹丕的三種角色:皇帝、文學批評家、詩人》(1986)考察了歷史中曹丕的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楊力宇的博士論文是英語世界第一篇以《三國演義》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該論文的主要貢獻在于發掘了《三國演義》作為“演義”文體的獨特意義,指明羅貫中創作了中國小說新文體,通俗歷史敘事的“演義”類型,是中國對世界文學獨有的貢獻。楊力宇詳細闡發了《三國演義》不屬于通俗歷史、西方歷史小說、西方傳奇等文體,而是演義文體,而演義作為獨立文體的意義在于虛實結合。這顯然受到了夏志清(C.T.Hsia)《中國古典小說》中相關論述的影響。
繁榮期英語世界產生了4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分別是夏志清的《中國古典小說》(1968),浦安迪(A.H.Plaks)的《明代小說四大奇書》(1987),楊力宇等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與賞析指南:論文與參考文獻》(1978),瑪格麗特·白瑞的《中國古典小說》(1988)。4部著作以中國六大或四大古典小說為研究對象,前2部為學術專著,后2部為文獻參考書。
夏著研究《三國演義》的貢獻有三:一是從體裁上肯定《三國演義》是一部偉大的歷史演義小說,從而否定了胡適認為《三國演義》是平凡陋儒編輯的通俗史書的觀點;二是《三國演義》敘事融合了說書人傳統和史學傳統,其產生是羅貫中運用史學傳統對抗說書傳統的結果;三是三國人物是自我沖突的個人主義者,主要人物關羽、諸葛亮、曹操,次要人物禰衡、田豐等,都是抗擊命運的個人主義者。
浦著的主要貢獻在于借鑒西方敘事學理論、中國陰陽五行思想和傳統評點資源,力圖構建中國敘事學體系,詳細論證了包括《三國演義》在內的四大奇書是文人小說文體。
楊著的主要貢獻除對《三國演義》作者、演化、主要人物和主題作了提綱挈領的介紹外,第一次系統地梳理了英語世界所有關于《三國演義》譯介、研究的參考文獻,為該領域研究奠定了文獻基礎。
白著的主要貢獻在于不僅系統總結了英語世界《三國演義》研究成果,而且全面梳理了所有譯介和研究的英文參考文獻。白著借鑒最新研究成果,討論了《三國演義》的演義文體,列舉了《三國演義》四種主題——國家的興亡、過度擴張的野心、儒家“仁”的政治化反諷、主宰人類的因果報應,總結了《三國演義》八種結構特征——象征性開場白,以十章或十二章為單元的劃分,敘述事件的拋物線結構,指向虛無的結局,對比性搭檔或群組,事件的次序,復雜的時空結構,有意識的創作手段。白著收集的《三國演義》相關文獻含譯介10種、研究40種,被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譽為“1988年十大最好參考書之一”。
4部著作一經問世,便受到一致好評,影響深遠,直到現在都是該領域的必讀書。
四、多元期(1990—2019年)
多元期接續繁榮期,《三國演義》研究成果進一步增加,一手資料共65種,其中重要成果有4部文學史,6部博士論文,1部論文集。多元期的顯著特征有二:文化研究轉向;理論、方法、視角的多元。
多元期4部文學史為伊維德(W. Idema)和漢樂逸(L. Haft)的《中國文學導論》(1997),倪豪士英譯雷威安(A. Levy)主編的《中國文學史》(2000),梅維恒(V. H. Mair)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2001)和孫康宜(Sun Kang-I)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2010)。1部論文集為金葆莉與董保中(Constantine Tung)主編的《〈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2007),即“三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1年,成都)精選會議論文集。
上述研究成果呈現了明顯的文化研究轉向。伊維德的文學史分期并不強調政權更迭的歷史朝代,特別強調物質富裕、社會經濟結構、流行價值觀對文學體裁的塑造作用,強調對文學產生重大影響的物質文化發展,如紙的發明、印刷術的廣泛使用等。孫康宜與宇文所安的文學史在前言中明確說明:“竭力避免文學體裁對文學史所造成的分野,力圖創造一種文化史或文學文化史。”[5]《〈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是英語世界唯一一部以《三國演義》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集,收錄10篇論文,分4部分,探討了《三國演義》與傳統思想、歷史、藝術的關系及傳播情況,在更寬泛的文化語境下研究《三國演義》的主題、人物、視覺藝術改編、影響與接受等。
多元期6部博士論文呈現了理論多元、方法多元、視角多元的特征。
理論多元。姚垚(Yao Yao)的《〈三國演義〉的交錯結構》(1990)與盧盈秀的《〈三國演義〉與〈亞瑟王之死〉的英雄氣概和男性社誼欲望》(2012)分別運用了敘事學理論和女性主義理論研究《三國演義》。《三國演義》韻散結合的敘事方式,一直以來飽受西方學者詬病,有綴段化結構的譏評。姚垚利用敘事學理論中主要敘述者和次要敘述者不一致,解釋了韻散結合構成了《三國演義》的交錯結構,是中國小說對世界文學的獨特貢獻。盧盈秀利用女性主義考察了《三國演義》中男男同性關系及政治權利關系,認為《三國演義》中同榻可以解讀為同性戀關系,不會威脅社會秩序,但在《亞瑟王之死》中同榻會立刻引起對同性戀的恐懼,這揭示了中西方性別話語的不同特征。
研究方法多元。上述兩位學者都采用比較文學的跨文化比較方法,對比了《三國演義》與《亞瑟王之死》,在中外文學的異同中尋求互識、互補、互證。魏安(A.C.West)的《追求其原文:〈三國志演義〉的考證學》(1993)屬于傳統的版本研究,但采用了新方法,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魏安運用文字比對的“串句脫文”的方法,考證了24種版本的《三國演義》,找出了106個“串句脫文”的例子,全面詳盡地厘清了《三國演義》33個版本的淵源關系,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一致好評。沈伯俊稱贊魏安:“對《三國演義》版本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全面、最細致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具有創新意義,因而其論述具有很強的說服力。”[6]
視角多元。其他3部博士論文有貝莉(C. D. A. Bailey)的《中介之眼:毛倫毛宗崗與〈三國演義〉閱讀》,金葆莉(K. A. Besio)的《反抗的性格:元雜劇中作為喜劇英雄的張飛》和權赫燦(Hyuk-chan Kwon)的《從〈三國演義〉到〈三國志〉(Samgukchi):〈三國演義〉在韓國的歸化與挪用》,它們展示了評點學、文體學、傳播學等多元研究視角。其中,貝莉和權赫燦的論文都體現了闡釋學和讀者接受理論的影響。貝莉認為,毛氏父子的批注是文本與讀者的中介,評點家首先是讀者,幫助其他讀者欣賞小說的特質,在小說的敘事過程中,讀者具有主動建構的作用。權赫燦認為,《三國演義》在韓國長盛不衰的原因在于讀者接受,《三國演義》在韓國的社會政治文化語境中不斷被重新闡釋,讀者也經歷了不同的接受階段,從直接接受小說善惡二分的人物觀到保持超越的態度,再到贊同任何形式的改編。
五、結語
縱觀英語世界《三國演義》研究二百余年的歷程,可以發現明顯的階段性演化:從譯介為主的發軔期到專業研究萌芽的過渡期,到全面開花結果的繁榮期,再到分化變異的多元期。英語世界《三國演義》研究總體呈現如下趨勢:譯介—文學史概述—文學內部研究—敘事學—女性主義—讀者接受—多元理論。這條線索符合文學研究的潮流和規律,從作者研究轉向文本研究,再由文本研究轉向讀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