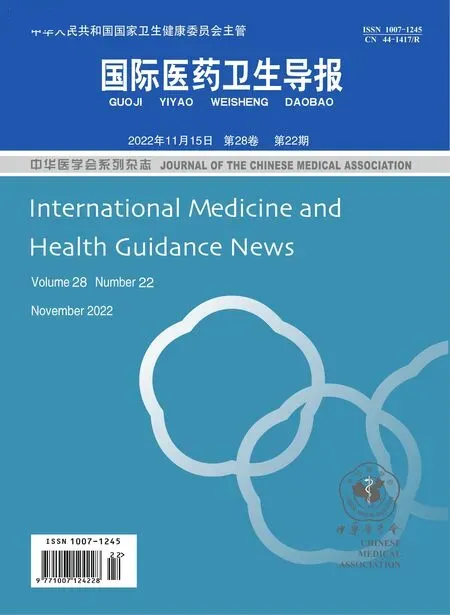炎性指標在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預后中的研究進展
彭暉 陳偉強
汕頭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神經外科,汕頭 515000
蛛網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是指腦表面、顱底、椎管內血管破壞時,血液流入蛛網膜下腔,進而引起相關腦卒中癥狀的一種腦血管病。顱內動脈瘤破裂是SAH最常見病因,其發病兇險,病死率、致殘率極高,是一種嚴重危害人類生命健康財產的腦血管疾病,據80至90年代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起的MONICA 項目記載,SAH 每10 萬人的年發病率為2.0(北京)~22.5(芬蘭),SAH 患者28 d 內平均病死率為 41.7%,發病后 1 d、2 d 和 7 d 的平均病死率分別為37.0%、60.0%和75.0%[1]。近年來,隨著技術的進步及理念的革新,關于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的診斷和治療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其導致患者高病死率、高致殘率的病理生理機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大多數研究者認為腦血管痙攣所導致的遲發性腦缺血,是造成多數aSAH者出現嚴重神經功能缺損、乃至死亡的重要因素[2]。關于aSAH 后出現的腦血管痙攣和遲發性腦缺血,最新多項研究表明其與早期腦損傷期間發生的神經炎性反應存在密切相關性[3-4]。目前,已有研究人員通過對腦出血患者進行抗炎治療而取得一定療效[5],與此相對應,也有研究指出,通過抗炎治療可以改善aSAH 患者的癥狀和預后[6],這表明炎癥參與了aSAH 的致病過程,是aSAH 誘發腦損傷的重要環節。因此,通過研究炎癥相關指標,有助于預測aSAH 患者預后,對于急危重癥患者的救治及療效判斷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就目前與aSAH預后相關的炎性指標進行綜述。
與神經炎癥有關的外周血細胞學指標
外周血系統性炎性細胞指標在臨床檢驗中最易獲取,相關指標近年已被證實對預測顱腦損傷、心肌梗死、腦血管意外等疾病預后有較高的參考價值。通過建立動物模型,研究人員發現,當SAH 發生時,炎癥存在于腦脊液、腦實質和腦血管中[7],白細胞浸潤和血小板活化在SAH 發生早期即可出現,白細胞浸潤可導致腦動脈痙攣、早期腦缺血,進而影響患者的功能預后[8-9]。在以外周血白細胞和血小板增多為主要特征的全身性炎性反應綜合征中,血小板活化程度和aSAH 后的腦神經功能預后密切相關[10-11]。目前認為,遲發性腦缺血(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DCI)是aSAH后不良預后的重要原因,血小板活化在aSAH 后DCI的發生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血小板活化后所表現的微血栓形成,造成aSAH后出現腦血管調節功能失衡和出凝血功能障礙,進而誘導DCI 的發生。通過監測血小板參數,可以實時反映血小板生成、活化、消耗等功能狀態,從而預測腦微小血管內血栓形成和DCI的發生[12-13]。
1、外周血白細胞計數
外周血白細胞在外滲到大腦過程中產生高活性氧分子,破壞了血腦屏障,是造成早期嚴重腦損傷的主要可能因素,白細胞中的中性粒細胞和巨噬細胞向蛛網膜下腔集結,是人體清除蛛網膜下腔積血主要方式,所以,早期外周白細胞計數也能間接反映出血后早期腦損傷的嚴重程度。已有科學研究證實,在發生aSAH 后早期,外周血白細胞計數對于DCI 的發生風險和神經功能預后有預測價值[14]。Al-Mufti等[15]甚至認為,外周血白細胞計數對DCI的預測能力,相對現有被廣泛應用和接受的改良Fisher 評分更加準確,在評估患者的DCI 發病風險方面可能更具臨床應用價值。國內則有研究者將外周血白細胞計數和頭顱CT 的Hu(Hounsfield Unit)值聯系起來,證實其對aSAH 后4~30 d 的DCI發生率有更強的預測能力[16]。
2、 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ratio,NLR)
NLR 是腦血管疾病中公認的炎性細胞學指標。臨床病理學研究發現,神經系統的炎性反應不僅促使外周血中性粒細胞在發病后短時間內迅速增高,也通過免疫抑制反應加速淋巴細胞的衰竭,因此在腦出血、腦梗塞等出現神經系統炎性反應的疾病中均可顯示出NLR 水平的特征性改變[17-19]。目前已有臨床研究證實了NLR 對aSAH 預后具有預測價值,賈傳宇等[20]將 113 例 aSAH 患者按照格拉斯哥預后評分(GOS)標準分為預后不良組(GOS≤3 分,共26 例)和預后良好組(GOS >3 分,共87 例),收集并分析其臨床數據資料,多因素分析結果發現NLR 水平對預測aSHA 患者不良預后的準確率最高,證實了NLR 作為最易獲得的全身系統性炎性指標,在aSAH患者發病早期具有良好的預后預測價值。
3、血小板相關指標
血小板在病理狀態下可促進斑塊的形成、破裂,當斑塊破裂后,血小板迅速聚集,進而形成血栓并觸發炎性反應[21]。腦微血栓形成與炎癥級聯反應的啟動誘導了aSAH患者 DCI 的發生[22]。因此,aSAH 患者 DCI 發生可能與血小板功能存在密切聯系。目前研究報道的與aSAH 預后有關的血小板相關指標包括血小板活化因子(platelet activating factor,PAF)、相關血小板參數如平均血小板體積(mean platelet volume,MPV)、血小板體積指數(PVI)[MPV 與血小板計數(PLT)的比值]、血小板分布寬度(platelet volume distribution width,PDW)。
PAF 被認為與SAH 后腦血管痙攣的發生有重要關系[23],其作用機制為aSAH后PAF通過趨化并激活多形白細胞,促使多形白細胞合成釋放多種炎性細胞介質,進而引起腦血管痙攣,減少腦組織灌注,增加血管通透性,反過來又加重腦血管痙攣、腦血流量進一步減少,神經元死亡加快,進入惡性循環[24]。有臨床試驗證實了使用PAF受體拮抗劑E5880 對治療aSAH 后腦血管痙攣具有有效性及安全性[25],這也從側面反映了PAF 與腦血管痙攣相關,進而影響aSAH患者預后。
血小板參數可反映血小板的生成、活化及人體骨髓的代償增殖情況,其中MPV和PDW 表現血小板細胞的活化程度及功能狀況,同時MPV 還能反映骨髓的巨核細胞增殖和血小板細胞形成過程,在血小板活化后,機體將獲取更大反應表面積的血小板,使其形態從盤狀轉化為球狀,并伸出偽足,因此從血液學指標上顯示為 MPV 及 PDW 的增加[26]。PVI 為MPV 與PLT 的比值,可作為血小板血栓形成的預測指標[27]。近年來,PVI 作為預測血小板相關系統血栓生成的重要指標被科研人員廣泛應用[28-29],并且也有研究表明,隨PVI水平增加,血小板血栓形成的危險性也越來越高。
相關血小板參數在aSAH 預后上的預測價值近年來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比如,有對照研究發現,入院MPV 可能與aSAH 患者功能預后有關,入院MPV 值高的患者,其腦積水、遲發性腦缺血的發生率也隨之升高,提示MPV 是aSAH患者不良功能預后的獨立預測因子[12]。PVI 已被證實可作為預測 aSAH 后發生 DCI 的重要指標[27]。Ray 等[27]通過回顧性分析對比169 例患者PVI變化趨勢與DCI發生比例,得出了aSAH 發病早期PVI 的明顯上升,有助于預測DCI 的結論。國內康平等[30]分析了 120 例 aSAH 患者發生 DCI 的危險因素,結果發現除了腦積水程度、Hunt-Hess 分級、Fisher分級外,PVI 也是促使DCI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當PVI≥0.046 時,會顯著增加 aSAH 后 DCI 發生的風險(P<0.05)。研究發現,aSAH 后發生DCI 患者的PDW 水平比未發生DCI組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提示血小板活化與DCI 發生相關,進而影響患者預后[13,31]。
與aSAH預后有關的炎癥標志物
1、C 反應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和高敏C 反應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
CRP 是急性期炎性相關蛋白,它獲取方式簡單,檢測方便,成本低廉,是被廣泛用于評估炎癥和組織損傷的標志物。標準的CRP 檢測法檢測下限是3~8 mg/L,而hs-CRP則可將檢測下限拉低至0.1~0.2 mg/L,其靈敏度比CRP 高出100 倍。CRP,尤其是hs-CRP 已被證實可作為判斷冠脈綜合征、缺血性腦卒中等急性心腦血管疾病預后的標志物[32-35]。近年來,CRP 和 hs-CRP 在 aSAH 上的運用價值也愈加受到重視[36]。Turner 等[37]研究發現,對于低級別[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WFNS)分級1~2 級]aSAH 患者,入院時高水平CRP 與不良預后有關,CRP 有助于早期識別出一部分低級別aSAH 卻存在病情惡化乃至不良預后可能性的患者。另有延伸研究也將CRP 與其他炎性因子結合起來,如外周血白細胞,CRP/白蛋白比值,以提高其在臨床預后預測上的效度[38-40]。
2、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和核因子κB(NF-κB)
aSAH 后1~2 d,系統性炎癥活動達到峰值,其中細胞因子是強力的炎性反應調節因子。各種資料都證實,在aSAH 后腦脊液中各種細胞因子水平升高很常見[41],包括了出血后腦血管痙攣相關的細胞因子,如TNF-α、IL-6等多種促炎細胞因子和參與炎癥基因表達的NF-κB[42-43]。另一方面,也有臨床病理學研究顯示,在動脈瘤標本中以上炎癥因子呈現高表達狀態,這表明其在動脈瘤的形成、增大及破裂出血過程中發揮重要的生物學作用[44-46]。
TNF-α 一般是由被激活的單核細胞、巨噬細胞所生成分泌的,是一種可溶性多肽類細胞因子,其作用是參與人體炎性反應和免疫應答。TNF-α 與靶細胞上的TNF 受體1 相結合,引導內皮細胞凋亡路徑的組成蛋白在動脈瘤瘤體中增加表達,增加內皮細胞的通透性并造成細胞損傷[47]。動物實驗發現,在誘導制造兔SAH 后遲發性腦血管痙攣的模型中,TNF-α 表達增加,于第7 天達到高峰,之后逐漸下降,與遲發性腦血管痙攣炎性反應發生時間相一致。在遲發性腦血管痙攣中,TNF-α等炎性因子活性顯著增強,參與損傷級聯反應,從而加重腦組織損傷破壞[48]。同樣的,在臨床研究中也得出類似結論,張秋建等[49]通過采集比較了aSAH后腦血管痙攣組和非腦血管痙攣組、預后良好組和預后不良組中血漿的TNF-α 濃度,發現血漿TNF-α 濃度與患者預后存在相關性,預后不良組TNF-α濃度明顯高于預后良好組。
顱內動脈瘤破裂后,機體隨之出現全身及局部炎性反應,促成早期腦損傷,巨噬細胞、血管內皮細胞以及活化的小膠質細胞大量分泌IL-6。在aSAH 出現后的4 d 內,腦脊液中IL-6 濃度進行性升高,并與腦血管痙攣和DCI 的發生時間、較差的臨床預后存在關聯,具有一定的臨床預測價值[50]。血清IL-6 水平也與aSAH 患者術后炎性并發癥發生率緊密相關[51]。Ahn 等[52]的研究證實:血清IL-6 水平早期升高與不良臨床狀態及結果呈現正向相關性。此外,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早期IL-6 升高體現的是炎性反應強度,而不是腦損傷本身[53]。
NF-κB 是 TNF-α 等多種細胞因子的啟動子,其在aSAH 患者中的激活可能意味著體內開始啟動炎性反應。而NF-κB 作為一種主要的炎癥和免疫穩態調控因子,可通過介導泡沫細胞產生、增殖而促進血管炎性反應,從而提高TNF-α 的轉錄水平,而TNF-α 表達水平的提高又反過來推動NF-κB 的活化,二者共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正反饋系統,結果將導致更強烈的組織炎性反應,進而促使aSAH發病,加劇腦組織損傷[54]。呂洲與劉青蕊[55]研究表明,NF-κB 活化率和TNF-α 水平呈正向相關性,這就說明NF-κB 和 TNF-α 共同參與 aSAH 的致病過程,均與患者預后存在關系。梁漢才與楊福義[56]研究發現,aSAH 后NF-κB在腦血管痙攣組和非腦血管痙攣組中的表達有差異,但這種差異只體現在發病早期,這同樣暗示NF-κB 是在腦血管痙攣的炎癥早期發揮“啟動”作用。
小 結
綜上所述,外周血白細胞計數、NLR、血小板參數、CRP和hs-CRP、TNF-α、IL-6和NF-κB是預測aSAH預后的有效炎性指標。炎性反應是aSAH致病機制中的重要環節,相關炎性指標的早期識別有助于優化治療和改善醫療資源的分配,但單一炎性指標預測aSAH 患者的預后可能并不準確,需要聯合多個指標綜合評估。未來仍需深入挖掘更高信度和效度的炎性指標,建立更高效更實用的臨床預測模型,并研究這些指標與aSAH之間的病理生理學關系,從而進一步判斷和改善aSAH患者的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