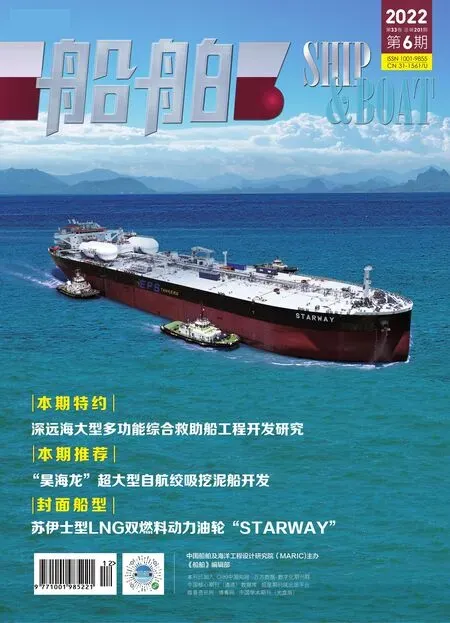船舶進出三峽升船機時下沉量模型試驗研究
胡方珍
(中國船舶集團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 上海 200031)
0 引 言
船舶在狹淺水域航行時阻塞效應明顯,下沉量較大。若船舶因下沉量過大觸底,將對船舶本身和通航設施造成損壞,影響通航安全。為了保證航運安全,許多學者對船舶下沉量進行了研究。洪碧光等[1]對比了目前國際上應用較為廣泛的幾種下沉量計算公式,發現不同公式對同一對象計算結果差別較大,大部分公式沒有根據船舶類型不同調整計算參數,適用范圍有限。李超等[2]對Ankudinov 公式進行了改進,計算精度有所提高,但改進公式表述比較復雜,需要借助軟件才能用于實踐,實用性有待提高。吳明等[3]運用CFD 方法獲得了S60 裸船模航行下沉量和縱傾,但模擬航行工況較少,無法給其他船型提供借鑒和參考。呂建偉等[4]提出了特定斷面航道船舶下沉量計算公式,適用范圍仍然受到一定限制。戴冉等[5]在海港水域開展了大型油輪和散貨船的下沉量實船測試研究,但測試周期較長、難度較大而且成本很高。
雖然針對船舶狹淺水域航行下沉量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這些研究多集中于數值計算理論和方法。船舶在狹淺水域航行過程融合了船體運動、螺旋槳旋轉、航行水域水體流動、通航設施邊界影響以及上述各個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現有的數值計算方法和軟件難以準確模擬上述動態過程,因而其結果可靠性和工程適用性有待進一步研究。實船測試可獲得較為可靠的結果,但測試難度較大而且成本很高。考慮技術可行和經濟成本,通過模型試驗研究船舶在狹淺水域航行下沉量仍是主要手段。此外,以往的研究對象大多針對海船,少有關于內河船下沉量的研究。
船閘、升船機等是典型的內河通航建筑物,在滿足設計通航船舶尺度和預期貨運量的前提下,為降低工程造價,通航建筑物的通航尺寸和水深一般取最低限度[6],其所在水域屬于典型的狹淺水域。相對來說,升船機比船閘尺寸更小,其附近水域通航條件更差,對通行船舶限制條件更為嚴格。本文擬以船舶進出三峽升船機為例,通過模型試驗研究船舶的航行下沉量,提出適用于估算船舶航行下沉量的方法,為航運管理部門制定通航管理規定和船舶設計單位設計相關船型提供技術支撐。
1 船舶航行下沉量理論分析
船舶進出升船機過程涉及螺旋槳啟停、船體運動、升船機內水體流動、升船機邊界影響以及上述各個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是一個復雜的多因素耦合問題。為簡化分析模型,假設船舶航行于半無限長的狹淺水域。船舶前行過程中,流經船體周圍(船底尤為明顯)水流速度增加。根據伯努利方程可知:此時船底所受壓力減小,船舶出現下沉;與此同時,船舶在行進過程中生成的波浪傳遞至船廂另一端,經壁面反射后與行進波共同形成廂內水面波動,使船舶產生縱向傾斜而引起船舶下沉。
實際上,上述2 種因素產生的下沉通常疊加在一起,很難加以區分[7],工程上只關心兩者耦合后的船舶綜合航行下沉量δ(以下簡稱“船舶航行下沉量”)。船舶進出升船機的過程可簡化為圖1所示。

圖1 船舶航行下沉量原理圖
圖中:δ為船舶航行下沉量,m;f為船舯橫剖面水線以下面積,m2;V為船舶航速,m/s;u為水體回流速度,m/s;H為船廂水深,m;F為船廂過水橫斷面面積,m2。
根據質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定理可知,圖1所示的系統應滿足以下方程:
連續性方程:

能量守恒方程:

根據上述方程,若將δ視作因變量,則V、F、f與u均會影響δ的大小,而水體回流可看作航速V的結果,故δ只與V、F、f相關。基于此,可將上述因素作為試驗變量體現到模型試驗的設 計中。
2 試驗模型
試驗模型的選擇及處理主要包含通航設施模擬(即三峽升船機及上下游引航道),以及試驗船舶(即需通行三峽升船機的代表性船舶)。通航設施模型須真實反映船舶通行三峽升船機途經的最不利航道條件;試驗船舶模型選擇既要滿足三峽升船機通航限制條件,又要符合升船機的快速過壩通道功能定位,應當是具有代表性的主流船型和未來大力發展的適應船型。
2.1 通航設施模型
根據實地調研,三峽升船機上游為開闊的庫區水域和引航道,水面寬闊、水深條件良好且對船舶航行影響較小;三峽升船機下游為下游引航道,其航道較窄且水深較淺。本試驗重點研究對船舶航行相對不利的下游引航道。為真實還原船舶進出三峽升船機的場景,建立的通航設施模型包括三峽升船機船廂和下游引航道,物理模型總長約90 m、最大寬度約20 m,模型比尺為 1∶12,模型實物見圖2。

圖2 三峽升船機船廂及下游引航道物理模型
2.2 試驗船舶模型
試驗船舶的選擇主要基于如下因素:
(1)試驗船舶要滿足三峽升船機限制條件。由于水域及空間有限,因此,三峽升船機對通航船舶的長、寬、吃水以及排水量均有要求。船舶總長和總寬分別不超過110 m 和17.2 m,以免因安全距離不足而使船舶碰撞升船機廂門或側壁;考慮船舶航行下沉量并預留部分安全余量以避免船舶觸及升船機廂底,故船舶吃水不超過2.7 m。此外,若升船機運行中出現意外漏水導致廂內水體排空,則船舶將直接接觸升船機廂體,所有重量也將會施加在升船機廂體上,故為保證升船機廂體結構安全,船舶的排水量不應超過3 000 t。
(2)試驗船舶的選擇應符合升船機的功能定位。三峽升船機是船舶快速過壩通道[7]。在通行三峽樞紐的船舶中,客運船舶、特殊任務船舶以及對時效性要求較高的集裝箱快班輪和商品汽車滾裝船是具有優先通過權的船舶。因此,在選取試驗對象時,上述類型船舶應優先考慮。此外,干散貨運輸船舶通過三峽樞紐的頻次最高,在選取時應重點考慮。
(3)船舶進出三峽升船機的試驗航速應不大于1 m/s。交通部頒布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水上交通管制區域通航安全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五款規定,船舶進出升船機最大允許速度分別為0.7 m/s、0.5 m/s;根據國內相關科研單位的研究結論[6-7,10],船舶出升船機速度一般控制在0.5 m/s 以內。船舶進出三峽升船機的試驗航速應滿足上述要求。為了獲得更多的數據樣本,本次試驗將進出航速限定在1 m/s 內。
基于上述因素,試驗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4 型船舶,其船型尺度和試驗工況如表1所示,船舶模型見下頁圖3。

圖3 試驗船舶模型

表1 試驗船舶尺度及試驗工況
3 試驗及測量方法
船舶在承船廂及引航道內航行時,船體周圍流場變化將引起航行速度的改變。如果采用自航模進行試驗,由于阻力變化,船舶航行速度將不穩定。此外,自航模試驗方法不利于試驗數據采集,同時也給數據分析帶來不便。因此,本試驗采用牽引系統拖曳船模方式進行[8]:在航道模型上設置鋁制導軌,船模牽引車拖曳試驗船舶沿著導軌行進,其速度可調可控,船模牽引車行進方向固定;試驗船舶由牽引車拖曳航行與牽引車同步運動,不會出現航道偏移或者碰撞側壁的情況。
試驗過程中,在船舶首、尾上方軌道分別安裝1個超聲波水位傳感器,牽引系統驅動超聲波水位傳感器在軌道上與船舶做同步運動,可測得船模首、尾與基準面(水平軌道)的距離,進而求得船模在航行過程中的升沉高度。以上參數通過布置在船模上的便攜式采集系統直接采集,并通過無線網絡傳輸到計算機自動測量,船模牽引系統及測量設備見圖4。

圖4 船模牽引系統及測量設備
船舶下沉時是沿著縱向傾斜(參見圖1)。船舶可視為剛體,自身沒有變形,則下沉量的最大、最小值只會出現在艏艉兩端。測得了艏艉的下沉量,取其大者即為船舶最大下沉量。
4 試驗結果及分析
在3.5 m 水深條件下,依次對選定的船舶模型進行拖曳試驗,并測量相關參數。由于水體流動和船舶運動的影響,船舶航行升沉量是一個動態變化過程。以3 500 噸級干散貨船為例,在分別以 0.5 m/s、0.9 m/s 的速度駛出船廂時,其升沉量變化如下頁圖5所示。
由圖5可知,對于3 500 噸級干散貨船,船舶出廂最大下沉量基本發生在船舶啟動行駛50 m 時,即距離上游臥倒門60 m 處的船廂中部;船舶出現最大下沉量后,下沉量隨著位移增加而逐漸減小,最后維持在平衡位置;隨著船舶航速增加,最大下沉量也隨之增大。動態曲線便于對船舶單次航行下沉量的理解,但不便于得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規律。工程上更關注的是整個航行過程下沉量的最大值,因此,對試驗結果進行統計,得出各型船舶以不同航速進出升船機的最大下沉量,如下頁表2所示。

圖5 3 500 噸級干散貨船升沉量變化曲線
對表2數據進行梳理,可得出如下結論:

表2 船舶進出船廂最大下沉量
(1)對于同一船型,船舶航行下沉量隨著航速增加顯著增大。以3 500 噸級干散貨船為例,在出廂航速為0.3 m/s 時,其下沉量為13.6 cm;當航速為0.9 m/s 時,其下沉量為66.7 cm,約為0.3 m/s的5 倍。船舶航速是影響船舶下沉量的重要因素,為控制船舶下沉量,應優先考慮控制船舶航速。
(2)同一航速下,斷面系數小的船舶下沉量大,即下沉量受船舶舯斷面水線以下面積(即船舶肥瘦程度)的影響。以3 500 噸級干散貨船和500車商品車滾裝船為例,其斷面系數分別為1.59 和1.57,可知3 500 噸級干散貨船的船舶舯斷面面積大于500 車商品車滾裝船,在0.5 m/s 出廂工況下,其下沉量分別為22.9 cm 和18.5 cm。船舶線型越豐滿,其下沉量越大;船舶線型越纖瘦,其下沉量越小。船舶線型對下沉量的影響相對較小,且既有船舶無法改變其線型。但在設計新的船型時,應當考慮。
(3)船舶進出船廂的下沉量不同,船舶出廂下沉量大于進廂下沉量。以325 TEU 集裝箱船為例,在航速0.5 m/s、0.7 m/s 和0.9 m/s 工況下,出廂下沉量均大于進廂下沉量。根據已有研究,該現象可解釋為:船舶進廂時,尾部水體與外部水體是連通的,船舶行進產生的缺失水體空間可由外部水體迅速補充,尾部水體水位基本維持在原有水平,故船舶尾部下沉量較小;船舶出船廂時,尾部水體與外部斷開,船舶行進產生的缺失水體空間不能得到有效補充,水位下降明顯,故船舶下沉量較大[6-7]。綜合以上分析,應將船舶出船廂過程作為最大下沉量的控制工況[7,9]。
對下沉量δ、船速V、船廂水深H和斷面系數n(斷面系數n的定義見表1)作如下處理,記:

對表2所有船舶出廂工況數據進行處理,得到無量綱的P、K參數,將對應的P、K值繪制散點圖,如圖6所示,由圖可見無量綱的P-K之間存在線性關系。

圖6 無量綱P、K 參數散點分布
將圖6所示的散點數據通過最小二乘法進行擬合,并將公式(3)代入,可得如下公式:

對于3 500 噸級干散貨船、325 TEU 集裝箱船、500 車商品汽車滾裝船和未來新船型-I,其[a,b]取值分別為[2.156,0.017]、[2.82,0.02]、[2.63,0.01]、[2.285,0.035],相關系數R2分別為0.969 5、0.923、0.981 6、0.960 7,公式擬合性較好。在工程上,可以用上述4 艘船舶的擬合公式為樣本來估算類似船型的航行下沉量。
5 牽引試驗可靠性驗證分析
為便于試驗數據采集和結果分析,上述試驗是采用牽引系統拖曳船模以定速航行的方式實現的,這與船舶實際的航行方式不同。為確保試驗結果的可靠性,本節擬采用船模自航試驗對牽引試驗結果進行驗證。為使結果更加精確,試驗采用2 種自航方式:
(1)船模螺旋槳轉速恒定,變速進出船廂;
(2)通過調整螺旋槳轉速保持船模航速恒定,恒速進出船廂。
試驗時,牽引系統根據相同試驗條件下自航船模航行的速度-位移曲線,拖曳船模以相同的速度變化進出船廂,作為對比組來分析2 種試驗方法對下沉量的影響。
5.1 自航變速試驗
圖7為自航船模和牽引船模變速出廂過程船舶航行下沉量變化曲線。由圖可知,自航船模啟動加速過程受螺旋槳轉動影響,下沉量較牽引船模略 大;但隨著船舶出廂距離增加,船舶航速增大趨穩,自航船模與牽引船模下沉量大小已無明顯差別;最大下沉量均發生在距下游船廂門約25 m 的位置。因此,螺旋槳僅對加速過程的下沉量有所影響,但對最大下沉影響不大,基本可以忽略螺旋槳對船舶最大下沉量的影響。

圖7 自航船模變速航行下沉量曲線
5.2 自航恒速試驗
下頁圖8為自航船模和牽引船模恒速出廂過程船舶航行下沉量變化曲線。由圖可知,2 種試驗方式測得的下沉量變化曲線無明顯差異,只是自航船模以較高速度出廂時,船首水位壅高,航行阻力增大。為維持恒定速度,需要提高螺旋槳轉速,自航船模下沉量受螺旋槳轉動影響較牽引船模略大。

圖8 自航船模恒速航行下沉量曲線
表3為自航船模和牽引船模恒速出廂時的最大下沉量對比。由表可見:船舶以0.6~0.8 m/s 低速出廂時,二者的最大下沉量誤差在5%以內;當船舶以1.2~1.4 m/s 高速出廂時,自航船模的最大下沉量較牽引船模增加12%~19%,誤差相對增加。

表3 船模恒速航行最大下沉量對比
綜合分析自航試驗和牽引試驗結果,其最大下沉量差異不大,螺旋槳僅對船舶加速過程的下沉量有所影響;船舶高速航行時,由于螺旋槳轉動的影響,自航船模最大下沉量較牽引船模增加2~5 cm;而考慮到實際操作中,升船機及船閘對通航船舶的限速一般不超過1.0 m/s[7,10],在該速度范圍內,自航試驗與牽引試驗結果基本一致。因此,牽引試驗結果是準確可靠的。
6 結 語
本文以船舶通行三峽升船機為例,通過牽引船模試驗測得不同船型在三峽升船機及下游引航道航行時的下沉量,通過數據處理獲得不同船型下沉量與船舶航速、航道水深和船舶線型之間的關系。為保證試驗結果的可靠性,通過自航試驗對牽引試驗的結果進行了對比驗證。研究表明:航速是影響船舶航行下沉量的重要因素,并且船舶駛出船閘、升船機的下沉量大于駛入時的下沉量,船舶出船閘、升船機過程應作為最大下沉量的控制工況。
本文給出的下沉量計算擬合公式,可作為計算類似船型航行下沉量的依據;通過對比牽引試驗和自航試驗結果,證實所采用的牽引試驗測量船舶最大航行下沉量的方法準確可靠。所得的研究結論,亦可為航運管理部門制定通航管理規定和船舶設計單位設計相關船型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