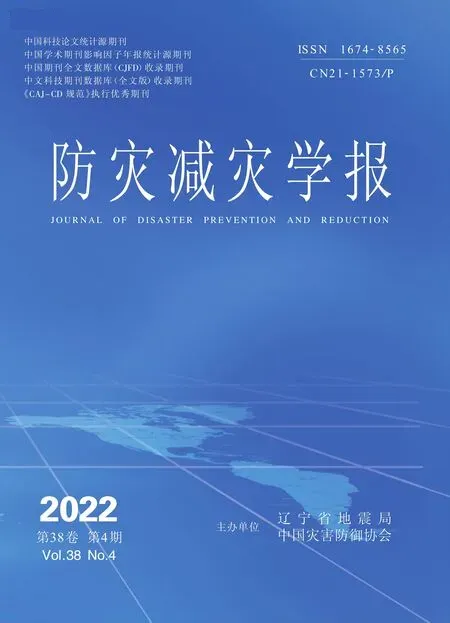甘洛縣泥石流災害的特征及分布規律
翟毅飛,陳寧生,王 濤,胡桂勝,3,田樹峰
(1.西藏大學,西藏 拉薩 850000;2.中國科學院、水利部 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41;3.高原科學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青海 西寧 810016)
0 引言
我國泥石流災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區,對當地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以及財產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脅。經統計,四川省泥石流災害數量有3171處,各省排名位于第三[1],涼山州有1358處發生過泥石流災害,其數量位居四川省第一[2]。泥石流災害爆發突然、沖淤力強、沖擊力大,且易阻塞河道形成災害鏈,給人民群眾帶來巨大的財產損失,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如1981年利子依達溝和新基姑爆發泥石流災害,對鐵路造成影響,其中利子依達溝泥石流災害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000余萬元,130人死亡和失蹤,是建國以來破壞最嚴重、損失最大的鐵路泥石流災害[3]。
甘洛縣泥石流災害頻發,給當地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帶來了嚴重的威脅,嚴重影響了甘洛縣社會與經濟的發展,是該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大阻力。泥石流災害的分布規律可為泥石流災害的高效能防治提供科學依據。目前已有部分關于甘洛縣的泥石流災害的類型以及規模頻率特征的研究,但大多數只是針對單一的泥石流溝,對于甘洛縣整個縣城泥石流災害的分布規律研究較少。Lin[4]認為通過對臺灣1999年地震后的災害事件統計,得出震后地質災害事件的頻率和規模有明顯的增加的結論;Chen等[5]認為地震與干旱的疊加可以促進中國山區大型災害性泥石流的發育;唐曉春[6]認為四川盆周山地災害的宏觀分布主要受區域大地構造的控制;楊紅娟[1]認為四川省泥石流災害主要分布在安寧河斷裂帶和龍門斷裂帶周圍;巴仁基[7]發現大渡河流域泥石流災害主要分布在大渡河中游的丹巴至石棉段,其分布主要受斷裂帶控制,黃成[8]對都汶公路沿線的32條泥石流溝的地形因子進行了統計并建立綜合地形因子的臨界模型G,發現地形因子越大越易爆發泥石流災害,且坡度在所有地形因子中權重最大;高翔[9]認為甘洛縣泥石流主要為暴雨型泥石流,泥石流主要分布在尼日河兩岸,其次為田壩河與甘洛河兩側、植被較差的地方、背斜構造以及陡坡處,泥石流集中在雨季,且呈現明顯的夜發性;王治農[10]認為1981年利子依達溝泥石流的爆發主要受地形和地質構造的控制,暴雨為其激發因素;李鈺[11]認為降雨誘發了甘洛縣2019年群發性山洪泥石流災害。本文通過對甘洛縣的泥石流溝進行調查,研究泥石流災害與孕災環境的關系,對泥石流災害的空間分布特征以及災害特征進行研究。
1 地質環境條件
1.1 氣象水文
甘洛縣地處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地理位置為102°27′29.3″~103°1′47.4″E,28°38′33.9″~29°18′22.0″N,與峨邊縣、美姑縣、越西縣、石棉縣接壤,與漢源縣隔江相望。甘洛縣屬于低緯度高海拔地區,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多年平均降雨量為980 mm。時間上,降雨主要集中在6-8月,且多為暴雨和大暴雨。空間上,甘洛縣水平方向上,降雨量由南向北遞減,垂直方向上降雨量隨著海拔的升高而升高(圖1),降雨往往從山頭形成,易形成洪峰。甘洛縣水系為大渡河水系,尼日河為其主干水系,其次有甘洛河、田壩河等。

圖1 甘洛縣圖Fig.1 Ganluo County Map
1.2 地形地貌
甘洛縣處于四川盆地與青藏高原過渡的地帶,屬于高山峽谷地貌,其地勢東、西、南三面高,北部和中部較低,以中山為主,內高差可達3718米。甘洛縣的地貌主要有侵蝕堆積地貌、侵蝕構造地貌、溶蝕構造地貌以及剝蝕夷平面地貌四種。
1.3 地層巖性
甘洛縣地層發育連續,巖性較為復雜,巖漿巖、沉積巖和變質巖均有出露,其特點是四周地層較中部地層老,最年輕的地層分布于河流兩岸,巖性大多為石灰巖(圖1)。
元古界:前震旦系峨邊群(Pt1eb)玄武巖;震旦系下統蘇雄、開建橋組(Zas-k)超基性-基性-中性-酸性侵入巖及火山巖;震旦系上統燈影組(Zbd)、觀音崖組(Zbq)硅質白云巖;列古六組(Zbl)泥巖夾砂巖、砂礫巖。
新生界:上新統昔格達組(N2x)粉砂巖、砂質粘土巖及砂礫巖;第四系河流沖積(Qhal)、冰積(Qpgl)、殘坡積(Qheld)。
1.4 地質構造
甘洛縣作為康滇古陸的一部分,白堊紀末期的“四川運動”在四川盆地的邊緣發生劇烈的褶皺,并形成大量的逆掩斷層,因此該區域地質構造復雜,褶皺和斷層十分發育(圖1),縣內斷層多為北西向,馬哈拉斷裂、阿巴而及斷裂及石棉—馬前門斷裂貫穿全縣,褶皺軸向多與斷層平行,形成嶺谷相間分布的深切峽谷地貌。
正是由于甘洛縣獨特的地質地形條件以及氣象水文條件,使得該縣巖體破碎,松散堆積物豐富,所以泥石流活動十分頻繁。
2 研究方法
30米分辨率的Landsat 8遙感影像云量較少,能清晰的看出泥石流溝的流域、堆積范圍等基礎信息,因此本文選取30米分辨率的Landsat 8遙感影像對泥石流災害進行遙感解譯,并結合野外調查,確定了甘洛縣境內63條泥石流溝的地理位置以及流域面積、堆積扇面積、溝道、高差以及溝道長度、溝道縱比降等參數。通過ArcMap的疊加分析功能,可得到泥石流災害與地形地貌、坡度、巖性以及地質構造的關系;根據《工程巖體分級標準》(GB/T 50218-2014)將巖石堅硬程度分為堅硬巖、較堅硬巖、較軟巖、軟巖和極軟巖,甘洛縣的巖性可分為堅硬巖,包括各種巖漿巖、碳酸鹽巖與碎屑巖互層;較硬巖,包括砂巖、頁巖、灰巖及砂巖、頁巖、灰巖互層;較軟巖,包括砂巖、泥巖、灰巖、礫巖與灰巖互層;軟巖,包括泥巖;極軟巖,包括第四紀堆積物;建立漁網,使其與研究區斷層相交,統計每個單元內斷層的長度,每個單元內斷層總長度與面積之比即為斷層密度[12];通過生成臨近表來計算泥石流流域與斷層的距離,進而分析斷層對泥石流災害的影響范圍。
3 甘洛縣泥石流災害的主要特征
3.1 規模特征
泥石流災害的規模可以根據泥石流一次性沖出固體物質的量劃分為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4個等級[13],如表1甘洛縣泥石流規模統計表,甘洛縣共有63條泥石流溝,其中小型泥石流溝有53條,占比84.1%,中型泥石流溝有9條,占比14.3%,大型泥石流溝有1條,占比1.6%,該區泥石流主要為小型泥石流。大型以上規模較少。

表1 甘洛縣泥石流規模統計表
3.2 爆發特征
甘洛縣泥石流集中分布于河流、公路兩側,泥石流災害發生頻繁,給道路交通等造成重大損失。
3.2.1 群發性
受斷層、巖性以及人類活動等影響,甘洛縣在暴雨等極端天氣下易形成群發性地質災害造成巨大的損失。如1987年6月5日,甘洛縣共7條溝爆發泥石流,共造成6人死亡[10]。2019年7月29日,甘洛縣爆發10處泥石流災害,此次災害共造成12人死亡,倒塌房屋12戶40間,農村道路損毀72公里,成昆鐵路中斷,多個工礦企業受到不同程度損失,涼紅電站廠房被沖毀,此次災害共造成損失約15億元[11]。2020年8月30日,甘洛縣爆發山洪泥石流,多個鄉鎮遭受泥石流災害影響,成昆鐵路K295+375段鐵路橋梁垮塌中斷,沖毀2所學校,蘇雄大橋、阿茲覺中橋、小老木吊橋、阿茲覺大橋全部被毀,3人失聯,此次災害共造成經濟損失約1.22億元。
3.2.2 夜發性
甘洛縣雨季降雨主要以夜間降雨為主,據調查,甘洛縣泥石流多在夜間發生。如1981年3月16日凌晨2時32分左右成昆線阿寨—白果間K341+037m新基姑發生泥石流;1987年6月5日凌晨4時自勒溝和拉古子溝爆發泥石流;2004年7月31日凌晨2時左右海棠鎮大橋村無名溝發生泥石流,2009年7月31日凌晨1時左右前進鄉自物村發生泥石流。災害發生時居民往往都在睡眠之中,無法對泥石流災害做出相應避險措施,這也是該縣泥石流災害造成經濟損失重大的原因之一。
3.2.3 沖溝泥石流活化特征
研究區構造運動活躍、地形陡峻且植被破壞嚴重,加之強烈的風化作用,在斜坡上分布著較多沖溝,這些沖溝表層土體疏松,坡度陡,高差大,流域形態呈長條形或柳葉形,且流域面積較小。在一些生態環境惡劣的地段,很久未曾發生過泥石流的沖溝再一次發生泥石流災害,且其活動性有進一步增強趨勢。如特克棚洞上方兩條沖溝于2009年7月29日突然爆發坡面碎屑流,其巨大的沖擊力導致棚洞垮塌,并造成7人死亡。
4 甘洛縣泥石流災害的分布狀況
甘洛縣泥石流災害的發育在空間展布上極不均勻,前進鄉泥石流災害點密度達24.31個/100km2,吉米鎮泥石流災害點密度達15.75個/100km2,而烏史大橋鄉泥石流災害點密度僅為0.83個/100km2,如圖2甘洛縣泥石流災害分布圖和表2甘洛縣各鄉鎮泥石流災害密度;此外泥石流還沿著主要河流與主要交通干線分布,泥石流災害在尼日河上游以及田壩河分布較為密集,如圖2甘洛縣泥石流災害分布圖和表3河流兩側泥石流災害分布表,其密度分別為0.61條/km和0.57條/km,泥石流災害的分布明顯沿著斷層與褶皺呈現出條帶狀分布,且集中分布于中部斷層交錯的區域,如圖2甘洛縣泥石流災害分布圖。

圖2 甘洛縣泥石流災害分布圖Fig.2 Debris flow disaster distribution map in Ganluo County

表2 甘洛縣各鄉鎮泥石流災害密度

表3 河流兩側泥石流災害分布表
5 泥石流災害與地形參數及巖性構造的關系
泥石流的形成有三個基本條件:地質條件、地形條件以及水源條件,地質和地形條件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物源和動能,水源為泥石流的激發因素[14]。
5.1 泥石流發育與地形參數的關系
5.1.1 泥石流發育與坡度的關系
對甘洛縣63條泥石流溝進行統計分析,發現泥石流溝流域坡度集中在20°~30°范圍內,如表4泥石流流域坡度統計表。一般來說,泥石流溝山坡坡度越大,就越利于泥石流匯水區水流的匯集和啟動,且大的坡度使得泥石流溝溝道兩側形成臨空面,增加滑坡和崩塌的概率,從而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物源。

表4 泥石流流域坡度統計表
5.1.2 泥石流發育與溝道平均縱坡降和高差的關系
甘洛縣泥石流的溝道平均縱坡降主要集中在200‰~500‰之間,占總數的82.5%,如圖3泥石流溝道平均縱坡降統計圖。溝道平均縱坡降過小時,洪流沒有足夠的攜帶及沖刷能力,而溝道平均縱坡降>600‰時,松散物質難以在溝道堆積,因而泥石流災害較少。

圖3 泥石流溝道平均縱坡降統計圖Fig.3 Statistical graph of average longitudinal drop of debris flow channel
高差為泥石流的啟動提供了勢能以及勢能轉化為動能的條件。研究區泥石流溝高差在600m以上明顯增加,但是在高差大于1400m后泥石流溝的數量就明顯減少了,如圖4泥石流流域高差統計圖,研究區泥石流的流域高差在201~3024m之間,高差在600~1400m最為發育。

圖4 泥石流流域高差統計圖Fig.4 Statistics of height difference in debris flow basin
5.2 泥石流發育與巖性構造的關系
5.2.1 泥石流發育與巖性的關系
巖性對泥石流的物源有一定的影響,研究區泥石流溝在較硬巖區域最為發育,其次為較軟巖區域,如表5泥石流溝各巖性面密度和圖5甘洛縣泥石流溝巖性分布圖,其原因為研究區堅硬巖與較軟巖分布廣泛,其次研究區斷層發育,巖石普遍較為破碎,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松散物質。

圖5 甘洛縣泥石流溝巖性分布圖(彩色)Fig.5 Lithology distribution map of debris flow gully in Ganluo County

表5 泥石流溝各巖性面密度
5.2.2 泥石流發育與構造的關系
(1)泥石流發育與斷層密度的關系
對甘洛縣進行斷層密度劃分,用自然斷點法將斷層密度小于25km/100km2的為低,介于25km/100km2~80km/100km2的為中,大于80km/100km2的為高。經統計,研究區的泥石流災害在斷層密度高的地方最為發育,斷層密度低的地方最不發育,如圖6泥石流斷層密度分布圖和表6泥石流斷層密度統計表。泥石流在斷層密度為高的地方有6條泥石流溝,占比9.5%,其密度為6.88條/100km2,斷層密度為中的區域有20條,占比31.7%,其密度為4.01條/100km2,斷層密度為低的區域有37條泥石流溝,占比58.7%,其密度為2.38條/100km2。

表6 泥石流斷層密度統計表

圖6 泥石流斷層密度分布圖(彩色)Fig.6 Debris flow fault density distribution map
(2)泥石流發育與斷層的關系
研究區泥石流沿斷裂帶展布,斷裂帶兩側巖土體結構破碎,強度和穩定性較低,易風化或者產生崩滑物,從而為泥石流提供物源。研究區有俄落斷裂、特克斷裂、馬拉哈斷裂、田壩斷裂、阿巴而及斷裂和石棉—馬前門斷裂通過,且多為高角度逆沖斷層,產狀陡峻,巖石破碎,北部斷層走向復雜,縱橫交錯,多為折線,因此研究區地形破碎,加之植被覆蓋度低,極易發生泥石流。研究區泥石流溝距離斷層越近越發育,如圖7甘洛縣泥石流溝距斷層距離統計圖,甘洛縣的泥石流溝主要在斷裂帶兩側1km范圍內。

圖7 甘洛縣泥石流溝距斷層距離統計圖Fig.7 Statistics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debris flow gully and the fault in Ganluo County
6 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甘洛縣泥石流災害的特征及分布規律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1)甘洛縣共有63處泥石流災害點,縣內泥石流災害分布不均,主要集中于前進鄉和吉米鎮,北部泥石流災害呈帶狀分布于斷層和河流兩側,南部泥石流災害集中分布于河流兩側,且數量較少。
(2)甘洛縣泥石流災害的發育分布受地質構造、巖性、地形地貌和坡度的綜合控制,強烈的新構造運動和高陡的谷坡使得本區域巖體破碎,崩塌和滑坡等松散物質極其豐富;河流下切快、比降大、谷坡陡,為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能量;在此基礎上,豐沛的降雨使得本區域泥石流災害較為發育。泥石流分布在距離斷層6km以內的區域以及斷層密度高的地方,離斷層越近、斷層密度越大,泥石流密度越高,44.4%的泥石流溝被斷層穿過,22.2%的泥石流溝位于斷層0~1km范圍內,斷層密度高的區域泥石流密度達6.88條/100km2。
(3)甘洛縣的泥石流災害共有63處,其規模以小型為主,共有53處,占比84.1%;泥石流災害的爆發具有群發性、夜發性以及沖溝泥石流活化特征,應加強山洪泥石流監測預警工作,進一步退耕還林,進行有效的水土保持工作。
(4)筆者僅對甘洛縣的泥石流災害分布以及孕災環境進行了分析,但是對于研究區泥石流災害的群發性和夜發性并未做出進一步的分析,這也將是筆者下一步研究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