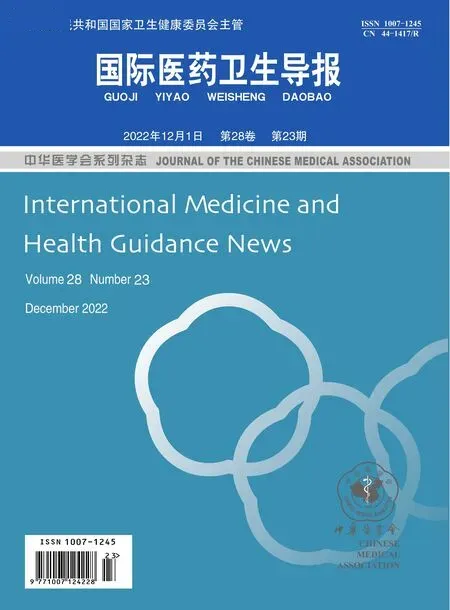納米脂質體藥物在類風濕性關節炎治療中的研究進展
王晶 朱美玉 康麗 韓娟娟 朱學凱
1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藥學部,濱州 256600;2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兒童消化與腎病中心,濱州 256600;3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骨關節外科,濱州 256600
類風濕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臨床常見的慢性炎癥性疾病,其病理特征是關節滑膜慢性炎癥,臨床表現包括關節疼痛、腫脹及僵硬等[1]。靶向給藥系統可分為脂質體、微囊、微球、納米粒等,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為靶向脂質體[2]。RA的發病機制仍不清楚,目前普遍認為關鍵因素是關節組織異常的免疫反應誘發關節炎癥,導致關節破壞。此外,RA常引發關節外表現,如類風濕結節、肺血管炎等[3]。
抑制或減輕炎癥是改善RA癥狀、保持關節結構完整及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的主要治療策略[4]。RA治療藥物主要分為3類:(1)非甾體抗炎藥(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通常用于治療疼痛、僵硬和炎癥,改善患者的軀體功能;(2)皮質類固醇(corticosteroids,CORT),具有明顯的抗炎、抗血管生成和免疫調節效應,能夠下調細胞粘附分子和細胞因子的表達,從而防止關節侵蝕;(3)抗風濕藥物(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DMARDs),其中一線藥物為甲氨蝶呤,用于防止關節損傷;(4)生物制劑,包括減少炎性反應的腫瘤壞死因子抑制劑(依那西普、英夫利昔單抗、阿達木單抗等)、干擾抗原提呈細胞和T細胞之間相互作用的T細胞共刺激抑制劑、導致循環B細胞的快速和持續耗竭的B細胞耗竭劑。此外,僅應用NSAIDs因無法改善關節的病理損傷從而無法改變RA的進展,且其長期應用還會增加胃腸道、心血管和腎臟疾病的風險[5]。CORT通常在RA的早期階段使用,在DMARDs發揮作用之前作為臨時輔助治療,或在其他類型藥物無法控制RA時作為慢性輔助治療,且其長時間或大劑量應用會引起一系列不良反應,如骨質疏松、高血壓、糖尿病、肥胖等。目前,RA仍無法治愈,現有治療藥物的作用是減輕癥狀和維持病人的正常生活[6]。
盡管目前RA治療藥物種類較多,但藥代動力學顯示其在體內清除均較快,因此需要頻繁的高劑量給藥,從而導致一系列的不良反應[7]。此外,當RA患者只有少數關節出現明顯癥狀,或全身給藥沒有顯示出明顯療效時,臨床上還會采用關節內直接注射藥物的方法,增加關節內的局部藥物濃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藥物使用劑量和不良反應。然而,關節內注射的缺點是藥物清除速度快,使得關節針刺頻率較高,常導致感染、關節殘疾、注射后眩暈和患者不耐受等[8]。
RA主動靶向的生物標志物
由于引起關節滑膜炎癥的因素非常多,眾多研究已對RA治療相關的靶點進行了廣泛的探索。大量研究顯示,關節滑膜巨噬細胞會過度表達葉酸受體β(folate receptor-β,FR-β),其與葉酸具有高親和性,能夠通過介導細胞內化將葉酸攝入細胞,因此將葉酸通過γ-羧基與抗炎藥物偶聯后通過FR-β可將藥物精準靶向攝入到炎性細胞內[9]。另有研究顯示,RA患者關節滑膜淋巴細胞、巨噬細胞和成纖維細胞均過度表達CD44分子,其與透明質酸具有高親和性,因此透明質酸同樣也是設計靶向抗RA藥物常用的偶聯劑[10]。
血管生成在RA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目前,αvβ3整合素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作為RA的治療靶點已被廣泛研究。其中VEGF是血管生成的典型調節因子,其在炎癥中過度表達,關節局部缺氧和VEGF能夠明顯促進血管通透性升高和新生血管生成,同時VEGF還能夠促進內皮細胞粘附分子、炎性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表達,最終上調關節內炎性細胞水平從而加劇關節炎癥[11]。αvβ3整合素是RA滑膜新生血管的表面受體,阻斷其表達能夠抗RA[12]。
選擇素是血管黏附分子中的重要成員,其家族有L-選擇素、E-選擇素、P-選擇素3個成員,其中E-選擇素在炎癥中上調。選擇素在炎性細胞中也過度表達,其能夠將白細胞募集到滑膜組織起到病理生理作用。研究表明,阻斷E-選擇素可能是治療RA的有效策略[13]。此外,目前RA治療相關的靶點還包括巨噬細胞表面抗原(如CD163等)及免疫細胞活化組分(如參與B細胞活化的布魯頓酪氨酸激酶B等)[14]。
納米藥物遞送系統
藥物遞送系統能夠克服傳統藥物治療的缺陷,包括藥物在體內難以跨越生物屏障,以及藥物在體內快速降解或與內源物相互作用等。藥物遞送系統可以改善藥物的藥代動力學和藥效學,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療指數[15]。在藥物遞送系統中,納米系統作為最重要的介質應用于多種疾病治療的研究,其可以通過多種給藥途徑進行局部或全身給藥,包括靜脈注射、腹腔注射、關節內注射、肌內注射、皮下注射、經鼻和經皮給藥等[16]。脂質體是首個獲批應用于臨床治療且目前仍被廣泛研究的納米藥物遞送系統。
應用于RA治療的脂質體制劑
應用納米藥物遞送系統治療RA目前仍為研究熱點。納米載體(如脂質體、水凝膠等)通過關節內給藥,能夠降低藥物清除率并提高患者依從性。最新研究報道了一種包裹磺胺吡啶前藥的脂質體制劑,其在弗氏佐劑誘導關節炎大鼠模型上經靜脈注射給藥,結果顯示,動物關節腫脹度、足爪體積、痛閾以及血清中炎性細胞因子、堿性磷酸酶及類風濕因子水平均顯著降低[17]。目前應用于治療RA的脂質體藥物遞送系統包裹的藥物包括NSAIDs、糖皮質激素、DMARDs、生物制劑及具有抗炎活性的天然產物等。
1、包裹NSAIDs的脂質體
由于NSAIDs在RA治療中僅能緩解癥狀而不能抑制關節損傷,因此包裹NSAIDs的脂質體應用于RA治療的研究相對較少。研究顯示,包裹吲哚美辛的脂質體制劑能夠對角叉菜膠誘導的大鼠足腫脹及弗氏佐劑性關節炎大鼠足腫脹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結果表明脂質體藥物比游離藥物更有效,且明顯減輕潰瘍等不良反應[18]。此外,單次靜脈注射雙氯芬酸脂質體凝膠制劑可減輕抗原誘導兔關節炎模型的關節腫脹,改善軟骨和骨的破壞[19]。局部給予含有雙氯芬酸脂質體的乳液應用于角叉菜膠誘導的大鼠足腫脹模型,且使用超聲波增強皮膚滲透,能夠表現出明顯的抗炎活性[20]。
2、包裹糖皮質激素的脂質體
因抗炎活性顯著,地塞米松是糖皮質激素脂質體應用于RA治療研究最多的藥物,其次是潑尼松。所有已開發的地塞米松脂質體制劑的治療效應均高于游離地塞米松[21-22]。即使在脂質體中采用較低的藥物劑量,也能更有效地減輕關節腫脹、炎癥和骨破壞。地塞米松脂質體明顯降低了給藥劑量,減少了給藥頻率及不良反應[23]。潑尼松脂質體同樣能發揮降低給藥劑量及減毒增效的優勢,研究顯示,與游離潑尼松相比,潑尼松脂質體能夠更加明顯的緩解關節炎癥,減少軟骨損傷及骨破壞,逆轉體重明顯下降[24]。目前,潑尼松PEG脂質體有望首先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3、包裹DMARDs的脂質體
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靶向研究,甲氨蝶呤在包裹DMARDs的脂質體中研究最為廣泛。在關節炎動物模型制備的同時給與游離甲氨蝶呤或更低劑量的甲氨蝶呤脂質體,結果表明均明顯發揮了抗關節炎的作用,但在動物模型制備成功后再給藥,游離藥及脂質體均不能發揮抗關節炎的作用[25]。另有研究顯示,與游離甲氨蝶呤相比,其脂質體的抗炎活性明顯增強,能夠明顯降低關節炎大鼠的足腫脹及關節炎指數,PEG藥物脂質體則具有更明顯的抗炎活性且僅需更低的給藥頻率[26]。
4、包裹生物制劑的脂質體
首個應用于脂質體抗RA的生物活性物質為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SOD是一種具有抗炎活性的酶,可以催化分解超氧自由基到分子氧和過氧化氫。包裹SOD的脂質體在AIA大鼠模型上表現出了明顯的抗炎活性及較低的毒性[27]。另有研究比較了包裹常規SOD的脂質體及包裹酰化SOD的脂質體對RA的抗炎活性,包裹酰化SOD的脂質體顯示出更快的抗炎活性,可能是因為其部分暴露在脂質體表面從而不需要釋放酶[27]。此外,ART-1插入到IL-27脂質體上能夠使其主動靶向滑膜內皮細胞,研究顯示,其對AIA大鼠模型的抗炎活性顯著高于非靶向IL-27脂質體或游離的IL-27[28]。還有研究將金納米粒共價連接到抗IL-23抗體的脂質體表面,結果顯示該脂質體能夠主動捕獲和滅活IL-23,明顯減輕RA炎癥和減少免疫細胞招募[29]。
5、包裹藥物組合的脂質體
近年來,有研究還評價了包裹不同類別藥物脂質體的抗RA作用,通常同時將葉酸插入到脂質體上使其具有主動靶向功能。例如,將潑尼松和甲氨蝶呤同時包裹入脂質體中(潑尼松龍62.0%~71.0%,甲氨蝶呤44.0%~47.0%),通過靜脈注射評估其對RA大鼠的治療作用。與單獨的游離藥物混合物和含有這2種藥物的非靶向脂質體相比,此研究中的葉酸靶向脂質體使得RA大鼠關節內的藥物濃度明顯升高,更加顯著的抑制了RA鼠足腫脹,顯示出更大的治療潛力[30]。另有研究制備了包裹p65 siRNA及甲氨蝶呤的葉酸靶向脂質體,結果表明,與游離的siRNA、游離的甲氨蝶呤或含有兩種化合物的非靶向脂質體相比,該脂質體能夠更加顯著的抑制RA鼠足腫脹及降低關節炎指數[31]。有趣的是,雖然游離甲氨蝶呤能夠減輕足腫脹,但游離的siRNA不能產生任何治療效果,這證明了納米系統在遺傳物質遞送方面具有巨大的優勢。
6、包裹非常規藥物的脂質體
除了RA治療中常用的4大類藥物外,目前包裹天然產物的脂質體也已應用于RA治療的研究。有研究制備了包裹鹽酸青藤堿的熱敏脂質體,其可經微波熱療后釋放鹽酸青藤堿,與游離青藤堿或單獨熱療相比,炎癥部位經熱療可使該脂質體釋放青藤堿,從而產生靶向抗炎效應,包括明顯抑制足腫脹,降低關節炎指數,減少滑膜炎癥和骨侵蝕[32]。
臨床轉化
1、納米給藥系統治療RA的臨床研究現狀
適宜的納米給藥系統有可能對人類RA治療產生重大影響。目前,在用于RA治療的臨床試驗中,研究重點仍然是傳統或生物藥物,納米給藥系統的比例不到1.0%,這表明納米給藥系統在這一領域的臨床轉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通過改善藥物的藥代動力學或藥效學特性(例如,載體保護藥物免受早期降解,并使其更容易跨越生物屏障),使用納米給藥系統可以提高藥物的治療指數,將藥物直接遞送到特定靶點,并明顯降低不良反應[33]。盡管如此,目前應用于臨床研究中的納米載體種類仍有限。總之,盡管越來越多的納米藥物遞送系統已應用于RA治療的研究,但在臨床前階段具有良好療效的納米藥物在臨床試驗中能否同樣顯示出良好的治療潛力仍不能保證。
2、納米給藥系統臨床轉化的影響因素
影響納米藥物臨床轉化的關鍵因素很多,其中包括納米系統的理化性質表征、擴大到工業生產水平以及評估其體內藥代動力學和藥效學特性方面的困難,在其開發階段考慮所有這些因素可能會改善臨床轉化。對其安全性評估也缺乏標準,它們通常不符合GMP標準。此外,納米系統需要重復藥物的所有研究,包括療效和毒性等,因其與包裹藥物相比具有不同的藥代動力學和生物分布特征,因此制備及工藝優化的成本較高也阻礙了納米系統的臨床應用[34]。
納米載體的復雜性是另一個阻礙其轉化成功的障礙。因此,研究人員在開發時應避免高度復雜的設計,因為這將簡化制造和表征過程,增強重復性,并降低成本。應開發遵循GMP指南的系統,以確保一致的質量,使用較好生物相容性的材料和技術,以促進商業化過程。此外,還應與臨床應用的金標準進行比較。在RA中,治療方案高度依賴于患者對每種治療的反應,并且經常同時使用多個類別的藥物,這妨礙了對納米載體治療價值的正確評估。
總之,學術界、臨床醫生、藥物開發各個階段的專家和監管機構之間必須繼續在全球范圍內制定標準化方案和統一法規,以縮短其成功轉化為臨床制劑的時間。
小 結
盡管RA有多種治療方法,但目前尚無治愈方法,而且由于長期治療,每種療法都會產生明顯的不良反應。靶向脂質體具有巨大的治療潛力,因其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藥物的不良反應,并能夠特異性地傳遞到靶點和控制藥物釋放。由于靶向脂質體在人體內的有效靶向效應仍較低,以及缺乏統一的法規,臨床前研究中取得的成功目前尚不能轉化進入臨床試驗。總之,相信解決目前的障礙后,納米脂質體制劑將會很快被批準用于RA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