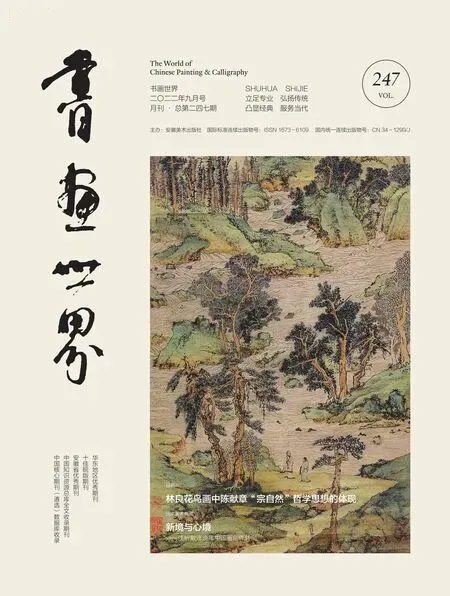課程思政視域下高校通識書法教學的內涵與價值
文_苗玉紅
北京師范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內容提要:隨著美育教育的逐步實施,書法教學在高校通識課程教學中角色日益凸顯。本文探析在課程思政的視域和理念下,如何有效地挖掘高校通識書法美育中的價值資源和人文內涵,將優秀傳統文化的育人理念融入課堂實踐,并通過書法藝術中的隱性育人元素,形成體系化的藝術實踐和藝術活動,共同提升師生的傳統道德修養和文化自信,緩解后疫情時代當代大學生的焦慮情緒,滋養有性靈、有心性的人格修養和生命境界,為新時代高校的課程思政建設發揮積極作用。
2020年,教育部《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印發。其提出,要將思政教育同具體專業課程有效結合,發揮更好的育人作用。與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學科德育”等概念有所不同,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主張將思政教育跟其他學科教育有機融合,并主張將一些具體的思政教育元素隱性植入課堂,以實現人才培養的目標。就高校通識教育而言,書法藝術所具備的立德樹人的思想資源、藝術療愈的實踐資源和心性修養的情感資源,能夠為高校的課程思政建設提供有效的內涵建設和價值指引。
一、立德樹人的思想資源
從文字出現以來,文字書寫便有了教化功能。比如,自漢唐以來,受過高等教育的政府官員通過書法來表達他們的政治和道德思想,這些思想體現在“書如其人”“書以人貴”“心正則筆正”“論書如論相,觀書如觀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等諸多評價中。雖然這些評價在今天看來缺少所謂“性格學”依據(由于一個人的內在和外在是統一的,其品德便可以從這個人的外在表現,比如外觀、行為或審美追求來推斷),但書寫者筆跡中表現出的人格、學養以及道德等,在政府選拔人才時依然是評估候選人的重要依據。那些即將成為政府官員的人,不僅要通過他們的文章,同時也要通過言談、書法來展示他們的個人能力。唐代對人從體貌豐偉、言辭辯證、楷法遒美和文理優長四個方面進行評價,在具備這四個條件后,再以德為先[1]。基于對性格學的文化認同,書法風格被賦予道德意義,書法遂變成個人價值公開表達的重要場域。王充《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 對書法典范的選擇被賦予政治和道德內涵,書法評價遂成為儒家道德系統的一個重要方面。
以北師大珠海分校為例,通識類課程有幾百門,書法藝術涵蓋其中并面向全校學生開放選修,每學年開放容量大概有800人次。在教學內容的設計方面,教師會從文字學和書學的相互關系入手,選取“道”“德”“文”“化”等漢字,介紹字形和字義的演變,以毛筆書寫的方式,引領學生體驗字體演進和文化傳承的相關性;在一個新的媒介時代,與古為徒,返本開新,體察漢字的道德鏡鑒與教化功能,以反哺文化傳統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潛移默化的教育啟發和價值影響。
在不同字體和書體的個案方面,教師選取像秦漢碑刻、“二王”、“初唐四大家”、“楷書四大家”等課程資源,從王羲之《蘭亭序》到顏真卿《自書告身帖》,從蔡邕《書勢》到孫過庭《書譜》,講解書法實踐和書法美學中所蘊含的人生情感和道德價值。如顏真卿“敢于直言、忠烈耿直”的家國情懷和英雄氣概,強烈表征著儒家文化的價值擔當。顏真卿代表性楷書作品《顏氏家廟碑》、行書作品《祭侄文稿》,其風格、人格的統一性歷來被當作國家和民族文化認同的典范,可以正確引導學生了解書法文化中所彰顯出來的人格魅力和價值指引,逐步養成其民族和家國意識。
在顏真卿書法美學中,“厚”作為一個重要的審美范疇,無論在視覺心理還是在文化精神層面,都彰顯著“中正平和”“內美雄渾”“溫柔敦厚”的儒家風范和文化氣質。歐陽修、蔡襄等人對“顏體”圓潤的、中鋒的用筆和厚重、樸拙、宏偉的篆籀之氣的推崇,以及“顏體”開放的、均衡的字形和穩定垂直的中軸線設計,都反映了書法藝術評價中書寫線條所表征的人格要素。歐陽修曾在顏真卿斷碑上題跋:“忠誠烈士、道德君子,端莊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歐陽修《集古錄》卷七)教師綜合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中對顏真卿的書法建筑在其人格基礎上的觀點,引導學生在具體的書寫實踐中,通過運筆的凝重,以及墨色、線條的跌宕起伏,體驗“顏體”筆墨的沉靜、開放與包容,在毛筆書寫的尺幅空間中打開胸襟,對話古人,沉浸式感受傳統文化的無聲教化和以美育人的功能指引。“厚”作為顏真卿書法中“德才兼備”的表征符號和傳統書法實踐的美學觀,可以在思想政治素質、人文素養、專業表達、情感體驗和身份認同等方面,引導大學生養成寬博的人格和獨立的審美意志。課程思政建設從道德修養、筆墨語言和評價體系等方面有效融入傳統書法中所蘊含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內涵,將書法知識和技巧的傳授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下的大文科教育進行有機融合,實踐文化自信和“立德樹人”的思政教育宗旨。
二、藝術療愈的實踐資源
人的感官和直覺經驗在日益受工具理性支配的當代語境中,愈發被壓抑和制約,這種現象包含著人們共有的價值觀和社會心理,構成了這個時代人們整體的“情感結構”。
研究表明,當代青年大學生的心理亞健康狀態呈逐年上升趨勢[2]。比如崇尚精神自由,但是在人際交往中缺乏信心;雖身處校園,但過早承受社會壓力而形成學習和生活的焦慮心理;意志薄弱,缺乏應對情感受挫的能力而容易導致負面情緒蔓延。重視大學生的這種心理狀況,幫助大學生養成積極健康的學習和生活態度,成為高校教育思政建設的重要工作內容。研究認為,藝術療愈在今天已經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在美育教學活動中,高校設置通識書法藝術課程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輔助性治療手段。當代藝術的發展也豐富了我們對書法實踐的認識,身體現象學方法論也為我們提供了反思書法實踐對身體療愈的理論資源和價值論域[3]。
在現代學科專業化之前,書法存在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書法書寫的實踐性都毋庸置疑。書法以特定的材料為載體,并有其獨特的工具屬性,其文字輸出方式迥異于當代數碼技術。毛筆書寫的字跡總是指示著身體的具體動作和工具、材料,在書法欣賞活動中,雖然我們看的是書寫者留下的墨跡,但隨著閱讀的不斷深入,我們就會主動聯想書寫者手指、手腕、手臂以至整個身體的動作,并在筆墨痕跡中感悟作者的情感世界。如何在書法書寫的姿勢中喚醒日益工具化的身體,成為探索書法藝術療愈功能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教學中,部分書法課程內容以兩漢到隋唐書法家為例,引導學生了解古代書家文武兼修、出將入相;比較唐宋書法在“力”美學范疇中的表現差異,引導學生正確認識習武、腕力和書跡之間的審美關聯[4],結合學校必修課太極拳等傳統體育的“云手”動作和氣息控制來打開身體和感官。傳統中國哲學有“氣論”一說,認為“氣”是宇宙萬物的本原。這種天地之氣的哲學觀必然反映在藝術作品的表達中。“氣”成為推動書法筆墨呈現之根本動力,“精、血、氣、骨、肉”等美學范疇將書法作品當作一個有機生命體來看待。在這里,書法作品既是一個心靈可感的精神世界,又是一個視覺化、情感化和肢體化的,可以觸摸與玩味的生命世界。
古人云:“筆跡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其由筆及人、由跡而化的意味,實在是對書法筆墨相發時所流露出來的元氣淋漓、玄妙莫測的音樂般生命情態的最好表達。教學中,教師會以古琴音樂營造習書的氛圍,讓學生在舒緩和婉轉的音樂節奏中冥想和感通,漸入式調整肢體動作和姿勢,調節呼氣節律,筆筆相生,念念相續,進入類似禪修的精神狀態。筆、墨、紙和整個身體融為一種飽滿的、結構化的而非對象化的生命狀態,達到物我兩忘、空明澄澈的精神境界。這種“尚意”的書法實踐狀態,是書寫心性和精神的自然流露,表現出一種幽遠的意境。
長時期的“筆墨磨人”“以禪入字”的方法訓練,既鍛煉了學生堅忍的意志力,又培養了他們注意力;學生在與經典碑帖的“對話”中,找到無限的人文精神和審美樂趣。正是在身體和書寫、觸摸與聆聽的感通互動中,身心和書寫關聯,功能與意義互生。生命在歷史與現實、身體與筆墨之間達到一種完整和飽滿的情感狀態,緊張焦慮的心理得到很好的放松。學生從傳統的書寫媒介中獲得意義感和成就感,在后疫情時代,對緩解焦慮、緊張的情緒大有裨益。
三、心性修養的情感資源
關于“心性”的解釋繁多,筆者以人本主義思想和人格修養完善來做簡要概括。以書養性是中國書法領域的一個悠久傳統,尤其是自宋元以來,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在書法的實用性之外,模擬出一種理想的人格系統。其視覺藝術從形出發又不拘于形,彰顯一種“超然物外”的美學主張,用來表征自己不凡的心性修養和審美情操。
趙壹在《非草書》中說:“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丑,在心與手,可強為哉?”[5]2揚雄云:“書,心畫也。”王僧虔云:“書之妙道,以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遠紹于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筆,手忘于書,心手達情,書不妄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孫過庭認為書法藝術可以 “達其性情,形其哀樂”,有托物言志、寄情遣興的功能。蘇軾講:“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盛熙明在《法書考》中曰:“夫書者,心之跡也。故有諸中而形諸外,得于心而應于手。然揮運之妙,必由神悟;而操執之要,尤為先務也。”宋曹在《書法約言》中說:“學書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轉腕,手能轉筆。”[5]563周星蓮《臨池管見》曰:“作書能養氣,亦能助氣。靜坐作楷法數十字或數百字,便覺矜躁俱平。若行草,任意揮灑,至痛快淋漓之候,又覺靈心煥發。下筆作詩、作文,自有頭頭是道、汩汩其來之勢。故知書道,亦足以恢擴才情、醞釀學問也。”[5]730以上種種歷史書論,從書寫中的身心關系到欣賞中的生命情態,乃是對書法中人格、心性與修養的歷史性表達。
在教學中,教師通過不同工具、材料和筆法形態的感知體驗,引導學生將書學歷史文本和身體經驗中的人格、心性的含義進行轉化,在筆墨和紙張的相互觀照中覺知自心、凝神靜慮、調節心性、釋放情感。尤其是行草書,線條牽絲綿延,形態的跌宕起伏,意蘊自然流露。因為受疫情影響,學生的活動范圍基本局限在校園。現在很多學生在課余時間基本以刷視頻的方式度過,戶外運動很少且人際關系單一。在書法通識課的系統化學習中,線上和線下教學相結合,師生通過課堂作業批改、經典書法鑒賞與實踐、線上展覽、微信群解答等方式進行互動。這種方式既增強了師生之間的感情,也在學生中實現了情感的交流和信息的交換。在相互觀照的氛圍中,學生涵泳經典,滋養性情,傳承文化,形成樂觀自省的心性和人生態度。
康有為認為,學書通過模仿而得性情,所以臨摹也是涵養心性的一個重要的途徑。正如蔡邕所言:“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若迫于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5]5王羲之認為“凡書貴乎沉靜”,要學會在靜中取法,由專而博。
結語
綜上所述,高校通識類書法教學針對大學生群體,通過書法藝術課程內容的系統化設置,在歷史與文化、情感與經驗的架構中,充分利用書法的傳統價值資源,從道德教育、藝術療愈和心性修養三個層面,潛移默化地融入課堂思政的系統化建設,從形式到內容,從文字到書法,從義理到實踐,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民族觀念與國家認同感。在傳承文化藝術的同時,要求學生樹立宏大的歷史觀和家國情懷,吸收書法學科中蘊含的道德倫理觀念,通過自己的作品來表達和構建完整的人格體系,積極挖掘書法藝術的審美內涵和價值,學會在傳承中開闊民族文化藝術視野,助力課程思政的內涵建設和價值引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