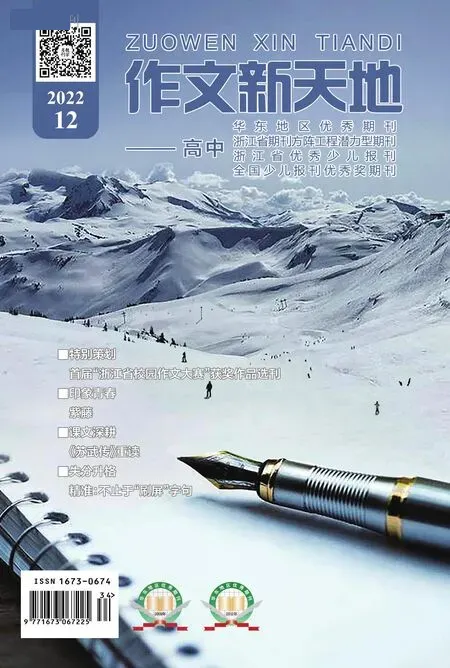《蘇武傳》重讀
◎張 勇 四川省綿陽中學

在文本解讀中,需要找到文本的潛在觸發點,這個點即文本的魂,也是解讀文本的抓手。在《蘇武傳》的解讀中,“節”就是一個重要的抓手,蘇武持節出使、持節守義、持節鑄魂。“節”由一種出使憑證演變成了道義和忠義的化身,蘇武持節鑄就了堅貞不屈的精神風范。
持節出使
節即旄節,以竹為竿,上綴以牦牛尾,是使者所持的信物或憑證。節由符節演化而來,而符節是中國古代朝廷傳達命令、征調兵將以及用于其他各項事務的一種憑證,一般用金、銅、玉、角、竹、木、鉛等原料制成,使用時雙方各執一半,合之以驗真假,如兵符、虎符等。符節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期。《史記·五帝本紀》中便有黃帝“合符釜山”的記載。后來,符節廣泛應用于官吏的任免、軍事的調動及外交活動。據《史記·孝武本紀》記載:“于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西漢時期,持節行事在社會生活中廣泛發生,持節處理政事、外交禮儀活動及出使少數民族及周邊國家等。可見在西漢,持節已成為了外交出使的必備憑證。節是對外交流的身份象征。蘇武持節出使,不僅表明外交使者的身份,還代表著西漢皇帝的威權。
蘇武持節出使匈奴源于兩國關系的緩和。自秦朝開始,匈奴和漢朝的邊境紛爭就不曾斷過,這種紛爭一直延續到后世。西漢建國初期,由于國力等因素,對匈奴實施的是交戰與和親并存的策略。雙方相互攻擊互派間諜互留使者,班固《漢書》載:“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后十余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這種狀況持續了較長的一段時間。公元前100年,單于初立,擔心漢朝突然襲擊,因此主動求和向漢朝示好,放回漢朝的使節路充國等人,作為回應,漢武帝也送回留在漢朝的匈奴使者。從出使的陣容來看,漢朝正式屬官只有蘇武和張勝,其余的是臨時充任的屬官,還有百余人的偵察團隊。蘇武出使匈奴表面上是送回使者,實際上也有兩國實力較量之意。因此,蘇武持節出使具有了較高的意義,不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代表著國家意志的行為。
持節守義
蘇武等人持節出使本意是想交好匈奴,然而到達匈奴國后“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單于的表現單方面宣告了漢匈交好的破產,也為蘇武之后的遭遇埋下了伏筆。
匈奴國內叛變的首領之一虞常與張勝交好,虞常叛變失敗被活捉后,招出張勝,因此,蘇武受到了牽連。無疑,蘇武受到牽連勢必會影響到匈奴和西漢兩朝的關系和戰略格局。“見犯乃死,重負國!”“‘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對于蘇武而言,“屈節辱命”包含了對于個人節操的堅守和對于忠君愛國與國家形象的維護。持節出使的蘇武此時持節守義,不論匈奴國如何勸降,作為義的化身,蘇武始終持節守義,富貴不顧,威武不屈。此時,“節”演變成了節操、道義和忠義的化身,演化成了一種獨立不屈的精神象征。“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即使在艱險堪稱絕境之地,蘇武依然能存活下來,不得不說是源于這種精神的力量。
最后,“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羝乳乃得歸”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的北海“仗漢節牧羊,”他“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持節守義,堅守節操。其間,匈奴曾讓李陵來勸降蘇武,蘇武毅然拒絕了。蘇武被流放北海完成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表面上看匈奴國獲得了勝利,實際上正因蘇武持節守義,堅貞不屈,維護了漢朝的節氣,在與匈奴的較量中,以蘇武為代表的西漢王朝獲得了勝利。這種節代表的是忠君之節:“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亡所恨。”蘇武咒罵衛律“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以及聽說皇上駕崩“南向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等表現,都是他忠君之節的體現。他持節堅守了大義,維護了國家形象和國家利益。
持節鑄魂
蘇武在北海持節牧羊十九年,堅守節操和道義,持節鑄魂儼然成了獨立不屈、忠君愛國的形象化身。建構主義理論認為,閱讀者解讀文本的過程也即重塑文本的過程,解讀文本實質上是一種對文本的不斷建構。從漢代以后,蘇武及蘇武牧羊的故事就處于一個不斷被建構的過程之中。蘇武作為一種精神資源,他的形象在各個時期的解讀中也在不斷地被重塑、被消費,構成了文學創作和精神重塑的重要來源。蘇武成為了忠義的精神符號一直影響著千百年來人們的日常生活,這種符號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已經內化為一種精神信仰。這種精神符號既可以成為作家創作的素材來源、一種民族精神的潛在觸點,也可以是知識分子寄托“心中之塊壘”的重要憑借。
蘇武及其故事廣泛地在詩詞、戲曲、歌劇、小說和雕塑等藝術形式中不斷被改寫和演繹,成為一種重要的精神資源。在戲曲中有京劇《蘇武牧羊》《漢蘇武》,南戲《蘇武牧羊記》《牧羊記》,清代雜劇《雁書記》,豫劇《蘇武牧羊》,話劇《蘇武》,地方劇《大漢蘇武》,新編歷史劇《漢武》《漢魂歌》,戲曲電影《蘇武牧羊》,歌劇《大漢蘇武》等,戲劇中突出的是蘇武牧羊的艱苦及精神的可貴。小說有陳敏的《蘇武的北海》、日本作家中島敦的《李陵》,日本《平家物語》中也引用了蘇武的故事,小說中著重表現的是蘇武情感的矛盾和豐富。詩詞有文天祥《題蘇武忠節圖》、李綱《蘇武令》、汪元量《居擬蘇武四首》、陳杰《讀蘇武傳》、方鳳《懷古題雪十首·蘇武窖雪》、徐鈞《蘇武》、柴望《蘇武》等,寫蘇武的詩詞以宋代詩人為主,他們著重表現蘇武忠君報國之情和堅守抗爭之義。另外,還有藝術家借助連環畫、雕塑等藝術形式表現蘇武的故事。蘇武在不同時期不同的藝術形式中不斷被演繹,突出的都是他的忠君愛國的節義精神。這種精神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明確提出了語文核心素養。文化傳承與理解作為語文核心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學生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文化傳承與理解不僅重在對于中華優秀文化資源的了解,更注重對于中華文化精神和風范的傳承。從這個意義而言,蘇武的故事及其精神無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而這也是《蘇武傳》的文本價值所在。《蘇武傳》經久不衰并入選多個版本的教材,原因可能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