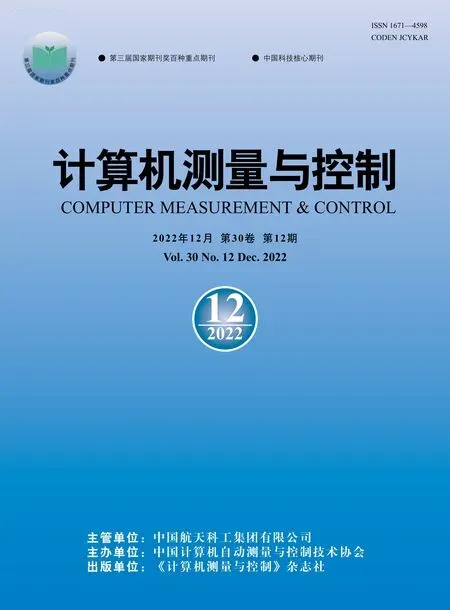基于解釋結構模型的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分析方法
張 宇, 程中華, 連光耀, 趙潤澤,3, 王金幗
(1.陸軍工程大學石家莊校區,石家莊 050003; 2.中國人民解放軍 32181部隊,西安 710032;3.陸軍裝備部駐石家莊地區第三軍事代表室,石家莊 050003)
0 引言
測試性屬于裝備通用質量特性,是指裝備能及時準確地確定其狀態(可工作、不可工作或性能下降),并有效隔離其內部故障的一種設計特性,已經成為影響裝備保障效能發揮的重要因素[1-2],良好的測試性設計可以電子裝備故障檢測隔離效率,顯著降低裝備維修保障難度和全壽命周期費用,對保證裝備戰備完好性和任務成功性具有重要作用[3-4]。
測試性最早由F.Liour等人于1975年針對復雜電子及機電設備的測試有效性問題在《設備自動測試性設計》中提出,并相繼應用于自動測試系統、診斷設計優化等領域[5]。20世紀70年代開始,國外開始廣泛重視測試性研究,尤其以美軍為主,其國防部于1985年頒布了測試性領域總結性的標準MIL-STD-2165,規定了測試性是裝備設計中必須考慮的重要指標要求,并明確了各階段的工作要求[6]。
國內于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引進測試性理論,并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標準規范,典型的有HB6437-90《電子系統和設備的可測試性大綱》[7]、GJB3385-98《測試與診斷術語》[8]、GJB2547A《裝備測試性工作通用要求》[3]等。此外,北京理工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國防科技大學、軍械工程研究所等單位學者也都開展了測試性研究,大大促進了測試性工作的快速發展[9-10]。
近年來,在武器裝備研制過程中,研制單位已經越來越重視測試性設計工作,裝備管理和設計理念也在不斷變革, 裝備測試性研究已取得了較多學術成果[11]。不過,當前的研究主要是針對諸如FMECA方法、故障注入技術、測試性驗證試驗與評估等相對具體的技術和方法,而從宏觀出發,研究整個裝備測試性設計研制過程中,影響裝備測試性水平因素的成果相對匱乏。
因此,有三個問題需要本文在研究中重點解決:一是裝備測試性的影響因素有哪些?二是各影響因素之間具有怎樣的結構關系?三是研制方如何針對關鍵性影響因素進行裝備測試性提升?為回答上述研究問題,本文基于德爾菲法提煉出影響裝備測試性的 16個因素,并運用解釋結構模型(ISM, interpretive structure model)方法,構建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的解釋結構模型,可以清晰地厘清各影響因素之間的規律關聯性和結構層次性,并找出關鍵因素,可為進一步提高裝備測試性水平提供對策。
1 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分析
裝備測試性設計研制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其影響因素復雜多樣,從不同角度可提煉出不同的影響因素。本文基于裝備測試性驗證試驗不同階段的具體工作內容并結合相關文獻,初步確定裝備測試性的相關影響因素,之后通過德爾菲法,確定最終影響裝備測試性的因素,主要從受試裝備自身、研制外部條件、具體實施方法和測試系統自身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1.1 受試裝備自身
裝備的測試性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自身先決條件的影響,裝備的系統復雜程度以及裝備的實時技術狀態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12]。
1.2 研制外部條件
研制外部條件包括研制經費、研制方技術水平、實驗室設備及環境條件和操作人員專業程度等[4],良好的外部研制條件也是提升裝備測試性水平的重要因素。
1.3 具體實施方法
具體實施方法是指在裝備測試性研制過程中所需要用到的資料和方法,包括FMECA報告質量水平、故障模式篩選合理性、故障樣本選取方法合理性、測試點選擇合理性、故障注入方法合理性以及指標評估方法合理性等[13]。
1.4 測試系統自身
測試系統自身主要是指其監視和測試能力以及分系統間的兼容性,包括系統狀態監視能力、人工檢測能力、機內測試能力和測試分系統間接口兼容性[14]等。
考慮以上4個方面并參考近年的相關文獻資料,篩定了裝備測試性水平的16個相關影響因素(見表1)。

表1 裝備測試性相關影響因素
2 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的ISM模型構建
解釋結構模型(ISM,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是美國J.N.Warfield教授在解析復雜技術系統層級構造問題時所提供的一個靜態結構分析方法。該模式主要是指學者通過運用在該學科領域長期工作的經驗認識和所學理論知識去尋找對象體系的各種影響及其各種因素,進而逐漸明確了其中各因素間存在的相互作用關系,并通過矩陣分析和有向圖法把該系統結構中各有關因素先后細分為各種特征的構成層次,最后建立一種更為清晰明確的多層遞階結構模型[15]。通過解釋結構模型,可將影響裝備設計過程的各種因素分成了表面、中間層和深層三個維度,而各影響元素之間的相互聯系關系及其影響范圍,即可在該模型中得以更清晰直接的表達,因此,運用ISM方法構建裝備測試性的影響因素模型較為合適。
根據解釋結構模型的建模流程,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的ISM模型構建主要包括以下4個過程:
2.1 建立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間的鄰接矩陣
鄰接矩陣是用來準確簡單描述裝備測試性各因素間基本二元關系的矩陣。裝備測試性中兩個影響因素(行因素Em、列因素En)之間的相互具有傳遞性的關系即為二元關系[16],其中兩個因素間的關系可用矩陣元素Emn來表示,各影響因素間的相互關系進行量化,用數字“1”和“0”表示各影響因素間的相互關系。如果行因素Em對列因素En有影響,則Emn=1;如果行因素Em對列因素En無影響,則Emn=0。
為了使構建的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鄰接矩陣更加具有科學性和有效性,針對表1中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成立由15名領域專家所構成的研究小組開展了意見征詢,考慮到專家看法中可能會存在意見不一致的現象,該研究選擇了閾值為0.8來判斷各種因素之間的邏輯關系,即在研究隊伍中如果有12或以上科學家認為行因素Em直接影響了對應的列元素En,則可判定結果為1,否則為0。據此,最終整理形成 16×16 的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的鄰接矩陣A,如公式(1)所示:

(1)
2.2 確定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間的可達矩陣
鄰接矩陣充分地顯示出裝備測試性各因素間的直接關系,但是它卻很難體現各因素間的間接關系,而可達矩陣可以直觀地揭示裝備測試性各因素間直接與間接的關系,很好地彌補了這一不足。其方法是在鄰接矩陣計算公式的基礎上加上一個單位矩陣,在推理與演算的過程中一般采用布爾代數運算(0+0=0,0+1=1,1+1=1,0×0=0,0×1=0,1×1=1),從而求得可達矩陣。
基于布爾代數運算的冪運算求得的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的可達矩陣B,如公式(2)所示:

(2)
2.3 對可達矩陣進行級別劃分
求解出裝備測試的相關影響因素的可達矩陣時,必須按照可達集與先行集的等級劃分,使各相關因素間的相互聯系可以比較清晰地表達,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解釋結構模型。具體做法為:首先,將因素Em的可達集設定為R(Em),它是由可達矩陣中第m行中所有矩陣元素為1的列對應的要素集合,與此同時,將因素Em的先行集設定為Q(Em),它是由可達矩陣中第m列中所有矩陣元素為 1 的行對應的要素集合,如R(E5)={5,8,9,11,12,13},Q(E5)={1,3,4,5 }。
然后,在可達集和先行集已知的基礎上,對裝備測試性的影響因素按照不同等級進行劃分,將可達集R(Em)和先行集Q(Em)的共同集設定為A(Em),即A(Em)=R(Em)∩Q(Em)。
裝備測試性相關影響因素的可達集、先行集與共同集如表2所示。

表2 可達集、先行集與共同集
當集合滿足A(Em)=R(Em)∩Q(Em)或A(Em)=R(Em)時就是最高一級因素集合。如表2所示,A(E11)=R(E11),A(E12)=R(E12),因此,最高級要素即終止集要素為F(E)={E11,E12}。而后去掉這2個要素,再求剩余要素的可達集、先行集及共同集,直到得出最低一級的集合,即起始集。最后,在可達矩陣中先劃去最高等級影響因素集合所在的行和列,接著再在剩下的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可達矩陣里尋找最高級的影響因素集合。
2.4 得到ISM模型
根據級位劃分,進行層次分解,從而得到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多級遞階結構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裝備測試性水平影響因素多級遞階結構模型
根據ISM的層次遞階結構理論,對裝備測試性水平16個影響因素進行更深層次的劃分:
第一級和第二級為表層影響因素,是指可以直接作用于裝備測試性水平的具體因素,包括故障模式篩選合理性、故障樣本選取方法合理性、故障注入方法合理性和指標評估方法合理性[7],這些因素可直接體現出測試性水平的高低,所處層級也是最低的,容易受到更高層次的因素影響,穩定性不強。
第三級和第四級為中層影響因素,這些因素既受深層影響因素的影響,又能直接作用于表層影響因素,包括測試分系統間接口兼容性、測試點選擇合理性、實驗室設備及環境條件、操作人員專業程度、受試裝備技術狀態、FMECA報告質量水平、系統狀態監視能力、人工檢測能力和機內測試能力,主要起到聯接表層和深層因素的紐帶作用。
第五級和第六級為深層影響因素,包括裝備系統復雜程度、研制方技術及管理水平和研制經費,這些因素所處層級最高,穩定性最強,是裝備測試性水平的根本影響因素,是需要重點考慮和提出相應改善建議的因素。
通過對16個影響因素的深層次劃分,可以找出其中在相關影響因素中對裝備測試性水平影響大,較基礎的因素。評判關鍵影響因素,本文采取 “手段-目的分析”網絡方法,以任一因素為起點,以裝備測試性水平為終點,沿箭頭尋求路徑到達,然后求得每個因素作為起點抵達終點的路徑數,最后計算各因素路徑數的平均值, 并按降序排列,高于平均值為關鍵影響因素,結果見表3。
平均路徑數大約為9,可得到裝備測試性指標的關鍵影響因素為:裝備系統復雜程度、研制方技術及管理水平、研制經費、測試分系統間接口兼容性以及測試點選擇合理性。
3 評價與建議
3.1 分析方法評價
為了驗證通過ISM分析方法找出的裝備測試性關鍵影響因素是否合理,還需要針對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的解釋結構模型進行評價分析,常用的評價方法有層次分析法、網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判法、粗糙集等方法,本文采取層次分析法進行評價[17]。
層次分析法(AHP),是20世紀80年代由美國運籌學教授T.L.Sstty提出的一種快速、有效而又可靠的多要素決策方法。其基本過程是:綜合考慮研究對象的各種社會性質和目標能力,提出一個能力總目標,然后逐步中將每個具體問題目標分別按若干個功能層次予以分解,通過對同一層次的諸多因素進行兩兩比較的方法,從而確定相對于上層目標的各自權重系數。這樣層層分析,最終按它們各自針對總目標的重要性程度來進行最后的排序[18]。
運用AHP方法對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的解釋結構模型進行評價分析的基本思路為:將裝備測試性水平提高作為總目標,將受試裝備自身、研制外部條件、具體實施方法和測試系統自身作為中間層要素,將裝備系統復雜程度、受試裝備技術狀態等16個影響因素作為底層要素,構建基于裝備測試性的評價指標體系,如圖2所示。
然后通過對處于同一目標層次之間的各個影響因素進行兩兩比較,確定它們相對于上一目標層的權系數。權系數需要通過專業領域的專家小組成員進行評價,設總目標為μ,對每一指標相對重要程度,采用1~9標度法進行兩兩比較。以總目標判斷矩陣和具體實施方法判斷矩陣為例,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 總目標判斷矩陣

表5 具體實施方法判斷矩陣
AHP法是各因素間兩兩比較,因而會出現判斷不一致的情況,為保證結果有滿意的一致性,需要對一致性指標進行檢驗。經檢驗,各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指標CR均小于0.1,因此滿足一致性。
在各個判斷矩陣的基礎上,最終得到了裝備測試性評價指標體系權重總排序,如表6所示。其權重總排序柱狀圖如圖3所示。

圖3 裝備測試性評價指標體系權重柱狀圖

表6 裝備測試性評價指標體系權重(總排序)
通過運用AHP方法對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評價,最終得到了各個影響因素的權重總排序。結果表明,裝備系統復雜程度、研制方技術及管理水平、研制經費、測試分系統間接口兼容性和測試點選擇合理性這五個影響因素的權重相對較高,屬于關鍵影響因素,這與裝備測試性印象因素的解釋結構模型所得到的結果基本一致,因此,運用AHP評價方法證明了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的解釋結構模型分析方法的合理性。
3.2 意見建議
本文通過對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分析,利用ISM方法,構建了裝備測試性相關影響因素的解釋結構模型,結果表明裝備測試性水平相關影響因素可分為6個層級,其中裝備系統復雜程度、研制方技術及管理水平、研制經費、測試分系統間接口兼容性以及測試點選擇合理性處于本質因素層。因此,提高裝備測試性水平,應注重以下3個方面。
1)注重根據裝備實際情況開展測試性設計。隨著諸多高新技術的出現,裝備自身系統,尤其是電子系統,也朝著復雜化和集成化的方向發展,使得系統的測試性評估和電子裝備故障診斷的難度越來越大[19],然而對于系統的測試時間、測試成本和測試效率等多項指標的要求在航天軍事等重要領域卻越來越苛刻,裝備系統的復雜性已成為了影響裝備測試性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對此,我們在對裝備進行測試性研制設計時,應該充分考慮具體裝備的任務需求、所處環境條件等實際情況,針對裝備系統的復雜程度設計與之相適合研制方案,以此來切實提高裝備測試性水平。
2)注重裝備測試性的研制及投入。由于我國在裝備測試性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目前主要應用領域正在由航空裝備向航海和地面等裝備慢慢推廣,測試性知識尚不普及,而測試性作為一種設計特性,是和可靠性、維修性和保障性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20],因此,在下一代的裝備研制中,在保證其他設計特性達到要求的前提下,可適當增加針對裝備測試性設計的經費投入,同時也要注重研制單位和研制人員的專業培養,發展以測試性為核心的裝備綜合診斷技術來提升裝備保障能力。
3)注重測試性相關技術的創新與發展。伴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裝備測試性受重視程度的提高,許多新技術、新方法都應用到了測試性之中,測試性經歷了由外部測試到機內測試性,將來還會到智能BIT和預測與健康管理的發展過程,需要用到的諸如故障模式分析方法、故障注入技術、測點優化技術等相關知識也在日益完善與發展[21],因此,在兼顧各測試分系統兼容性的同時,必須注重相關技術方法的不斷創新,提高裝備測試性水平,以適應新型裝備不斷提高的任務和性能要求,從而增強裝備的戰備完好性和安全性。
4 結束語
本文通過對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分析,利用ISM方法,構建了裝備測試性水平相關影響因素的解釋結構模型,運用“手段-目的分析”方法識別出裝備系統復雜程度、研制方技術及管理水平、研制經費、測試分系統間接口兼容性以及測試點選擇合理性的分析5個影響裝備測試性最關鍵的因素,并針對性提出了相關意見建議,為進一步提高裝備測試性水平提供對策。
同時,本文對于裝備測試性相關影響因素的研究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例如,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復雜且繁多,而本文僅從裝備測試性驗證試驗一個方面去分析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使得研究稍欠缺些說服力。另外,作為一種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分析方法,解釋結構模型只是對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之間的互相關系進行了定量地計算和定性地分層,對于各影響因素間的結構機理卻并未進行系統性深入研究。這使得往后的研究方向應著眼于從多個維度深入研究裝備測試性影響因素,并結合各類具體裝備測試性設計、試驗和評估等多方面對各影響因素間的作用機制及其相關機理進行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