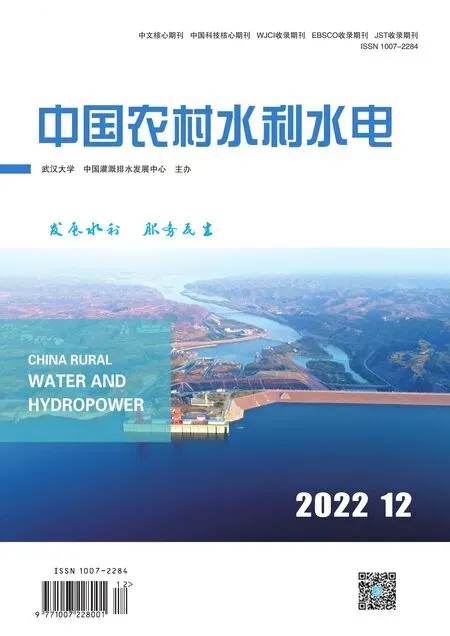中國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機制分類研究
代小平,劉闖,萬福兵,馬建強
(1.河海大學農業科學與工程學院,江蘇南京 210098;2.華北水利水電大學水利學院,河南鄭州 450046)
0 引言
水權交易是促進水資源的節約、保護和優化配置的重要措施。我國自2000 年左右開始建設水權制度,經過20 余年的發展,水權市場發展迅速,積累了豐富的水權交易案例。農業水權交易是水權交易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國目前的農業水權交易主要集中在缺水地區,農業水權交易案例和交易規模不足,自主的用水戶間水權交易較少。為進一步建設活躍的農業水權市場,急需探明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機制。
王學淵和韓洪云[1]綜述了農業水權轉移的前提條件、必要條件和影響因素。其中,前提條件包括明晰的水權界定、政府機構的市場化改革;必要條件包括現實和潛在的經濟效益、低交易費用與低開發成本、糾紛與外部性處理補償原則。農業水權轉移的影響因素可分為工程技術因素、社會經濟因素、自然環境影響因素三類。工程技術影響因素包括水利設施狀況[2,3]、計量裝置[2]、灌溉技術[4]等。社會經濟影響因素包括作物種植結構[4-6]、水權立法保障[2]、分配水量[7]、水權期限[7]、水權的穩定程度[7]、水權交易政策[5]、水供給信息的提供[6]、灌溉設施管理的用水者參與程度[6]、農產品價格[5]、居民水需求[5]、節水成本[8]等。自然環境影響因素包括耕地面積[5-7]、水供給狀況[5,9,10]、灌區位置[4]等。韓洪云[8]等進一步研究發現灌溉用水效率的改善是農業水權轉移的必要條件,水權和水價機制的建立、用水者協會的發展和灌區管理體制改革是農業水權轉移的充分條件。李海鵬[11]將西北地區農業與非農業用水間的水權交易誘因總結為產業間配水量與需水量差異增大、產業間水資源利用效率差異、產業間水資源歧視性價格差幾個方面。已有研究總結了農業水權交易的影響因素,但未闡明各因素對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方式。Svensson[12]等分析了不同因素對中國水權交易的作用途徑,發現水權交易試點、私有化水權、交易平臺的組合是產生農業水權交易的重要驅動路徑。Dustin[13]等總結了全球典型地區的農業與城市間的農業用水轉移,發現農村地區的城市化、城市為了降低獲取水資源的成本是驅動農業用水向城市轉移的重要因素。但已有研究尚未將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因素系統化,未闡明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機制,不能有效指導農業水權交易實踐。本文在分析農業水權交易的交易需求和交易激勵類別的基礎上,構建一個農業水權交易驅動機制分類框架,基于該框架可從驅動機制角度對農業水權交易進行分類分析,為建設活躍的農業水權市場提供參考。
1 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機制分類
農業水權交易受到工程技術因素、社會經濟因素以及自然環境因素的綜合影響。在不同因素的影響下交易主體的行為產生農業水權交易的關鍵。本文從交易主體的交易需求和交易激勵兩個角度對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機制進行分類。本文中,交易需求指用水主體因為水權富余或不足而有進行水權交易的內在動力。交易激勵是使用水主體產生水權交易行為的外界刺激。
1.1 交易需求類別
水權交易需求可分為購買需求和出售需求,主要來源于水權量與需水量的差異性,當需水量超過水權量時產生購買需求,反之產生出售需求。我國用水戶出售農業水權的需求來自灌區節水改造、種植結構調整、節水技術采用等,對該需求的認識比較充分,但對購買水權的需求認識不足。本文根據農業水權購買需求的來源,把交易需求分為水權分配差異需求、灌溉用水差異需求、經濟發展需求和生態恢復需求四類。
1.1.1 水權分配差異需求
水權分配差異需求指因為農業水權分配量與實際需求量不符導致的交易需求。主要表現為分配水權的耕地面積與農戶的實際耕地面積不匹配。當政府不按實際耕地面積分配水權而是按照二輪承包地面積或者壓縮的耕地面積分配水權時,即可導致該類交易需求。
1.1.2 灌溉用水差異需求
在農業水權按耕地面積平均分配的情況下,農業用水戶的灌溉用水差異也可能導致灌溉用水需求和農業水權不一致,從而產生交易需求。灌溉用水差異來自種植結構差異、灌溉用水技術差異、耕地地形差異、土壤保水性差異等。該差異存在于不同農戶、不同村、不同鎮以及不同灌區之間,由此產生不同層次的農業水權交易需求。
1.1.3 經濟發展需求
經濟發展需求指區域經濟發展導致非農業用水超過分配的水權而產生的購買農業水權的需求。區域經濟發展導致的用水增長體現為工業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增加。當城市用水超過分配的水權量,工業企業和城市自來水供水企業有購買水權的需求。
1.1.4 生態恢復需求
生態恢復需求指為了保護水生態環境而產生的購買農業水權的需求。當水資源利用超過生態承載能力時,可能導致土地荒漠化、地下水超采等問題。為了增加生態用水量,促進生態恢復,政府作為生態環境保護的主體有購買農業水權用于生態的需求。
在以上四類交易需求中,水權分配差異需求和灌溉用水差異需求為農業內部交易需求,經濟發展需求和生態恢復需求為跨行業農業水權交易需求。其中,水權分配差異需求由行政行為產生;灌溉用水差異需求由用水戶的個人行為和自然條件差異產生;經濟發展需求主要受到市場的影響;生態恢復需求主要受到政府的影響。
1.2 交易激勵類別
水權交易需求只是水權交易的必要條件,該交易需求受到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制約,并不一定產生水權交易。例如農業用水戶在水權量不足時,除了通過水權交易獲得水權,還可以通過繳納累進加價水費獲得水權,或者通過調整種植結構、減少種植面積、采用農業節水技術等措施減少需水。非農業用水戶在水權量小于需水量時,也可以選擇繳納高價水費、開發替代水源等方式獲得用水。因此水權交易需求需要在足夠強的交易激勵下才能產生水權交易。水權交易中的賣方可以通過水權交易獲得交易收益,其激勵機制是明確的,但買方的激勵機制卻有多種類型。根據買方的激勵機制,把農業水權交易激勵分為水權約束激勵、成本節約激勵和水權回購激勵三類。
1.2.1 水權約束激勵
水權約束激勵是指在政府嚴格控制水權指標的情況下,政府規定超過水權的用水只能通過水權交易獲得從而產生的交易激勵。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交易成本較高,交易收益較小,也能產生水權交易,但政府對水權的監管成本較高。
1.2.2 成本節約激勵
成本節約激勵指因為水權交易能減少用水成本而產生的交易激勵。對于農業用水戶,這種交易激勵產生的條件為灌溉用水的累進加價制度或者不同耕地的差別水價制度。在灌溉用水的累進加價制度中,超過用水定額后的灌溉用水水價高于定額內水價。如果這種水價差異足夠高,農民通過購買其他農戶定額內的低價水可以減少水費,就能產生水權交易激勵。不同耕地的差別水價制度指在不同的耕地上實行不同的水價標準。如政府規定二輪承包地以內的耕地按定額內灌溉水價計費,二輪承包地以外的耕地按累進加價水價計費。農民通過購買其他農戶的低價水來灌溉二輪承包地以外的耕地就可以減少水費支出從而產生交易激勵。對于非農業用水戶,新建水源工程通常成本高、耗時長,如果水權交易能降低獲取水資源的成本就能產生跨行業農業水權交易激勵。
1.2.3 水權回購激勵
水權回購激勵是指在用水戶之間水權交易激勵不足的情況下,為了激勵農戶節約用水或者保障其他行業的供水,政府或灌區管理機構作為交易主體購買農業水權從而產生的交易激勵。
在以上3種水權交易激勵中,水權約束型激勵受政府影響;成本節約型激勵受政府和市場的共同影響;水權回購型激勵由政府直接參與,受政府的影響程度最大。
1.3 驅動機制分類
基于交易需求和交易激勵的組合,理論上可以得到12種農業水權交易驅動機制,見表1。但因為生態恢復用水需求—逐漸增長而受到水權約束,不存在生態恢復需求—水權約束型交易驅動機制。對于水權分配差異型和灌溉用水差異型水權交易需求,因為已經有潛在水權購買方,不需要政府進行回購,因此不存在水權分配差異—水權回購型和灌溉用水差異—水權回購型水權交易驅動機制。因而實際可能存在的農業水權交易驅動機制為9 種。其中,水權分配差異—水權約束型交易驅動機制受政府影響最大,灌溉用水差異——成本節約型交易驅動機制受市場影響最大。

表1 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機制分類Tab.1 Classification of driving mechanisms of agricultural water rights trading
2 農業水權交易驅動機制的典型案例分析
以我國農業水權交易為對象,采用農業水權交易驅動機制分類框架對其進行分類,不同類型的典型案例見表2。其中,生態恢復需求—成本節約型農業水權交易缺少案例。

表2 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機制典型案例Tab.2 Typical examples of driving mechanisms for agricultural water rights trading
2.1 農業內部水權交易典型案例
農業內部水權交易由水權分配差異和灌溉用水差異產生交易需求,由水權約束、成本約束產生交易激勵,包括4 種類型。
2.1.1 水權分配差異—水權約束型
改革開放以來,安徽經濟快速增長,特別是2004年“中部崛起”概念提出后,更連續10年GDP增速超過10%。但經濟增長質量不高也是個不爭的事實,長期以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要素驅動型增長模式不僅給資源和環境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同時也不具有可持續性。自2011年開始,安徽經濟增速逐漸放緩,揭示了要素驅動型經濟增長的日益乏力,如何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也日益受到了政府與學者們的關注。而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關鍵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依靠技術進步、生產效率和資源的有效利用來促進經濟可持續的增長,而不是依賴于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的投入。
“水權分配差異—水權約束型”農業水權交易的主要特征為交易需求產生于政府主導的水權分配,交易激勵產生于政府的水權交易政策,并且需要政府對水權進行嚴格的控制,受政府影響很大。其典型案例為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的農業水權交易。
涼州區的農業水權交易需求產生的主要原因是農業水權并非按實際耕地面積分配,而是按壓縮的耕地面積進行分配。壓縮水權面積的主要目的是減少石羊河流域中上游灌溉用水量以保障石羊河下游的生態用水,防止民勤綠洲荒漠化。在水權分配時,涼州區的農田配水面積按《石羊河流域重點治理規劃》確定的,以農業人口人均耕地面積為依據逐年壓縮[14]。根據《石羊河流域重點治理規劃》,涼州區基本灌溉農田按人均0.13 hm2配水,由此確定的配水面積為法定灌溉面積。“涼州區以法定面積為基礎,對人均法定面積小于0.07 hm2的村組按人均0.07 hm2配置水權,對人均法定面積在0.07~0.13 hm2的村組,按實有法定面積配置水權;對人均法定面積超出0.13 hm2的村組,按0.13 hm2配置水權”[15]。2007 年,涼州區法定面積86 486.7 hm2,統計外面積30 340 hm2,統計外面積約占總耕地面積的26%[16]。由于政府未按農戶的實際耕地面積分配水權,導致農業水權和農業需水不匹配,進而產生較大的交易需求。
涼州區的農業水權交易激勵來自政府的行政要求。為了控制農業用水量,涼州區政府采取了嚴格的總量控制和定額管理措施,要求超過農業水權的用水量都必須通過水權交易獲得。這種措施對農業水權交易產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如涼州區西營灌區在2008-2018 年的農業內部年均交易水量為549萬m3。2013 年后,即使在無償交易的情況下,依然存在農業水權交易。
2.1.2 水權分配差異—成本節約型
“水權分配差異—成本節約型”水權交易通過水權分配產生交易需求,通過經濟驅動產生交易激勵,其市場化程度高于“水權分配差異—水權約束型”水權交易。該類水權交易的交易激勵程度與水權交易節約的用水成本有關,交易激勵程度的變化較大。其典型案例為新疆呼圖壁縣農業水權交易。
呼圖壁縣的農業水權未按實際耕地面積分配,而是根據二輪承包地面積分配,以減少灌溉面積,遏制地下水超采。2015年,呼圖壁縣耕地面積96 666.7 hm2,二輪承包土地面積53 333.3 hm2[17]。二輪承包地以外的耕地約占總耕地面積的36%,產生了很大的農業水權交易潛力。
呼圖壁縣根據耕地類型和用水量實行累進加價制度,即“對二輪承包土地用水指標以內的用水,按照基本水價進行征收;二輪承包土地超定額的水量和二輪承包土地以外的用水,按照成本水價的2 倍計征,并加收水資源費和水資源補償費各0.1元/m3”[16,17]。按該規定,2015年基本水價和超額水價的差異達到0.308 元/m3,并且呼圖壁縣人均耕地面積較多,通過水權交易能節約較多水費,產生很強的水權交易激勵。如呼圖壁縣五工臺鎮龍王廟村在2017年購買三次水權,平均單筆交易水量達208.4 萬m3,單筆交易可節約水費64.2萬元。
2.1.3 灌溉用水差異—水權約束型
“灌溉用水差異—水權約束型”農業水權交易的交易需求來自用水戶間的灌溉需水差別,交易激勵來自政府的行政規定,受政府的影響較大。典型案例為張掖市山丹縣馬營河灌區的農業水權交易。
馬營河灌區從2001年開始實行超額累進水價制度,超定額水價為基本水價的1~3 倍。灌區2001 年水價為0.071 元/m3[18],基本水價和超額累進水價的差異為0.071~0.142 元/m3,交易激勵較小。為了控制灌區總用水量,灌區管理機構要求農戶超過水權的用水量需要通過水權交易獲得,由此產生交易激勵。主要交易方式是農戶將節余水權返還給灌區水管單位,水管單位將水價提高一倍后配置給水權購買者,并將加價所得收益返還給水權轉讓者[8]。
2.1.4 灌溉用水差異—成本節約型
“灌溉用水差異—成本節約型”農業水權交易的交易需求來自灌溉用水差異,交易激勵來自用水成本節約。典型案例為山西省清徐縣的農業水權交易。
清徐縣同一個村的農業水權按耕地面積平均分配,水權分配不能產生交易需求。但由于村內不同農戶的種植結構不同,種植蔬菜的用水戶灌溉用水較多,產生交易需求[18]。清徐縣根據用水量實行累進加價制度,水權內用水收費在0.45~0.7 元/m3之間,超用20%加價0.05~0.1 元/m3,超用40%加價0.1~0.3 元/m3。基本水價和超額水價的差異為0.05~0.3 元/m3[19]。清徐縣2019-2020年的農戶間平均交易水量為440.7 m3,單筆水權交易可節約的水費為22~132.2 元。為了節約用水成本,農戶借用親戚朋友的富余水權灌溉,或者通過水權交易獲得水權灌溉。
2.2 跨行業農業水權交易典型案例
我國跨行業農業水權交易的交易需求來自生態恢復和經濟發展,交易激勵來自水權回購、水權約束和用水成本節約,包括四種類型。
2.2.1 生態恢復需求—水權回購型
“生態恢復需求-水權回購型”農業水權交易是在用水戶間缺少交易需求和交易激勵的情況下,政府為了恢復生態而充當買方的水權交易。這種交易是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結合的結果,主要受到政府的影響。該類交易的交易程序簡單,交易規模和交易可持續性受到政府財政收入的限制。典型案例為河北省成安縣農業水權回購。
為了治理地下水超采,成安縣探索采用水權制度促進農業節水。成安縣的水權分配方式是按耕地面積平均分配,這種分配方式的公平性較高,但也導致農戶的水權缺少差異,在農戶間種植結構差異較小的情況下不能產生水權交易需求。
成安縣政府未要求超用水權必須要通過水權交易獲得用水量,不能產生水權約束型交易激勵。成安縣規定農業用水量超水權額度加收0.1 元/m3,基本水價和超額水價的差異較小,通過水權交易能節約的水費有限。如成安縣在2017 和2019 年的8 筆村級水權回購的平均交易水量為5.5 萬m3,通過水權交易可節約的水費為0.55 萬元/筆。在缺乏交易需求和交易激勵的情況下,政府為了激勵農業節水,遏制地下水超采而回購農業水權。政府回購的水權交易價格為0.2 元/m3,村級水權交易的平均收益為1.1 萬元/筆。
2.2.2 經濟發展需求—水權約束型
經濟發展需求—水權約束型農業水權交易的交易潛力來自經濟發展產生的水資源稀缺,其交易激勵來自區域水權總量的剛性約束。典型案例為寧夏、內蒙古開展的黃河水權轉換。
黃河水權轉換產生的背景為區域能源工業發展迅速,用水量激增,但區域用水已經超過黃河分水指標,對工業發展產生剛性約束。例如,2017 年,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因無用水指標而無法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達200 余個,需水量約5 億m3[20]。與此同時,寧夏、內蒙古的引黃灌區用水粗放,節水潛力大,如內蒙古南岸灌區和河套灌區渠道襯砌的計算節水潛力為1.68 和10.36 億m3[21]。為解決新增工業項目的用水問題,產生了由企業投資灌區農業節水,獲得節約的農業水權的水權轉換模式。
2.2.3 經濟發展需求—水權回購型
經濟發展需求—水權回購型農業水權交易產生的原因為區域經濟發展導致非農業用水需求增大,灌區管理機構為了保障非農業用水而回購農業水權。典型案例為湖南省長沙縣銅仁橋灌區的農業水權回購。
湖南省長沙縣桐仁橋水庫既承擔著2 133.3 hm2的灌溉任務,也是長沙縣北部16 萬余人的飲用水水源地,且飲用水需求量以每年32%的速度快速增長。為了保障飲用水安全,桐仁橋灌區管理所在2017 年面向灌區內5 個鎮14 個村農民用水戶協會統一回購水權429.82 萬m3。
該類型水權交易以灌區管理機構為中心,本質上是灌區管理機構采用市場手段獲得農戶節約的水權,進而擴大非農業供水,與直接擴大非農業供水相比是一種進步。
2.2.4 經濟發展需求-成本節約型
經濟發展需求-成本節約型農業水權交易產生的原因為區域經濟發展導致非農業用水需求不能得到滿足,而增加水資源供給的成本較高,為了節約供水成本而購買農業水權。典型案例為浙江省東陽義烏水權交易。
浙江省義烏市因為經濟發展迅速,城市生活用水快速增加,區域水資源供給能力不能滿足需求。義烏市可以選擇在本市興建水庫、在原有水庫基礎上擴建或者在鄰縣購買庫址建設水庫等方案增加供水,但只能解決短期供水問題,并且成本較高[22]。為了低成本解決城市供水問題,2000 年,義烏市通過水權交易購買了東陽市橫錦水庫5 000 萬m3水的永久使用權。
3 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路徑分析
根據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機制,對農業內部水權交易和行業間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路徑進行梳理,分別見圖1和圖2。

圖1 農業內部水權交易的驅動路徑Fig.1 Driving paths for intra-agricultural water rights trading

圖2 行業間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路徑Fig.2 The driving path of inter-industry agricultural water rights trading
我國目前的農業內部水權交易主要起因于水生態惡化問題,在水生態惡化嚴重時,政府迫切需要通過水權制度約束農業用水,見圖1。在農業用水總量減少后,農業水權交易成為調劑農業用水余缺,促進農業節水的重要措施。但在灌溉用水差異較小時難以產生水權交易需求,在定額內和超額農業水價差異較小時,難以產生水權交易激勵。地方政府雖然可以通過差別化的水權分配政策和嚴格的水權約束推動農業水權交易,但這種差別化水權分配政策是否公平有待商榷,嚴格的水權管理措施能否持久也有待考驗。這種依靠行政手段推動的農業內部水權交易是否能促進節水也有待檢驗。部分地區通過增大農業用水累進加價差別,為農業內部水權交易提供了交易激勵。該經濟激勵可望促進農戶調整種植結構、采用節水技術,但在多大的激勵下才能產生自發的農業水權交易,農業水權交易對節水的促進作用如何尚需研究。
我國跨行業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路徑有經濟發展驅動和水生態惡化驅動兩類,見圖2。城市化和工業發展發展導致城市用水增多,在城市用水不足時產生水權交易需求。隨著經濟的發展,水資源開發程度增大,水資源開發成本隨之增高,當通過農業水權交易能減少供水成本時可產生水權交易激勵。但隨著灌區節水潛力的減少,灌區節水成本增大,水資源緊缺地區跨行業農業水權交易的難度也越來越大。豐水地區非農行業用水并不缺乏,交易需求不足,如何開展跨行業農業水權交易還有待探索。
水生態惡化區域通常通過水權制度約束生產和生活用水。當城市用水因為水權約束不能得到滿足時,產生農業水權交易需求和交易激勵。在水生態惡化并且經濟不發達地區,缺少水權交易需求,政府回購是短期內可采取的水權交易激勵方式。但政府回購的水權如果不能交易到非農行業用水戶,將給財政帶來較大的負擔,可持續性較差。
綜上所述,水權約束型農業水權交易的行政成本較高,僅適用于水生態嚴重惡化地區。水權回購型農業水權交易因財政壓力大而難以持續。目前只有成本節約型農業水權交易能產生足夠的經濟激勵,是未來農業水權交易的希望所在。
4 結語
基于我國已開展的農業水權交易實踐,從交易需求和交易激勵兩方面構建了農業水權交易驅動機制的分析框架,并對不同驅動機制的典型案例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農業水權交易的交易需求來自水權分配差異、灌溉用水差異、生態恢復需求和經濟發展需求,農業水權交易激勵來自水權約束、用水成本節約和水權回購。基于交易需求和交易激勵可得到9種農業水權交易驅動機制。分析農業水權驅動路徑發現水權約束型農業水權交易僅適用于水生態嚴重惡化地區,水權回購型農業水權交易的可持續性低,用水成本節約型農業水權交易是最有發展潛力類型。
該成果有助于認識我國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機制,可為進一步研究農業水權交易的驅動機制和交易潛力提供基礎,為不同區域建設農業水權市場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