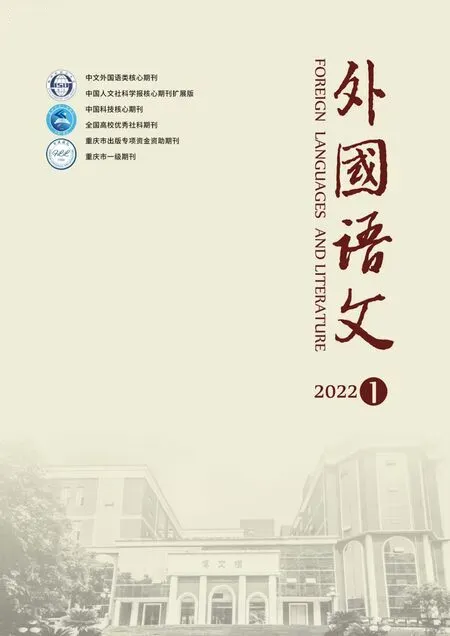空間之物:奧康納短篇小說中的南方書寫研究
張魯寧 韓啟群
(南京林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南京 210037)
0 引言
1925年,南方文藝復興后期的重要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出生于美國佐治亞州的一個典型南方小鎮——薩凡納,而就在這一年,南方文藝復興旗手福克納已經開始出版首部小說《士兵的報酬》。20世紀40年代中期,奧康納加入著名的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結識了羅伯特·潘·沃倫、蘭瑟姆等南方評論界重要人物并得到提攜和幫助,從此開始了短暫而輝煌的文學創作生涯。1946年,奧康納開始在《塞沃尼評論》(SewaneeReview)上發表短篇小說,雖然這一時期的創作風格明顯受到納撒尼爾·霍桑、愛倫·坡、亨利·詹姆士等作家的影響,但她后來逐漸憑借怪誕、神秘等風格奠定了在南方文壇的地位。奧康納的天主教背景為其作品注入了明顯的宗教元素與宗教思考,使她的創作有別于同期其他南方作家。20世紀50年代之后,奧康納進入創作盛期,相繼出版《好人難尋》(AGoodManisHardtoFind)、《暴力奪魁》(TheViolentBearItAway)等佳作,奠定了她在美國南方作家中舉足輕重的地位。1952年奧康納被診斷患有系統性紅斑狼瘡,她一邊與病魔作斗爭,一邊潛心創作,直至1964年離世,享年39歲,成為和托馬斯·沃爾夫一樣才華橫溢卻英年早逝的南方作家。
奧康納的作品一經問世,就得到評論界高度關注。雖然在短暫的一生中她僅創作兩部長篇小說、31篇短篇小說,但幾乎每部小說都是經典之作,《短篇小說全集》(CompleteStories)于1972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批評積累,到20世紀90年代奧康納研究已形成豐富的批評史,其作品得到多維觀照,涉及現代主義創作技法、宗教主題、與同時期南方作家的平行比較、對當代南方作家的創作影響等研究。新千年以來,國際奧康納研究一直處于上升階段,形成自 20 世紀 80年代以來的第二次“奧康納研究熱”,評論界致力于解讀“奧康納作品所生成的所有意義”(Arant et al., 2020: 3)。新的理論話語語境培養了奧康納研究領域的新動向,也更新了學術界對奧康納研究的一些傳統認知,如在《激進的情感矛盾:弗蘭納里·奧康納的種族研究》(RadicalAmbivalence:RaceinFlanneryO’Connor)中,奧康納研究專家安吉拉·阿萊默·歐唐奈爾(Angela Alaimo O’Donnell)結合作家本人一些未出版的信件研究奧康納對于黑人民權運動高潮時期各種種族運動的矛盾態度,被學界視為第一部結合奧康納信函等鮮見資料開展作家種族觀研究的專著(2020: 封 4)。21世紀以來的空間轉向推動了評論界對奧康納空間書寫的關注,如克拉克·M.布里坦(Clark M. Brittain)認為奧康納深受亨利·詹姆斯心理書寫的影響,善用物理建筑書寫表達人物的心理狀態(1)引自Clark M. Brittain, “The Architecture of Redemption: Spatiality in the Short Stories of Flannery O’Connor.”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Religion Vol. 4,詳情見http:∥jsr.fsu.edu/2001/brittainart.htm 2020.12.12.。
雖然奧康納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南方的薩凡納,但她在表現各種類型的物理空間時有著驚人的空間想象能力。例如,在短篇小說《天竺葵》(TheGeranium)中,南方人老達德利搬到北方高樓林立的紐約與女兒同住,奧康納通過都市建筑的物質書寫表現了老達德利難以融入紐約都市生活的痛苦;而在《火車》(TheTrain)中,奧康納將主要人物海茨·維克斯置于火車空間中,其中的物質細節特征表現了南方人因離開故土帶來的迷失和孤獨。雖然已有學者研究奧康納的建筑空間,但是對于其建筑空間的物質性構成,如建筑距離、顏色、形狀、空間方位、內部裝飾等關注不夠。物質書寫的文本細讀不但可以幫助讀者換個角度賞析奧康納對南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助于挖掘奧康納對南方書寫傳統的繼承與開拓。
對于空間之物在文學批評中的重要性,和奧康納一樣同處南方文藝復興創作時期的韋爾蒂很早就有相關論述。在著名論文《小說中的地方》(Place in Fiction)中,韋爾蒂從小說美學層面將地方、人與物三者相結合,強調了將小說“植根于地方的重要性”(Welty, 1998:781)。韋爾蒂尤其強調地方之物對人類情感和意識的塑造,“西班牙的魔山、黑色森林里的綠色宮殿”等物理環境賦予地方一種特定的質感,而富有質感的地方擁有價值觀念和復雜情感,與人物的感覺息息相關”(Welty, 1990:122)。21世紀以來,文學批評的空間轉向不再僅限于像韋爾蒂那樣從小說美學層面揭示地方之物對于人物塑造的意義,而是從更為宏闊的文化批評視野審視物理空間的文學、文化內涵,研究地方或空間的物質載體對于構建持久心理身份的重要性。在《空間與地方》(SpaceandPlace)中,段義孚(Tuan Yi-Fu)從空間地理視域論證了地方之物如何幫助穩定、“強化人類的身份意識”(1977: 159)。本文選取兩部具有濃郁空間書寫特色的短篇小說《天竺葵》《火車》為研讀對象,結合21世紀以來與空間、地方、物相關的理論話語,闡釋奧康納如何借助空間物質細節書寫塑造處于20世紀前半葉轉型期南方人漂泊無根的現代主體身份,進而透視奧康納在傳達現代性悖論經驗時的創作美學。
1 摩天樓與天竺葵的對峙:《天竺葵》中的空間書寫
1946年,《塞沃尼評論》的編輯安德魯·萊特(Andrew Lytle)最早出版了包括《天竺葵》在內的幾部短篇小說,此時奧康納還在愛荷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47年奧康納順利畢業,這部小說也成為她畢業論文的一部分。雖然《天竺葵》只是塑造了搬到紐約與女兒一家同住卻倍感格格不入的南方人形象,并不像《公園之心》(TheHeartofthePark)等作品那樣具有鮮明的宗教情感,但卻代表了奧康納創作中的一個重要題材,即書寫處于變革、流動語境中的南方人的心理身份。在奧康納時代,城鎮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增加了南方居民生活的流動性,南方社會經歷了激烈的現代性變革,“南方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國化”(Egerton,1974: xxi)。但是,植根于南方社會深層結構的一種南方精神依然存在,這一點不但體現為南方作家創作中流露的地方意識,也表現在南方文學中具有強烈鄉土情結的南方人身上。
在《天竺葵》中,“天竺葵”是典型南方植物,卻出現在北方摩天大樓的陽臺上。小說中的主要人物老達德利是個土生土長的南方人,卻身處北方紐約都市。人與物在空間上的平行并置暗示了居住在北方都市公寓大樓的南方人就像移植到不同環境的植物一樣難以適應。隨著情節的展開,奧康納詳細描述了一個背井離鄉的南方人老達德利在紐約的各種不適和困窘經歷,尤其是關于其所處公寓高樓的空間書寫集中呈現了老達德利無法融入陌生都市環境的情感體驗。
小說從一開始就暗示了狹窄的樓間距是對老達德利形成壓抑的都市空間。從窗外望去,“15英尺外”就是另一戶人家的另一扇窗戶。“被熏黑”的窗框紅磚更是加重了這種壓抑感,從而在敘事層面為整個小說鋪墊了壓抑、不適的情感基調。公寓的狹窄空間也擠壓了人與人之間的空間,“找不到一處沒有人的地方。廚房對著浴室,浴室對著一切。你一轉身就回到原處了”(8);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系被割裂,尖嘴猴腮的人們探出窗外,“望向別人家的窗子,那些長得和他們一樣的人也回望去”(7)。深入文本細讀,讀者了解到老達德利女兒的家“住在一棟大樓里——在一排一模一樣的大樓之間”;街道就像“遛狗道”,所有建筑物看起來都一樣;所有大樓“全都是烏紅色或灰色”(5),深色調的裝飾給讀者傳遞了所有建筑趨于同質的特征。建筑的同質化實則指涉了現代工業社會的同質化,揭示了現代工業社會的內在矛盾:一方面,人們面對一個商品充斥的社會,商品大規模生產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內在要求,但另一方面,個體為了追求個性不斷地卷入反對同質性的斗爭(Kopytoff, 1986: 66-67)。小說中,除了同質化的公寓樓,浴室、廚房等標配也讓公寓樓里面的每個房間變得同質化。小說中黑人白人同居一樓成為鄰居,表明建筑的同質化也推動了種族階層的融合。這些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變化對于傳統南方人老達德利而言,感到無所適從,長期居住于此只會加重他的異化和焦慮。他周圍都是帶來負面情緒的物質意象:“走廊盡頭有一個女人面向大街尖聲喊叫,說著誰也聽不懂的話;收音機微弱地播放著肥皂劇憔悴的配樂;一個垃圾桶噼里啪啦地滾到下面的防火通道。隔壁公寓的門砰地關上了,尖利的腳步聲嘚嘚地敲打著地板。”(8)“憔悴”“微弱”“尖利”等令人頹喪的字眼,混雜著各種令人煩躁的聽覺意象,集中烘托了老達德利深感壓抑的都市空間體驗。
雖然蓋斯頓·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間的詩學》(ThePoeticsofSpace)中曾論述過建筑如何作為一個“垂直性的存在”幫助穩定人物的心理身份(1964:17),但在奧康納看來,高度同質化的都市建筑在審美上讓人覺得乏味。20世紀上半期,美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建設從水平轉為垂直方向發展,各種高樓大廈拔地而起,成為眾多大城市的地標建筑,奧康納筆下的紐約更是如此。作為現代城市的代名詞,摩天大樓成為“城市生活體驗與動態變化的象征”,“為人們提供了新的空間體驗與環境感知維度”(馬特,2020:222)。老達德利居住的公寓大樓高聳入云,上上下下的樓道里就“只有那些走廊,讓你想到拉長的皮尺,它的每英寸都有一扇門”(7-8)。人與人的關聯被垂直向上的大樓切斷,正如豪威爾斯(William Dean Howells)指出,“摩天樓將城市的社交空間變成了無人的孤島”(1909:479)。向下伸展的樓梯更是暗示了現代工業文明對人的吞噬:“如同地里一條深深的傷口。樓梯穿過一條山洞般的豁口,張開,向下,再向下。”(22)這些垂直上下的樓梯,在奧康納筆下成了弗蘭肯斯坦般的科學怪人,有著壓迫、吞噬人的力量,呼應了現代都市促成人的異化。劉英在論及摩天樓意象時認為,“城市人創造了巨物,但他們卻被這個巨物所鉗制”(127)。由此可見,小說中垂直上下的建筑空間設計模式對遠離故鄉的南方老人帶來心理壓迫,甚至使他眩暈、窒息。習慣了南方田園生活的老達德利對此心生厭倦,“那些討厭的大樓全都一個樣”(14);他只能像小說開頭所展示的,經常蜷縮在椅子里尋找安慰;他的“身體形狀”漸漸與椅子“渾然一體”,這一意象耐人尋味,一方面暗示了身體與椅子的親密接觸,另一方面也可理解為老達德利與物交互中逐漸物化,呈現物人不分的間性特征。這一物質細節真實地暗示了現代南方人在面臨現代工業文明沖擊時的逃避和異化。
如果說建筑象征了現代工業社會的同質化,天竺葵則代表了如物質文化研究者克比托夫所說的獨特性。天竺葵與土地有著天然聯系,也成為對抗現代都市生活同質性的一個象征。此外,天竺葵來自南方,是老達德利思念南方的重要精神寄托。老達德利在妻子去世后雖然獨居,但在黑人雷比一家的陪伴下生活充實。除了和雷比一起打獵釣魚,老達德利還常可以吃到雷比妻子做的食物。雷比妻子尤其擅長種植“天竺葵”等花卉植物。正是這些南方家園的日常事件揭示了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聯系。段義夫認為,家園由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聯系和關系構成,“潛意識的強烈依戀可能來自共同活動和日積月累的家庭樂趣中的熟悉和輕松、撫育和安全的保證、對聲音和氣味的記憶”(Tuan, 1977: 159)。這些日常活動使家園和居住者之間形成了一種深厚的情感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天竺葵具有南方性、南方氣息的植物,是老達德利思念南方故鄉的情感連接,也代表了期待回歸的精神家園,正如奧康納寫道,在他眼里,“女兒住的地方都不能稱之為家”(奧康納,2016:5)。
天竺葵在小說中不但和摩天樓形成敘事并置,成為現代工業文明和南方傳統文化對峙的隱喻,也在小說中被呈現為老達德利的物質提喻。和老達德利在都市空間的格格不入一樣,紐約都市的天竺葵看起來有些另類,淺粉色的花朵上掛著褪色的蝴蝶結,而故鄉的天竺葵則顏色鮮艷,看起來“更好看”,而且是“千真萬確的天竺葵”(1)。這種對比暗示了來到紐約都市的老達德利就像被移植到北方陽臺的天竺葵一樣難以適應新環境。除了身份境遇相似,天竺葵也常喚起老達德利的思鄉之情,“老達德利常常盯著窗外鄰居家的天竺葵,忍不住流下寂寞的眼淚”(5)。小說結尾天竺葵從窗臺上掉落,老達德利的命運悲劇被推向高潮;天竺葵的根離開土壤,“裸露在空氣中”(18),這一核心意象集中體現了裹挾在兩種文明對峙中的南方人的無助和疏離,而奧康納將“天竺葵”作為小說標題,內涵深厚。雖是作家早年練筆之作,《天竺葵》以空間物質細節書寫開啟了貫穿奧康納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即傳統南方居民被現代化進程所裹挾前行的無措與失序。
2 流動南方的物質表征:《火車》中的空間書寫
和《天竺葵》一樣,《火車》(1947)最早發表于《塞沃尼評論》,后來被奧康納改寫拓展,成為長篇小說《智血》(WiseBlood)的第一章。小說主要描寫了南方青年海茨·維克斯乘坐火車前往托金漢姆的旅程。雖然情節并不復雜,但是海茨·維克斯思緒穿梭于南方故鄉與所困的火車空間,使小說頗具魔幻現實主義格調。離開故鄉多年的海茨總是將火車上的一切與故鄉田納西州伊斯特羅德聯系在一起,而且認定火車上一位列車員就是自己家鄉一個名叫凱西的人早年丟失的兒子,盡管列車員一再申明自己來自芝加哥,甚至從未聽說過田納西州的伊斯特羅德;沉浸在對家鄉模糊記憶的海茨一路上漏洞百出,與旅客的交流詞不達意,還魯莽地撞倒列車員。這些細節書寫使得小說中所刻畫的故土難尋、家園難覓的現代南方人形象躍然紙上。
火車作為具有獨特結構空間的物體,是奧康納時代“流動的南方”語境的物質表征。奧康納出生于20世紀20年代,正是美國南方鐵路發展的黃金期。著名的“迪克西鐵路公司”(Dixie Limited)合并后成為可以連接密西西比、田納西、密蘇里等南方數州的區域性運營商,在促進南方現代化進程的同時,也增強了南方居民的遷徙流動性。據傳記家記載,奧康納在被診斷患有紅斑狼瘡前經常乘火車前往愛荷華大學;1950年乘坐火車回南方的途中,奧康納身體感到極度不適,一下火車即被送到醫院就診(Kirk,2008:8)。在她多部作品中,主要人物前往異地求學或工作時乘坐的也是火車,火車成為其小說中最具南方現代工業文明象征意味的意象。雖然無法考證海茨·維克斯在火車上的體驗與奧康納當年困囿于火車上急于下車就醫的經歷有何關聯,但是主人公在火車上極度難過的空間體驗被奧康納描寫得十分細致,尤其車廂內外翔實的物質細節書寫使得現代交通工具火車在小說中高度前景化,成為透視小說審美價值的重要媒介。
小說開篇不久,奧康納就呈現了現代工業文明產物火車的速度和力量:“火車在灰白的光線中疾駛,掠過片片樹影和塊塊田野,靜止不動的天空飛速后退,暮色漸濃。”(80)“疾駛”“掠過”“飛速”表明了火車速度之快,但“快”并沒有帶來相應的舒適體驗,均消解在“灰白”“暮色”等令人壓抑的景觀書寫中。在這樣一個“現代性標志”的龐然大物面前,“靜止”之物在快速流動之物的參照之下迅速“后退”,這一頗具雙關意味的流動意象隱喻了南方人在面對滾滾前行的南方車輪時的停滯不前或落后。奧康納寥寥數筆勾勒出火車兼具“現代性”和“移動性”的雙重特征。“把頭靠在椅背上,向窗外望去”的主人公從一開始就被置于快速前行的車輪之上,成為處于移動空間的敘事主體。
和火車“移動性”特征的簡潔描述相比,奧康納用大量語言書寫了火車空間的“物質性”特征。先是車廂的過道很“狹窄”,以至于乘客走路“搖搖晃晃”,而且時不時需要“緊貼側壁,讓幾個人進去”(107);其次是過道的“漆黑”和“陰森”,低垂而又厚重的“綠色窗簾”擋住了車窗外的光線,就連燈光也很“昏暗”(109),“緩慢地照出腳下的地毯,不住地晃動,令人眩暈”(115)。這些“物質性”特征不斷出現,烘托了火車車廂空間的擁擠和封閉。封閉空間“物質性”最能體現在海茨的臥鋪。需要借助梯子才能爬上去的臥鋪最重要的特點是“沒有窗子”,而且不斷被奧康納強調:“側壁上沒有窗子”;“里面也沒有暗窗”;“側壁上面鋪開一張漁網一樣的東西;然而沒有窗子”(111)。沒有窗戶的物理特征集中顯示了火車車廂微空間的封閉,而重復修辭更將封閉的意象前景化,乃至讓海茨感覺躺在里面就像躺在“黑暗的棺材”里。約翰·庫里(John Curry)指出,在火車空間里,乘客被迫與大批陌生人處在新型的封閉空間,“脫離了日常生活環境,引發新的社會關系問題”(Curry,2007:104)。
除描述海茨的個體疏離感,小說還聚焦了車廂內疏離、冷漠的人際關系。正如德·賽托(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實踐》(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中指出:“火車車廂是個封閉空間,車廂內有固定座位,座位有固定數目,旅客除了能去休息室和衛生間短暫活動外,就只能被束縛在車廂座椅上。”(1984:112)小說中的海茨不但難以和列車員進行交流,和乘客的交流也詞不達意。在車廂微空間里,人與人的疏離讓海茨感覺孤獨,即便在餐車吃飯,他也感到非常難受,想象著其他食客盯著他的目光。無論火車駛向何方,他都感覺被困在那里,渾身濕透、寒冷、頭暈目眩。快速移動的火車在速度上讓現代主體脫離傳統意義上的時空束縛,但是小說中的海茨·維克斯從一搭乘火車起,便處于另一種意義上的封閉空間,這種帶有反諷意味的空間轉換正是現代性悖論的體現;而火車車廂內部封閉壓抑的物質細節以及主人公被束縛壓抑的空間體驗正集中體現了現代人失去根基的無序感。
如果說《天竺葵》這部小說是通過與南方土地相連的植物來傳達南方人的漂泊感,那么小說《火車》則是通過海茨·維克斯在流動性、封閉性火車空間里的經歷與回憶呈現了南方人離開故土的陌生感。小說中有著濃厚鄉土情結的海茨被嵌入“流動南方”的語境中,空間之物火車參與建構了奧康納筆下漂泊無根的南方白人的心理空間。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奧康納一方面通過封閉壓抑的火車車廂微空間的物質細節刻畫了海茨流離漂泊的心理身份,另一方面還通過回憶與想象的形式呈現了海茨的記憶之物:故鄉的小路、房屋、谷倉。他想象自己睡在了廚房的地板上,睡在母親曾經購買的胡桃木衣櫥旁邊(102)。和冰冷的車廂空間相比,想象中與家園相關的各種充滿溫情的物品讓海茨感到了慰藉,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斷裂感和異化感。正如段義孚所說,家園給人帶來的親密感與其說是整個建筑所激發的,不如說是建筑的“各個部分和其中的陳設所喚起的”(Tuan,1977:144)。由此看來,記憶之物成為故鄉的物質提喻;家園因為母親曾經居住過而具備情感屬性。想象之物故鄉老房子牢牢印在記憶深處,和現實中身體所處的不停移動的火車空間形成并置和對比。通過海茨想象和現實的敘事并置,奧康納凸顯了海茲對于故鄉與火車兩個不同空間的情感體驗。火車旅行本身象征了失去故鄉的海茨介于現實和想象之間的尋根之行。
遺憾的是,無論是故鄉住房的“空無一人”,還是那件隨時會被偷走的衣櫥家具,都隱喻了海茨的南方傳統家園不復存在,無論海茨付出多少努力來保住它都注定是徒勞。此外,各種記憶之物的暗淡與消亡也進一步暗示了海茨最后的歸宿注定是絕望。正如小說暗示的,“他在那條路上轉過身,在黑暗中,或者說是在半明半暗中看見了那封上門窗的倉庫,還有門大開的谷倉,里面漆黑一片;那棟小一點的房子,有一半被運走了,門廊不見了,客廳里的地板也沒有了”(112)。物在記憶深處逐漸消失,尋根之旅以虛幻與失敗的結局告終。
3 結語
無論是《天竺葵》中的老達德利,還是《火車》中開啟尋根之旅的海茨,奧康納都塑造了處于變革時期的南方人家園難覓、疏離失序的戀地情節。如果說沃爾夫通過嗅覺景觀書寫塑造人物身份,小說中人物在回望南方的追尋中找回南方的味道,那么奧康納則是將人物置于“流動的南方”語境中,通過地方之物的書寫,凸顯離開故土的南方人如何淪為流浪在現代生活“荒原”上的“無根人”。
奧康納受現代主義思潮影響,在創作中著眼于南方社會轉型沖突的現代性經驗,構成了兼具南方性和現代性的創作風格。因此,無論是摩天樓、天竺葵等物質書寫,還是車廂物質性書寫,或是記憶之物的模糊與暗淡,這些空間之物也可以被視為奧康納現代性書寫的獨特呈現。離開故土、失去南方家園的老達德利、海茨等在南方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下異化為一個無家可歸的“空心人”,只能流浪在現代生活的荒原上,被現代工商業文明社會放棄。從這個意義而言,奧康納借助空間之物的細膩呈現實現了對現代性的反抗和解構,傳達了她對于現代性悖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