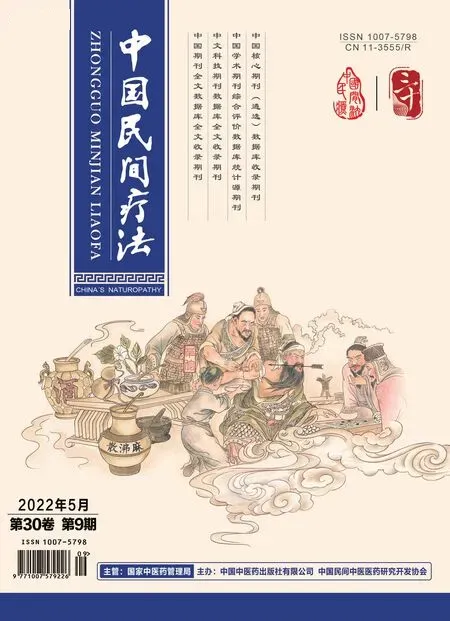陳朝明應用針刺結合整脊治療外傷性嗅覺障礙的醫案報告
葉沈早,陳朝明
(1.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23;2.江蘇省南京市中醫院,江蘇 南京 210022)
嗅覺障礙指嗅覺通路各環節出現功能性和/或器質性病變,導致機體對氣味感知異常的一種疾病[1]。此病按受損程度分為嗅覺喪失、嗅覺減退,按嗅覺受損性質分為器質性和精神性嗅覺障礙兩類,其中器質性分為傳導性、感覺神經性和混合性,精神性又分為嗅覺過敏、倒錯及惡嗅覺[2]。嗅覺障礙的常見病因有鼻-鼻竇疾病、上呼吸道感染及頭部外傷等,其中外傷性嗅覺障礙病因明確,有頭部外傷史,嗅覺喪失的程度與損傷部位及程度相關。目前西醫多采用糖皮質激素鼻腔局部或全身應用治療嗅覺障礙,療效尚不理想,且存在不良反應[3]。
中醫在恢復嗅覺功能方面發揮獨特作用,相較于西醫的藥物、激光照射、嗅覺訓練、外科手術等治療方法,針灸、中藥或聯合治療的方法療效更佳、治愈率更高[4]。陳朝明教授系南京市名中醫,南京市中醫院主任醫師,脊柱病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整脊分會常委,南京中醫藥學會整脊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從事醫、教、研工作30余年,擅長治療脊柱相關疾病。陳師在門診接診1例外傷性嗅覺障礙患者,因其接受西藥治療后療效不佳,遂尋求中醫針灸治療,應用綜合方法治療收效可觀。現將陳師應用針刺結合整脊治療外傷性嗅覺障礙醫案1則介紹如下,以期為臨床治療嗅覺障礙提供新思路與新方法。
1 病歷摘要
患者,女,33歲,2020年5月14日初診。主訴:外傷后嗅覺障礙3個月余。患者于2020年1月25日因“車禍后頭面部外傷致神志不清3 h”轉入合肥市第二人民醫院神經外科就診,提示左側上頜骨骨折、額骨骨折、雙側額葉腦挫傷、額鼻眼部嚴重皮膚裂傷、右側眶骨骨折、鼻骨骨折、顱底骨折、左側顳骨骨折。經手術及相關對癥治療后,患者生命體征平穩,病情穩定后出院。患者出院后自覺嗅覺喪失,于2020年3月至眼耳鼻喉科專科醫院就診,查鼻內鏡檢查示:雙側下鼻甲腫大,雙側鼻道粘連,右鼻嗅裂粘連,結合既往病史診斷為外傷性嗅覺障礙,予以布地奈德鼻噴霧劑收縮鼻腔黏膜治療,嗅覺喪失未改善。現為求進一步診治,遂至我院針灸科就診。癥見嗅覺喪失,不聞香臭,伴右側前額及顳部麻木明顯,無頭暈頭痛,無咳嗽咯痰,無惡寒發熱,胃納可,夜寐一般,二便調,舌淡暗,苔薄白,脈細,尺脈弱。西醫診斷:外傷性嗅覺障礙。中醫診斷:鼻聾(腎虛血瘀證)。治療方案:針刺結合整脊(頸椎定位旋扳法)。針灸取穴:迎香(雙)、上迎香(雙)、印堂、上星、百會、通天(雙)、風池(雙)、合谷(雙)、足三里(雙)、太溪(雙)。針刺操作:選用華佗牌一次性無菌針灸針,于迎香略向內上方斜刺8~12 mm,于上迎香向內上方斜刺8~12 mm,于印堂從上向下平刺8~12 mm,于上星向前平刺12~20 mm,于百會向前平刺12~20 mm,于通天向前平刺8~12 mm,于風池向鼻尖方向斜刺20~30 mm,于合谷直刺15~20 mm,于足三里直刺25~35 mm,于太溪直刺12~20 mm。分別選取上星、印堂及兩側迎香作為兩組輸出電極,使用華佗牌SDZ-Ⅱ型電子針療儀的導線連接針柄,選取低頻連續波進行刺激,強度以患者可耐受為宜,時間30 min。出針后施以頸椎定位旋扳法,具體操作:患者取端正坐位,囑其放松,醫者位于其后方,若頸椎棘突向左偏,醫者左手拇指抵住偏凸的棘突,右臂屈肘環抱患者下頜,右手四指固定偏凸段以上的頸椎節段,逐漸屈曲患者頸部,直至感受到偏凸棘突上的關節間隙打開,維持此時頸部屈曲幅度,接著向右旋轉頸部至彈性限制位,保持斜向上的牽引力,保證寰樞關節、寰枕關節的穩定性,稍作停頓后右臂做一突發且有控制的扳動,同時左手拇指頂推偏凸棘突,最后查體以保證復位的成功。若頸椎棘突向右偏,則操作方向相反,方法同前。每周3次。2020年6月5日二診:患者嗅覺稍有恢復,可聞及洗發水等濃烈的香味及嬰兒糞便等較為強烈的臭味。繼續當前治療,治療頻次改為每周2次。2020年7月10日三診:患者嗅覺改善,可聞及生姜、八角等香料的味道。后每1~2周治療1次鞏固療效。2020年9月4日復診:患者嗅覺明顯恢復,日常生活不受影響。隨訪3個月,患者嗅覺基本恢復正常。
2 討論
2.1 病因病機 嗅覺通路由嗅上皮、嗅球、嗅覺皮層三部分組成,任何1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導致嗅覺障礙。研究顯示,外傷性嗅覺障礙一般非單一因素造成,而是由外周嗅神經元到嗅中樞的多種病理改變引起,主要與外傷后鼻腔內結構的異常改變、嗅神經及嗅覺中樞的損傷等相關[5]。該患者頭部外傷病史明確,鼻內鏡結果顯示鼻腔黏膜水腫、雙側鼻道粘連及右鼻嗅裂粘連,推測以下兩點原因造成嗅覺喪失;外傷后患者鼻腔黏膜水腫、雙側鼻道粘連,鼻腔不通暢,同時右側嗅裂粘連阻塞,因此含有嗅素的氣流不能順暢到達嗅區;外傷后直接造成患者嗅神經纖維的損傷,局部組織改變影響新生嗅感覺神經元軸突穿過篩板與嗅球中的僧帽細胞建立突觸聯系,因此嗅覺通路的完整性遭到破壞。
中醫認為,嗅覺障礙屬于“鼻聾”“鼻不聞香臭”等范疇。《外科大成》云:“鼻聾者,為不聞香臭也。”此病病因較為復雜,與肺、脾、肝關系密切,外邪襲表、脾失健運、肝失疏泄等均能引發嗅覺障礙,患者年老腎元不足、外傷等致病因素也可導致該病。該患者因外傷致鼻部氣機不暢,瘀血內阻,其素體偏虛,腎氣不足,當標本兼治,治以祛瘀通絡、補腎助陽為主。
2.2 針刺結合經絡整脊治療 局部取穴迎香、上迎香、印堂,三穴均鄰近鼻,腧穴所在,主治所在,共奏通調鼻部氣血之效。古籍中關于迎香的記載有“鼻窒不聞迎香間”(《針灸大全》),“不聞香臭從何治?迎香二穴可堪攻”(《玉龍歌》)。現代研究顯示,電針迎香可減輕嗅黏膜炎癥,亦能促進嗅覺系統嗅感神經元的再生,從而改善嗅覺功能[6-7]。上迎香,又稱鼻通,為經外奇穴,位于鼻翼軟骨與鼻甲的交接處,治療嗅覺障礙屬于該穴的近治作用。印堂位于兩眉之間、鼻之上,與肺經氣相通[8],向下平刺可引導氣至病所,為治療鼻部疾患要穴。研究發現,在迎香、印堂進行穴位注射治療,可有效減少變應性鼻炎大鼠鼻黏膜炎癥介質組胺生物學效應的發揮,從而抑制鼻黏膜的炎性反應[9]。頭為諸陽之會,頭部取穴上星、百會、通天、風池,針刺可調動陽氣。上星、百會同屬督脈,《針灸資生經》記載其治鼻塞不聞香臭;通天屬足太陽經,《針灸大成》云:“通天去鼻內無聞之苦。”可通徹上竅,治療鼻疾效果佳。風池為足少陽經與陽維脈的交會穴,針刺可使針感循經脈到達頭面部,則“氣至而有效”,從而有效改善嗅覺神經功能。遠部取穴合谷、足三里、太溪,合谷為手陽明經原穴,符合循經取穴的要義,也為“四關穴”中要穴,與迎香、上迎香等穴遠近配伍,共奏通經絡、調氣血之功。足三里為補益要穴,太溪為足少陰腎經的原穴,該患者腎氣不足,取上述兩穴可補腎助陽,起到標本兼治之效。
整脊療法是通過調整異常的脊柱骨間關系,通筋活絡、理筋整復以調整臟腑功能的一種療法[10]。整脊治療該病的機制并不十分明確,推測可能是頸部定位旋扳法通過實現脊柱的結構穩定,恢復脊柱功能的動態平衡,同時改善椎基底動脈供血情況,以促進嗅神經功能恢復[11]。有病案報道,一位老年患者4年前于心臟消融術后出現嗅覺喪失,使用類固醇藥物無效,后因腰痛接受脊柱推拿治療,意外發現自身的嗅覺功能得到改善,推測可能是推拿治療改善了椎旁神經肌肉功能,增強了神經可塑性,從而修復了嗅神經[12]。中醫方面,督脈行于背部正中,脊柱與督脈關系密切,《針灸大成》載:“督脈者起下極之腧,并于脊里,上至風府,入腦上顛,循額至鼻柱,屬陽脈之海。”督脈循行至鼻部,鼻司嗅覺,通調督脈使督脈氣血調達,從而使頭面五官氣血充盛,有助于嗅覺的恢復。
本例患者病因推測為頭部外傷后導致鼻腔黏膜水腫、嗅神經損傷而出現嗅覺喪失,發病初期使用糖皮質激素鼻腔內局部抗感染治療療效欠佳,研究顯示嗅覺最佳恢復期為患病初期,若病程較長嗅覺未有改善跡象,則恢復率低[13]。發病3個月后接受針刺結合整脊治療,經過相當頻次及時間的治療后,患者嗅覺基本恢復正常,提示針刺結合整脊治療外傷性嗅覺障礙療效確切。由此推測,治療有效的機制可能為通過減輕鼻腔黏膜炎癥水平、促進嗅感神經元再生等以促進恢復嗅覺功能。
筆者檢索針灸治療外傷性嗅覺障礙的相關病案報道,文獻數量較少。曲舒涵等[14]應用腹針療法健脾益腎榮腦使鼻竅通達,具體選穴為中脘、下脘、氣海、關元、商曲、右側上風濕點、右側大橫、中脘上;陳雨婷等[15]應用針刺結合艾灸補氣活血通絡、振奮陽氣使鼻竅通暢,針刺百會、上星、印堂、迎香、上迎香、合谷,艾灸百會;劉婉玉等[16]應用鼻周皮部(督脈皮部、足太陽膀胱經皮部和足陽明胃經皮部)淺刺法通過刺激“皮部-絡脈-經脈-臟腑”以疏通經絡、調和氣血;關瑞橋等[17]選用百會、四神聰、頭維、風池、合谷、迎香等穴位針刺治療顱腦外傷嗅覺障礙,治療后總有效率為84.4%。綜上,針灸治療外傷性嗅覺障礙方法各具特色,其中未見有此案報道的針刺結合整脊療法,故此案對臨床治療有一定借鑒作用。此案例也有其局限性,如療效評價較為主觀,患者未復查鼻內鏡檢查,未行嗅覺測試,僅憑其主觀描述判斷療效等,是否具有普遍性及作用機制仍待進一步研究。
目前針灸與嗅覺障礙相關的基礎實驗、臨床研究數量亦較少,可拓展的研究空間很充足。在基礎研究方面,針灸對于嗅感神經元的再生、嗅球體積的影響等方面的作用值得研究,為將來明確作用機制提供有力佐證;其次,未來可進一步開展多中心、高質量的隨機對照研究;針灸治療嗅覺障礙提供有力的循證醫學證據,納入標準可限定為某一類型的嗅覺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