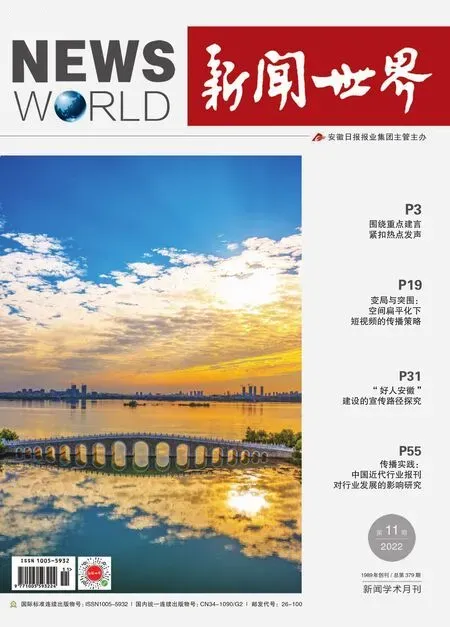融媒時(shí)代下館藏文物的有聲傳播路徑探析
○馬翔宇 燕耀
一、融媒時(shí)代下館藏文物傳播現(xiàn)狀
(一)館藏文物傳播的重要性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文物藏品是我國(guó)古代勞動(dòng)人民的智慧結(jié)晶,它不僅最直接見(jiàn)證了我國(guó)數(shù)千年中華文明歷史發(fā)展,還具有濃厚的歷史價(jià)值、藝術(shù)價(jià)值以及科學(xué)價(jià)值。近幾年,黨中央高度重視歷史文物保護(hù)與數(shù)字化傳承工作,館藏文物所蘊(yùn)含的文化傳播功能與價(jià)值是對(duì)傳統(tǒng)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傳承和發(fā)揚(yáng)。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的《“十四五”文化發(fā)展規(guī)劃》指出:應(yīng)對(du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交織影響,文化是重要軟實(shí)力,必須樹(shù)牢保護(hù)歷史文化遺產(chǎn)責(zé)任重大的觀念,增強(qiáng)對(duì)歷史文物的敬畏之心,加強(qiáng)對(duì)不可移動(dòng)文物和館藏文物保護(hù)修復(fù),提出實(shí)施中華文物全媒體傳播計(jì)劃。因此,對(duì)館藏文物的保護(hù)及傳承,充分挖掘其潛在的文化信息,讓館藏文物的文化內(nèi)涵得到充分傳播,對(duì)于快速實(shí)現(xiàn)館藏文物價(jià)值的全面發(fā)揮并且深入服務(wù)于社會(huì)文化建設(shè)具有重要意義。
(二)館藏文物傳播存在不足
1.在地性局限
館藏文物作為珍貴的歷史遺產(chǎn),記錄和反映了人類社會(huì)生產(chǎn)、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不可復(fù)制、不可再生的特征。館藏文物陳列展覽中最明顯的局限性之一便是其無(wú)法脫離實(shí)體的展覽方式。傳統(tǒng)的展覽形式是通過(guò)實(shí)體的博物館展廳來(lái)展示,在觀眾參觀時(shí)再輔以對(duì)文物的聲音講解。如今,這種文物與講解簡(jiǎn)單組合的展覽方式缺乏創(chuàng)新性和互動(dòng)性,已經(jīng)不再適應(yīng)觀眾的參觀需求。同時(shí),展覽展出的文物數(shù)量有限且更換周期較長(zhǎng),影響了觀眾的參觀體驗(yàn),更難以吸引年輕一代的興趣,也就難以更好地發(fā)揮文物的文化傳播功能。
2020年以來(lái),持續(xù)的新冠肺炎疫情為博物館事業(yè)的穩(wěn)定發(fā)展帶來(lái)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但同時(shí)也給運(yùn)用數(shù)字化技術(shù)傳播文物提供了契機(jī)。各式媒介綜合運(yùn)用于文物展示,打破了時(shí)間空間的限制,觀眾可以隨時(shí)隨地參觀了解,不僅增強(qiáng)了觀眾互動(dòng)體驗(yàn)的樂(lè)趣,也以其互動(dòng)性、動(dòng)態(tài)性、活態(tài)性等特點(diǎn)實(shí)現(xiàn)了傳統(tǒng)文物與數(shù)字技術(shù)之間的嫁接,充分發(fā)揮出數(shù)字時(shí)代博物館的社會(huì)價(jià)值,這也是博物館未來(lái)不斷發(fā)力的方向。
2.欠缺文化深度
文物作為文化的載體,包含的信息是全方位的。基于館藏文物在地性上的局限,以往傳統(tǒng)的陳列模式傳遞出的信息十分有限,參觀者無(wú)法深入了解到文物背后的故事和精神堅(jiān)守,傳播效果大打折扣。尤其是對(duì)于傳播革命傳統(tǒng)和紅色精神的文物,單向直接的傳播結(jié)構(gòu)過(guò)于單一,無(wú)法發(fā)揮其歷史教育和傳播功能。因此,激活館藏文物背后的歷史文化精神,挖掘文物背后的文化內(nèi)涵顯得極其重要。
3.宣傳形式單一
近年來(lái),隨著“文博熱”在年輕一代群體中的形成,觀眾對(duì)館藏文物的參觀需求和興趣不斷提高,不過(guò)想要隨時(shí)隨地到不同城市參觀并非易事。文物如果只是冷冰冰地躺在博物館里,很難引起大眾的注意。現(xiàn)如今文物的傳播形式單一,如何更好地讓游客和學(xué)者領(lǐng)略文物博大精深的文化內(nèi)涵,在不接觸文物實(shí)體的基礎(chǔ)上達(dá)到宣傳或研究的目的,如何讓文物活起來(lái)走出去,是一項(xiàng)重要議題。
二、館藏文物有聲傳播的契機(jī)
(一)數(shù)字時(shí)代的“聽(tīng)覺(jué)回歸”
近年來(lái),在媒體融合與數(shù)字技術(shù)快速發(fā)展的浪潮下,聲音媒介以其強(qiáng)大的伴隨性特征與大眾碎片化的媒介使用習(xí)慣有機(jī)結(jié)合在一起,聲音資源被進(jìn)一步激活和開(kāi)發(fā),有望被運(yùn)用于更多的傳播場(chǎng)景中。聲音以其獨(dú)特的媒介屬性以在線音頻的形式重新進(jìn)入大眾視野,帶動(dòng)了數(shù)字時(shí)代的“聽(tīng)覺(jué)回歸”。因此,館藏文物與聲音的融合也將成為館藏文物傳播發(fā)展的重要路徑。
艾媒咨詢數(shù)據(jù)顯示,近年來(lái)中國(guó)在線音頻用戶規(guī)模和市場(chǎng)規(guī)模都保持連續(xù)增長(zhǎng),2021年用戶規(guī)模已達(dá)到6.40 億人,預(yù)計(jì)2022 年將達(dá)6.90 億人。我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音頻市場(chǎng)規(guī)模也從2017年僅有25 億元,預(yù)計(jì)2022 年將達(dá)到312 億元。同時(shí)用戶付費(fèi)意愿不斷增強(qiáng),進(jìn)一步釋放了知識(shí)付費(fèi)的市場(chǎng)需求,賦予了音頻媒介新的可能。有聲傳播融合了視聽(tīng)、圖像、文字等多種元素,將逐步從單一的聲音媒體向聲視并茂的媒體轉(zhuǎn)變,在媒體融合的發(fā)展趨勢(shì)下,它將在未來(lái)市場(chǎng)擁有一席之地。
(二)“聲音”于館藏文物傳播的意義
聲音是文化傳承媒介的重要組成部分,聲音作為媒介在當(dāng)代藝術(shù)中已經(jīng)廣泛使用,作為無(wú)形的媒介,聲音使文物的傳播形式更具可變性。以有聲產(chǎn)品的形式傳播文物信息,力圖描摹文物的有聲世界,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精神堅(jiān)守,是一個(gè)有益的嘗試。在媒介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聽(tīng)眾的反應(yīng)證明了通過(guò)聲音傳播完全可以感知傳統(tǒng)文化,甚至有時(shí)比起視覺(jué)更能喚起逼真的現(xiàn)場(chǎng)感,會(huì)有更強(qiáng)的角色代入感,感悟到其更深層次的精神內(nèi)涵。
1.有聲產(chǎn)品為館藏文物信息傳播提供重要渠道
有聲傳播在數(shù)字技術(shù)的加持之下,突破了文物在地性上的局限,增強(qiáng)了公眾的互動(dòng)體驗(yàn),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眾的時(shí)間效率,并由此帶來(lái)了文物信息共享及傳播形式的創(chuàng)新性變化。如今,隨著獲取信息的方式更加碎片化、靈活化、自由化,有聲傳播發(fā)揮其優(yōu)勢(shì)為擴(kuò)大文物受眾群體、普及文物歷史知識(shí)以及增強(qiáng)文物吸引力提供了重要渠道,這使得移動(dòng)有聲產(chǎn)品作為最適宜的館藏文物信息獲取渠道快速出位。
2.有聲產(chǎn)品為館藏文物深度傳播提供可能
任何一件文物都有它的前世,館藏文物的有聲傳播不只是信息文本書(shū)摘式的朗讀,而是對(duì)文物信息的重新生產(chǎn),是對(duì)文物歷史文化進(jìn)行理解之后的提煉、加工和再創(chuàng)造,同時(shí)要幫助聽(tīng)眾梳理文物背后的歷史故事、時(shí)代背景以及知識(shí)脈絡(luò)、打通古今文化隔膜等。館藏文物的有聲產(chǎn)品將原本散落在互聯(lián)網(wǎng)中的知識(shí)碎片轉(zhuǎn)化為體系化的知識(shí)產(chǎn)品矩陣,可以傳達(dá)文物背后的歷史價(jià)值和深度內(nèi)涵,在融媒體時(shí)代下實(shí)現(xiàn)文物傳播和學(xué)習(xí)的新布局。
3.有聲產(chǎn)品為館藏文物全媒體傳播增添“音軌”
人們通過(guò)數(shù)字化聽(tīng)覺(jué)空間的營(yíng)造,不僅可以聽(tīng)到聲音,更能感受到聲音背后所傳遞的情感。對(duì)于館藏文物的傳播來(lái)講,每一件文物的選擇、每一個(gè)文物故事的講述、每一層意義的挖掘,都是在情感共鳴基礎(chǔ)上建立起觀眾與文物的連接。在有情感需求的場(chǎng)景中,聲音能更有效激發(fā)聽(tīng)眾的情感共鳴。有聲產(chǎn)品能夠?qū)Ω鱾€(gè)文物的信息進(jìn)行梳理加工,并且通過(guò)聲音達(dá)到對(duì)場(chǎng)景氛圍的渲染功能,有聲傳播能夠激發(fā)聽(tīng)眾對(duì)文物內(nèi)涵和時(shí)代精神的細(xì)微感觸,使聽(tīng)眾更快沉浸在文物所傳達(dá)的情感中。
三、館藏文物的有聲傳播路徑探索
(一)打造文物的“聲音檔案”
在融媒體背景下,通過(guò)數(shù)字技術(shù)傳播方式來(lái)弘揚(yáng)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具有重要的時(shí)代價(jià)值、現(xiàn)實(shí)意義和歷史意義。以聲音元素為載體,打造文物的“聲音檔案”成為文物有聲傳播的路徑之一。用聲音傳遞文物背后的歷史故事和時(shí)代精神,處處凸顯媒體融合背景下的創(chuàng)新。
為獻(xiàn)禮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中國(guó)之聲”傾力打造了《紅色印記——百件革命文物的聲音檔案》系列節(jié)目,它打破了大眾對(duì)紅色文物傳統(tǒng)與單一的認(rèn)知,為文物的文化傳播發(fā)揚(yáng)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讓人們看到了聲音也可以成為為文物傳播賦能的重要手段。通過(guò)100名聲音工作者對(duì)100件代表性革命文物進(jìn)行深情講述,還原了百年歲月中與革命文物相關(guān)的重要場(chǎng)景,重塑了黨波瀾壯闊的百年奮斗歷史,詮釋、傳遞出文物背后所承載的革命精神。從生動(dòng)、鮮活的講解中,聽(tīng)眾更深入地學(xué)習(xí)了中共百年黨史,體會(huì)到一代代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人所傳承的紅色精神,喚起了真切的情感共鳴。
除此之外,《紅色印記》作為生動(dòng)講述百年黨史的新時(shí)代文物聲音“傳記”,還將進(jìn)入全國(guó)各地的革命博物館、紀(jì)念館,受眾在參觀文物展覽的同時(shí),可以通過(guò)有聲導(dǎo)覽接受生動(dòng)鮮活的黨史教育,成為館藏文物有聲傳播的發(fā)展路徑之一。因此,在媒體環(huán)境發(fā)生巨大變化的今天,我們要重視文物“聲音檔案”對(duì)文物傳播的良性功能,用聲音記錄文物記憶,傳遞文物蘊(yùn)含的精神。同時(shí),加強(qiáng)對(duì)文物類廣播節(jié)目以及短音頻等形式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更好地用聲音為文物傳播賦能。
(二)青年傳播主體“流量”加持
青年作為國(guó)家未來(lái)發(fā)展的主力軍,其對(duì)傳承和復(fù)興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視。近年來(lái),一批批青年學(xué)子投身文物領(lǐng)域,從文物青年說(shuō)大賽上青年人的講述身影到一線青年文物修復(fù)工作者的嚴(yán)謹(jǐn)態(tài)度,越來(lái)越多的青少年愛(ài)上文博,尤其是在青年中引起的“文博熱”,他們通過(guò)數(shù)字化平臺(tái)展現(xiàn)了對(duì)歷史文物以及傳統(tǒng)文化的濃厚興趣。
青年一代是數(shù)字化時(shí)代下傳統(tǒng)文化傳播中一股勢(shì)不可擋的新生力量,《紅色文物青年說(shuō)》便是以青年學(xué)生的視角去講述、回憶,通過(guò)青年學(xué)生代表的講述將文字作品轉(zhuǎn)化成有聲語(yǔ)言,將百個(gè)具有代表性的紅色文物故事搬上了熒屏。在媒介飛速發(fā)展的時(shí)代,《紅色文物青年說(shuō)》運(yùn)用有聲語(yǔ)言的傳播方式,用語(yǔ)言技巧觸發(fā)情感共鳴,讓文物精神在青年人身上得到繼承和發(fā)揚(yáng)。
2022 年是國(guó)家博物館創(chuàng)建110 周年,國(guó)家博物館官方微博粉絲數(shù)量突破500 萬(wàn),躋身文博領(lǐng)域大V 行列,再次證明文物可以擁有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流量的加持。當(dāng)前,涉及文博領(lǐng)域的短視頻、自媒體平臺(tái)仍較為缺乏,但文物正在融入“青年群”,圈粉“新生代”,其潛在用戶非常龐大。館藏文物見(jiàn)證了文明的傳承與發(fā)展,承載著厚重的文化歷史記憶,我們要抓住青年一代在文物傳播中的主體力量,注重音頻的內(nèi)容生產(chǎn),用青年人的聲音給文物注入旺盛的生命力。
(三)“有聲讀物”賦予文物新內(nèi)涵
當(dāng)前,傳統(tǒng)出版業(yè)和數(shù)字技術(shù)的結(jié)合,顛覆了以往傳統(tǒng)的閱讀方式,聽(tīng)書(shū)成為了快節(jié)奏生活中人們獲取知識(shí)的重要渠道,有聲讀物迅速占領(lǐng)了數(shù)字出版市場(chǎng),成為當(dāng)下最流行的閱讀方式之一。
文物有聲讀物已成為當(dāng)下受到大眾熱捧的傳播形式,以其快速便捷形式為文物“塑身鑄魂”,幫助大眾獲取知識(shí)。目前《三星堆·榮耀覺(jué)醒》有聲讀物的上線使三星堆文化在音頻的有效傳播下擴(kuò)散到更廣泛的用戶群體。在有聲讀物的音效氛圍下,聽(tīng)眾沉浸在三星堆故事中,感受三星堆文化。
有聲讀物不是教科書(shū)式的“照搬”,而是結(jié)合新時(shí)代的特點(diǎn),賦予文物以新內(nèi)涵,對(duì)歷史傳承下來(lái)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進(jìn)行著書(shū)解句、深入分析,對(duì)其精髓進(jìn)行提煉,使其成為最適宜的館藏文物信息獲取渠道。在新媒體環(huán)境下,受眾主體性和參與性不斷提高,有聲讀物是有聲語(yǔ)言創(chuàng)作的直接平臺(tái),給予了文物更旺盛的生命力。
(四)跨界合作
自國(guó)家文物局印發(fā)《博物館館藏資源著作權(quán)、商標(biāo)權(quán)和品牌授權(quán)操作指引》以來(lái),文博人不斷探索讓文物“活”起來(lái)的有效方式,以更加開(kāi)放的思維方式進(jìn)行跨界合作。從《國(guó)家寶藏》到《唐宮夜宴》,到“青綠腰”,一件件文物“從博物館里走出來(lái)”,讓文物和當(dāng)代觀眾產(chǎn)生了情感上的認(rèn)同與共鳴,我們看到了文物跨界的融合發(fā)展優(yōu)勢(shì)十分明顯。
近年來(lái),音頻產(chǎn)業(yè)與數(shù)字文化領(lǐng)域緊密合作,“聲音”與“文物”的碰撞與融合也表現(xiàn)出了多種可能。例如要讓文物藏品存在的商業(yè)價(jià)值得到更大程度的發(fā)揮,就要積極主動(dòng)地開(kāi)發(fā)館藏文物的文化衍生產(chǎn)品,這不僅能夠給博物館帶來(lái)經(jīng)濟(jì)效益,還能持續(xù)強(qiáng)化其教育功能。除此之外,在融媒時(shí)代下崛起的“直播帶貨”形式也充分展現(xiàn)了文物的商業(yè)價(jià)值,將信息轉(zhuǎn)變?yōu)榭上M(fèi)的形式,成為宣傳文物周邊的重要渠道之一。
除此之外,廣播劇、脫口秀以及各類語(yǔ)言類綜藝也在不斷發(fā)展,逐漸向音頻平臺(tái)轉(zhuǎn)移。利用有聲傳播讓文物跳出宏大敘事走進(jìn)日常生活,這不僅可以降低大眾對(duì)于文物接受的門檻,還使得館藏文物的傳播不再僅僅停留在博物館的實(shí)體參觀中。媒介融合發(fā)展需要我們重新審視館藏文物與媒體的關(guān)系,館藏文物的傳播需要通過(guò)新的媒介形式和數(shù)字技術(shù)來(lái)確立新的傳播方向和傳播思維。
結(jié)語(yǔ)
融媒體的發(fā)展是有聲傳播面臨的新機(jī)遇,有聲媒體創(chuàng)新了人們接受文物的新方式,為館藏文物開(kāi)辟了更廣闊的傳播前景和傳播空間。未來(lái)還將依托新媒介和數(shù)字化手段,搭載聲音傳播的開(kāi)放性、情感性、互動(dòng)性、想象性等,建立起以聽(tīng)眾為中心的傳播體系,為館藏文物的傳播和發(fā)展提供新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