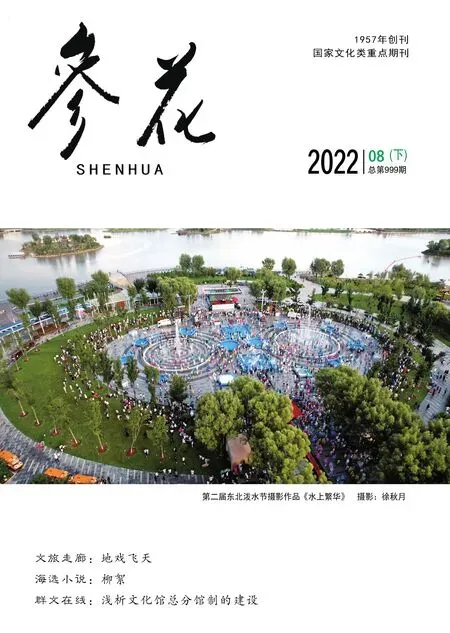試論《狗兒爺涅槃》與《欲望號街車》中的瘋癲形象與創作動機
◎岳洵
一、引言
《狗兒爺涅槃》的劇作者錦云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他對西方現代派作品,尤其是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的熟悉,讓他在創作時,能將中國戲曲在時空表現上的優勢和現代派作品細致入微的心理刻畫兼容并收。作為新現實主義戲劇的代表人物,于1978年、1983年兩度訪問中國的阿瑟·米勒將強勁的舞臺表現帶到中國,對煥發文藝生機的中國話劇產生了重要影響。阿瑟·米勒認為,中國話劇正“借著觀察西方戲劇,找到新的當代中國戲劇的形式和表現風格”。
作為一部享譽世界的現象級戲劇,從1979年杜定宇在《戲劇學習》上撰文介紹威廉斯開始,中國話劇界對《欲望號街車》的接受經歷了一個從立于故事表層“同情弱者”到分析作品深處蘊含的“精神悲劇和詩化特質”的轉型。這既是社會與文化40多年來在接受旨趣上變化的結果,也符合從內容向形式深化的批評規律。因此,《狗兒爺涅槃》與《欲望號街車》中的兩位主要人物,狗兒爺和布蘭琪,重新構成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核心。他們的瘋癲是社會變革重壓下欲望造成的內在撕裂,但在恍惚與譫妄之中,他們卻又在表述中保留了不同的瘋癲表征。本文將聚焦兩個人物的瘋癲形式,深入分析精神異常狀態,以及這種狀態所折射的迥異的創作意圖。
二、瘋癲的表征:“揭露”與“虛構”
臨床上瘋癲,即精神分裂,被定義為“思維過程松散,不合邏輯的聯想,荒謬的妄想,情感不恰當或平淡,社會功能缺損”。雖然狗兒爺和布蘭琪都具有瘋癲的特征,但二者在表征上還存在較大差異,分屬“揭露”與“虛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導致精神異常的策因不同,另一方面,則與兩部戲劇對瘋癲這一事件做了不盡相同的處理有關。
《狗兒爺涅槃》中,狗兒爺的瘋癲非常顯著,倒敘的結構讓地主祁永年的幻影一開篇便出現在角色與觀眾的雙重視野下。狗兒爺瘋了的這一判斷不僅在舞臺提示和其他角色的聲音中直接出現,而且貫穿了整部戲劇,他一直保持譫妄、癲狂、無法分辨人物、記憶混亂的狀態,直到20年后重新拿回土地。《欲望號街車》中,落魄的布蘭琪虛構出舊情人謝普·亨特利,寄希望于通過重溫舊情,得到經濟上的支援,但隨著謊言與精神上的創口被一再撕裂,謝普·亨特利的幻影徹底與現實“攪和到一起”,她徹底失去了理智。
福柯認為,戲劇中的瘋癲處于“結構的中心”,因為“它既是一個孕育著某種秘密‘轉折’的虛假結局,又是走向最終復歸理性和真理的第一步”。《狗兒爺涅槃》中,狗兒爺發瘋這一事件出現在戲劇結構的中段,時間正好與“失去土地—復得土地”的特定歷史進程一致。因為無法正確理解土地的公共意義,直接導致了精神異常,與此同時,成為一個具有豁免意義的隱喻者。一方面,瘋癲者能被更大程度地允許言說,另一方面,他也構成戲劇寫作的當下,一種能夠被用以介入反思的形象。而《欲望號街車》中,布蘭琪的瘋癲由來已久,雖然眾多評論都將出現精神異常的時刻指向妹夫斯坦利的強暴,但若考慮到她無節制地酗酒、頻繁地歇斯底里、神經質地故作姿態,尤其是對謝普·亨特利的幻想,她的精神分裂可能出現在很久以前,斯坦利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讓她再也分不清現實與謊言。似乎福柯所言的結構意義,并沒有很清晰地出現在《欲望號街車》中,但若將布蘭琪對幻想人物謝普·亨特利的認識,從自欺欺人、以假亂真到以假為真視為瘋癲的指標,那么布蘭琪的悲劇正好構成了一個反題式的回應——揭露秘密的代價是在自我虛構中越陷越深。
三、瘋癲之下:現實表達與主觀虛構
狗兒爺和布蘭琪實際上在瘋癲之下呈現出兩種對現實不同的理解。福柯認為:“瘋癲是從人與真理的關系被攪得模糊不清的地方開始的。正是在這種關系中,同時也正是在這種關系的破壞中,瘋癲獲得了它的一般含義和各種特殊形態。”與正常普遍的真實觀發生斷裂是判斷瘋癲的重要指標,在克里奇頓“譫妄—幻覺—癡呆”的瘋癲序列中,狗兒爺與布蘭琪各自走向了不同的結果:前者選擇了現實化的表達立場,而后者體現出主觀化的自我虛構。
對于狗兒爺,瘋癲前后,歷史現實都沒有改變,甚至很多在發瘋之前的遭遇,都被弗洛伊德視角下的“自我”消化,而這些回蕩在潛意識、無法被坦然言及的感受在瘋癲之后才終于找到出口。狗兒爺所有的敘述內容既是個體性的,也是遙遠的、客觀發生的。可以說,發瘋之后的狗兒爺相較瘋癲前,占據了更大的表達空間,看似是瘋話胡話的順口溜,實則耐人尋味。在似懂非懂間,發瘋的狗兒爺兼具影射的功能,馮金花和李萬江結婚,蘇連玉攔著他不讓進,他撂下一句,“這不是牲口圈?這是洞房。”狗兒爺的敘述內容指向現實,他并沒有因為瘋癲而對現實有效性作出改寫。狗兒爺將智者與愚人這組矛盾的概念同一化,一般人眼里怪異的胡言亂語在有心者看來就是暗含春秋的讖言警句。20多年過去,狗兒爺再與李萬江一同喝酒時說,“我什么時候糊涂過?”正指向亦瘋亦慧的二重性。
與狗兒爺不同,布蘭琪則是順從了自我制造的幻覺,在與現實相去甚遠的主觀虛構中沉溺,最終迷失了自我。弗洛伊德說:“妄想來自欲望,是一種自慰。”如果不將早在第四場就出現的謝普·亨特利視為布蘭琪出于虛榮而虛構的謊言,那么從這一幻覺就可以推知,布蘭琪顯著的精神分裂最晚在那時就已經開始。而在這之前,斯坦利在前一晚把布蘭琪正在聽的收音機摔出窗外,暴打了斯黛拉,大鬧一場。面對一個有暴力傾向的易怒男性,布蘭琪感到一種沒有依傍的不安,而那個自丈夫死去就沒有填補的欲望缺口,此時在焦慮中被妄想篡奪,現實世界與她的想象世界悄然發生并軌。布蘭琪所體現的,就是在譫妄中不斷遠離客觀真實,這不只是因為有外界的傷害與刺激,更重要的是她自身渴望用幻想取代沒有希望、無法回到過去的死氣沉沉的現實生活。在與米奇生活的希望落空之后,她迷狂地說道:“我可不想腳踏實地。我要魔法巫術!對,對,就是魔法巫術!我一心想給人的就是這個。我誤導他們。我說的不是事實,我說的是應該的事實。如果這就是罪過,那就讓我為此而永世不得超生吧!”“應該的事實”是往昔南方莊園里無憂無慮的生活,是自己還停留在青春靚麗的年紀,是每一段邂逅都發展為純真的愛情,而不是祖傳基業坐吃山空,親人與年華煙消云散,在欲望的沉淪中忙碌奔勞、遍體鱗傷。她美化過往,是希望過往就如此發生。
福柯描述了瘋癲的四種癥狀,分別出于自戀、狂妄自大、尋求正義懲罰與絕望的情欲,布蘭琪幾乎可以直接作為描述四種癥狀的模板。“……在這種虛妄的自戀中,人產生了自己的瘋癲幻象。這種瘋癲象征從此成為一面鏡子,它不反映任何現實,而是秘密地向自我觀照的人提供自以為是的夢幻。”瘋癲幻象就是布蘭琪手里的銀鏡,她希望一切如她想象的一般。但對于以往那些她不堪回首的放縱,只能用狂妄之下“虛妄的自戀”遮蔽。
四、深層創作動機:反思與發現
歷史投射下狗兒爺的現實表達與布蘭琪自我虛構的主觀表達,反映的是兩部戲劇不同的創作意圖。《狗兒爺涅槃》尋求一種對歷史過往的反思,因此需要一種“外位性”的視野。而《欲望號街車》則試圖在20世紀中葉,為南方種植園經濟在北方工業資本主義席卷下的失敗,發現一副心力交瘁的面孔。于是,反思與發現,構成兩部戲劇不同的深層邏輯。
錦云是基于一個農村干部的耳聞目睹,去體察中國農民的命運變化,但同時,他又自言,在與筆下的人物“拉開一定距離”時,他看到了“可愛、可憐”之外復雜立體的面相。這種反思需要選擇一種超出特定立場的敘述視角,所以單純以作為農民的狗兒爺和作為干部的李萬江都不能實現,而瘋癲狀態下的敘述卻能創設出一種超越時間、超越個體的客觀立場,一種“外位性”的姿態。巴赫金談到藝術作品中的瘋癲時說:“主要主人公的瘋癲或愚蠢這種主題,是對同一個問題的另一種處理方式。人們探索著從外部和內部擺脫垂死的但還占據統治地位的世界觀的所有形式和教條,為的是用另一種眼光去觀察世界,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世界。主人公的瘋癲或愚蠢給人們提供了這樣去看的權利。”反思需要“外位性”的立場,只有發瘋以后的狗兒爺才具有了不囿于普通人生存的超凡,才能夠說出正常語境無法言陳的內容。
而在《欲望號街車》中,布蘭琪的精神狀況與她的過往一樣,戲劇有意在發展中披露,通過“懷疑—回避—查訪—承認”的結構,一個真實的布蘭琪才逐漸浮出水面。與此同時,她的精神狀況也在不斷的打擊中走向崩潰。新舊時代交替里,一個疲憊脆弱的女人慢慢被拆穿所有的謊言,褪去華美的袍子,她蒼白得讓人難堪。“發現,如該詞本身所示,指從不知到知的轉變。……有時,一方的身份是明確的,因此發現實際上只是另一方的事;有時,雙方則須互相發現。”從悲劇傳統中走出的“發現”結構再一次撼人至深,田納西·威廉斯用發現真相帶來的不安給所有人以當頭棒喝。
毋庸置疑,布蘭琪是威廉斯懷揣著深厚同情寫下的,因而布蘭琪并不作為一個需要被排除和管控的異己出現,她的幻想也不能被簡單視為癡人說夢。戲劇結尾,斯黛拉和斯坦利叫來精神病醫生,威廉斯借此制造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尷尬處境。布蘭琪是否發瘋,是通過精神病院的出現,以提供一份她精神異常的承諾,讓所有與之相關的角色卸下道德的重負,用帶走—監禁的行為反證布蘭琪此前是對理性的闖入。其結果,是將“她的精神是否真的異常”“她的精神異常是由什么造成的”等疑問存而不論。顯然,布蘭琪對斯黛拉描述了斯坦利強暴她的實情,但斯黛拉說服自己不能去相信,“我不能聽信她那套說辭,要不然就沒辦法跟斯坦利過下去了。”這時,布蘭琪瘋掉了就成了回避這個巨大而殘酷的道德難題最好的定心丸,只要她是胡言亂語的瘋子,那這個真實發生的事實就能被解釋為純屬虛構,既然無事發生,那么日子就還可以過下去。所以,布蘭琪就必須得是瘋子,至于究竟是不是,精神病院提供了認定她是瘋子的一切合法性。至此,威廉斯留下的最后一個“發現”也呼之欲出:布蘭琪的遭遇其實是對權力機構無力反駁的每一個人。而最值得玩味的是斯黛拉的自我說服,不知不覺間,她也步了姐姐布蘭琪的后塵,試圖去用自我虛構的主觀真實遮蔽丑陋不堪、一地敗絮的殘酷現實。
五、結語
面對歷史,兩種不同的書寫方式演化為傾向外部觀察的現實揭露和內部探照的心靈發現。瘋癲一方面作為破除普通生活情境的戲劇化沖突,強化了造成精神間離的社會重壓,另一方面又在反思和發現兩種不同創作思路下,承載了作者各自的寫作意圖。《狗兒爺涅槃》選定確知的歷史認定,因此,瘋癲的人物實際上都言有所指;而《欲望號街車》中,逐漸崩潰的人物呈現為開放性的象征,這種社會性寓言也得以超越歷史,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