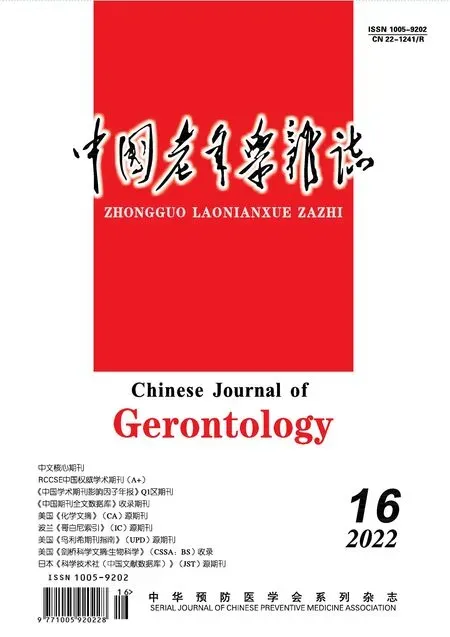腦卒中后認知功能障礙危險因素與腸道微生物群的研究進展
周英群 吳李碩 李先鋒 羅毓婷 周鳳昆 張春麗
(南寧市第一人民醫院 1醫學檢驗科,廣西 南寧 530022;2神經內科)
目前我國已成為全世界腦卒中發病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并呈現日漸年輕化的趨勢。其中腦卒中后認知功能障礙(PSCI)是腦卒中常見的并發癥,被認為是影響中老年人生活質量的常見原因,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極大的負擔。因此對PSCI的預防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就顯得尤為重要。PSCI已知的危險因素為:有腦卒中病史、高血壓、糖尿病(DM)、高尿酸(UA)血癥、冠狀動脈疾病(CAD)等。研究發現腸道微生物群(GM)通過利用腦-腸軸通過神經、免疫、內分泌和代謝途徑來影響這些危險因素的發生。本文就PSCI的危險因素與GM的關系進行綜述,進一步探討PSCI的發生、發展與GM的聯系,為臨床治療提供更好的思路。PSCI是繼發于腦卒中后的一種常見并發癥,腦卒中事件發生后認知障礙的患病率可達20%~80%。Jokinen等〔1〕的研究表明,腦卒中后3個月內有83%的患者出現至少有一個認知域受損,50%的患者在3個或3個以上認知域出現損害。在其他不同的研究中也發現,腦卒中3個月內的癡呆比率為6%~27%〔2,3〕,就算是在3個月內通過臨床治療恢復良好的病例中,出現認知障礙的比例仍高達71%。因此,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PSCI常困擾腦卒中幸存者,是腦卒中患者認知和身體康復的主要障礙。正確認識PSCI,并在癡呆發生前進行早期預防和治療,已成為醫學界急需解決的重點和難點。已有證據表明,PSCI與腦卒中病史、高血壓〔4〕、DM〔5〕、CAD〔6〕、高UA血癥〔7〕等密切相關。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類GM在這些疾病中發揮著潛在的作用。人類的腸道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擁有約1 014種微生物的復雜微生物群落。GM對人體健康起著重要的作用,參與能量提取、維生素的生物合成、防止病原體過度生長和免疫系統的發育等,它們與寄主的免疫系統處于穩態,在維持動態的代謝生態平衡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8〕。除此以外,神經炎癥、壓力軸的激活、神經傳遞和神經發生已被很多研究者證實這些行為的發生是受到GM和中樞神經系統的影響〔9~15〕,其主要機制是通過微生物-內臟-大腦軸來影響大腦的關鍵過程,進而調節復雜的行為,如個人的社交能力和焦慮等。
1 腦卒中與GM
腦卒中又稱“中風”“腦血管意外”,是腦血管病危險因素、腦血管突然破裂或血管阻塞導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腦而引起的表現為從輕度認知障礙到癡呆的腦組織損傷的一組疾病。PSCI是腦卒中后常見嚴重并發癥,它是指不同程度的腦卒中事件發生后6個月內出現并達到認知功能障礙診斷標準的一系列臨床綜合征,主要表現在語言、記憶、學習、執行力等領域的認知損害〔16〕。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嚴重腦缺血后GM的變化和腦卒中后的生物失調與炎癥性免疫反應的誘導有關,腦缺血后調節菌群平衡可改善腦卒中的預后〔17〕。
更值得關注的是,已有研究表明,GM可能參與了該病的發病機制,影響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形成〔18,19〕。GM參與磷脂酰膽堿的代謝,其代謝產物膽堿、甜菜堿,特別是三甲胺n-氧化物(TMAO;宿主產物三甲胺氧化),已被確定為心血管疾病風險的預測因子〔19,20〕。一項臨床研究通過比較無癥狀動脈粥樣硬化、腦卒中和短暫性缺血發作患者之間GM的分布,發現有頸動脈斑塊的無癥狀動脈粥樣硬化組與無頸動脈斑塊的無癥狀動脈粥樣硬化組具有相似的氧化三甲胺水平,且GM的分布也很相似。相比之下,腦卒中和短暫性缺血發作患者在微生物組成方面與無癥狀組存在顯著差異,但其三甲胺n-氧化物水平低于無癥狀組〔21〕。此外,最近還報道了小鼠中腦動脈栓塞(MCAo)模型和輕度創傷性腦損傷后模型GM的特異性變化。在MCAo動物中,消化球菌科和普雷沃菌科的改變與梗死嚴重程度相關;創傷性腦損傷也會引起GM的變化,腦損傷后GM的變化可能影響患者的康復和治療〔22〕。一項對DM小鼠的研究發現,在雙側頸總動脈阻塞后,補充丁酸梭狀芽胞桿菌對缺血/再灌注誘導的腦損傷效果明顯,通過丁酸鈣治療可減少神經損傷,從而改善認知功能〔23〕。這些數據表明,微生物組的代謝物也可能對疾病的發展提供一定程度的預防作用。然而,臨床環境下的GM研究比動物實驗研究更具挑戰性。人類的研究群體通常更加多樣化,因為他們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與被調查的疾病無關,這些因素也可能影響GM的組成〔24〕。
2 高血壓與腸道微生物
高血壓為腦卒中發病的重要危險因素,影響著全球至少11.3億人,引起腦卒中后常會導致認知功能減退甚至癡呆。長期的血壓升高可導致高血壓相關性病理改變:小血管病變與腦動脈硬化、炎癥反應、氧化應激、低灌注、自身調節障礙、血腦屏障破壞及腦淀粉樣血管病等,進而引起認知功能障礙〔25,26〕。在印尼的Karya Kasih養老院,研究人員通過采用橫斷面分析法進行分析觀察發現高血壓病史與認知功能受損有顯著關系,老年高血壓患者認知功能障礙的病史或持續時間與高血壓的嚴重程度存在相關性〔27〕。Osovska等〔28〕通過對患者心內血流動力學參數的分析,發現認知障礙患者的病理變化明顯多于非認知障礙患者,收縮壓的變異性隨著患者認知功能的惡化而增加。此外,在研究外周血管狀態(外周阻力增加、搏動指數增加、線速度增加、內膜-中膜復合體增厚)時也觀察到了重構的跡象,這是認知障礙發生的主要原因,可反映認知障礙的程度,揭示了認知障礙程度與血壓日變化程度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性。
據報道,在心血管疾病的發展過程中,人體GM的組成發生了變化,很多研究人員旨在評估腸道失調在高血壓中的作用。Mell等〔29〕首先發現Dahl鹽敏感大鼠和Dahl耐鹽大鼠盲腸微生物成分存在差異。同年,Yang等〔30〕也發現自發性高血壓大鼠(SHR)GM組成與常壓性Wistar-Kyoto大鼠在豐富度和多樣性上存在差異,高血壓個體GM的多樣性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Mushtaq等〔31〕發現在腸道內的主要菌群中,以擬桿菌門、厚壁菌門和變形桿菌為主;然而,與健康對照組相比,高血壓患者的厚壁菌門與擬桿菌門的比值顯著增加。GM參與神經遞質(如血清素、氨基丁酸、去甲腎上腺素和乙酰膽堿)的生成,可能調節中樞和外周神經系統。臨床研究表明,自主神經系統可能影響GM〔32〕。Santisteban等〔33〕報道了室旁核和腸道交感神經之間通訊的增加、腸道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活動的不平衡都會導致與高血壓相關的腸道病理改變、失調和免疫系統的激活。這些結果都提示高血壓患者GM發生了改變,了解這些微生物組成變化的機制可能會為治療高血壓及其他相關疾病開辟新的思路。
3 DM與GM
DM是一組以高血糖為特征的代謝性疾病,它是引起腦卒中的公認的危險因素之一,其會增加認知障礙的風險和嚴重程度,尤其是在缺血性腦卒中之后。腦血管系統的病理重建被認為是DM患者神經修復不良和認知功能障礙惡化的原因之一。Ward等〔34〕通過確定DM對海馬神經與血管的重構的影響及由此導致PSCI的嚴重程度不同,和比較影響缺血海馬神經與血管的損傷在DM雄性和雌性動物的差異,為DM對腦卒中嚴重程度和PSCI的影響提供了進一步的了解。Groeneveld等〔35〕的研究發現2型DM(T2DM)增加了血管性認知障礙的風險,T2DM的存在與更明顯的腦萎縮和更高的腔隙性梗死的負擔有關。Xiu等〔36〕采用簡易精神狀態檢查(MMSE)量表對中國北京1 039名年齡≥55歲的社區居民的認知功能狀況進行評價,發現與血糖正常的受試者相比,DM或空腹血糖受損的受試者在MMSE中的表現較差,存在不同的認知障礙危險因素。
GM作為人體最大的微生態系統,不僅參與機體的物質和能量代謝,且對其產生重大影響。研究表明,DM的危險因素除了胰島功能障礙、肥胖、妊娠、遺傳等因素外,GM紊亂也可致DM。研究人員對突尼斯患有和未患有DM的參與者的GM進行研究,發現DM患者的GM發生了改變,其GM的分布,特別是黏液菌群的分布受到血糖失調的影響〔37〕。Adachi等〔38〕研究發現T2DM患者的雙歧桿菌水平與碳水化合物攝入量呈負相關,而乳酸桿菌目細菌水平與蛋白質攝入量呈負相關。T2DM患者存在GM失調,可能導致發病并影響預后〔38〕。而中醫藥在治療DM方面歷史悠久,最近的研究表明,中藥可以通過重塑GM來改善葡萄糖代謝,這為進一步研究降糖機制開辟了新的途徑〔39〕。大黃在中藥中廣泛用于便秘的治療,從大黃中提取蒽醌苷類化合物(RAGP)對T2DM大鼠的治療作用及其機制進行研究,發現RAGP的降糖作用機制包括調節GM、激活胰高糖素樣肽(GLP)-1/環磷酸腺苷(cAMP)通路以改善胰島素抵抗,這可能是一種修復GM的新方法〔40〕。因此,這些研究為臨床預防和治療DM提供了新的思路。
4 高UA血癥與GM
高UA血癥近年來呈現高流行、年輕化的趨勢,是多種心血管疾病、代謝性疾病、慢性腎病的獨立危險因素。UA是人體中最豐富的一種神經保護抗氧化劑,是人類嘌呤化合物的終末代謝產物,同時可能是心腦血管疾病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既往研究發現,高血UA水平與心肌梗死和腦卒中的風險相關〔41〕。大多數流行病學證據表明〔42〕,血清UA水平與心血管發病率和死亡率之間存在顯著的、分級的、獨立的和特定的關聯。這在心血管高危人群中尤其明顯,包括高血壓、DM和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而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43~46〕,血清UA水平可能是腦出血的危險因素之一,是認知障礙的獨立危險因素;它可通過獲得促氧化特性而使認知功能惡化,也可預防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吳婧等〔47〕將缺血性腦卒中患者根據蒙特利爾認知功能評定(MoCA)量表分為A組(有認知功能障礙)和B組(無認知功能障礙),結果A組血清UA明顯高于B組,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UA水平是PSCI的獨立危險因素。相反,不同的研究認為〔48〕,在正常范圍內較高的血UA水平與MCI患病率的降低呈正相關,而且這種相關性在高UA血癥患者中并不顯著。已有多項研究證明血UA對認知功能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有利于減少癡呆〔49~51〕。目前研究人員正試圖揭示UA與認知障礙之間的這種矛盾關系。
長期以來,飲食一直被認為是血清UA水平不可忽視的決定因素〔52,53〕;而GM也被認為是血清UA水平的另一個重要決定因素,因為它們直接參與食物的消化和吸收〔54〕,因此控制GM失調可能有助于預防高UA血癥。Wang等〔55〕研究發現,從酸菜中分離到的短乳桿菌DM9218具有調節高果糖誘導的腸道失調和降低高果糖誘導的UA升高的作用。此外,有研究發現痛風患者的GM分布與健康人群的GM存在顯著差異,GM與UA代謝和排泄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后者可能調節血清UA水平〔56〕。目前降低血清UA的治療方法包括黃嘌呤氧化酶抑制劑、重組UA酶和排UA藥物。然而,所有這些藥物都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57〕。因此,對糞便微生物群進行分析評估高UA血癥和益生菌補充對細菌群落結構的影響,開發降低UA濃度的療法將可能成為有用的替代治療策略。
5 CAD與GM
CAD在發展中國家日益流行,是許多工業化社會主要的死亡原因。腦卒中的發生是冠狀動脈介入術后嚴重的并發癥之一,認知功能障礙也是其常見的癥狀,但其發病機制尚未闡明。有研究發現〔57〕,在輕度認知障礙患者中,冠狀動脈狹窄程度越高,與認知功能相關的特定腦區灰質的損失越大。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GM與心血管疾病的關系密切〔58~60〕。Emoto等〔61,62〕先是通過分析CAD患者GM的組成,證明GM與CAD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系,但尚未能確定GM的變化是否參與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之后又通過終端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T-RFLP)數據挖掘分析,對冠心病患者的GM進行了分類,并證明了GM是冠心病的診斷標志。有研究發現老年冠心病組和合并心衰組患者GM豐度低于健康對照組,且GM的多樣性也發生混亂〔63〕。Karlsson等〔64〕通過對頸靜脈粥樣硬化斑塊患者及健康對照組的糞便進行宏基因組測序,發現患者組中富含與肽聚糖生物合成相關的基因,而肽聚糖是革蘭陽性細菌和革蘭陰性細菌細胞壁中的主要成分,這表明腸道中肽聚糖生成的增加可能通過啟動先天免疫系統和增強中性粒細胞功能作為宿主炎癥通路而導致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腸道宏基因組可能在有癥狀的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中發揮作用。而目前,使用高效他汀類藥物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是預防冠心病和心血管事件的重要治療措施,但如何降低他汀類藥物的殘留風險仍待解決。因此,針對CAD及其危險因素的一種新途徑——GM作為冠心病的診斷和治療靶點,正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
綜上,PSCI的發生是腦血管性機制和腦神經退行性機制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炎癥、氧化應激和興奮性氨基酸的細胞毒性等機制在神經元損傷和神經血管功能損害中起了重要作用。目前,糞便微生物菌群移植除了在腸道疾病和與微生物菌群失調相關的腸道外疾病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被用于治療代謝和自身免疫性疾病〔65〕。另外還有病例報道,它在治療自閉癥、帕金森病、多發性硬化癥、慢性疲勞綜合征〔66~69〕等方面療效顯著。因此,盡管GM與PSCI之間相互影響的具體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已有的研究表明GM與PSCI的多種危險因素相關,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推測GM的變化與PSCI患者存在某種聯系。高通量測序技術和宏基因組學的快速發展,使得微生物的研究,特別是GM研究在醫學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關注,這也將極大推動PSCI與GM相關機制的研究,對PSCI的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