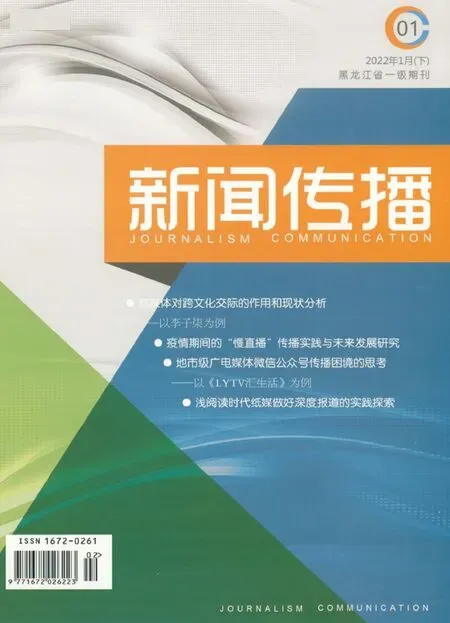商業電影運作中的粉絲式參與文化
高澤宇
(山西大學新聞學院 太原 030006)
一、形式與內涵:跨媒介敘事、參與式文化、粉絲文化
(一)跨媒體敘事
跨媒體敘事鼓勵消費者加入協作敘事成為故事世界的參與者。它并非是同一文本的不同媒體“改編”,而是一個豐富的經過設計的“故事世界”,將故事的不同部分與線索散布于多種媒體平臺中,等待著參與者將之串起。
這些平臺既包括一些傳統的線下平臺,如書籍、漫畫、主題樂園、影片取景地等等,也包含電影、游戲等現代數碼媒體,任意一個媒體平臺都可以成為這一系列產品的進入點。影視作品的觀眾們,最初可能從各種不同的媒介進入到故事世界中,而非局限于通過觀看電影來成為參與者。這些不同的媒體平臺共享著一個主題、一個背景、一個世界觀乃至一個故事,卻都只能從中看到故事的一角。
(二)參與式文化
參與式文化是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盜獵者》一書中所提出的,脫胎于“文化消費主義”,在早期有著草根文化面對傳統文化工業抗爭意味的名詞。之后在《融合文化:新媒體和舊媒體的沖突地帶》一書中變為“邀請粉絲和其他消費者積極參與到新內容的創作和傳播中來的文化”[1]。此時的參與式文化,是依托于新型網絡社交媒介,通過粉絲間社群關系所建立的集體智慧。
可以看到,在跨媒介跨平臺的敘事方法中,沒有參與式文化就無法產生將不同平臺的故事碎片串聯起來的可能。在這不可見的“合作”中,創作者只負責在不同的媒體文本中留下線索,而受眾在探索過程中將這些線索串聯成為創作者心中的世界全貌。也正是在這樣的探索串聯中,故事文本被不斷豐富,成為正如詹金斯所言的參與的力量。使來自改寫、修改、補充、拓展的不同思路,賦予文本更廣泛的多樣性觀點,然后再進行傳播,將之反饋到主流媒體中。在這一正一反的雙向補充中,敘事者和參與者缺一不可。
(三)粉絲文化
關于粉絲文化的討論從早期對于書籍文本的愛好者劃分就已開始,法國當代思想家米歇爾·德賽都認為,讀者是游離于不同文本之中,對文本意義與自身體驗相結合,挪用文本內容以獲取新的意義的群體。而自稱為“粉絲型學者”的詹金斯,既繼承了德賽都的粉絲文化研究,并深受約翰·費斯克的影響,嘗試建立一種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詹金斯在《文本盜獵者》一書中認為,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對于受眾以被動接受的定位,粉絲消費者是在不斷“闖入”文本生產者所設立的文化禁區,并不斷從中挪用對其有用的部分,再結合個人的喜好進行加工的群體。粉絲并非傳統意義上可控、易控、缺乏思想的個體,而是一個呈現主動性、具有自身思考、能夠積極消費的良性群體。參與式文化的語境之下,粉絲保持著與官方傳播內容之間積極的互動關系,粉絲使用自己對官方文本意義的解讀,使其能指產生新的意涵,進而產生對官方文本的意義重組。
二、群體的狂歡儀式
前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認為,儀式化特征存在于任何一種文化形式當中,而這些文化形式中存在的儀式行為往往會表現為群體參與的狂歡。在粉絲們的“草根”文化無法與階級固化的商業文化相接觸時,參與式文化無疑給了粉絲群體一個集體參與的機會,無論是彈幕、評論類的即時參與,還是改編、鬼畜或同人類的創作參與,這一多平臺文化儀式所提供的情感宣泄和身份認同才是粉絲們能夠對參與創作樂此不疲的真正源泉。
(一)多平臺帶來的敘事變化
當今數字媒體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互聯網社交平臺、內容平臺乃至線下數字技術的井噴式增長,不僅使官方文本有了更加多樣的傳播渠道,更加廣泛快捷地實現跨媒介敘事。同時使得粉絲文化得以有更加完善多元的表現形式,各類文化作品受眾有了更多發聲的途徑和方法。因此新媒體時代的粉絲受眾,不同于傳統媒體時代的受眾被發聲渠道所桎梏,能夠使用觸手可得、制作簡單的傳播媒介在對文化產品的解讀中展現更加多樣化的參與行為。
拿星球大戰系列舉例,從1977年的第一部《星球大戰:新希望》,到2019年的《星球大戰:天行者崛起》,除了制片公司眾多官方渠道(如電影、漫畫、小說、動畫、電視連續劇、周邊產品等)的宣傳之外,粉絲們也在利用著多樣的平臺進行自己的群體娛樂。無論是視頻網站、同人小說、線上社交還是線下星戰迷聚會,這些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粉絲行為,才是讓“星球大戰”成為一個普遍知識的主要推動者。
(二)粉絲的情感宣泄
粉絲在作為一個參與式文化群體時,其集體組成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弱關系連結,并不是生活所必需的基礎關系。但對于現代社會中的人類個體來說,情感宣泄這一對自身狀態的疏解卻是必要的。因而在粉絲的參與活動之中,媒介文化所建構的空間成為了情感消費的場域,并從受眾情感需求的角度出發,就相關文化產品進行制造與傳播。
詹金斯在其早期對粉絲文化的研究中,將粉絲行為的成因歸結為對相應文化的迷戀及挫敗感。“迷戀”顯然主要是出于對文本主體敘事的喜愛,而“挫敗感”也正是對于文本主體的失望或不滿所帶來的參與欲望,情感需求使得受眾從被動的接收者變為了主動的創作者。因此可以發現,在粉絲參與式文化中,情感消費是其主要動力。
(三)個體與群體性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在現有研究中主要指主體對于自身的認知和描述,在社會生活的背景下,可以被解釋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以及對社會身份的認同兩方面。自我身份是社會身份構成的基礎,社會身份則是自我身份的補充,兩者共同組成了主體本身的認知。而如蔡驥所認為的,粉絲在參與創造媒介內容的過程中,獲得了對于這一文化群體的歸屬感以及造物主式的創造快感[2]。他們在共同參與的過程中加深了彼此間的情感聯系,既通過創造實現了自我身份的建構,也在產生了群體歸屬感時達成了社會身份認同。
粉絲對于媒體文化的接受不可能也不會在完全孤立中進行,而是一個連結的過程。無論是官方文本的變化還是其他粉絲的活動產物,都會對一個粉絲對其的接受度進行改變,還有一部分則是由在社會文化社群內互動的欲望所驅動的。同時在粉絲群體之中,無論發布者現實當中的身份如何,對圈內文化內容長期穩定的輸出就可以在粉絲群中獲得一定地位,成為意見領袖。甚至會被內容版權方關注乃至嘉獎,這不僅是對創作者個人的鼓勵指導,同時也是對這一創作模式樹立榜樣,對這一粉絲群體進行著“官方”維系。這使粉絲對自我價值會產生更高的判斷,對自我身份的定位也會借由所參與文化文本的關聯而更加清晰。
三、新模式所誕生的“新商業電影
約翰·費斯克將粉絲文化稱作“影子文化經濟”[3],它不是本體文化的延續,而是其對應在自由創作領域的“影子”。它與文化工業有著對照性的相似之處,但卻完全脫離文化工業,二者成為相互依托相輔相成的關系。而在這種新的“共生”模式之下,“新商業電影”也隨之適應演化而來。
首先是粉絲參與式文化造就了大量且繁雜的細節,許多甚至是商業文本自身都未曾考慮的。因為粉絲們的參與形式并不存在以往文化創作的高門檻,而是處于隨意化、個人化制作特點明顯的層級。其內容一部分基于粉絲對社群的關注而表現出高度的專業化,另一部分則因粉絲社群的龐雜而表現出極高的包容性和開放性。這一包容開放的特性在商業電影系列的宣發之中就成為了極為重要的補充部分,《哈里波特》在原書作者J.K.羅琳完成原作的七部曲之后,書籍的讀者以及華納公司所拍攝的電影觀眾們成就了《哈利波特》龐大的粉絲社群,而這一龐大的社群規模也直接導致了衍生粉絲作品的數量龐大。超出書中本有的英國魔法世界,囊括全球的魔法世界觀被架構起來。
同時粉絲參與式文化強調社區及社區成員的積極參與,相較于傳統自上而下的傳播網絡以及以市場為主要考慮因素的商業傳播模式,參與式文化更有可能成為社會底層以及被忽略聲音的發聲通道。當對一文化內容的參與權被賦予這些社區成員時,發表意見和觀點的話語權也同時轉移到了他們身上。拿漫威來舉例,部分在粉絲群體中擁有一定話語權的內容生產者,在一些活動中被授權進入漫威官方的測評環節甚至創作機構,直接參與作品的修改創作。
粉絲參與式文化所帶來的獨特符號化特征,使“新商業電影”的另一大特征體現為刻意塑造的符號化信息。符號化所產生的社會認同,特別是在文化的某一參與創造過程中所產生的特殊符號,既能簡化信息的傳播,又很容易成為某一粉絲圈的群體認同標志。一些電影中的標識符號,已經成為了對應粉絲的群體暗語,在粉絲交流中成為了心照不宣的意會與幽默,粉絲們可以輕易通過這些符號辨認出相同的愛好者。這些符號有可能是縮寫、代稱,也有可能是某句經典臺詞等。而一個特殊的表現方式則是“彩蛋謎題”,在一些影片中,彩蛋猶如一種福利,“隱藏”在影片結尾的字幕表后,既像預告式的提前放送,又如同一種對堅持到片尾的觀眾感謝。而在一些影片之中,彩蛋更像某種謎題,當熟悉影片文本的粉絲發現彩蛋時,猶如一場屬于愛好者的狂歡。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接受了相同知識的粉絲獲得了一個共同的附加樂趣。彩蛋儼然成為了認真觀看影片及在此前成為某一領域粉絲群體的獎勵,這種心照不宣促使已經身處社群之中的粉絲深受激勵,也促使初階觀眾受探索彩蛋出處的欲望驅動而觀看了更多的相關作品,與之相關的參與式文化也得以隨之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