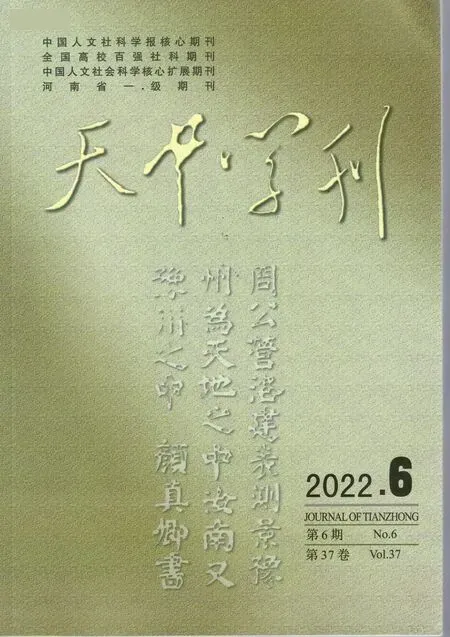《尚書·顧命、康王之誥》成文文體研究
唐旭東
《尚書·顧命、康王之誥》成文文體研究
唐旭東
(周口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周口 466001)
今文《尚書》中只有《顧命》而無《康王之誥》,《康王之誥》內容包含于《顧命》之內。孔氏古文《尚書》亦即今本《尚書》分為《顧命》與《康王之誥》。從實際來看,兩篇文獻敘事相連,的確是同一事件的連續敘述,今文《尚書》將其合二為一是有道理的。其中可以輯錄出命體文2篇,即《顧命》與《嗣位之命》;答對體文1篇,即《答〈嗣位之命〉》;訓體文1篇,即《嗣位之訓》;誥體文1篇,即《康王之誥》,共4種文體,5篇成文。就記言敘事而言,亦可將《尚書·顧命、康王之誥》視為一篇記言敘事的散文。該文詳細生動地敘述了周成王病重去世到周康王繼位這一特定歷史事件的具體經過,尤其是周康王繼位這一歷史事件的具體過程。這樣《尚書·顧命、康王之誥》就不再只是2篇文獻資料,而是5篇出于當事人創作而由史官記言的應用文和1篇敘事描寫的散文,研究先秦散文的文獻資源將得到極大開拓。
《尚書》;《顧命》;《康王之誥》;文體
《尚書·顧命、康王之誥》①具有重要的文體學史料價值,在今傳孔氏古文《尚書》中雖只有兩篇,但可以從中輯錄出5篇帶有議論性質的應用文與1篇敘事描寫的散文,這樣研究先秦散文尤其是論說文與記敘性散文的文例和文獻資源將得到開拓和增加,但目前尚未見到前人對《尚書·顧命、康王之誥》作文體研究的專門成果。茲不揣淺陋,在前哲時賢認識成果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做一探討,以就教于諸位方家。
一、命體文
所謂命體文,已見于孔安國“六體”之說。命本源于巫術咒語,為巫覡所執掌,后來歸屬于祝官,為祝官最原始的宗教職能之一。命用于人,多指帝王向臣下發布的旨令①,亦即命由命神之辭演變成帝王對臣下發布的封官、胙土、賜胤、命令之文體。在三代時,命也兼有誥、誓之功能,其與“誥”“誓”連稱,則有命令之意。戰國時期,“命”稱“令”,秦改稱為“制”,漢代作為封官之文稱為“策”,作為誥命之文則稱為“制”。由三代至魏晉,“命”體文不但名稱發生變化,體式形態也發生了不少變化。因此,《尚書》“命”體之文是后世“制”“策”之文的源頭和濫觴[1]導言50。據《文心雕龍·詔策》,命有二體:其一為封官賜胤之命,約相當于今之委任狀;其二誥命,相當于今之命令。實際上如果嚴格細分,命體文包括封官命職②、飾職③、賞賜④、遺詔⑤、令事⑥、命龜⑦等不同的類型。《尚書·顧命、康王之誥》包含命體文兩篇,即周成王所作《顧命》和周成王與周史官所作《嗣位之命》,前一篇為遺詔類文體,后一篇為傳位類文體。為了討論方便,茲引述其文并逐一分析如下:
顧命
周成王
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據《史記·周本紀》、《尚書·顧命、康王之誥》小序、《經典釋文》卷四、《尚書注疏》卷十七引馬融注及《蔡傳》,則上文為周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不任,乃命召公奭、畢公高率諸侯輔佐太子釗而作。據《說文解字》“顧”字條、《詩經·檜風·匪風》鄭《箋》、《尚書注疏》卷十七孔《傳》、《尚書注疏》卷十七與《史記集解》卷四引鄭玄注,則“顧命”為臨終而顧念身后之事,乃命重臣竭誠輔佐新王之文,有的還包含對新王誥誡之辭,后世“顧命大臣”一詞蓋當源于此。然《史記·周本紀》以太保召公奭、太師畢公高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⑧時對周康王釗的告誡之辭為《顧命》,或以為其辭末句“無壞乃高祖之寡命”之“寡命”即“顧命”⑨,此說與傳統說法不合,然亦有理,這里姑且從前說。司馬遷以為告誡周康王釗者乃召公奭、畢公高,而《尚書》本篇明載登基典禮后告誡周康王釗者乃召公奭與芮伯,茲從《尚書·顧命》[1]119。
《尚書·顧命》不但記載了周成王臨終顧命之辭,還詳細記載了周成王的喪禮和康王的即位典禮,誠如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一《周書顧命考》所言“古《禮經》既佚,后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惟此篇而已”[2],確為不可多得的寶貴史料。其中記載了周康王即位后顧命大臣對康王釗的告誡之辭和康王釗的誥辭,康王之誥辭當即《史記·周本紀》所載康王即位后遍告諸侯的所謂《康誥》,按今天文體概念來看,本篇作為康王即位典禮之一部分,有完整的篇章結構,自足為一篇完整的成文,可以單獨成篇[1]119。
據《尚書·顧命、康王之誥》,成康之際,新天子即位大典于王崩之日起算的第九天舉行而不待來年,更不待三年之喪而后即位;新天子即位大典時新王與群臣皆去喪服而改穿朝服,典禮后則換喪服繼續守喪,與后代之禮不同。《顧命》所載諸般禮儀,為當時實行之禮,亦即當時之正禮,反映了當時禮儀的實際狀況。禮有因革,后代之禮與之有異,亦屬正常,不能據后代禮儀指責本篇所載不實或當時有所失禮[1]119–120。
關于此文的創作時間,因從無將其視為單篇之文者,故對其作時之討論皆是與《尚書·顧命》一體進行的。實際上此文的具體創作時間,當在周成王末年四月甲子日(周成王崩前一日),與《嗣位之命》作于同一天,與下文《嗣位之訓》《康王之誥》并非同一天(這兩篇作于周成王崩當日起算的第九天)。當然,具體年份則因對周武王伐紂滅商年份、周武王在位年數以及周成王在位年數的認識不一致,而岐說紛紜。此文屬于《尚書》“六體”中的“命”體,屬事務文類,行政公務文族,命體文種,顧命之體。顧命,顧名思義,當指帝王臨終囑托重臣之言,內容通常包括:向重臣講述自己的病況及作顧命之原因,如蜀漢先主劉備遺詔:“朕初得疾,但下痢爾,后轉生雜病,殆不自濟”;回顧先祖創業艱難及自己繼位后恭謹守成的態度,有時候也對自己的品德和功業作一番回顧,但大多表現為謙辭,如蜀漢先主劉備遺詔:“卿父德薄,不足效也”;對顧命大臣表達希望他們盡心輔佐新君的殷切期望,有的還表達對繼位者(太子)恭謹勤奮、恢弘先祖功業之殷切期望或者其他囑托之言,如蜀漢先主劉備遺詔:“卿與丞相事,事之如父。”此類文體,后來演變成了遺詔或者傳位詔書之類文體。
《顧命》即周成王誦的顧命之辭。《尚書·顧命》于此文前有“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颒水。相被冕服,憑玉幾。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當為周史官對事件發生背景和周成王《顧命》寫作背景的介紹說明[1]120。
《顧命》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自“嗚呼!疾大漸”至“茲予審訓命汝”)載周成王對顧命大臣講述自己的病況及作顧命之原因;第二部分(自“昔君文王、武王”至“無敢昏逾”)載周成王回顧周文王、武王之功業及自己繼位后的恭謹態度;第三個部分(“今天降疾”至文末)載周成王對顧命大臣表達希望他們盡心輔佐新君的殷切期望。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周成王之《顧命》深刻表達了其對天命的敬畏和繼承發揚祖先功業的愿望,生動表現了周初最高統治者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滿懷敬畏、唯恐一朝失德痛失天命與天下的恭謹心態。
周成王之《顧命》層次清楚,語言簡潔,樸實無華,可見成王雖已經病危但頭腦仍然清楚,足見其素常為人行事之精明干練。作者擺事實、講道理,正反結合論述,說理有據有力。
嗣位之命
周成王、周史
皇后憑玉幾,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嗣位之命》創作于周成王崩前一天。但“皇后憑玉幾,道揚末命”為史官之言,當創作于周康王即位當天,亦即周成王崩當日起算的第九天。謹按:據《尚書·顧命》,周康王釗即位典禮于周成王誦崩駕之日起算的第九天舉行,地點當在天子路寢(五門的最內一門路門,亦稱畢門)之內的殯宮堂上。據禮俗,“廟”為鬼神所居之地,因成王靈柩殯于此,故路寢得臨時稱“廟”,而非宗廟⑩。《嗣位之命》宣命者為太史,姓名不詳,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太史一職世襲,則此太史或為史佚之后。《嗣位之命》當為太史轉述周成王遺命之語。
《嗣位之命》共分兩部分,“皇后憑玉幾,道揚末命”是太史敘述之辭。此下為第二層次,為太史轉述周成王命辭之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命太子釗嗣位君臨天下;叮囑太子釗繼承先王遺訓,無改于先王之道;叮囑太子釗遵循先王的政治大法;要求太子釗燮和天下[1]120。
《嗣位之命》作為新陟王(剛去世的王)命太子繼位之文,屬命體之傳位遺詔一類。“命女嗣訓,臨君周邦”即所謂傳位遺詔的命辭部分,亦即本文命題所謂《嗣位之命》的根據。作為新陟王臨終遺命,通常在發布命辭之后要對繼任者做一番叮囑,這既是永別之際的人之常情,亦為此類文體必有之內容,正所謂“言為身之文,言為心聲”也。作為當眾宣讀之命辭,該文四言句居多,具有典麗整飭之特點,亦間有多字句,使全文整飭中有跳宕,活潑而不板滯,頗富文采。
二、答對之文
答者,應答之意;對者,亦應答或回答之意,則答對之文為對他人之言(包括口頭或者書面語)之答對行為所產生的文體,屬于按行為方式分類所得到的文體名稱。吳訥《文章辨體》不列答對體?,徐師曾《文體明辨》亦不列答對體?。然作為社會生活中之人,往來應答是必有之事,亦是常有之事。當然,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場合,針對不同的事務,面對不同的應答對象,其內容、態度和語體必有所不同。《尚書·顧命、康王之誥》包含答對文1篇,即周康王釗所作《答〈嗣位之命〉》,為了討論方便,茲引述其文并分析如下:
答《嗣位之命》
周康王
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該文創作于周成王崩當日起算的第九天,亦即周康王即位當天。謹按:據《史記·周本紀》《古本竹書紀年》,周康王釗(約前1005年至約前980年在位),姬姓,名釗,周文王昌曾孫,周武王發之孫,周成王誦之子,周昭王瑕之父,周穆王滿之祖。繼位時天下已定,《古本竹書紀年》載:“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3]《顧命》載其答嗣位之命之辭和告誡諸侯之誥辭,另據《史記·周本紀》和《尚書·畢命》小序,可知其作品還有《畢命》[1]120–121。
《答〈嗣位之命〉》雖只一句話,但作為典禮儀節之完整答辭,亦自足成篇。全文康王釗用了“眇眇”與“末”表示自謙,又用反問的句式表示謙辭,意思是說,我哪有這個本事?當然,此種謙辭作為禮儀之言,亦反映了鮮明的周代前期思想文化特點。“敬忌天威”則必敬德,因周人已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觀念,則要做到“敬忌天威”,必順民欲而從之,亦即必施行德政以保民富足安康。“亂四方”乃“敬忌天威”的心理作用之下必然采取的實際政治行為和政治效果,是行德政以保民而王之事,故其答言與周公諸誥一再強調的敬畏天命、敬德保民是一致的。此后孔子的“仁政”說、孟子的“保民而王”皆與此一脈相承[1]121。
三、訓體文
“訓”,即訓導教誡之言,漢許慎《說文解字》曰:“訓,說教也。”[4]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云:“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5]1478–982順應人情事理而教導啟發之,則帝王對于臣下、父祖長輩對子孫的訓教之言為訓體。宋林之奇《尚書全解》卷十五云:“訓亦《書》之一體,有諄諄警戒之意……若其它忠臣良弼所以陳其嘉謀于上,如伊尹、傅說、周公之所陳者,無非訓也……某竊以謂‘訓’者,不必拘于篇名,凡以一言一話之出于人主之意,主于格君心之非以成其德者,皆為訓之體也。”[6]55–281則伊尹、傅說、周公之流為帝王倚重的賢輔、托孤之重臣對幼主的訓誡、規諫、教導之言皆為“訓”體。故“訓”之體,其特質為言事說理,循循善誘,長于通過訓導以引導向善,通過教誡規諫過失[1]導言41。雖然從政治地位來說,君尊臣卑,但本文作為長輩老臣(召公奭于周康王當為爺爺輩)訓誡教導晚輩新君之文,仍屬于下行文。《尚書·顧命、康王之誥》包含訓體文1篇,即召公奭與芮伯所作《嗣位之訓》。為了討論方便,茲引其文如下:
嗣位之訓
召公奭、芮伯
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張惶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嗣位之訓》創作于周成王崩當日起算的第九天,亦即周康王即位當天。謹按:《嗣位之訓》為召公奭與芮伯向周康王釗所陳訓誡之辭,進誡地點在正朝,即王朝五門由外而內第四重門應門(王朝之正門,門內即治朝)和第五重門路門?之間。據《漢書·古今人表》及顏師古注、《詩經·大雅·桑柔》鄭《箋》、孔《疏》、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三引杜預說、朱鶴齡《尚書埤傳》卷末、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閻若璩《四書釋地》、王夫之《尚書稗疏》卷四下,可知芮伯,姬姓,其名與生卒年不詳,周畿內諸侯,世在王朝,為王卿士。其封地在今陜西省大荔縣境內。風陵渡東山西省瀕河北岸之芮城蓋其后徙居地。至于“虞芮質厥成”之芮則在今陜西省隴縣之北部地區,不聞其姓,二者當非同姓。
訓辭內容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闡述文武二王以德感天、滅商建周與成王戡滅暴亂、致太平之豐功偉業,為新王樹立榜樣;第二個層次勉勵新王效法先王,恭謹從事,張惶六師,永保列祖所受上天之大命。本文雖篇幅短小,然結構完整,層次清楚,語言整齊中有跳宕,端整而不失活潑,典麗而搖曳多姿,雖為典禮應用之文,卻具有豐富鮮明的文學藝術色彩[1]121。
四、誥體文
誥為孔安國《尚書序》所言“六體”之一。誥之命名亦系從行為方式角度命名,而《康誥》篇名與文本內容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與郭店楚墓竹簡及《墨子》《孟子》《荀子》等已見稱引,《仲虺之誥》則標題及文本見于《孟子》稱引。雖《左傳》多次稱引《康誥》內容不見于今本《康誥》,但至少已經將誥視為文體名稱,可知先秦人已將誥視為文之一體。《尚書》中以“誥”名篇者多達8篇,無其名而有其實者還有十幾篇,為《尚書》中應用最廣泛的文體。《文心雕龍·詔策篇》有“誥以敷政”,說明誥是一種政治性很強的實用文體,作者可以是王,可以是公卿,由于作者和內容都有較強的普適性,因而運用較廣,保存作品最多,是《尚書》中保存最多的一類文體。綜觀《尚書》誥體諸篇,以朝會等場合對眾講話之文與對某人進行告誡教導勉勵之文為主,說明誥體的主要特質為告誡勉勵。林之奇《尚書全解》卷十四:“要之,凡曰誥者,但有所誥戒之辭。”[6]55–259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所謂“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5]1478–982亦包含殷殷囑咐、諄諄告誡之意,所言皆揭示了誥體為告誡勉勵之文的基本特質。故《漢語大詞典》釋誥:“《書》六體之一。用于告誡或勉勵。《書》有《仲虺之誥》、《洛誥》等。”[7]《尚書·顧命、康王之誥》包含誥體文1篇,即《康王之誥》。為了論述方便,茲引述其文如下:
康王之誥
周康王
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本文即《尚書·康王之誥》得名之主要內容,亦即《史記·周本紀》所謂的《康誥》。
據《史記·周本紀》與《尚書·顧命、康王之誥》小序,本文為周康王釗即位之初詔告諸侯之辭,創作于周成王崩當日起算的第九天,亦即周康王即位當天,作誥地點亦在正朝。唯周公既前作《康誥》,此不宜如《史記》復稱《康誥》,當依《尚書·顧命、康王之誥》小序以“《康王之誥》”為妥[1]121。
《康王之誥》自開頭至“報誥”為開頭語和引言;承上起至“用端命于上帝”為正文第一層次,以歷史事實說明以文王、武王之圣德,猶有忠勇之士保乂王家;至末為第二層次,希望各路諸侯效法先祖,竭忠盡力輔佐先王。全文體現了周康王釗作為新繼位之王希望各位諸侯盡忠輔佐自己的熱切誠懇之心[1]121。
五、記言敘事文
《尚書·顧命、康王之誥》除了可以輯錄出基于不同的行為方式而產生的命、答對、訓、誥4體之文5篇,還可以視為一篇記言敘事文。前所論數篇,不過是對從《尚書·顧命、康王之誥》中輯錄出的幾篇應用文體加以分析,正如劉知幾《史通·外篇·申左》所言:“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征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8]劉氏敏銳地認識到《左氏春秋》所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等為左丘明編次“當時國史已有成文”這一事實,也就是說《左傳》所記之“言”,有許多為左丘明撰寫《左氏春秋》時所采用的前人現成的文章[1]總序1。準之于《尚書》,可知其中多篇亦史官采取已有成文史料,加上自己了解的史實連綴成篇,或于篇首加敘述性文字以為背景介紹,如《西伯戡黎》《多士》等;或于篇末加敘述性文字以為記言之補充,如《洛誥》等。《顧命》篇必有關于周成王臨終顧命之辭,周康王即位時太史代為宣讀的命周康王釗繼位之命辭,周康王繼位典禮后召公奭與芮伯所作訓辭與周康王誥天下諸侯之誥辭,這些為負責記言之史官所錄。史官采用這些真實可靠的文獻,加上負責記事的史官所記錄的周成王崩駕到周康王登基諸事,連綴成篇。故《尚書·顧命、康王之誥》原本應為一個整體,除了前面幾篇析出的應用文,其他文字應為周王朝史官所記所作,屬于孔安國和孔穎達沒有關注到的“記”體,為《尚書》中少數的長篇記敘文之一。為了討論方便,茲引述其文并分析如下:
顧命
周史官、周成王、召公奭、芮伯、周康王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颒水,相被冕服,憑玉幾。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弊,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作為一種敘述性或曰記敘性文體,本文敘事詳細、結構完足,具體生動地表現了周成王之崩到周康王即位之過程,為我們展現了西周前期先王崩駕到新王登基的儀式和禮制,為后人研究西周前期禮儀制度提供了詳實可靠的史料,為我們展現了不同于后代帝王即位典禮的歷史面貌。
總的來說,《尚書·顧命、康王之誥》中包含命、答對、訓、誥4體之文5篇,皆為基于行為方式而產生文體和篇章,皆帶有口頭議論文的要素、性質和特征。就表達方式而言,《尚書·顧命、康王之誥》皆用語言描寫、行為動作描寫和場面描寫來記言敘事,故亦可將《尚書·顧命、康王之誥》視為一篇記言敘事的散文。對《尚書·顧命、康王之誥》做文體分析,可以給學界提供研究先秦文獻一個新的切入點,使我們得以從這一角度認識西周初期各體散文的創作水平和創作狀況,進而發現周初人們已經在論說文與記敘描寫類文體寫作方面進行了很有意思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創作經驗,足以給后人提供一些可資借鑒的啟示。而且,通過對《尚書·顧命、康王之誥》的文體分析,我們會驚喜地發現研究先秦散文的文獻資源可以得到開拓和增加。當我們以散文的眼光審視《尚書·顧命、康王之誥》的時候,在我們的眼中就不再只是《尚書·顧命、康王之誥》兩篇文獻資料,而是5篇帶有議論性質和1篇帶有記言敘事描寫性質的文例以及文獻資料了。如果以這樣的眼光和視角來看待其他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我們還會有多少這樣的令人驚喜的發現呢?這就是本文所做探索的啟發性和示范性意義。
① 漢今文《尚書·顧命》包含今本《尚書》之《顧命》與《康王之誥》,然漢今文《尚書》只存零星殘文。故此用今傳本孔氏古文《尚書》之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篇題亦采用今本孔氏古文《尚書》之名。
② “授官錫胤”之文,漢代稱“策書”,相當于后世的任命書、委任狀,其中封官之命如《冏命》《君陳》《畢命》等、封建之命(封邦建國,冊命諸侯)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等。
③ 對官員履行職責提出具體的要求和說明,如《說命上》“朝夕納誨”至“其惟有終”等。
④ 帝王或國君賞賜有功諸侯或功臣,如《文侯之命》等。
⑤ 帝王對輔政大臣之遺囑,有對重臣盡心輔佐新王的叮囑,如《尚書·顧命》所載周成王駕崩前一天對重臣的所做對重臣盡心輔佐新王的講話;有對新王繼位的命令,如《尚書·顧命》所載史官宣讀的周成王傳位之命。
⑥ 指令下級做某事之文,《尚書》無具體文例,然《召誥》“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乃周公令庶殷興建雒邑之文,說明當時有此一類令事之文。此類文后來從“命”中分化,專名為“令”,秦漢更曰“制”。
⑦ 龜卜時刻于龜甲上的說明情況及要卜問的問題的文體,如《大誥》自“有大艱于西土”至“我有大事。休?”一段。
⑧ 按:《史記》有誤,當為路寢殯宮之堂上,廟為鬼神所居之地,因成王靈柩殯于此,故得臨時稱“廟”
⑨ “顧”通“嘏”ɡǔ,意為大、光。
⑩ 在路門之外,在五門由外而內第三道門雉門和第四道門應門之間。
? 其中有“問對”一體,其定義曰:“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實際上是有問有答之文體,與這里所說的答對不是一回事。
? 其中亦有“問對”一體,其定義曰:“按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邃古篇》之類是也(今并不錄);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論(宋劉敞有《諭客》,今不錄),曰答,曰應(宋柳開有《應責》,今不錄),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于《左傳》、《史》、《漢》諸書。后人仿之,乃設詞以見志,于是有問對之文;而反復縱橫,真可以舒憤郁而通意慮,蓋文之不可闕者也,故采數首列之。”其實徐師曾是從后世設為問答之類文學作品而言的,其溯源至《左傳》《史》《漢》諸書,猶未到位。蓋《尚書》載帝堯向群臣詢問可用之臣,眾臣推薦丹朱、共工、鯀、舜之言亦答對之言,《逸周書》更載多篇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等疑問,而周公旦作答之辭亦答對之文。但《尚書》等還有非答問之辭,而是對訓、誥、命之辭作答之文,非盡可以以“問對”稱之。
? 亦稱“畢門”。
[1] 唐旭東.今文尚書文系年注析[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2] 王國維.觀堂集林[M].北京:中華書局,1959:50.
[3] 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4] 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51.
[5]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M]//永瑢,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6.
[6] 林之奇.尚書全解[M]//永瑢,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6.
[7]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K].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5:11–230.
[8] 劉知幾.史通[M].白云,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656.
I269.6
A
1006–5261(2022)06–0075–08
2022-03-08
國家社科基金2016年度一般項目(16BZW033)
唐旭東(1970―),男,山東煙臺棲霞人,編審,博士。
〔責任編輯 楊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