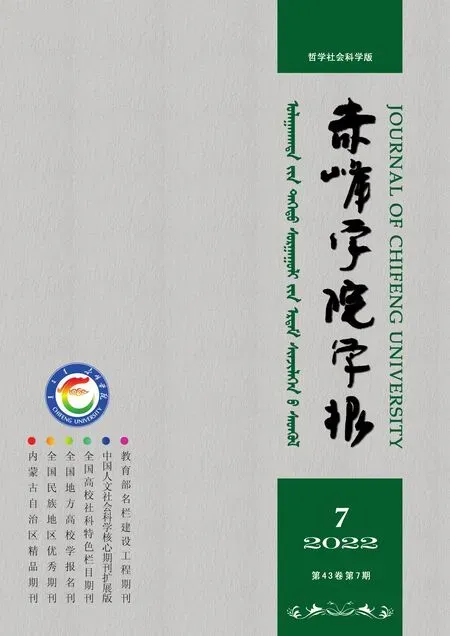新世紀以來紅山文化分期研究述評
曹彩霞
(赤峰學院,內蒙古 赤峰 024000)
任何一種考古學文化都在時間與空間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分期表述其時間的差異,即考古學文化的歷史過程的持續和連貫[1]。眾所周知,紅山文化的年代跨度長達1500年,在如此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中,紅山文化必然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階段性差異。而對該文化進行系統的分期研究,不但可以從歷時性的角度揭示該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不同時段特點,亦可從共時性的角度窺見該文化與周鄰諸考古學文化的互動過程。更重要的是,文化分期這類基礎性研究是諸如生業、宗教與社會等方面專題研究的前提,對其進行精細且準確的研究可以將各項專題研究置于一個比較堅實的平臺之上。因此,紅山文化的分期研究很早就受到學界的重視。進入21世紀后,這方面的研究依然在有條不紊地開展著,在此筆者將從紅山文化整體分期研究與單個紅山文化遺址個案分期研究兩方面擇要概述。
一、紅山文化的整體分期研究
總結21世紀以來的紅山文化分期研究成果,必須進一步向前追溯此前階段這一課題研究的基本情況,從而深入認識21世紀這一課題持續開展的現實基礎。
1989年,楊虎先生將紅山文化統一分為以興隆洼文化F133 遺存、西水泉類型和東山嘴類型為代表的三個階段,并就各個階段的時代特點作了扼要的分析,將紅山文化的絕對年代劃定為距今6500—5000年[2]。這是一項具有奠基性意義的研究成果,無論是分期方案、年代跨度還是在此基礎上對于紅山文化源流關系的解讀,大體都得到了后來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的印證,因而成為紅山文化研究史上的經典文獻。1991年,張星德先生以經過正式發掘的遺址為骨干,從層位關系出發,對若干處典型遺址進行了細致分析,排出了數種常見器物的演變序列。在此基礎之上將紅山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指出這三期分別與后岡一期文化、廟底溝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相當[3]。她將當時已經發表的材料進行了全面整合分析,分期刻度與年代等與楊虎先生大同小異,但論證過程更為詳細,特別是從單位出發進行的分析更為全面。同時由分期結果出發,深刻揭示出紅山文化分布范圍的動態變化及其與黃河流域相關考古學文化的互動態勢,可謂既詳又全。總之,在21世紀以前,上述兩項研究代表了20世紀紅山文化分期研究的前沿,為下一階段這一課題的深入探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具有引領性與示范性。
2004年,趙賓福先生基于既有的研究成果,將紅山文化整合為早晚兩期,即“西水泉期”和“東山嘴期”,考慮到過去多有人述及的興隆洼遺址F133和F106 發表材料較少,故未做進一步討論[4]。該文對于紅山文化的分期雖然是綱領性的,但有效地澄清了以往將紅山文化的“分期”與“類型”混淆的現象。
2008年,陳國慶先生以最新發表的層位關系較好的牛河梁遺址和白音長汗遺址為突破口,將已有的20 余處紅山文化遺址(包括墓葬)材料進行了再分期,通過橫向與縱向類比,最終劃分為四個階段[5],標志著紅山文化分期研究進一步精細化。
2011年,索秀芬先生在楊虎先生、朱延平先生及自己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紅山文化劃分為四期五段。提出紅山文化第一期的年代處于距今6700—6500年,早于通常所認為的紅山文化年代上限[6]。
鑒于已有的紅山文化年代和階段劃分研究論證不夠深入、細致的現實情況,趙賓福先生于2012年再次撰文[7]重新審視和論證紅山文化的發展階段問題。他首先從出土遺存較多、層位關系明確的牛河梁遺址和西水泉遺址的分組出發,將兩個遺址的分組結果進行了對應關系分析。然后以此為標尺,基于陶器器型與紋飾方面的共性與差異,對其他遺址出土的紅山文化遺存進行了逐一比較分析,判別其組別和年代,進而將紅山文化劃分為三個大的發展階段。同時,通過與黃河流域考古學文化的對比,推定了這三個階段的絕對年代。該文論證有力,邏輯嚴密,循序漸進,是新世紀以來紅山文化分期研究的一篇力作,為該課題的探索搭建了一個新的平臺,其分析思路與研究范式對于此類問題的研究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2014年,趙賓福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杜戰偉所撰寫的學位論文《中國東北南部地區新石器文化的時空框架與譜系格局研究》,也涉及了紅山文化的分期問題。該文以上述趙賓福先生的文章為基礎,對最新發表的近十處紅山文化遺址出土材料做了補充分析[8]。二文對于紅山文化分期刻度與絕對年代的把握基本一致,前后呼應,支撐起紅山文化分期研究的整體架構,稱之為姊妹篇當無問題。
2015年,劉國祥先生在其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紅山文化研究》中同樣將紅山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每期又進一步細分為早、晚兩段,即三大期六小段[9]。相比于原有認識,這一分期結果可謂十分精細,標志著該問題的研究又邁入一個新的階段。同年底,該文在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10],成為紅山文化綜合研究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二、紅山文化遺址個案分期研究
遺址是由遺跡單位所組成的,而考古學文化又是由有機聯系的若干處遺址出土遺存所構成的,遺址的分期及不同遺址期別的銜接與對應構成了考古學文化分期研究的基礎。就21世紀以來的紅山文化研究而言,既有基于文化整體的宏觀分期,又有基于單個遺址的微觀分期,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表里,共同推動著紅山文化基礎研究的深入開展。
在已公布材料的紅山文化遺址中,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白音長汗遺址以及遼寧省朝陽市小東山遺址、牛河梁遺址出土遺存較多,層位關系復雜,因而這幾處遺址出土紅山文化遺存的分期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既而出現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2004年,索秀芬先生基于白音長汗遺址一手發掘材料,通過對層位關系和陶器演變線索的分析,將該遺址紅山文化遺存分為二期三段[11],為西拉木倫河以北地區紅山文化的發展過程研究確立了一個可信的時間坐標。
2010年,張星德先生將小東山遺址出土的紅山文化遺存分為三個組合,指出這三個組合實際上具有年代早晚關系的斷代意義[12]。同年,趙賓福先生也就這一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他梳理出五組具有分期意義的層位關系,通過區分與合并最后劃分為早晚兩期,指出小東山遺址的這兩期整體上相當于之前劃分的“西水泉期”,同時,這兩期又將“西水泉期”細化為兩個階段[13],從而為2012年劃分的紅山文化早中晚三期做好了鋪墊。
如果說紅山文化是中國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最為著名的考古學文化,那么牛河梁遺址則無疑是紅山文化中最為重要的遺址。該遺址出土遺存十分豐富,遺跡間的疊壓打破關系也非常復雜,從而為分期研究創造了極佳的條件。特別是伴隨著牛河梁遺址發掘報告的正式出版[14],相關研究成果近年來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
2007年,索秀芬先生從牛河梁遺址第五、二、十六地點出發,通過典型遺物與遺跡特征的比較,將該遺址紅山文化遺存分為三期,其中將第一期劃分為早期,第二、三期劃分為晚期。在此基礎上長時段地分析了牛河梁遺址中紅山文化先民活動內容的變化情況,并以此為窗口窺探了紅山文化社會的演進狀況[15]。這是將考古學文化基礎研究與專題研究有機融合的典范,既有形而下的根基,又有形而上的高度。
2016年,趙賓福先生將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遺存分為兩期三段。三段由早到晚分別相當于牛河梁遺址發掘報告所劃分的下層遺存、下層積石冢階段遺存、上層積石冢階段遺存,進而指出這三段分別屬于紅山文化的早、中、晚期。并提出牛河梁遺址的早期屬于“居址”,晚期代表“墓地”發展的兩個階段[16]。這一觀點的提出為紅山文化的社會復原研究搭建了一個可靠的時間框架,貢獻了許多新的學術意見。
同年,王芬先生專文探討了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遺存的分期與年代問題。通過層位關系和類型學對比將積石冢分為兩期四段,早期的一、二段相當于報告所分的下層積石冢和上層積石冢N2Z4B 所代表的階段,晚期的三段相當于上層積石冢N2Z4A 所代表的階段,晚期的四段是第一地點所代表的階段。同時,將牛河梁遺址積石冢的絕對年代判定在距今5700—5100年之間[17]。牛河梁遺址的發掘者認為,第一地點的年代可能處于下層積石冢與上層積石冢之間,王芬則認為前者晚于上層積石冢,這是一種較為新穎的理解。
2019 和2021年,高云逸通過陶器及其所在遺跡間的疊壓打破與共存關系,明確提出著名的牛河梁遺址“女神廟”屬于該遺址下層積石冢階段遺存,在紅山文化的分期框架中處于中期階段,而非學界通常所認為的紅山文化晚期,并就這一遺跡期別調整對于紅山文化文明化進程研究的意義做了較為詳細的闡述[18]。同時,他比較了牛河梁遺址的分段結果,首次提出東山嘴遺址存在年代相當于牛河梁遺址下層積石冢階段的遺存,該遺址出土的紅山文化遺存至少可細分為兩個階段[19]。這些都是基于實事求是的分析所提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認識。
2020年,郭明先生依據層位關系遺跡石棺的砌筑方式和死者頭向的差異與變化,將牛河梁遺址上層積石冢階段墓葬細分為五個階段[20]。這是迄今所知牛河梁遺址上層積石冢階段墓葬最為精細的分期方案,為紅山文化晚期階段社會分化與人群關系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細致的時間框架。
除紅山文化的整體分期以及單個遺址的分期研究以外,還有學者就紅山文化的某一期進行了更為精微的分期探索。例如,2015年張星德先生將紅山文化早期即其所謂的“后岡期紅山文化”進一步細分為三期,并對其與后岡一期文化的階段性特點作了較為詳細的比較[21]。2018年,她又將牛河梁遺址的“西陰期紅山文化”陶器細分為三期[22]。這些都是史無前例的嘗試,率先將紅山文化的分期研究細化到了分子的水平。
三、結語
縱觀21世紀以來紅山文化分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我們可以發現,這項研究越來越朝著精細化的方向前進,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之所以會形成這種現象,主要是主客觀兩方面因素的驅動。客觀方面,新的材料不斷涌現,可供分期研究利用的層位關系隨之逐漸增加,這是分期研究漸趨細化的必要條件。主觀方面,聚落考古及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這種對于共時性要求極高的課題的深入開展,亟待我們建立起一個精確且可靠的年代框架。已有的紅山文化分期研究成果盡管已經支撐各項專題研究取得了諸多新的進展,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紅山文化的分期研究仍有許多需要細化與完善的空間。此外,老哈河至西拉木倫河流域缺少紅山文化晚期階段遺存,也在制約著當前的紅山文化研究,這些也是急需考古工作填補的地域與時代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