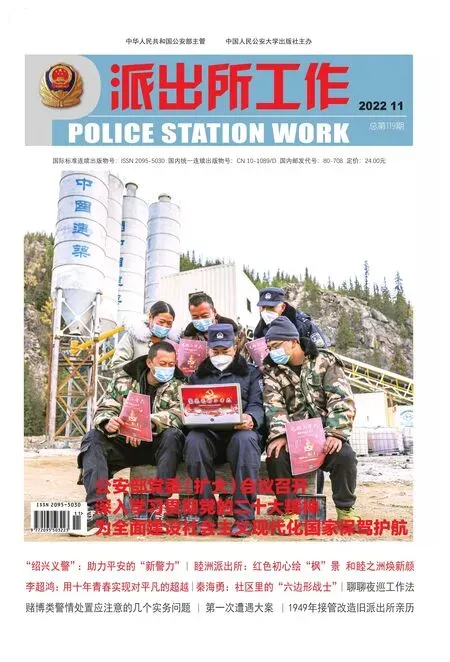老警搭檔
文/米可
調解室內,王志龍抱著胳膊,笑而不語。他的兩側坐著兩位大媽,盛裝華服已不足以形容二位爭奇斗艷的姿態。此時正是“中場休戰”時刻,易建奎借機下了樓,和搭檔使了個眼色。王志龍會意,起身出了調解室,在兩位大媽的視線盲區“吵”了起來。
易建奎:還拖著干嘛,直接拘了吧。
王志龍:兩位都六十多歲了,不值當。
易建奎:為了搶男舞伴,就值當啦?
王志龍:我也是這么說吶,總得顧及子女的臉面。
易建奎:老王,辦案是有期限的,所長可盯著吶。
王志龍:都是老相識了,能把矛盾解開,總比結下梁子好。
易建奎:我等不了你了。哎!小費,準備打印拘留手續。
易建奎轉身上樓,皮鞋踩得樓梯隆隆作響,耳朵卻豎著。半分鐘不到,聽到兩位大媽沖出調解室,央求王志龍愿意調解。他挺起老腰,“嘿嘿”一笑。
去年年末,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八公山分局落實“放管服”便民利民舉措,強化婚戀、鄰里、債務等疑難復雜矛盾糾紛的調處工作,邀請一批群眾基礎好、調解經驗豐富的老同志成立了老警調解工作隊。王志龍和易建奎已年近退休,雖然電腦玩不轉,但在群眾中可謂是如魚得水,便搭檔組成了一支工作隊,在新莊孜派出所開展矛盾調解工作。王志龍個頭不高,成天笑瞇瞇的,褶子里透著一份親切。易建奎原是分局籃球隊中鋒,大高個,不怒自威。調解矛盾時,兩人經常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解開了許多群眾之間的“老疙瘩”。
這天,所長交給兩位老警一項調解任務。矛盾雙方是一對年逾七旬的叔嫂。前些日子,在社區舉辦的“老礦區”懷舊展上,老嫂子不顧工作人員勸阻,將一盞寫了小叔子名字的豆油燈強行帶回家中,還威脅要與豆油燈同歸于盡。老嫂子搶豆油燈,不圖財,定是心里有怨氣。王志龍和易建奎開始查看過往警情記錄,發現老嫂子和小叔子之間的積怨,和他們額上的皺紋一樣密、一樣深。
老嫂子操持家務,辛勞半生,別說是丈夫和公婆,就連小叔子也沒少跟著享福。上天不仁,不僅沒有賜予老嫂子兒女,又早早帶走了丈夫,只留她獨自終老。上天仁慈,小叔子開花結果,子子孫孫一大家子。兩相對照,老嫂子愈發孤僻和敏感。在丈夫的葬禮上,老嫂子見小叔子一大家子忙里忙外,既感悲涼,又自覺低人一等,心生妒意。不久,小叔子帶子女好心探望,卻被老嫂子以“看笑話”為由罵出了家門。自此,兩家結下了梁子。被老嫂子毒舌次數多了,小叔子家里的后生們亦反唇相譏。話趕話,矛盾便“壘起了沙袋”,越積越深。
老嫂子獨居一戶小院。這天傍晚,王志龍打頭陣,親切喊了聲大媽。剛推開院門,就見老嫂子舉著那盞破舊的豆油燈。王志龍滿臉堆笑,“大媽,你舉著個油燈做啥?”老嫂子繃著臉,“照一照你們是好人還是壞人。”王志龍說,“那也得把燈修好啊,你看這燈捻子都沒了。”老嫂子哼了一聲,“反正我要帶著它一起進棺材。”易建奎虎著臉說,“這么寶貴的東西,毀了多可惜。”或許是易建奎高大的身板嚇到了老嫂子,只見她突然將油燈舉過頭頂,厲聲道,“你們要是搶,我就把它砸碎。”見狀,王志龍和易建奎只得退出小院。
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王志龍和易建奎卻是極有耐心。加上兩位老警都是當地“土著”,很快便從老街坊那兒,弄清了豆油燈的權屬問題,還聽說了豆油燈背后的一段往事。
王志龍和易建奎分頭行動,將這段往事講給小叔子家的一眾小輩,一點點瓦解了他們“同仇敵愾”的氛圍,最終促成了小叔子的思想松動,自覺日后沒臉帶著這份仇恨,去見已逝的大哥。
七月即墨,火燒云在天邊翻滾,映紅了每一個行人的臉頰。在王志龍和易建奎的陪同下,小叔子來到老嫂子小院外。看到“仇人”上門,老嫂子擲來水舀、掃帚,都被易建奎高接低擋擋開了。王志龍捅了捅小叔子的腰眼,最終小叔子艱難地喊了聲“嫂子”。
正是這一聲“嫂子”,讓小院立時安靜下來。小叔子鼓起勇氣,開始重述王志龍和易建奎聽說的那段往事:“這盞豆油燈,是咱媽給咱爸置辦的,花了家里不少積蓄。解放前,咱爸舉著這盞燈,穿煤場,爬矸石山,腳下就沒有踩空過。解放后,咱爸退了休,大哥接了班。礦上雖然通了電,但到了夜里,老房子那一片還很黑。咱爸就舉著豆油燈,在巷口等下夜班的大哥。再后來,我上山下鄉去了云南,咱爸又把這盞豆油燈送給了我。”
小叔子沉默著,目光發虛,像是回想那段被豆油燈照亮的日子,半晌才又開口:“咱爸去世時,我和大哥點亮了豆油燈,油燈一共燒了三天三夜,一直把燈捻子燒斷,才被珍藏起來。如今,我看到了這盞燈,就會想起咱爸,想起大哥,想起許多事情。”
小叔子低頭絮叨著,不像是和大嫂說話,倒像是在自言自語。直到王志龍拍了拍他的肩膀,才猛然發現老嫂子正站在他的身前,手里捧著那盞擦拭一新的豆油燈。兩位老人在沉默和局促中,相對而立。
易建奎見狀,從老嫂子手中接過了豆油燈,翻轉著看了一圈說道:“接上捻子,沒準還能亮。”王志龍也接過話頭:“把咱們心里都照得亮堂堂的。”
說完,王志龍偷眼瞥向老嫂子,只見落日的余暉照在了老嫂子的臉上,讓那一道道皺紋不再灰暗,而是泛起了云卷云舒般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