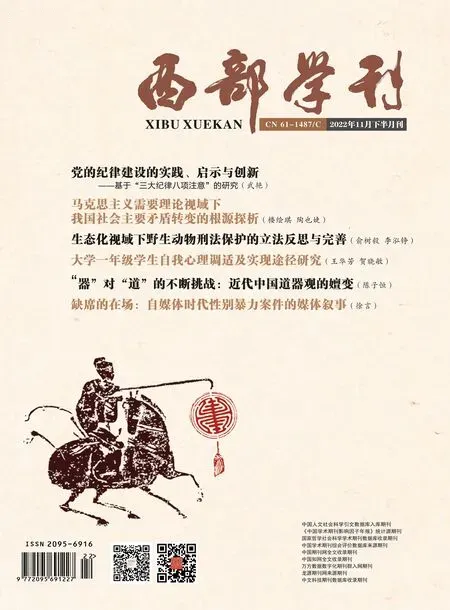大數據時代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的嬗變與反思
劉東宇
21世紀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推進了社會生產力的變革。大數據技術的廣泛應用,致使眾多的勞動者卷入數據信息的生產過程中,重塑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數字資本主義成為了當今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形式,生產勞動也衍生出更具抽象性的數字勞動。無處不在的數據信息充斥著生活的各方面,相較于傳統勞動,數字勞動產生了新的異化形式,對于勞動價值的滲透手段也更為隱蔽,追尋人類解放的道路也更加復雜,本文擬就諸類現象進行探討,深化理論創新的現實價值與解決路徑的切實可行性。
一、大數據時代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的嬗變
在大數據時代,私有制與算法締造的數字勞動淡化了異化勞動與自由的對立關系,其多樣化的勞動形式縱使趨利的數字平臺順利嫁接在生活的各方面。一方面,數字勞動能解決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煩惱,甚至可以勝任許多高危的工作,加快產業轉型升級,釋放更多的創新價值。另一方面,這也讓更多人面臨失業的風險,人們在無形的網絡中依舊遭受資本的剝削,人的本質仍然發生異化。辯證看待當下的異化勞動,需要理性認識和科學應對,讓科技進步成為人類社會發展變革的內驅力。
(一)資本對勞動的覬覦
大數據時代下的高新科技產品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所產生的數據實際上都匯聚到了背后潛藏的平臺中。“人工智能技術奏響了產業革命的號角,社會生產方式隨之革故鼎新,這不光是物質與制度層面的轉型升級,人們的思想同樣在接受科技的洗禮。”[1]人們享受使用科技提供的便利時,產生的數據被資本平臺壟斷,在無形中壓榨著人們的勞動,讓勞動產品與自身分離,成為資本家們牟利的工具。
1.主體性地位剝奪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在京發布的第5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74.4%,抖音短視頻用戶規模為8.88億,網民人均單日使用時長為125分鐘。馬克思認為人的自由是用價值尺度體現人的需要和物的屬人關系,而大眾媒體通過信息流的強輸出使得人們的大腦已無法及時作出甄別,被動地任由一堆天花亂墜的數據灌輸。打開抖音,嘈雜的音樂與詼諧的內容充斥著大腦,我們不由自主地被短視頻占據了時間,大腦喪失了思考的能力,只是機械式地滑動手指,收獲感官的刺激,樂此不疲。主觀能動性淪陷在海量信息中,對信息的價值評判失去了衡量標準,人仿佛成了一副來者不拒的空殼,而眼前的智能設備才是意識的來源,雙眼一閉,感受到的只有對虛擬與現實違和的不知所措。
2.數字平臺對勞動價值的竊取
數字平臺本應提高生產的效率或者替代人們的勞動,從而達到減輕人民負擔的理想效果,人們所需要投入的往往只是情感、時間或者想法。這些用非物質要素就能換取到勞動成果,看似實現了人們類本質的復歸,可正是人們隨時隨地都能進行的數據勞動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概念,人們可以隨時為數字平臺勞動,而數字平臺卻沒有支付他們額外的工資,這無疑是一種更為隱蔽的剝削方式。智能設備解放了人類的體力勞動,勞動的形式愈發不受主體限制,間接地加劇了資本家對數字勞動者剩余價值的掠奪。襯以信息化的資本細膩地掩蓋了對數字勞動者的剝削,冠以便捷高效的數字平臺,給勞動者們戴上了無形的枷鎖,讓他們不自知將數據勞動時間延長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非雇用的前提下自覺地生產數據,勞動價值悄然轉移。
3.數字化背景下的大眾失業恐慌
科技進步帶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就業人員的分配結構與往昔迥然不同。“人工智能將人腦獨立于身體之外,從而擺脫了個人能力的不足或是情感的妥協,通過多元化的思維疊加產生遠超個體的智力成果。”[2]人工智能投入勞動密集型產業,冗余的從業者慘遭淘汰,而在面臨失業風險時仍需為機器所生產的物品買賬。就業市場結構在契合科技創新的同時,對崗位的擠壓難免會令人擔憂。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發布的就業預測相關報告中稱,隨著科技的進步,未來全球大概有3.75億人口將面臨重新就業,其中中國占1億。人們對失業的恐慌反映出現代科技對人們就業的沖擊,是一種對現實的擔憂以及對未來的迷茫。新潮流的出現是驚世駭俗的,但它代替舊事物的過程是緩慢的,社會需要時間來調整并適應生產力的變革。
(二)異化勞動的隱蔽性多元化
資本主義數字化的背景下,核心技術被少數資本家占據,成為斂財的新型工具,進一步強化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現代化既是一種自主的喜悅,又是無家可歸的迷失。自主彰顯的是自我擔當,而獨自擔當做出選擇的后果卻又是無所依托,逃避自由。”[3]從生產數據時的無感,到數字平臺中勞資關系的潛藏,都難以察覺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甚至誤以為資本的積累依賴于先進的技術,而忽視了數字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
1.數字勞動的非物質性
在大數據時代下,人們在虛擬世界中不斷地豐富著自己的非物質形象,通過與他人的社交建立了一種超越現實的聯系,同時也在進行著網絡上的數字勞動,生產著大量的數據。“非物質產品在短時間內海量斂財,而這些財富卻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4]人們把時間精力花費在游戲廠商運用算法與模型構建的體系內,按照設計好的路徑操作,在虛構的鏡花水月中找尋充實感與滿足感,實際上也在為運營商創造著數據,這對系統的優化以及捕捉玩家的偏好提供了量化指標。人們在游戲中向運營商反映了自身的需求以及價值導向,運營商就可以針對這些“弱點”有的放矢,設計出更具吸引力的機制,讓體驗者更易淪陷到游戲中。數據生產與消費的過程都處于用戶自發的非物質勞動中,其中的異化關系看似不會對用戶產生任何不良影響,所耗費的時間精力也不易衡量,其中的壓榨更具隱蔽性。
2.數據產銷融合化
線上交易已不再是單純的單向買賣,生產與消費的劇情應允同臺出演。“數字平臺通過價值引導,沖淡了作為數字勞工的被剝奪感,讓人們的感官與時間被數字平臺加持時心甘情愿奉上產生的數據。”[5]人們在拼多多上為了獲得更優惠的價格,不斷地分享鏈接給好友參與砍價,這正是平臺商家利用了大眾的認知偏差,以微薄的讓利換來代勞的宣傳。每一次邀請都產生了信息傳播,一旦獲得了群體的認同與情感價值的附加,便能很快在網絡間推廣,拼多多借此拓寬了商品的受眾面,也間接促進了銷量增長。人們在獲得商品折扣的同時,同樣充當了免費勞動力的角色,只是產銷雙方的利益著眼點有所區別,大眾圍繞既定利益考慮,而電商平臺則是致力于長遠的推銷布局。
二、對大數據時代數字勞動異化的反思
回顧過往,人類的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是對主體自由解放的推進。技術的革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質的飛躍,獲得了更多屬于自己的自由時間,也就是在勞動之外所剩余的可由自己支配的時間。人工智能對勞動的替代,讓人們有更充沛的自由時間去追尋自身的需求,也預留了時間去校正自身與智能設備的錯誤定位,重新審視自身的真正需求,激發全面發展的潛能。
(一)重審人機關系內核
隨著人機關系聯絡日益密切,人工智能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現了智能機器生產的倫理問題和基于智能算法的審核問題,人工智能的道德屬性尤為重要。
倫理道德上,需要凝聚社會共識和集體信念。一方面,要開展面向社會大眾的思想宣傳,針對當下人工智能的熱點問題,采取正面的宣傳引導,積極引領人民群眾形成良好的社會心理。另一方面,技術研究群體應加強人工智能倫理的創新型研究,在遵循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科學預判未來發展趨勢,豐富大數據時代的倫理體系,賦予機器符合人類需求的道德評判指標,保障社會生活的安全穩定。
智能算法的審核尚處于探索階段,部分算法的功能還不健全,難免會像人類一樣存在著偏見與誤判,對于多語義與概念的模糊定性往往容易造成漏檢與誤報。對此,算法的審核流程應注重社會效益,盡快建立完善相關的法律審查機制,在算法無法精確識別的情況下,支持人工介入處理,讓機器輔佐人工,共同營造清爽的互聯網環境。“任何階段的人類社會都會存在相對較低層次的勞動,對此人工智能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代替繁重且被動的工作,使人類最大程度自主選擇形成的社會分工。”[6]隨著人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逐漸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人們將以一種嶄新的方式實現自由全面的解放。
(二)重構個人社會主體
數據無所不及的覆蓋面和精確性時常讓人深信不疑,孔子曾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人們信奉用數據堆砌的言說,實則是仰仗數據背后的效益。通過大數據精準預測的手段,節省了因信息偏差而造成的資源浪費,市場的資源配置也更為靈活。實現了生產與消費的良性互動,產品的供給更符合人們所需,消費觀念也更加趨于理性。數字勞動帶來的價值創新昭示著指標化的數據需要創新智用,創新型勞動賦予的新的價值將會推動社會需求的改良,最終實現社會資本的優良運作。
數字勞動價值的創新讓自我主體的確證不再是通過對物的占有來體現,不再過度注重產品私有的歸屬感,而是更加關注產品的功能,更加傾向于共享經濟和適度消費。這是以滿足人們需要的使用價值的創新,是更能彰顯人生價值的有用勞動。“勞動的有用性,是包含實現人自身內在價值的權利,勞動過程有助于人的全面發展,勞動成果能夠回報社會,是光榮踐行人類本質的活動。”[7]勞動價值的創新是發自勞動主體內在需求的優化,是人對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做出的蛻變。數字勞動價值的創新在于重新界定人本身的需求,而技術的創新在于對現存的生產力問題提出改良方案。用理性科學的方法處理二者的關系,就需要以提高主體的價值為最終目標,既要重視從主體的新的需求中挖掘潛在的經濟價值,彰顯主體價值決策的優越性,同時又要兼顧技術的突破,為社會的接續發展錦上添花。
(三)重塑企業價值理性
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特征具有社會性。要想揚棄大數據時代的異化關系,企業經營者必須用價值理性統御一味追求功利的工具理性,重塑企業價值觀。
隨著數據躍升為生產要素之一,在數字化經濟時代,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決策依據愈發離不開對數據資源的價值提煉。在要素市場中,市場與消費者的供需關系轉換,消費者成為了要素的貢獻者,而企業則成為了要素的需求者,以此來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將更切合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產品投放到商品市場中。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在堅持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勞動收入的穩步增長。這便需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契合,將所有制形式創新,推動數據要素資本化。對于已實現數據價值且能帶來可觀未來收益的數據信息,企業可以將其剩余價值轉化為股份亦或是利潤的分紅,從而達到數據要素保值增值的經濟屬性。“勞動力不僅僅是商品,它同樣能作為資本,在獲得商品價格酬勞時,也能取得充當勞動者股份的紅利。”[8]數據要素資本化是群策群力的褒獎,也是釋放要素內在價值活力,提升數據利用效率與所有者權益的顯現。在數據總量呈指數型增長的時代,數據不應因覆裹假面而被束之高閣,而應是一座座亟待挖掘探析的金山銀山,是賦能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可再生新能源”,更是規劃國家前瞻性布局的幕僚高參。
(四)重鑄社會高效治理
現今資本主義出現的異化關系仍是資本和勞動的沖突,產生的社會矛盾也為社會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時代存在的悖論并不是一個關乎技術的問題,而是關乎制度的問題。“在全新的信息化社會語境下,異化由物質勞動轉變成數字勞動,在虛擬與現實的交錯中狡黠地實現了勞資關系的剝削,這仍吻合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的批判邏輯。”[9]唯有將大數據應用于社會主義的大環境下,讓大數據創造的財富成為人們的共同財富,方可抵達共同富裕的理想社會。
實現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既要考慮數據勞動的成果不被他人無償占有,又要顧及通過勞動能讓人們切實獲得自己想要的生活,這就需要將數據確權。通過明晰數據所有權與經營權,加強對數據的價值引導與算法把關,保障網絡用戶的合法知情權免受資本侵害。
近期施行的網絡監管條例將各類運用算法向用戶提供具有導向性的推薦服務掌控于法律的監管范圍之內,劍指大數據針對用戶特征的差別對待,對消費者的知情權與選擇權落實予以高度重視。首先,數據不是無主之物,對其治理要在法律的陽光下進行,讓數字勞動的參與者把握話語權,探尋利益與技術的共鳴,打造朗朗乾坤的網絡生態環境。在數字平臺間建立協同監管機制,讓監管部門能夠通過數據共享密切關注平臺資本動向,與政府實時數據互通,在數字平臺上建立可視化信息共享管理體系,讓數據共享真正成為為人民謀福祉的甘霖。“大數據的聚合和規整,可以有效解決數據的數量和價值問題,讓政府的宏觀調控更具前瞻性、科學性和系統性。”[10]其次,應出臺并完善數字信息保護的相關法律,將人民的隱私信息保護落實到位,對于網絡犯罪行為嚴懲不貸,確保數據的傳輸合法有序。智用技術革新的力量駕馭資本,澆鑄人類主體的價值創新,推進經濟的永續發展與社會的全面進步。
結語
大數據時代出現的異化勞動新形式隱含的是資本邏輯與勞動主體的沖突,是智能時代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所展現出的社會基本矛盾。不是要消滅提高生產力的機器,而是要摒棄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正確引導數字勞動,讓民生享有福報,讓不涉及核心技術的數據人人共享。技術會迭代,但不會自主服從于人類,在社會發展中人類自身仍需起生產決策的主導作用。善智以善能為前提,只有積極主動了解社會治理和技術變革的知識,在思想上堅定主體地位,促進科技的發展始終以解放人的勞動為目標,給予人更多的自由。未來利用大數據為人們造福的同時,也要兼顧對自然規律的尊重,需加強對技術應用的管控,避免因盲目追求利益而造成對環境的破壞,樹立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