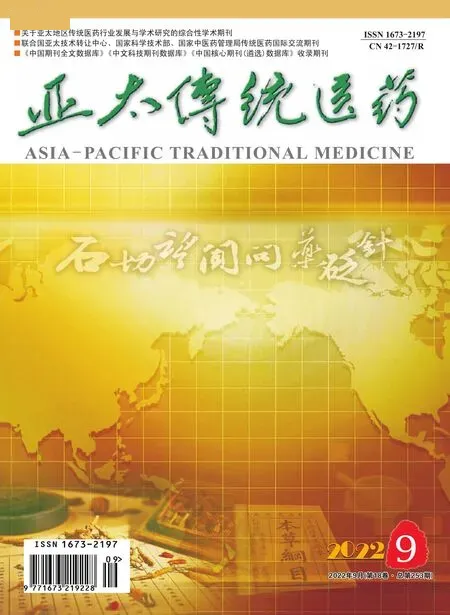藏藥材鑒定方法不統一成因探究
色 珍,單巴旺久,米 久
(1.西藏藏醫藥大學,西藏 拉薩 850000;2.西藏林芝藏醫院,西藏 林芝 860000)
藥材品種混亂是當前傳統藥材開發和研究中的共性問題,同一藥材在不同文獻典籍中描述不同是藥材品種混亂的主要原因。至今,在藏醫藥常用藥材中仍存在諸多品種認識不統一、用藥品種不規范等問題。本研究通過搜集、整理文獻,探討藏藥材鑒定方法不統一的成因,以期為科學、合理、安全使用藏藥提供依據。
1 藏藥材鑒定方法不統一問題的歷史性
1.1 斯吉其瑪[1]
十六世紀末的《四部醫典注疏·祖先遺訓》[2]中提及西藏北邊的一種黃沙,為該藥材最早記載的原用藥材。而關于其是草芥種子的鑒定方法常被認為有誤。《藏醫解注》《草本圖解》認為斯吉其瑪是一種海濱的沙子而非植物,但并未得到藏醫界一致認同。十八世紀的《四部醫典注解》[3]中認為,斯吉其瑪是一種存在于木材背面的黃色粉末狀物質,從海洋中獲得的黃色沙樣漂浮物可用作替代藥。與以往鑒定依據不同,斯吉其瑪在此處被認為是一種植物的分泌物。目前,對斯吉其瑪的鑒別仍有兩種不同理論:一種認為其是碎精金石;另一種認為其是海金沙。
1.2 扎雄
較早的藏醫藥文獻認為,扎雄是在陽光長時間照射下具五寶山上的一種巖石熔化汁[4]。而《四部醫典注疏·祖先遺訓》[2]則記載其是與巖石漿液混合的動物(飛鼠)糞便,即五靈脂。但十八世紀的藏醫學者達摩門然巴認為扎雄不是動物所排糞便[5]。
1.3 地嚓色布、黎布梅[6]
這些藥材在不同年代的古籍文獻中鑒別方法各異[7]。至今,仍存在因無統一鑒定方法,而隨意使用的情況,給藏醫臨床安全、科學、合理用藥造成困擾。
2 藏藥材鑒定方法不統一問題產生的原因
2.1 無法辨別歸屬
古代藏醫草本圖解中大多缺乏描繪藥材特征的詳細記載,使得后人對該藥材的辨別、鑒別無從應對,如對昻蒂的描述為:“花白,葉與根莖且長,味苦性糙,可治一切癰類病。”[8]但有白花、葉莖長、味苦等特征的草藥眾多,無法僅從文字描述上明確該植物的科、屬、種。
2.2 無法確定基原
由于古代藏醫藥圖解對某些藥材的記載極少或重視程度較高,易導致后期藏醫藥學者對該類藥材的相關注述出現不符合實際的夸大描述,使得后人無法確定該藥材基原。如較早關于牛黃的記載為牛黃來源于六牙象。藏醫學者蘇卡洛珠嘉布、明旺桑吉嘉措均曾講述其聽過牛黃來源于大象肝臟的傳言,但未曾親見。蒂瑪旦增彭措也曾認為藏醫所用牛黃出自大象,甚至為此做了諸多解釋,且補充了黃牛、牛犢等瞳孔偏黃類的動物,在夜間發鳴者可產藥用牛黃[9]。林曼巴《四部醫典注解》[3]則認為牛黃主要來源于牛,其別稱為象精。筆者查閱《藏藥解注》及相關經典論著,并未發現關于牛黃來源于大象的用藥記載。
2.3 鑒定方法多樣
古籍文獻中關于原藥材與替代藥材的描述不清,藏醫藥工作者常根據藥材生境、產量等形成各自的鑒定方法。如菊崗為梵語,藏語意為“竹之精華”,原藥材產于竹子[10]。但由于西藏的地理氣候和交通條件等因素,阿里等地常用當地的一種白色塵土作替代藥,并有該替代藥較原藥材藥效好的說法[11]。
2.4 重復亞名
在臨床用藥中,藥名長期混淆導致出現“一藥多名”“一名多藥”現象,部分藥效相同的藥物使用相同的亞名,增加了藥材鑒定難度。如巴夏嘎的原藥材為木本植物[12],但由于具有相似藥效的植物較多,從而形成多種來源的替代藥,且這些替代藥均被稱為巴夏嘎[13]。
2.5 多種鑒定版本
藏醫藥繪畫記載技術獨樹一幟,享譽世界。但現存藥物圖解古籍文獻較少,尚存的古籍文獻大多實物圖集嚴重稀缺,圖像模糊,導致后期形成了多種藥材鑒定版本。如藏藥菊崗,據藏醫典籍《藏藥本草》記載,其上品是產自北印度的一種竹芯[14];十九世紀的藏醫學家嘉央青澤認為《晶珠本草》中所述竹芯非真正的菊崗;藏醫南派創始人蘇卡洛珠嘉布則認為,菊崗可能是木材或土壤中的某種成分,有達西、梓降等別稱。在多數藏醫醫典中,菊崗被解釋為竹木的芯里[15]。
2.6 多支藏醫藥學派
由于對古籍文獻記載內容的理解不同,因而對藥材的鑒定方法也有不同,導致出現多支藏醫藥學派。如藏藥石材帕旺隆布,藏醫南派學者拉達次旺、蘇卡里歇措、達摩門然巴,北派學者明旺桑吉嘉措等均認為其與朵哲希石同為一種藥用石材,但在《晶珠本草》[9]中則認為帕旺隆布需要冶煉,朵哲希石是與其完全不同的一種,需煉制才可入藥的藥用石材。
2.7 記載與原藥材不符
有些藥材原本只在一處地方生長和使用,后被移植于其他地方,因生境的改變使其植株發生變異,導致外形特征與原藥材不同。如早期文獻記載:“印度豆蔻色白狀似三角,內里果實也呈三角板狀,磨之為香,乃極品也”,即產自印度的豆蔻為極品,西藏藏南的豆蔻為次。后期對豆蔻的鑒別與分類出現了多種說法,但大體分為印度豆蔻和藏地豆蔻兩種。其中,印度豆蔻在《晶珠本草》中亦分兩類:“體型大而味重,內里果實大且堅實,舶來品,藥效好,即白豆蔻;體型較小,味清,產自彼達等地,曰小豆蔻,藥效較前者比稍遜。”有派別認為,白豆蔻產自印度,小豆蔻則是于十八世紀末被引進內地種植。公元265年以前有關印度豆蔻的記載表明,豆蔻藥材隨著歷史推移發生了藥源的根本變化,導致后期對其鑒定方法不統一。
3 藏藥材鑒定方法統一的措施
藥材鑒定方法不統一問題在藏地不同時期均曾出現,至今仍未制定出統一的鑒定標準。究其原因,一是不同時期的古籍文獻對某種藏藥材的鑒定記載不盡相同;二是不同藏醫學派在傳承過程中形成的對某種藏藥材鑒定的不同見解,已在一定區域得到認可,不愿再接受其他理念;三是針對臨床療效的調研較少,缺少判定何種鑒定方法更可靠的實踐依據。
歷代藏醫典籍常出現某種藏藥材名稱多樣的情況,使得該種藥材的真名、亞名、別名等混淆。長期藥名混淆導致出現“一藥多名”“一名多藥”的現象,給藥材辨認和鑒定造成困擾,臨床使用易造成嚴重后果。因此,明確藥材基原是藏醫藥研究的首要任務。
3.1 對經典圖解及專家所述進行歸類
由于在藏醫藥史上存在因辨證講解不同而形成的南北兩派(也稱之為兩道),因而對藏藥材的鑒定方法也眾說紛紜。因此,規范藥材鑒定方法對藏醫藥事業長足發展至關重要[16]。
如《晶珠本草》中記載地嚓色布是紅黃石燃燒產生的鉛,分為兩種:一種是像金石一樣的黃色石,石體沾有綠色渾濁物或表面銹成黃色樣,有些表面是紅色,用火燒會出現煙霧;另一種像銀石,燃燒會滲出青色的地嚓巖漿。這里所述的地嚓色布來源是按藏醫南派知名學者金巴才旺的著作,以及蘇卡洛珠嘉布《論述部釋祖先心鑒定》所述,即地嚓色布是一種鉛軟石,若熔化則產生紅黃兩種顏色的鉛[17]。此外,藏醫大師帝瑪旦增彭措曾提出地嚓色布的識別方法,藏醫學者達摩門然巴和明旺桑吉嘉措也曾記載其是一種礦石,燃燒可得到地嚓,黃色礦石為上品,紅色較黃色藥效低。
3.2 借鑒現代科學技術
事實證明,藥材基原鑒別標準應以臨床實踐療效為依據,運用現代藥材鑒定方法和手段才能正本清源[18]。如《晶珠本草》闡述藏藥達森浸泡于水后會使水色發藍,利用現代熒光技術可知秦皮浸水后可顯藍光,但有藏醫學者認為杜仲才是達森。因此,在藥材鑒定,尤其是藥材基原鑒定的研究中還需大膽猜測和嘗試,反復實驗以證明。
3.3 注重臨床用藥效果
統一規范藏藥材鑒定方法的目的是使名著典籍中提及的藥材在臨床上能得以正確運用,使其療效得以有效發揮,提升藏醫臨床認可度[19]。
如藏醫學家蘇卡洛珠嘉布認為藏藥斯吉其瑪是海邊的黃沙,而達熱措希認為其是一種叫溫伯久巴的植被,扎崩巴則認為其是一種木材背面滲出的黃色分泌物。因而,斯吉其瑪有礦物藥、植物藥之分,但均具有治療腎病和小便失禁的功效并沿用至今。筆者認為可通過臨床療效來確認斯吉其瑪,而其他藥材則作為替代藥使用。
4 結語
傳統藏醫藥理論體系囊括了食療、行為學、醫藥學、外治學等領域。藏醫藥學是藏醫藥理論體系的精髓,是世代生活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先民的智慧結晶,守護著高原生靈健康。當前,部分藏藥的功效在藏醫臨床使用中,出現了療效未及經典所述乃至功效相反的現象,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藥材選用出現問題所致。因此,藏醫藥專家、學者和科研工作者應正確認識該問題,在實際工作中注重古籍文獻記載與臨床使用相結合,運用現代藥材鑒定方法,更加科學嚴謹鑒定藥材,為藏醫藥的傳承、發展與創新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