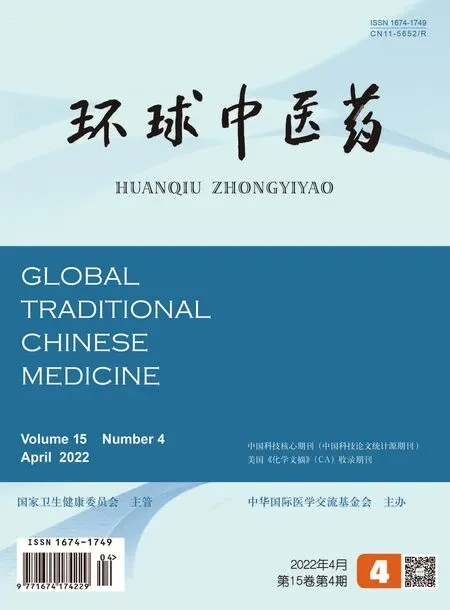基于臟腑風濕論治化療后周圍神經病變
曹璐暢 李杰 吳靜遠 許博文 張瀟瀟
化療誘導的外周神經毒性,即藥物誘發的周圍神經病變(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CIPN)是化療常見的一種進行性、持久性且目前治療效果欠理想的不良反應,呈劑量限制性,發生率僅次于血液毒性,多見于鉑類、紫杉烷類、埃博霉素、長春花生物堿、硼替佐米、沙利度胺等。其臨床表現復雜多變,但以感覺神經病變為主,可見感覺異常、弱化或缺失,麻木、針刺感、灼燒感、疼痛及運動異常等癥狀[1]。目前CIPN的發病機理尚未完全了解,其預防和治療策略仍是醫學上亟待解決的問題。CIPN據其臨床癥狀與發病特點,歸屬中醫“痹證”“血痹”“不仁”等范疇,中醫藥在降低CIPN發生率、減輕外周神經毒性、改善臨床癥狀等方面優勢顯著。
CIPN與《黃帝內經》所載痹病外邪侵襲、經脈痹阻、氣滯血瘀、著而內舍病機相比類,且在發病特點、微觀病理方面與臟腑風濕相似,符合當代臨床認識,故試論臟腑風濕學說在CIPN臨證中的應用,以望豐富CIPN的臨證論治思路,為中醫藥改善化療后周圍神經毒性奠定理論基礎。
1 CIPN的發病特點符合臟腑風濕論
1.1 外邪侵襲的發病方式
CIPN患者臨床常見四肢末端麻木感、針刺樣疼痛,此因外來之風、寒、濕、毒侵脾擾心所致。患者素感風邪,又加化療之寒、濕、毒邪入體,傷心血脈、礙脾氣機,寒濕瘀阻,陰邪傷陽,阻礙陽氣升發,肢體失煦為麻木刺痛;或風邪挾外之寒濕毒、內之寒濕瘀邪走竄,風寒濕瘀毒五邪溜居,四體失濡失暢而發為麻木刺痛。CIPN患者陽氣虧虛,加之風、寒、濕等外邪侵襲而罹病,與臟腑風濕正虛感受外來邪氣而發病的特點相符合。
1.2 伏氣潛藏的臨床表現
外來之風、寒、濕、毒經血脈內入臟腑,量微之時,正氣尚可抗衡,邪氣化為伏氣潛藏。后數侵而襲,損傷陽氣,陽虛血澀,加之寒濕毒邪困阻氣機,日久生瘀,風寒濕毒瘀混雜,邪漸盛正愈衰則發病。胡峰明等[2]研究表明,神經毒性發生率隨化療次數增多而逐漸增加,結果具有顯著性差異(P<0.01),且不同藥物蓄積量的神經毒性發生率有明顯差異(P<0.01),低、中、高劑量發生率呈增長勢,可見化療次數越多、蓄積量越大,CIPN發生率越高。根據取象比類,藥物蓄積量、化療次數和發病的正相關性與伏氣潛藏特點相合。在化療初期,藥物蓄積量少,或不表現臨床癥狀,但邪氣潛移,暗耗元氣,深溜溪谷,后邪盛發病,正邪膠結,邪氣纏綿難以根除,故CIPN大多不可逆[3]。
CIPN的臨床癥狀在化療初期即可出現,并可隨該次化療結束而逐漸消失。但化療為周期性治療,隨著化療次數的增加,患者屢感外邪,伏氣與外邪相引,癥狀也可長期存在,難以逆轉。此與臟腑風濕內伏邪氣與外來邪氣相引而反復發作或與伏留邪氣與內在病理產物相夾而纏綿難愈的發病特點相吻合,伏邪難祛,內積難解,日久而成頑疾。
2 CIPN的微觀病理符合臟腑風濕表現
CIPN患者臨證常表現為四末麻木、刺痛,遇冷加重,甚或出現肌力下降、肌肉萎縮,舌質色黯,脈沉細弦或澀。研究發現,鉑類藥物引起的CIPN是由鉑加合物在背根神經節和三叉神經節神經元中積累所引起的[4]。其中奧沙利鉑在背根神經節積聚,引起自由基清除能力下降,導致自由基堆積[5],且顯著增加超氧陰離子的產生并誘導坐骨神經和脊髓中脂質過氧化、蛋白質和DNA氧化[6],細胞內高水平的活性氧反過來導致酶、蛋白質和脂質的破壞[7],并誘導運動軸突中鈉通道失活的可逆性減慢。順鉑和奧沙利鉑還可在背根神經節神經元中產生MAPK相關凋亡[8],從而誘發產生周圍神經毒性。長春新堿可誘導大型髓鞘軸突細胞骨架的超微結構變化以及背側感覺神經節神經元中神經絲的堆積[9]。化療誘導的神經膠質細胞活化及白介素-1β、白介素-6和腫瘤壞死因子-α等促炎性細胞因子的釋放和升高是CIPN神經性疼痛的常見機制[10-12]。
基于中醫微觀辨證對CIPN的病理改變進行認識,鈉通道失活的可逆性減慢為機體代謝減退,與陽虛的病理現象相符[13]。藥物及其化合物、自由基等在神經元、神經節中累積,有形當屬實邪,病性遷延、纏綿、難解;癥狀遇冷加重,與寒濕瘀毒致病特點相近,且與伏邪形成過程相比類。神經元中MAPK相關凋亡、神經膠質細胞活化及白介素-1β、白介素-6和腫瘤壞死因子-α等促炎性細胞因子的釋放和升高,酶、蛋白質和脂質的破壞等,具有“生、動”特性,與伏邪潛藏日久、郁而化熱的病機相仿。故CIPN的病理變化亦符合臟腑風濕正氣虧虛、伏邪內留的微觀表現。
3 名家學術觀點及臨床經驗支持“臟腑風濕”與CIPN相關
徐芃芃[14]對50例CIPN患者進行中醫體質分類與判定,結果顯示CIPN患者體質分布以陽虛質為主,與藥物累積量呈正相關(P<0.05),且陽虛質患者臨床癥狀出現較晚,程度最重。張培宇根據臨證經驗認為化療早期營衛俱虛,風寒外邪入里塞絡,痰瘀隨之而生,風寒濕痰瘀阻滯絡脈而見CIPN癥狀,風寒濕瘀稽留日久而成痹證,即外邪侵襲、內外邪氣相兼發病[15]。楊曉燕[16]總結各醫家觀點,認為“虛”“瘀”“風寒”“濕”“毒”為CIPN的主要病因病機。仝小林等[17]認為疾病免疫復合物的形成與伏邪致病過程類似,可將其視為伏邪,而CIPN神經節中自由基堆積、神經元中神經絲堆積及軸突細胞超微結構變化等微觀改變與免疫復合物形成過程相似,故可等同為伏邪。
張培宇臨床辨治CIPN注重祛除內外邪氣,以溫陽通絡、補益肝腎、祛風除濕為主,療效肯定[15]。姜毅治療CIPN從陽虛血瘀著手,治療采用溫陽活血通絡法,可改善患者臨床癥狀,降低周圍神經毒性分級[18]。李元青等[19]對56例CIPN患者行黃芪桂枝五物湯合身痛逐瘀湯加減干預1個月,結果與安慰劑對照組相比,干預組周圍神經毒性分級較對照組提高(P<0.05),EORTC QLQ-C30疲乏評分明顯下降(P<0.01),提示溫陽化瘀、祛風除濕法可改善CIPN癥狀,降低神經毒性分級。丁蓉等[20]將48例接受奧沙利鉑化療的患者隨機分為單純化療的對照組與化療聯合當歸四逆湯口服的治療組,結果顯示治療組可改善中醫證候總有效率,降低周圍神經毒性(P均<0.05),表明益氣養血、散寒通脈法可減輕CIPN發生程度。
當代各醫家對CIPN的臨證經驗及認識重在風寒濕瘀毒虛,正虛外邪入體,阻礙氣機則內外邪相膠加,日久成痹,且微觀病理變化具有伏邪特性。臨床采用溫陽、活血、祛風、除濕等治法可收獲一定療效,在臨床證據方面亦論證了臟腑風濕與CIPN的相關性。
4 從“臟腑風濕”探討CIPN病機
臟腑風濕以“正虛外感風寒濕邪,邪氣遺留,伏而后發或再感而發”為病機特點,對符合此發病機制的疾病具有一定廣適性,仝小林院士指出以臟腑風濕理論為基礎論治部分源于外感的疑難雜癥多可收獲效驗[17]。CIPN受外來化療寒濕毒邪侵害,以陽氣虧虛為本,風寒濕毒浸淫為標,伏氣潛藏為要,與臟腑風濕病機相合。
4.1 CIPN與“四體風濕”的關系
臟腑風濕作為一種病機學說,可應用于多種疾病。根據發病部位的不同故病名有所差異,如發于中焦脾胃的“脾胃系風濕病”,發于下焦的“胞宮風濕病”等。CIPN患者痹氣留滯臟腑,氣血郁阻不濡四末,且邪氣伏潛,日久痹氣從臟腑外發五體,邪氣由里達外,溜居四末而見四肢麻冷等癥,病本在臟腑,病末在四肢,故應屬“臟腑風濕”下“四體風濕病”范疇[21]。
4.2 “四體風濕”理論下CIPN的病機分析
4.2.1 陽氣虛郁為罹病根源 CIPN患者臨床常見四肢末端麻木、寒冷、甚或疼痛,并有遇冷加重、得溫緩解的特點[22],《醫門法律》載“偏枯不仁,要皆陽氣虛餒,不能充灌所致”,指出不仁之癥病源為陽虛,而陽虛之由包括陽氣虧虛的“真”陽虛與陽氣郁滯所致的“假”陽虛。《雜病源流犀燭》言“麻,氣虛是本……陽氣虛敗,不能運動”,且研究發現大多腫瘤患者早期常見脾腎陽虛、氣血兩虛等[23]證,故陽虛內損、四體失煦為發病之一源;《靈樞·刺節真邪》謂“衛氣不行,則為不仁”,化療損困內陽,風寒濕毒滯塞氣機,陽郁不達,外見麻木,如《四圣心源》論“陽虧土濕,中氣不能四達……則生麻木”。王悅[24]研究發現CIPN與患者焦慮抑郁呈中度正相關,而焦慮抑郁的病機重在陽虛氣郁[25],故陽郁不達、四體失養為發病之二源。臨床CIPN陽虛與陽郁常常并見,陽氣既虛且郁,虛為本,郁為標,痹氣陰毒內伏,陰陽失和,故CIPN以陽氣虛郁為患病的根本。
4.2.2 四淫襲虛為致病關鍵因素 《素問·風論篇》:“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于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正氣虛餒、衛陽失固則風邪易至,風擾四肢則有不仁。《素問·風論篇》謂“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惰,四肢不欲動”,研究發現:CIPN患者除四肢末端麻木、疼痛外,常伴有疲倦、乏力、惡風、汗出等全身癥狀,與脾風癥狀相合[26],且臨床應用散寒祛風藥物可降低CIPN發生率,縮短周圍神經毒性發生時間[27]。
CIPN患者以數犯虛風之體接受化學藥物治療,在藥毒消減癌腫的同時,外來寒濕之氣直中三陰,折損陽氣,并阻遏陽氣疏達,寒、濕、毒邪日久淫溢,外聚四末,脈絡瘀阻而為麻木、疼痛。CIPN患者素感風邪,加之寒濕藥毒襲虛,風寒濕毒四淫相加,稽留體內,痹阻氣機,日久流竄而外散,是臟腑風濕致病的關鍵病因。
4.2.3 伏氣潛蓄為發病重要過程 《靈樞·賊風》曰“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痹”,若疾病假愈遺根,病氣伏藏,適逢邪引或正虛則可復發。CIPN受風、寒、濕、毒外邪侵襲,著而不去,化為痹氣潛藏于臟腑、血脈、分肉之間,重感化療之寒、濕、毒邪,或伏留的水濕、痰飲、瘀血、濁毒等病理產物暗耗正氣,待正邪平衡破壞之時則再次發病,此為臟腑風濕發病的重要過程。
5 基于臟腑風濕論證CIPN臨床辨治
針對CIPN陽氣虛郁夾雜的病機特點,其臨證治法應在固本清源、少火溫陽的基礎上,注重“通陽消陰、透痹和絡”,祛除伏阻的痹氣陰邪,暢通陽氣運行之機,邪去正自安。根據伏藏風寒濕瘀毒邪氣的偏重不同,治法有宣風和痹、溫陽托痹、除濕達痹、活血通痹之別。
5.1 宣風和痹
《諸病源候論》載“積聚者,由陰陽不和,腑臟虛弱,受于風邪,搏于腑臟之氣所為也”,龍之章指出“治病風藥斷不可少”,風邪作為百病之長,不僅可致外感疾患,兼夾他邪伏竄臟腑經絡,亦可發為積聚類不仁痹病。張培宇認為CIPN患者早期感受外來風寒,以風邪為主,日久風寒濕相摶,滯而成痹,臨證注重祛風散邪[15]。賈志洋[28]通過臨床研究發現,息風通絡是中醫藥防治CIPN的重要治法之一。史哲新教授臨床善用搜風通絡法辨治周圍神經病變,常以止痙散為底方靈活加減[29]。藥理研究證實多數風藥具有抗腫瘤作用[30],其中防風所含色原酮對多種刺激引起的疼痛呈明顯抑制作用[31],僵蠶中磷脂與鞘脂類化合物可能通過刺激神經生長因子合成以發揮營養神經作用[32],對CIPN具有一定療效。
5.2 溫陽托痹
《醫門法律》載“偏枯不仁,要皆陽氣虛餒,不能充灌所致”,陽虛失煦,陽郁不達,氣血不濡四末則為不仁。王泳等[33]認為CIPN為本虛標實之證,陽虛為本,痹阻為標,臨證辨治常以黃芪桂枝五物湯加減以振奮固護陽氣。張毅鵬[34]認為陽虛是腫瘤發生的內在關鍵,化療后陽氣更傷,臨床善用溫陽散寒法,靈活選用陽和湯加減治療,對CIPN具有預防與改善作用。黃兆勝等[35]研究發現,黃芪桂枝五物湯可以提高小鼠痛閾值,具有抗炎鎮痛效果。此外,有藥理研究顯示黃芪多糖可以保護神經[36],干姜乙醇提物具有鎮痛效應[37]。
5.3 除濕達痹
《雜病源流犀燭·麻木源流》言“麻木,風虛病亦兼寒濕痰血病也”,風邪襲虛挾濕走竄,溜居絡脈,伏而內結,氣血不通、不榮四末絡脈而為麻木。何健等[38]通過研究CIPN的中藥內治組方規律,發現祛風濕通絡是其重要的臨床治則之一。張金波[39]臨證以清熱化濕、養血活血通絡為法,采用柏川熏洗液外治CIPN療效肯定。藥理研究表示,桑枝總黃酮具有抗氧化活性,其作用機制側重于自由基的清除,并可抗炎、鎮痛[40-41];薏苡仁提取物可以清除自由基,清除能力與濃度呈正相關,并有鎮痛、抗炎等作用[42]。
5.4 活血通痹
《素問·痹論篇》載“榮衛之行澀……皮膚不營,故為不仁”,血行滯澀,不榮四末發為麻木刺痛。謝邦翔[43]認為化療后耗氣傷陽,血行不利,臨證多以益氣活血方化裁治療,對神經傳導速度具有顯著改善作用。陳榮生等[44]認為血脈瘀阻是CIPN的關鍵要素,臨床以養血活血通絡、益氣溫陽為法,善用通脈活血湯加減治療,對CIPN具有預防與拮抗作用。藥理研究證實,姜黃所含姜黃素具有抗炎鎮痛效應[45],川芎所含川芎嗪可減少氧自由基含量,并能減輕神經細胞損傷[46]。
6 小結
基于臟腑風濕學說論治CIPN,以陽氣虛郁、風寒濕毒瘀邪氣伏潛為病機切入點,臨證注重通陽消陰、透痹和絡,靈活選用宣風和痹、溫陽托痹、除濕達痹、活血通痹四法,動態調整扶正祛邪力度,不僅有助于CIPN癥狀的緩解,且基于伏邪理論的辨治對防治腫瘤復發轉移也有功用[47],體現了“異病同治”之奧秘,該理論在未來有待于進一步深入挖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