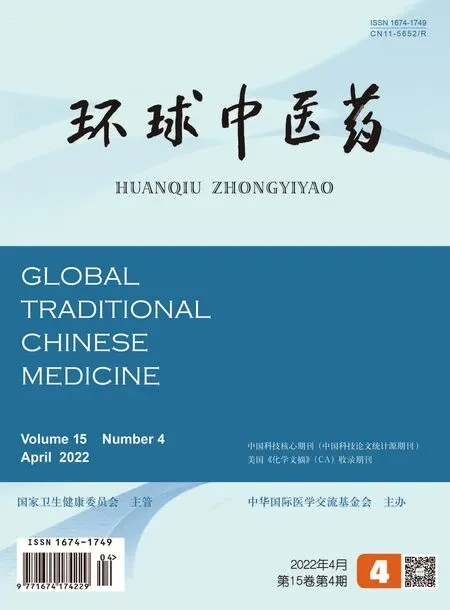丁甘仁中風病辨治方藥探賾及醫案舉隅
朱思行 顧博丁 尚力 嚴世蕓 陳麗云
中風病是由于正氣虧虛、飲食、情志、勞倦內傷等引起氣血逆亂,產生風、火、痰、瘀等病理產物,以腦脈痹阻或血溢腦脈之外為基本病機,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言語謇澀或不語、偏身麻木為主要臨床表現的病證[1]。《內經》雖沒有明確提出中風病名,但所記述的“大厥”“薄厥”“仆擊”“偏枯”“風痱”等病證,與中風病的臨床表現相似。至仲景《金匱要略·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則正式采用“中風”的病名。丁澤周,字甘仁,江蘇武進孟河人,清末民初孟河醫派四大家之一,海派中醫丁氏內科的創始人,同時亦創立了現今上海中醫藥大學的前身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是民國時期杰出的醫學家、教育家。其治學熔傷寒溫病于一爐,內外婦兒皆有所研,聲名海內外。丁甘仁對中風病的辨治,既有繼承又有創新,值得研究。
1 對真中風的認識與方藥運用
1.1 重視內虛,以陰陽為辨證綱領
丁甘仁先生對真中風的認識,實承襲唐代孫思邈關于中風病即外風及內虛外風的病因病機學說而來,但丁甘仁認為真中風是以臟腑內虛為主,以外風為誘因,與內風互結為其發病機理。與孫思邈論真中風比較,丁甘仁在思想上更加重視內虛,故其在所著《證治論要·論治中風》中自述曰:“蓋謂真中風雖因風從外來,實由臟腑內虛,外風引動內風,賊風入中臟腑、經絡、營衛,致以痹塞不行,陡然跌仆成中,此之謂真中風也。”又具體言其病因病機為“陽氣本虛”和“高年營陰虧耗”[2]。筆者認為,丁甘仁側重內虛,以陰陽為真中風內虛病機之辨證綱領。
丁甘仁重視真中風以內虛為主的思想極有可能是受到孫思邈和李東垣的影響。金元時期對于中風病從內虛而論者,當屬李東垣“正氣自虛”的病機學說,其在所著《醫學發明》中曰:“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多有此疾。壯歲之際,無有也。若肥盛,則間有之,亦形盛氣衰如此。”更有“口眼斜,亦有賊風襲虛傷之”之語[3]。由此看來,李東垣著眼于人體內虛之病因。丁甘仁精勉勤訓,臨床上博采眾家,用藥常顧護脾胃正氣,對李東垣補土益氣的學說自有心得體會。
對于真中風的辨證,丁甘仁在《證治論要·論治中風》中明確指出以本虛為主,痰熱蒙蔽清竅或痰濁堵塞靈機為邪實阻塞,故以陰陽為綱,把真中風的病機分為以陽氣本虛、痰濕稽留和營陰虧耗、痰熱蒙蔽兩種類型,這在其中風病醫案中也常有體現。對真中風的認識,丁甘仁未舍棄前賢關于外風入中為因的寶貴學術經驗和對應方藥,更是結合自己的經驗,從臨床出發,以內虛為發病之本,執陰陽虛損兩端而辨治,筆者認為此可視為丁甘仁的獨創,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對于把握真中風的辨證思路提供了捷徑。
1.2 治虛為主,標本緩急兼顧
針對真中風以虛為主、以風痰為患的病機,丁甘仁治虛以陰陽分論之,標本、緩急兼顧。對陽氣本虛、痰濕稽留、靈機堵塞者,采用小續命湯助陽祛風、開其寒痹以急治,并配合蘇合香丸疏通絡道,同時加竹瀝、姜汁等滌痰開竅。對營陰虧耗、外風引動內風、兼見痰熱蒙蔽清竅者,采用劉河間地黃飲子育陰息風,配合至寶丹化痰清神。在此基礎上,丁甘仁常用生地、麥冬、石斛、山萸肉、牡蠣、羚羊角滋陰息風,天竺黃、膽星、川貝、遠志、菖蒲化痰開竅。
如丁甘仁治胡左案:“中風已久,舌強言語謇澀,右手足無力,形寒身熱,胸悶不思飲食,神識時清時寐,舌苔膩布,脈象沉細而滑。陽虛外風乘隙而入,痰濕上阻濂泉。”丁甘仁辨為真中風之急癥,方以小續命湯加減[4]。藥用熟附塊、川桂枝助陽祛風,云茯苓、制半夏、陳廣皮、大砂仁化痰,全當歸、大川芎、光杏仁、嫩桑枝活血通經,炒谷麥芽健脾開胃。此案患者形寒身熱、神識時清時寐,顯然是陽虛外風直中,導致風痰阻滯清竅,當屬真中風之急癥,故用小續命湯加減治療無誤,體現了丁甘仁治虛為主,急則治標的真中風治療思想。
2 對類中風的認識與方藥運用
2.1 重視內風,以肝腎陰虛為本、風痰火為標
金元以降,醫家對中風病的病機逐漸由“外風”轉向了“內風”立論。其中,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首先提出了“腎水不足,心火暴甚”的中風病機,并由重視內虛轉為重視內因在中風病病因中的地位。此后,李東垣認為“正氣自虛,形盛氣衰”所致的脾胃虛損是引發中風的關鍵,而朱丹溪則把“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歸結為中風病的病機。直至元代王履從病因學角度將中風病分為“真中”“類中”,始開類中名稱的先河[5]。明代繆希雍稱類中為“內虛喑中”,張景岳又提出“非風”之說,認為“內傷積損”是導致本病的根本原因。明代李中梓又將中風病明確分為閉、脫二證,在臨床急救上給予了很大的指導作用。清代葉天士的“水不涵木,肝陽化風”說更是被丁甘仁先生推崇備至。基于上述中風病重視內因及類中的病機發展,筆者認為丁甘仁實是宗王履真中、類中之說,以朱丹溪、葉天士之論為據,把類中風的病因病機歸結為風痰火三者為實,肝腎氣陰本虧為虛,且虛實同見。
具體而言,丁甘仁把半體不用、足痿不行、舌強言謇、口角流涎之癥歸結為痰濕或痰熱阻于廉泉之竅,認為是風痱重癥;把神識不清者,歸結于肝火內熾、風陽上僭、痰熱阻竅所致。總之,丁甘仁把類中的病機概括為肝腎陰虧為本,風陽痰熱為標,并提出標急于本,先治其標,標由本生,緩圖其本的治療法度。
2.2 瀉實為主,兼顧肝腎陰虛
對于痰濕或痰熱阻于廉泉之竅者,丁甘仁治宜扶正養陰、熄風和絡,方用《古今驗錄》續命湯或地黃飲子加減,方中石膏清熱瀉火,確是治療熱證的良藥。對于肝火內熾、神識不清者,方用羚羊角、牛黃清心丸、至寶丹滌痰開竅,石決明、青龍齒鎮肝潛陽,天麻平肝熄風,僵蠶、蝎尾、鉤藤和絡。對于陽明熱盛者,用石膏與知母相配;痰阻舌根者,用竹瀝半夏、川貝、天竺黃、膽南星、蛇膽陳皮、遠志、菖蒲化痰開竅;半身不遂、口眼歪斜、項強不能轉側者,用牽正散加當歸、丹參活血和血,秦艽、木瓜祛風轉筋,地龍、絲瓜絡、嫩桑枝通絡,更用虎潛丸、大活絡丹強筋骨、祛風活絡;痰盛氣逆者,丁甘仁認為此證較急,故用礞石滾痰丸、竹瀝、姜汁化服以滌痰;而對正虛導致的手足麻木無力者,用人參再造丸、指迷茯苓丸扶正祛痰。《丁甘仁用藥一百十三法·雜病門·中風類》系丁甘仁當年門診處方記錄,由其門生歸納整理而成,將丁甘仁治類中風經驗總結為養陰熄風、熄風滌痰、豁痰開竅三法,可供參考。
如丁甘仁治錢左案:“類中偏左,半體不用,神識雖清,舌強言謇,咬牙嚼齒,牙縫滲血,呃逆頻作,舌絳,脈弦小而數。”丁甘仁診為“陰分大傷,肝陽化風上擾,肝風鼓火內煽,痰熱阻于廉泉之竅。”因呃逆之癥見于危重病癥過程中,屬于胃氣將絕、生命垂危之惡兆,故肺胃肅絳之令不行,是為危癥險關[4]79。方以地黃飲子、竹瀝飲合方加減挽墮拯危。其中地黃飲子去附子、肉桂、巴戟天等陽熱之藥,以防更傷陰液,甚則助陽化風,而加西洋參養陰清熱,瓜蔞皮、生蛤殼、枇杷葉、貝母、鮮竹茹等祛風化痰,柿蒂止呃逆。竹瀝飲方出吳儀洛《成方切用》,由竹瀝、生葛汁、生姜汁組成,再加真珍珠粉、真猴棗散另服,增強滌痰醒神之功效。兩方合用,肝風息而痰熱清,陰液漸復而諸癥得解。
3 淺析丁甘仁對于真中與類中的辨析
有研究者認為,丁甘仁對中風病的辨證處理,并不著重于“外風”或“內風”,而在于“臟腑內虛”[6]。從丁甘仁臨床醫案的記錄來看,似有混淆二者之意。如治董左案:“右半身不遂已久,近來舌強不能言語,苔薄膩,脈弦小而滑。”丁甘仁辨為“外風引動內風,挾濕痰阻于廉泉,橫竄絡道,為類中風之重癥。”治以熄風滌痰,和營通絡,藥用左牡蠣、花龍骨、煨天麻、嫩鉤鉤潛陽熄風,西秦艽、炙僵蠶祛風通絡,枳實炭行氣通滯,淡竹瀝、生姜汁、炙遠志、陳膽星、川象貝、仙半夏等化痰開竅[4]80。又如治金左案:“陡然右手足不用,舌強不能言語,神識時明時昧,口干欲飲,舌質紅苔薄膩,脈虛弦而滑。”丁甘仁同樣辨為“氣陰本虧,外風引動內風,挾濕痰阻于廉泉,橫竄絡道,為類中風之重癥”。不同的是,此為急癥,急予熄風潛陽、清神滌痰,藥用西洋參、川石斛、大麥冬滋養氣陰,生石決明、煨天麻、嫩鉤鉤潛陽熄風,炙僵蠶通絡,朱茯神、竹瀝半夏、炙遠志、川貝母、鮮石菖蒲、淡竹瀝清心滌痰,真猴棗散沖服加強化痰開竅的作用[4]79-80。
以上兩案雖同為外風引動內風,但一為濕痰阻遏,一為氣陰本虧,丁甘仁反而均辨為類中風之重癥,其辨治并非以病情的急緩或病因的不同而各異,故丁甘仁傳人沈仲理對此兩醫案的按語中亦認為丁甘仁對真中與類中的區別不甚嚴格[2]89-90。但從丁甘仁中風病醫案及醫論中可知,丁甘仁在學術認知上,對真中、類中仍是有所區分,尤其丁甘仁對外風入中的真中風,如外風入中而身發寒熱,或陽虛邪中者,采用續命湯驅散外風,并且收效顯著。通過對其中風病醫案的整理和分析,筆者認為丁甘仁對中風病的認識是在區分真中、類中的基礎上,即區分兩者不同的病因病機,但在臨床上,丁甘仁統外風與內風于辨證,把握虛實兩端為要,這體現了丁甘仁靈活把握辨證,執簡馭繁的臨床思維。這與王琳等[7]從虛實的病機角度來研究丁甘仁中風病不謀而合,但其未從學術認知的角度對丁甘仁學術思想及方藥形成的脈絡和淵源進行梳理研究和總結,筆者認為是其不足。另有一些學者從中經絡和中臟腑兩方面對丁甘仁中風病辨治進行歸納整理[8-9],這是屬于中風病的內因部分,與丁甘仁基于真中、類中的病因病機認識尚有偏差,不能全面地反映丁甘仁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如僅從丁甘仁治療中風的處方分析,簡單地把內虛為主、邪實為患的中風病病機歸結為氣虛、陽虛、陰虛,間夾風痰火瘀等邪實的結論似是而非,實是欠妥,是未明丁甘仁對中風病認識的本意。
綜上,筆者認為丁甘仁對真中、類中的辨治區別在于,兩者都有癥狀輕重急緩之分,但真中風是以外風為誘因,引動內風,以內虛為主,內虛以陰陽為綱分而論之,故治療以助陽祛風或育陰息風為主,兼化痰清竅。而類中風是以風痰火為標、肝腎陰虛為本,常采用臟腑虛實為辨證手段,治療上采用標本先后、虛實兼顧之法。但丁甘仁在臨床上統外風與內風于辨證,把握虛實兩端為要,淡化了學術上的區分,這從其醫案中可以見到。治療上,丁甘仁對續命湯和地黃飲子的運用頗具心得,常隨證加減,但均辨證以施治,不囿于真中、類中。
4 丁甘仁運用仲景小續命湯心得
丁甘仁治羅左案:“年甫半百,陽氣早虧,賊風入中經腧,營衛痹塞不行,陡然跌仆成中,舌強不語,神識似明似昧,嗜臥不醒,右手足不用……脈象尺部沉細、寸關弦緊而滑,苔白膩。”丁甘仁辨為“風性上升,痰濕隨之,阻于廉泉,堵塞神明……陰霾彌漫,陽不用事之證……急擬小續命湯加減以助陽祛風,開其痹塞,運中滌痰,而通經絡。”丁甘仁處方用麻黃、川桂枝、制附子助陽祛風,杏仁、姜半夏、生姜汁、淡竹瀝宣肺化痰,川芎、當歸活血行氣,甘草調和諸藥,另用再造丸扶正祛邪[4]75-76。服兩劑后,患者神識稍清、嗜寐漸減,是藥證相符的佳兆,故在原方基礎上去麻黃,加茯苓、枳實炭化痰行氣,炙僵蠶通絡。三劑后,患者神識較清,嗜寐大減,略能言語,惟右手足依然不用,腑氣六七日不行,苔膩。治以助陽益氣,以驅邪風,通胃滌痰,下濁垢而通腑氣。于上方中加入生黃芪益氣,風化硝、全瓜蔞、淡蓯蓉、半硫丸化痰通便。服上藥后,患者腑氣已通,神識已清,但舌強,言語未能自如,右手足依然不用,脈弦緊轉和,尺部沉細。仍助陽氣以祛邪風,化痰濕而通絡道,藥加秦艽、嫩桑枝祛風通絡,懷牛膝補肝腎。后患者諸恙見輕,屬于中風恢復期的范疇,故丁甘仁守方六十余貼,加用大量生黃芪祛風,鹿茸養血,大活絡丹通絡,最終使患者舌能言、手能握、足能履,并用膏滋方善后[10]。此案屬陽氣早虧、賊風入中經腧的真中風,所致跌仆、舌強甚至神識不清,故用小續命湯助陽祛風以通經絡為急,待病情穩定后,祛風通絡和補養肝腎精血兼顧,是急則治標、緩圖其本之法。
此案例詳盡,且效如桴鼓,但筆者認為,丁甘仁在其治療中風醫案中用仲景小續命湯的說法當屬有誤。小續命湯由麻黃、附子、甘草、桂心、防風、川芎、白芍、人參等藥物組成,方出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有備急之用。而張仲景《金匱要略·中風歷節病脈證病治》中確實也有續命湯治療中風病的記錄,不過此續命湯出自《古今驗錄》,且由麻黃、桂枝、杏仁、當歸、干姜、石膏、人參、甘草、川芎九味藥物組成,兩者雖有部分藥物一致,且都治療中風病,但其功效實與《備急千金要方》之小續命湯不同。從組成來看,該方近似《備急千金要方》之大續命湯,為治療外風入中、內有郁熱之中風風痱,肢體緩縱不收,皮膚不知痛癢,口不能言,不省人事,產婦出血較多,及老人、小兒見上述癥者。據此,筆者認為丁甘仁所用的小續命湯應當是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中的小續命湯。
5 丁甘仁運用地黃飲子心得
地黃飲子最早出自于《備急千金要方》,原名內補散,經前人略作加減后,以地黃飲之名收錄于《圣濟總錄》,被用于治療舌強不能言、足廢不能用之喑痱證,直至劉完素《宣明論方》以地黃飲子刊行于世后,才引起后世的廣泛關注。地黃飲子具有滋腎陰、補腎陽、化痰開竅的作用,方由熟地黃、巴戟天、山茱萸、石斛、肉蓯蓉、制附子、五味子、肉桂、茯苓、麥門冬、菖蒲、遠志組成。
筆者認為,在丁甘仁的中風病醫案中,不管是真中還是類中,常選用地黃飲子中的補陰藥,而舍陽藥不用,可能跟他承襲葉天士的“水不涵木,肝陽化風”之說有關,恐陽藥傷陰,使風愈熾。其組方常用生地、麥冬、川石斛三者養陰為主藥,間或加入西洋參、南沙參等物。如辨為氣陰兩虛、肝陽上亢者,則從肝之體用角度論治,以生地、生白芍養陰柔肝為主,穞豆衣、左牡蠣、煨天麻、滁菊花、鉤藤鎮肝熄風,陳皮、茯苓、陳膽星、竹瀝半夏、淡竹瀝、川象貝化痰,石菖蒲、炙遠志開竅。由此可見,丁甘仁雖未用地黃飲子全方,甚至只取其滋養肝陰之藥,但這與其治從肝腎陰虛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而用藥加減的變化也體現了其據證而靈活制方的思路。
如丁甘仁治沈左案:“年逾古稀,氣陰早衰,舊有頭痛目疾,今日陡然跌仆成中,舌強不語,人事不醒,左手足不用。舌質灰紅,脈象尺部沉弱,寸關弦滑而數,按之而勁。”丁甘仁辨為“水虧不能涵木,內風上旋,挾素蘊之痰熱,蒙蔽清竅,堵塞神明出入治路,致不省人事……中經兼中腑之重癥。”[4]76-77急以育陰息風,開竅滌痰。方以羚羊角片、至寶丹開竅為主急以治標,輔以麥冬、玄參養陰清熱,仙半夏、川貝、天竺黃、陳膽星、竹茹、枳實、全瓜蔞、淡竹瀝、生姜汁滌痰,天麻、嫩鉤鉤祛風除眩。兩劑后,患者人事漸知,但仍舌強不能言語,左手足不用,脈尺部細弱,寸關弦滑而數,舌灰紅。急癥已解除,丁甘仁考慮痰涎為營陰虧耗,內風擾胃,變化津液而成,故以地黃飲子加減緩緩圖之以治其本,認為“草木功能,非易驟生有情之精血也”。該案以虛實緩急為辨,治療上先標后本,虛實并治。值得注意的是,后方加減時以患者神情舌和,然手足仍不用為辨治的要點,用藥上減少化痰開竅藥而增加祛風通絡藥。
6 小結
與后世中風病的辨證不同,丁甘仁對中風病的認識是在精研歷代醫家學術和用藥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其臨床體會產生的,對中風病的辨治,既有繼承亦有創新。其首辨真中、類中,真中以內虛為主,由外風引動,與內風互結,故重視內虛為病,在此基礎上,內因以陰陽為辨證綱領,分為陽虛和陰虛,以治虛為主,標本、緩急、虛實兼顧。類中則以風、痰、火等內因標實為患,兼見肝腎陰液虧虛,虛實夾雜,故重視內因為患,以瀉實為主,兼顧肝腎。丁甘仁臨床上統外風與內風于辨證,要在把握虛實,注重標本緩急,靈活運用補瀉。治療上,丁甘仁對續命湯和地黃飲子的運用頗具心得,常隨證加減,但均辨證以施治,不囿于真中、類中。在用藥上,丁甘仁擷采眾家,輔以丸膏,特色鮮明。丁甘仁對中風病的辨治可謂執簡馭繁,無有偏廢,臨床上易于掌握。因此,對于學術的發展,不能泥于教材之辨證分型,而應廣泛繼承先輩經驗,重新挖掘經典方藥,發揚學術之爭鳴,豐富辨證思路與手段,才能有利于中醫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