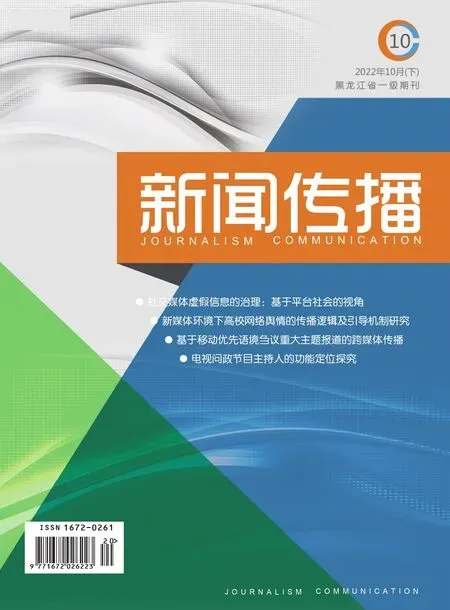從《伊犁河》探析紀錄片對城市記憶的建構方式
李先先 胡昌平
(塔里木大學人文學院 新疆阿拉爾 843300)
城市是媒介生存、發展的最佳空間,是記憶生成與傳播的中心,是城市居民承載、表達記憶的情感之地。城市記憶是在城市歷史發展中聚集下來的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它最終轉化為文化記憶與個體記憶,以特有的形式保存下來。《伊犁河》是伊犁市發生的人與城、物與城的故事,是伊犁市發展的縮影。《伊犁河》是如何建構伊犁的城市記憶?伊犁市的記憶塑造如何通過符號、空間傳播伊犁的城市形象?
一、記憶形成:紀錄片對城市記憶的符號表征
每一個城市在其發展與建設過程中,都會形成一些獨屬于自己城市的鮮明特征,這些個性特征能夠表現城市的獨特內涵,這就成了城市的標志性符號,即城市符號。城市符號是連接人與城市記憶的重要節點,它推動了城市記憶的形成。紀錄片中人物與其生活儀式操演就是典型的符號構建,二者的互動共同構成伊犁的城市符號。《伊犁河》是如何通過人物符號與儀式符號實現其城市記憶的表征,以此實現傳播城市形象的目標呢?
(一)人物符號表征的城市記憶
“城市記憶是一種集體構建的文化共同體,人們在記憶生產實踐中將個體生產的記憶整合進入集體記憶,讓城市的歷史文化具有連續性和身份特征,并具有與其他城市不同的形象與風貌。”[1]《伊犁河》第二集“物阜民安”中,世代定居在伊犁市的哈德爾一家是當地小有名氣的哈薩克醫生。哈薩克族醫生只為治病,不為錢財,這也是哈德爾醫生的座右銘。哈德爾醫生作為哈薩克醫學的表征符號,他治愈病人的過程是獨屬于他的個人記憶,但治愈每個病人構建起的記憶是伊犁城市獨有的城市記憶。哈德爾醫生的生產與實踐是哈薩克醫學發展的歷史縮影,哈薩克醫學的發展又是伊犁市記憶中的一部分,二者相輔相成。土生土長于伊犁市的哈德爾醫生致力于發展哈薩克的醫學,受其影響兒子海爾東也將從事哈薩克醫學工作,海爾東將治好更多的病人作為自己的職業目標,這就是哈薩克人祖輩的傳承。醫學的傳承是哈薩克醫學延續的重要保障,父與子間有關醫術記憶的生產成為伊犁市記憶的一部分,推動伊犁市記憶的形成。
除了世代定居在伊犁市的哈德爾醫生,還有作為移居者的鄧攀,也是伊犁城市記憶的生產者,是構建伊犁城市記憶的組成部分。《伊犁河》第四集“城里村外”中年近七十的老鄧已經移居到伊犁生活40多年,在伊犁市的生活經常讓他樂不思蜀,老鄧甚至將門前的河灘命名為鄧公灣。移居者作為城市記憶生產的主體之一,他們是構建空間和地方特征的重要組成部分,塑造并保存他們的身份認同。老鄧將自己門前的河灘以自己喜歡的名字命名,讓河灘有了自己的名字,抽象的精神有了符號載體。冬不拉是新疆哈薩克族獨有的樂器,彈冬不拉是老鄧生活的元素。老鄧制作的冬不拉受到當地人的喜愛;購買他種植的野酸梅樹種的人也絡繹不絕。在伊犁市生活的四十幾年中,老鄧玩木頭、制作冬不拉、種植酸梅樹成為他不變的生活記憶,這些記憶根植于老鄧的“第二故鄉”,也書寫了伊犁城市的記憶。
(二)儀式符號表征的城市記憶
當然,能夠傳播、豐富城市記憶的更多是日常性文化儀式。在城市符號系統中,山水、食物是最典型的城市符號。在《伊犁河》第一集“以夢為馬”中古麗娜蘭木是一名服裝設計專業的大學生,畢業后她選擇在自己的家鄉創業從事服裝縫紉工作。古麗娜蘭木設計的服裝大膽而奔放,她將時尚元素與天山大自然相結合,不失傳統又具現代風格,深受女性的喜愛,她的服裝生意也擴展到美國、加拿大等地。以杭州絲綢為制作原料,以日常所見的山水符號為設計元素,衣服的設計與創作是古麗娜蘭木的日常文化儀式,這種儀式不僅加深了古麗娜蘭木對家鄉的感情,同時也豐富了城市記憶內涵。“艾德萊斯花紋上的東西都是來自大自然的美”,這種真實的山水與抽象的設計理念為觀眾構筑了城市記憶的大廈。
《伊犁河》中主人公日常生活敘事作為一種儀式,觀眾看到的不僅僅是個體故事的表述,更是伊犁城市固有的儀式表征。“儀式首先是社會群體定期重新鞏固自身的手段,當人們感到他們團結起來了,他們就會集合在一起,并逐漸意識到了他們是道德統一體,這種團結部分是因為血緣紐帶,但更主要是他們結成了利益和傳統的共同體。”[2]日常聚會是生活中的儀式符號,《伊犁河》第六集的“不問西東”中于成忠經常與商業朋友舉行聚餐活動是典型的儀式活動。圓桌上擺放著自家生產的果蔬,來自不同國家的客人們以一種輕松愉快的方式在餐桌上完成了商業交流。果蔬與菜肴以一種符號的形式出現在儀式化的交流中,使于成忠與商業伙伴的友情得到深化,客人們對伊犁市的記憶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加深。正是古麗娜蘭木與于成忠這類人物的儀式活動促成了伊犁市記憶的書寫與傳播。
二、記憶保溫:紀錄片對城市記憶的空間生產
最占空間的往往是記憶,但最值得記憶的往往又是空間。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世界上出現過各種各樣不同類型的地點:推動事態的敏感地點、發號施令的政務地點、熱鬧繁華的商務地點、知識文化的匯聚地點,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具有高度象征意義的地點。當人們置身于或感知這樣的記憶空間,便會油然而生回憶或緬懷之情,記憶大門隨之打開。在生產記憶的過程中,紀錄片批判性地將記憶符碼注入記憶空間,以期在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建立聯系與意義。紀錄片作為城市記憶空間生產的主體之一,在其生產空間時如何通過敘事構建城市記憶?日常生活作為敘事主要內容又是如何產生城市記憶的呢?
(一)媒介敘事與城市記憶
近年來,城市記憶的媒介敘事從多方面展開,從西方現代性和中國現代化諸多問題的批判,到地方文化和鄉村記憶的發揚,城市記憶的書寫呈現多樣的敘事方式,構建了不同的城市記憶與記憶中的城市。城市空間不僅僅是現代都市生活的場所,還是紀念城市記憶的社會空間,成為構筑現代人精神和情感的家園。在阿斯曼看來,“文字、媒介、檔案館、紀念碑等載體保存、記錄過去的歷史而具有的記憶空間和文化記憶功能”[3],現代化的城市空間也成為文化記憶空間。
在《伊犁河》第二集“物阜民安”中,冉玉枝的父親是伊犁第一個試種薰衣草的種植戶。在父親去世后她接過父親的衣缽繼續種起了薰衣草,對她而言薰衣草不僅是謀生的工具,更是父親影響她的一種媒介,“我覺得他要堅持的東西是不會錯的”。冉玉枝通過薰衣草的種植來紀念父親,換句話說薰衣草這種媒介連接了她與父親互動交流的記憶,薰衣草的種植不僅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同時還增加了伊犁市的旅游收入。每年薰衣草節的活動,都是人們了解伊犁市的亮麗名片,伊犁市也通過這個節事活動為自己城市構建了獨屬于自己的城市形象,同時人們也在活動中構筑了自己對伊犁市的記憶,二者相輔相成。
傳統手工藝也是《伊犁河》敘事的主要對象,在伊犁城市記憶的傳播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冉玉枝每年手工制作的薰衣草精油。薰衣草精油是芳香療法中最常用的一種,它完全取自薰衣草的花朵。隨著城市的發展與市場需求的增大,冉玉枝的同行大都選擇機器加工技術來萃取精油,在機械復制的時代,傳統的手工方法日漸式微。在伊犁市選擇手工萃取精油的人寥寥無幾,冉玉枝卻是其中之一。冉玉枝對薰衣草精油原始的提煉方法是父親傳下來的,精油提煉需用火燒灶蒸餾,在這部分中對火候的把握要求極為嚴格。在這片堅持傳統手藝的土地上,薰衣草與通過提煉薰衣草制作的精油是講述手工藝制作方式的一種媒介,它需要制作人的細心、耐心與恒心,與機器加工生產的東西相比,純手工煉制的精油更富有人情味。這種媒介敘事架構了伊犁市尊重傳統手工藝的城市形象,也記錄了冉玉枝對父親精神的傳承,復雜傳統精油制作方法也使觀眾感受到精油背后制作人的濃厚情感,更是將這份富有人情味的城市記憶印刻在觀眾的腦海。
(二)日常生活與城市記憶
日常生活實踐產生城市記憶,身體化的操演往往是記憶的核心,城市居民通過生活實踐傳播城市記憶。城市記憶如果失去日常實踐,就失去了創作源泉,也失去了靈魂。在記憶符號化的過程中,城市將自身的歷史、文化、精神特征與記憶相結合,使城市記憶在時代演進中得以傳承。
作為城市記憶的“保溫器”,《伊犁河》第四集的“城里城外”中,卡力大叔生活的伊寧市在不斷擴大,原有的田園生活方式也隨之改變。為了補貼日常家用,卡力大叔學習了傳統舞蹈——薩瑪瓦爾舞,每天身著薩瑪舞蹈服,頭頂大茶壺再做著各種不同的動作,在伊寧市休閑場所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閑暇之余,卡力大叔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去集市上精心挑選一兩盆花。落英繽紛間埋藏著卡力大叔濃郁的鄉愁,也開啟著融入城市的未來。卡力大叔成長的小院會逐漸消失在伊犁河畔,取而代之的是伊寧市的新景觀——伊犁河景觀帶。卡力大叔通過表演向觀眾傳遞伊寧市特有的薩瑪瓦爾舞,在城市生活的同時為當地居民和觀眾再現過去的傳統記憶,營造一種懷舊感,在受眾被感染的同時增強城市記憶的傳播效果。
冉玉枝以薰衣草為媒介架構與父輩的記憶,卡力大叔在日常生活的實踐操演中講述著伊犁市街邊的故事,他們是城市記憶生產的主體,正是因為他們在城市空間內的實踐構造伊犁市獨特的文化景觀。
三、記憶書寫:紀錄片對城市記憶的傳播創新
媒體對城市記憶的書寫不僅決定媒體呈現“擬態環境”的真實樣貌,同時會對城市空間記憶的主體——環境的接受者產生重要的影響。城市記憶作為連接城與人關系的紐帶,為人們提供歸屬感。《伊犁河》通過拍攝承載城市記憶的城市元素,單元化的方式講述人物故事,利用多主體的場景回憶喚起群眾的城市記憶,為群眾的記憶構建營造一個想象空間。在這一空間中,《伊犁河》是如何創新傳播方式實現書寫城市記憶的目的呢?
(一)單元化的傳播方式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人們越來越依賴媒體來傳播和記憶,扁平化和碎片化的傳播特征容易讓人們陷入“信息爆炸”和“信息焦慮”中,人們沒有時間去進行深度記憶。個體記憶集中下落的風險增加,城市記憶被窄化積累。城市中的群體被媒體剝離并編織在去中心化的網絡中,城市記憶面臨斷裂和離散的危機。《伊犁河》采用單元化、多維度的傳播形態,通過專業內容生產,有效地提高了城市記憶的傳播效果。《伊犁河》共分為六集,分別是“以夢為馬”“物阜民安”“山河動力”“城里城外”“大河之戀”和“不問西東”,每集中講述三至五個人物與伊犁市發生的故事。故事并非選取高大上的人物,都是城市的本地居民及移居者,單元化講述故事的方式不易引起受眾的審美疲勞,給觀眾留下深度記憶的時間與空間。
(二)場景回憶的傳播方式
除了多渠道的傳播方式構筑想象空間傳播城市記憶,《伊犁河》還通過場景回憶的方式,為受眾進行情感建構,同時也實現了記憶講述者和傾聽者間的對話交流。人們有更多熱情參與城市記憶生產,沒有記憶的地方是他鄉,有記憶留存的地方即是故鄉。“沙太有輛馬車,四匹馬拉的”是鄧攀初到伊犁時的印象,在這里他遇到第一位哈薩克族的老師……周邊的鄰居每天都會到他的商店里喝二兩小酒然后開啟每天的生活。老鄧與鄰居坐在小店旁閑聊,回憶自己初到新疆時的場景,這種場景的回憶對老鄧而言是具有時代烙印的,城市在不斷發展,參與者將過去與現在的記憶進行對比,在這種記憶中反思找尋未來,拓展了城市記憶傳播的邊界。
單元化的傳播方式將同類型的人物故事拼接在一起,讓讀者觀看后對伊犁市的記憶更加深刻;場景回憶是紀錄片常用的傳播方式,它讓記憶主體講述自己與城市間發生的故事,能夠讓觀眾清晰地看到城市發展的前后變化,視覺對比留給觀眾關于城市記憶的想象空間。
結語
紀錄片的制作與傳播深深影響著城市記憶的建構,它的發展豐富了城市記憶內容的素材庫,為時空上多維度城市形象構建提供了更多可能。《伊犁河》將伊犁河承載的文化記憶作為內容基點,通過單元化的傳播方式,將其與城市記憶結合起來,突破影視中城市形象議題圍繞敘事學、美學的局限性,拓寬了紀錄片中城市形象議題的表達,還能喚起社會群體在內容觀看后的共同記憶,對建構城市記憶、傳播新疆城市形象、講好中國故事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