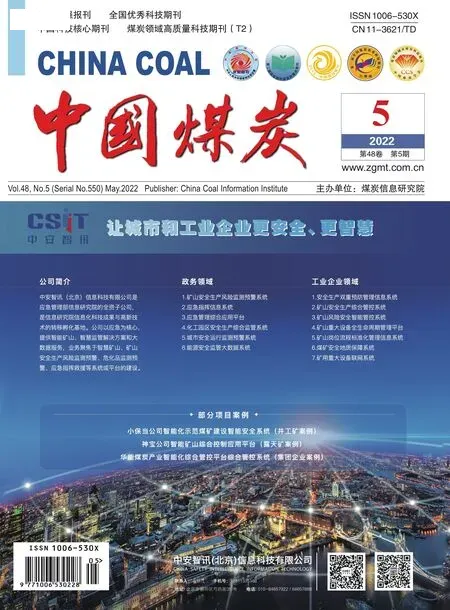礦業權出讓收益制度研究
曹旭升
(1.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北京市海淀區,100083;2.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北京市朝陽區,100025)
1 礦業權出讓收益制度的形成過程
礦業權出讓收益制度是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的產物,從2014年11月的最初制度設計,至2017年7月1日正式征收礦業權出讓收益,經歷了一個制度不斷演化和形成的過程。
1.1 國家層面相關政策鋪墊
2014年11月,國家發改委將《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上報國務院。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該意見第二十二條規定:“進一步深化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調整礦業權使用費征收標準。”
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首次提到礦產資源國家權益金制度。該方案第二十九條規定:“理清有償取得、占用和開采中所有者、投資者、使用者的產權關系,研究建立礦產資源國家權益金制度。”
2016年3月17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草案)》發布,其中第十二章規定:“保護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權益,公平分享自然資源資產收益。”第四十三章規定:“建立礦產資源國家權益金制度,健全礦產資源稅費制度。”
2016年11月29日,原國土資源部公布《全國礦產資源規劃(2016-2020年)》,其中第二章規定:“建立礦產資源國家權益金制度”,第三章規定:“建立礦產資源國家權益金制度,完善相關配套制度,保障國家所有者權益。”
1.2 《礦產資源權益制度改革方案》發布及其主要內容
2016年12月30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礦產資源權益金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方案》)。
2017年4月13日,國務院印發國發〔2017〕29號《國務院關于印發礦產資源權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以下簡稱“29號文”),全文照發了《方案》內容。
《方案》第二條規定:一是在礦業權出讓環節,將探礦權采礦權價款調整為礦業權出讓收益;二是在礦業權占有環節,將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整合為礦業權占用費;三是在礦產開采環節,組織實施資源稅改革;四是在礦山環境治理恢復環節,將礦山環境治理恢復保證金調整為礦山環境治理恢復基金。
1.3 《礦業權出讓收益征收管理暫行辦法》的出臺
2017年6月30日,財政部和原國土資源部根據29號文的規定,發布《關于印發<礦業權出讓收益征收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財綜〔2017〕35號)(以下簡稱“35號文”),對礦業權出讓收益如何征收做出了8條限制性規定和29條具體規定。35號文第二條規定:“礦業權出讓收益是國家基于自然資源所有權,將探礦權、采礦權(以下簡稱礦業權)出讓給探礦權人、采礦權人(以下簡稱礦業權人)而依法收取的國有資源有償使用收入。礦業權出讓收益包括探礦權出讓收益和采礦權出讓收益。”根據該條規定,國家對自然資源享有所有權,可依法收取國有資源有償使用收益。
1.4 35號文出臺前后實際情況的變化
礦業權出讓收益制度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由于環保、審計等原因,眾多礦業權因生態紅線、自然保護區、環保不達標等被關停退出。
我國隨著多次資源整合,通過優勝劣汰,礦業權人基本素質大幅提高,綠色礦山、智慧礦山建設方興未艾。但現在持有礦權的礦業權人普遍存在支付礦業開采前高額礦業權出讓收益的困難。
礦業權出讓收益于2017年7月1日在非油氣礦種中開始征收后,我國非油氣礦產資源勘查投資從2013年的460億元[1]下跌到2020年的161.61億元[2],下跌64.9%。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探礦權人在查明礦產資源時,勘查投入越多,繳納的探礦權出讓收益就越多,加重了礦業企業負擔。影響了我國礦業的高質量發展,對保障我國礦產資源安全不利。
因此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的大背景下,在構建新發展格局,做好“六穩六保”的國內經濟形勢之下,尤其在2021年礦產品價格大幅波動和我國已經將礦產資源安全上升為國家安全的今天,調整礦業權出讓收益制度,有利于激發探礦投資和采礦投資動力,為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礦產資源保障。
2 征收礦業權出讓收益引起的一系列問題
2.1 法律相關的問題
礦業權價款是基于國家出資查明礦產地而收取的投資補償,而礦業權出讓收益是基于國家對礦產資源享有所有權而征收的權益分成。35號文把基于國家出資探明礦產地而收取的補償性礦業權價款,調整為國家為實現礦產資源權益而征收的礦業權出讓收益。
礦業權出讓收益這一新的法律術語的出現,導致之前通用的法律、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與該法律術語匹配性差,而與之配套的規定并未出臺,從而導致新舊制度銜接不暢。現《礦產資源法》、國務院240號令至242號令作為35號文的上位法,雖然正在修改,但并未廢止,35號文作為下位法已經突破了上述上位法的規定。
2.2 其他相關問題
(1)溯及既往和一刀切。35號文規定,補交礦業權出讓收益最早可以溯及到2006年9月30日。這種溯及既往補交讓經歷國際礦業低谷后的中國礦業更加困難。同時,根據35號文的規定,現在新礦與老礦、探礦與采礦、常規與戰略、國家出資與企業出資、探明與預測、富礦與貧礦、共生與伴生、深部與淺部、特殊與一般、高風險與低風險、采選難與采選易、大礦與小礦等,一刀切地收取礦業權出讓收益,也導致探礦和采礦的積極性下降。
(2)市場價格倒掛。開采之前的礦業權評估價高于進入開采階段的礦業權市場價,導致礦業權出讓一級市場與礦業權轉讓二級市場價格普遍倒掛,礦業權交易市場冷清。現在開采年限超過30 a的礦業權,必須按30 a的評估結果計算平均礦業權出讓收益后,再累計計算出全部開采年限的礦業權出讓收益,也背離了審計制度。
(3)導致探礦積極性下降。礦山的開發需要一個漫長的周期,絕大多數礦業權人會被市場淘汰。“美國紐芒特礦業公司的一項內部研究表明,如果把每一個勘探礦權都視為一個項目,歷經多年的勘探和可研,國際上最終建成礦山的比例大約只有千分之一[3]。” 國際成熟礦業國家在探礦權階段不收取權益金,僅在生產環節征收權益金[4]。而35號文規定不但探礦權階段收取探礦權出讓收益,而且采礦權出讓收益要在取得采礦許可證之前收取;同時,繳納礦業權出讓收益與取得礦業權許可證掛鉤,這就導致我國探礦積極性下降,探明儲量無力轉采,且沒有采礦許可證就無法融資。
(4)授權不甚合理。35號文授權各省市自治區制定各自的基準價或基準率,這導致各地的征收標準、期限、首付金額、儲量標準等各地不一,同一礦種的征收標準差距懸殊。如:黃金的基準價最低1.5元/g,最高21元/g,相差14倍。導致相同品位相同開采條件的礦業權在不同地域的生產成本懸殊巨大,人為制造了成本壁壘,不利于我國礦業的高質量發展。
(5)影響我國礦業“走出去”。我國礦業“走出去”的步伐并不穩健,我國的礦業權出讓收益制度正在被我國礦業“走出去”目的國效仿,將會使得我國礦業“走出去”更加舉步維艱。在我國礦產品總需求持續增加、礦產品進口總額不斷攀升,以及目前國際復雜環境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大背景下,我國若不調整礦業權出讓收益制度,一旦我國對外依存度高的礦種斷供或成倍漲價,我國實體經濟將因原材料供應問題受到很大影響。
3 政策性建議
35號文作為部級行政規范性文件和暫行辦法,即將實施5周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修改和礦政改革的今天,應當對礦業權出讓收益制度重新審視和評估。
3.1 建議將稅、費法定原則和具體的稅、費項目寫入正在修改的礦法之中
一項基本制度的形成,需要長期的摸索和實踐。礦業權出讓收益制度的建立,從2016年12月30日中央文件到2017年4月13日國務院29號文再到2017年6月29日的35號文,不足7個月的時間就形成了一項重要的礦政管理制度,難免會存在一些問題。
前已述及,35號文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35號文實施之后,礦業行業經過優勝劣汰已經得到凈化。從這一角度說,35號文的實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在國內外礦產資源供需發生巨大變化的當下,35號文已經完成了暫行使命。
稅、費制度是國家的基本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稅收基本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由法律規定,因此,與礦業有關的稅、費制度應當寫入正在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之中。
3.2 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修改時,用礦業權出讓金替代礦業權出讓收益
礦產資源對保障國民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并且礦產和煤炭、石油、糧食一樣都是國家賴以生存的初級產品,因此礦產安全涉及國家安全。而如果繼續實施35號文,將導致我國探礦采礦積極性雙雙下降,影響礦業高質量發展和國家礦產安全,目前我國急需的礦產品對外進口依存度和集中度持續增高,由此建議廢止35號文。
2022年5月6日,全國人大官網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的修改已經列入全國人大2022年度的立法計劃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修改稿中已經加入了“礦業權出讓金”這一收費項目,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的修改得以通過,用礦業權出讓金替代礦業權出讓收益將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