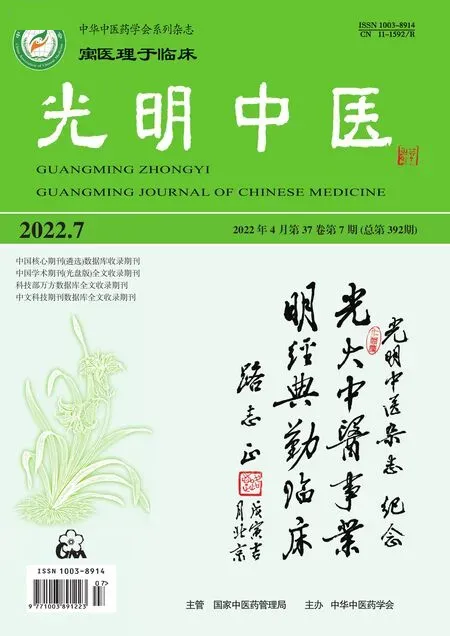從圓運動理論探討四逆散在腎系疾病的應用*
王寧玥 杜雨芃 林 燕△
“圓運動”一詞由清末民初醫學家彭子益提出。他以“天人合一”思想為基,以河圖象數之理為要,建立了“中氣如軸,四維如輪,軸運輪行,輪運軸靈”[1]的人體圓運動模型,并應用這一理論闡釋了人體生理特點、病理機制及選方思路。彭氏善從氣機角度論方,如論理中湯所治之證,為中軸停運,四維升降倒作,而致上下左右俱病,方中四味藥均為溫中、燥中之品,意在復軸運則病瘥。以此析理簡潔明了,頗具新意。四逆散是調和臟腑氣機升降運動的基礎方劑,臨床上亦常應用于腎系疾病的治療,故結合圓運動理論就四逆散在腎系疾病的應用略作淺述,以期明晰其作用機制,拓寬辨證應用思路。
1 圓運動理論
1.1 道法自然 運氣為圓《道德經》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天地萬物所遵循的客觀規律。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是天地萬物屬性的高度概括。彭子益論陰陽,謂孤陰直降,孤陽直升,陰陽交合,則升已而降,降已而生,環周不休,而生中氣,如此才會有生命的產生;《素問·天元紀大論》指出:“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自然界萬物的產生和演化,依靠大氣在天地間無休止的升降運動。一年中季節的變化是太陽熱量在地面、土壤中運動的結果,具體表現為春升夏浮,秋降冬沉,周而復始,夏秋之間,升降交合,則中氣化生;自然界的生物順應四季規律,隨一年中大氣的變化表現為生長化收藏。世間萬物皆由圓運動所生,同時也都遵循圓運動的規律。
1.2 法天則地 順應自然《素問·寶命全形論》言:“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與天地相參,人體氣機運行亦應圓運動法則。在君相二火的推動下,脾胃居中央如軸之運旋于內,其余臟腑如輪之升降于外,每一維相表里的臟腑又在經絡的聯通下組成各自的圓運動。無論軸輪的哪一部分運動失常,最終都會影響整體,圓運動的平衡被打破,則疾病叢生。
1.2.1 臟腑相合 升降相因人秉天地五行之氣而生臟腑[1],互為表里的臟腑生于同一大氣,具有相同的生理特性。氣血在經脈內運行流通,六氣通過經脈聚于臟腑,表里臟腑通過經脈相互絡屬。經氣運動一升一降,合為一圓運動,其運動規律與經絡循行的方向有關。如腎與膀胱同屬水氣,具封藏之性,然足太陽經與足少陰經的經氣運行方向一下一上,故膀胱壬水,其經氣的封藏之性自上而下;腎為癸水,其經氣的封藏之性自下而上[2]。一經病變,可致相表里的臟腑經氣運動失常,進而因氣機不調而致本臟本腑的病變,最終影響其余臟腑的氣機運行和功能活動。
1.2.2 中氣斡旋 脾胃為樞土氣居大氣升降之中,脾胃秉土氣而生,故脾胃居人體圓運動的中心,為人體圓運動的軸樞。其中,脾氣上升,胃氣下降,兩者升降相因,形成一圓運動,帶動著其余四臟的氣機運行。黃元御評價脾胃斡旋氣機的作用:“脾升則腎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則心肺亦降,金水不滯”。脾為諸升之關,胃為諸降之門[3],中軸旋轉停滯不僅可見腹滿、呃逆、痞滿等本臟病,還可因清濁不分致使精微下泄,痰濁上蒙,而見尿濁、眩暈等證;中軸升降失常,則外輪升降無序,可致木氣郁結,肺不肅降,心火上浮,腎寒陽微。
1.2.3 四維周旋 升降有序肝腎居人體下焦,心肺居人體上焦,在下者必升,在上者必降,《素問·五運行大論》云:“上者右行,下者左行”,故言“左升右降”。心腎水火相交,心火下降,溫暖腎水,腎水上升,滋潤心火,腎水需肝木溫升得以上承,心火需肺金涼潤得以下行[4]。肝肺皆主司氣的運行,肺氣右降,肝氣左升,升降得宜,則全身氣機舒展[5]。若肝肺升降失常,一方面會擾亂脾胃之升降;另一方面則心腎無以交通。心腎為氣機升降的根本,水涵則木榮,火旺則伐金,脾胃亦需水火交濟而潤燥相宜[6,7]。
1.2.4 君相二火 周流不已自然界中相火為太陽輻射地面的光熱,君火為地下上升的熱量,在人體亦有此二火。膽、心包、三焦皆歸屬于相火,相火得降,需金氣收斂,中氣運化;相火下行,中氣即運,金氣涼降,水氣封藏,水中有火。水中之火,是中氣之根。相火借肝木之氣溫升,由升而浮,則生君火,君火升極而成相火,如此周流不休,為人體圓運動的動力。
2 四逆散證治機制
2.1 四逆散方證溯源四逆散首見于仲景《傷寒雜病論》少陰病篇:“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為治療陽郁肢厥的基礎方。本方由柴胡、芍藥、枳實、炙甘草組成,重在調和肝脾,暢達氣機,透解郁熱。如出現或然證,則需根據方后注加減用藥,使效力更專。
2.2 以圓運動之理析四逆散四逆散為調節氣機的經典方劑,旨在恢復一身之氣的正常升降,恰合“軸輪并運”的復圓思想。在疏利氣機的同時,不忘培補中州,順勢而治,以平為期。
2.2.1 疏木養木 推動輪行四逆散是疏木運土的基礎方,柴胡疏肝散、逍遙散等常用的疏肝方劑皆由此加減而成。方中柴胡能“降膽胃之逆,升肝脾之陷”(《長沙藥解》),疏肝木之郁滯,散膽木之郁火,調節肝膽的疏泄;芍藥“味酸能養肝血,味苦能瀉膽火”(《醫學衷中參西錄》),與柴胡相伍,能防其“劫肝陰”之弊,使疏中有斂,散中有養,降甲木,舒乙木,意在恢復肝膽的一圓運動。
2.2.2 調和中州 啟脾胃之樞方中四藥皆與脾胃相關,《神農本草經》謂柴胡“善達少陽之木氣,則少陽之氣自能疏通胃土之郁,而其結氣飲食積聚自消化也”,以木能疏土,肝氣升發則脾氣得升;枳實為行氣破結,瀉痞消滿之品,與柴胡一降一升,啟脾胃樞機,使清氣得升,濁氣得降;甘草為調補中氣之品,又兼調和之性,佐升達之味則入肝脾,輔斂降之品則入肺胃[8],與柴胡、枳實相配,調和氣機的運行;與芍藥相伍,酸甘化陰,益氣養血,培土補虛。中氣健運則氣機升降有根,氣路暢通。
3 四逆散治療腎系疾病應用探析
朱丹溪言:“人生諸病,多生于郁”,臨床上許多醫家善從氣論治各種疾病。四逆散配伍精當,藥簡效宏,常用于治療以下腎系疾病。
3.1 腎性蛋白尿“蛋白”屬人體精微物質的范疇,精微的正常輸布有賴于氣機正常的升降出入。若中軸運轉失司,脾氣不升,精微下泄,胃氣不降,下焦不能封藏[3]則可見尿濁。肝膽失疏亦是本病的重要病機,肝氣上升,膽氣下降,心腎水火才能正常交通。膽經不降則相火不降,腎水寒則封藏失職;水中無火,可致中土失根,中氣衰弱,軸運失常。木氣乘土可直接影響脾胃的升降運動,影響水谷精微的正常輸布。四逆散疏利肝膽、調和脾胃,尤宜慢性腎病證屬肝膽氣滯、肝脾不和者,此類患者多伴情志不舒,胸脅脹滿,口干口苦,脘腹不舒等癥狀,常因氣機郁滯,陽氣運行受阻而見手足不溫,卻可見薄黃苔等熱象,脈象以弦脈多見。治療過程中,在使用四逆散樞轉氣機的同時,常根據兼證的不同加減化裁,腎虛者加菟絲子、枸杞子滋補肝腎,氣虛明顯者加人參、黃芪增益氣健脾之功,熱證明顯者加黃芩、黃連,瘀血停聚者加活血祛瘀之品[9],諸藥配合以助氣行,使氣機順暢,津血流轉,氣血乃和。腎絡得養,腎臟的生理功能得以恢復,水液精微輸布亦循常道。
3.2 尿路感染膀胱為州都之官,水液聚集之處,尿液的正常排泄需膀胱通利,膀胱通利需全身氣機的通暢。《黃帝內經素問集注》謂:“肝主疏泄水液,如癃非癃,而小便頻數不利者,厥陰之氣不化也”,木陷土濕是本病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土虛為發病之本,木郁為病起之標。患者因情志失調致肝木疏泄失職,氣行不暢,進而影響膀胱的氣化、開闔功能;肝木郁陷,脾濕下注,在下之相火不得正常升溫,熱灼膀胱,又會加重淋證的表現。本方常用于尿路感染急性發作期,證屬肝氣郁結者,此時以氣滯、濕熱等實證為主,多見尿路刺激征、排尿不暢、小腹拘急等癥狀,常因情志不舒而誘發。《長沙藥解》謂柴胡:“乙木下陷而生熱者,凡諸淋濁泄利之類,皆有殊功”,因其能降少陽之逆,升厥陰之陷,與枳實、芍藥、炙甘草合用,暢達氣機,補中散熱,使熱退郁消,復氣機升降之舊。芍藥甘草相配,酸甘化陰,柔肝止痛,對改善尿路感染引起的尿痛有良好的效果[10]。四逆散在治療本病時,多加用連翹、生地榆、石韋等清熱利濕之品,祛濕以健脾,清熱以達木[11]。
3.3 泌尿系結石泌尿系結石屬中醫“石淋”范疇,劇烈腰痛、血尿、排尿中斷是其主要的臨床表現。彭子益云:“劇痛者,人身陰陽二氣的圓運動不通也”[1],結石因濕熱蘊結,煎熬津液而生,砂石損傷脈絡,阻滯氣血運行而見諸癥。足厥陰肝經“循股陰,環陰器,抵小腹”,泌尿系結石引起的疼痛多屬肝經循行部位,故治療以疏利肝膽,開闔運樞為要。四逆散恰能開郁散結,緩急止痛,臨床應用時,本方多與金錢草、海金沙等排石通淋藥共用,現代藥理學亦證明本方有抗炎、松弛平滑肌、解痙止痛等作用,對改善疼痛癥狀、促進排石效果顯著[12]。
除上述病癥之外,在慢性腎臟病的后期,患者常因病久中氣不足,軸運失常而致濕濁瘀滯,肌酐、尿素氮等毒素在體內蓄積,毒素損傷臟腑,引起氣機逆亂,常見惡心嘔吐、食欲減退等消化道癥狀,運用四逆散升清降濁,暢達氣機,能有效地恢復脾胃的軸運功能,緩解胃腸道的不適癥狀[13]。
4 結語
“中軸旋轉停頓,四維升降倒作”[1]是彭子益先生對人身病理的精煉概括,臟腑氣機失常亦是尿濁、淋證等腎系疾病發生的重要原因。四逆散緊扣“肝脾氣機升降失常”的病機,升降相宜,疏斂得當,使中氣健運以復軸運,疏養木氣以正輪行,人體氣機得以正常運行。臨床應用四逆散時,需謹從病機,隨證加減,以恢復人體正常圓運動為目標,即可獲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