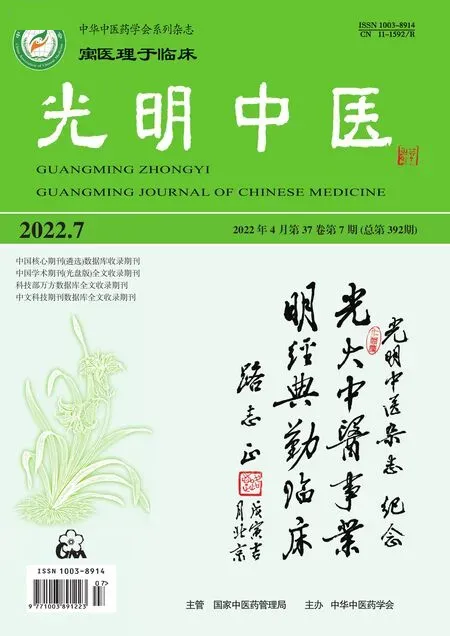淺析臟腑氣化在寒濕痹阻型膝骨性關節炎治療中的應用*
張麗芳 姜 燕 徐養紅 杜李偉 李 強 閆思佳 王小芳 高 楠 呂幸幸 徐云峰
骨性關節炎是一種常見的慢性骨關節疾病,多發于中老年人群。主要由于關節軟骨的非炎癥性退行性改變和繼發性骨質增生、關節邊緣有骨贅形成,從而發生關節疼痛、活動受限、關節畸形等臨床表現。此病多發于負重多的關節,其中以膝關節最為多見[1]。隨著社會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膝骨性關節炎的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其進行性加重的關節功能障礙,給社會經濟造成很大負擔。
1 膝骨性關節炎病因病機
膝骨性關節炎即中醫學所謂“鶴膝風”“骨痹”“痹證”等。膝骨性關節炎的發病首先因于臟腑虛弱。臨床上,多數膝骨性關節炎患者病因多為肝腎虛弱,寒濕痹阻經脈。《張氏醫通》:“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附,筋將憊矣。故膝痛無有不因肝腎虛者,虛則風寒濕氣襲之”。指出膝骨性關節炎發病的基礎原因是肝腎虛弱,風寒濕外邪侵襲。其中,肝為腎之子,母病可及子;且肝腎同源,相互資生,相互促進,腎虛則肝虛,故肝虛的根源也在腎虛。《中藏經》曰:“骨痹,乃嗜欲不節,傷與腎也”。進一步說明腎氣的虛弱與膝骨性關節炎的發病關系更為密切。《針灸甲乙經》云:“五臟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于合,故骨痹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腎……”,腎主骨,故腎氣的強弱與骨痹的發展最為密切,因此腎虛寒濕痹阻經脈是膝骨性關節炎的主要病機之一。
2 關于臟腑氣化與膝骨性關節炎
氣化理論是以系統論為指導思想的中醫學認識人體生命的哲學思維產物。中醫認為,氣是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種不斷運動的精微物質,是構成萬物的元素,一切事物的形成皆緣于氣的運動。
氣是物質存在的一種形態。大到無形的虛空,小至有形的萬物,均是氣的不同的存在形態而已[2]。《素問·六微旨大論》:“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說明氣化是氣的升降出入的運動及其運動所伴隨的能量轉化過程。
人體的真氣分布于臟腑,即為臟腑之氣。臟腑之氣是構成臟腑的最基本精微物質,也是推動臟腑進行各種生命活動的基礎。 《素問·六微旨大論》:“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各臟腑皆有氣化,臟腑之氣通過升降出入完成新陳代謝過程,實現臟腑的各自功能,因此臟腑氣化是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過程。臟腑之間的氣化存在于臟腑之間的協調活動中,各臟腑皆有氣化,其氣化的特點概括起來,即《素問·五臟別論》:“所謂五臟者, 藏精氣而不瀉也, 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
寒濕痹阻型膝骨性關節炎病機為腎臟虛弱,寒濕痹阻經脈,深而探之,腎臟的氣化功能不足在寒濕痹阻型膝骨性關節炎的發病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腎為先天之本,內含元陰元陽。同時腎為水臟,對機體水液代謝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3]。腎陰腎陽調節各個臟腑之氣,使臟腑功能協調,氣化之機通調,使氣血津液代謝正常進行。許叔微在《普濟本事方》云:“譬如鼎釜之中,置諸水谷,下無火力,雖終日米不熟,其何能化”?提出氣化之動力的來源在于腎,其中腎陽在氣化動力中發揮重要作用。《難經·八難》云:“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也指出十二經脈發源于腎間動氣,而腎間動氣是存在于兩腎臟間的熱能和動力,和腎陽密切相關。寒濕痹阻型膝骨性關節炎,與膝關節關聯的多條經脈經筋被痹阻,故治療時應重視經脈的發源處,重視腎間動氣和腎臟的臟腑氣化,加快病情的恢復。
3 關于腎虛寒濕痹阻經脈型膝骨性關節炎主要取穴
基于此,選取腎臟精氣輸布聚集于背部的腎俞穴治療膝骨性關節炎。腎俞穴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旁開1.5寸處,屬足太陽膀胱經,膀胱經為足太陽脈氣所發,絡腎屬膀胱,與督脈、手足三陽經相交會,故膀胱經可“諸陽主氣”。《素問·逆調論》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說明膀胱經有助益氣化功能,膀胱經氣化功能的發揮,與膀胱經諸陽主氣之功能、腎陽的虛衰有密切關系。腎俞穴可鼓舞腎間動氣,可補腎助陽,益腎強筋,促進生長發育和骨質代謝,促進經脈之氣通暢,可協調足少陰腎經,加強腎臟對機體氣化的主導調控功能,促進水液代謝和津液敷布,使膝關節之筋骨得到津液濡養而行使正常功能。
《靈樞·經筋》指出:“足太陽之筋……結于腘……足少陽之筋……上循脛外廉,結于膝外廉……足陽明之筋,上結于膝外廉……足太陰之筋,結于膝內輔骨……足少陰之筋……而上結于內輔之下……足厥陰之筋……上結內輔之下”。足之六條經筋都聚合于膝關節處,保持著膝關節周圍的力學平衡[4],保持著正常發揮膝關節各種運動的功能。《類經》曰:“筋雖主于肝,而維絡關節以立此身者,惟膝之筋為最,故膝為筋之府”。膝骨性關節炎發病與經筋病變密切,也與膝關節本身病變相關。《靈樞·經脈》:“膽足少陽之脈……是主骨所生病者……膝外之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指出膝骨性關節炎亦屬于骨所生病者,因此與足少陽膽經有密切關系。《難經》指出筋會陽陵泉,陽陵泉乃八脈交會穴之筋會,膽經下合穴。《玉龍歌》:“膝蓋疼痛鶴膝風,陽陵二穴方可攻”。故針陽陵泉穴,可舒筋通絡,調節筋之府之膝關節功能,促進膝關節骨代謝。另外,膽主生發,足少陽膽經亦可生發少陽陽氣,少陽陽氣可濡養膝關節部位的經筋,即《素問·生氣通天論》所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并且少陽之氣的生發,有溫陽利水之功,可促進水液代謝,促進臟腑氣化。故取陽陵泉穴還可協同腎俞穴促進臟腑氣化,促進膝關節功能的恢復。
膝關節功能的正常發揮有賴于氣血濡養,陽明為多氣多血之經,足陽明為五臟六腑之海,足三里穴為足陽明胃經之下合穴,有補益后天之氣功效。《素問·玉機真臟論》云:“五臟者,皆稟氣于胃,胃者,五臟之本也”。胃主受納,脾主運化,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胃強則氣血生化充足;脾主為胃行其津液,化生機體所需的精微物質,濡養臟腑,故胃為五臟之本,胃氣盛則五臟盛,胃氣衰則五臟衰。《素問·經脈別論》又云:“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于筋”。肝在體合筋,脾胃將飲食物化生的部分水谷精微,滋養肝臟,使肝血充足,膝關節經筋得養。《靈樞·四時氣》:“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提出寒濕痹阻經脈型膝骨性關節炎可取足三里治療。 針足三里可調動脾胃之氣,調動陽明生化氣血之功,加強氣化功能,使膝關節經筋得到充足的氣血濡養。《景岳全書》言:“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之有不足者,但得后天培養之力,則補天之功,亦可居其強半,此脾胃之氣所關乎人生者不小”。此段條文指出通過補益后天之力可達到補益先天不足的目的,因此,可通過胃之下合穴足三里來補益先天不足,即可補脾胃又可補腎氣。且補益脾胃之氣可運化水濕,加強臟腑氣化和水液代謝功能。
4 驗案
案1 鄭某,男,60歲。雙膝骨性關節炎3年,右側為甚。患者3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雙膝關節疼痛,右膝為甚,勞累后加重,臥床休息后緩解,右膝活動受限,納可眠可,二便可,舌淡暗,苔白膩,脈細。專科檢查:右膝關節呈屈曲內翻畸形,膝關節屈伸活動受限,右膝關節活動度減小,雙膝關節活動時于髕骨下方可觸及骨摩擦感。雙膝關節浮髕試驗(+) 抽屜試驗(-),右下肢可見迂曲靜脈。雙膝關節皮膚正常,右側膝關節皮膚溫度較涼。雙膝關節腫脹變形。證屬腎虛寒濕痹阻經脈。治以祛寒除濕,補腎舒筋通絡。溫針灸雙側腎俞穴、右內膝眼、右外膝眼、右陽陵泉、右足三里。針刺手法平補平瀉,針刺后針柄插艾條溫和灸,留針30 min,每日1次。 針2次后活動受限緩解,繼針5次后右膝關節活動有輕松感,右膝活動較前范圍增大,癥狀明顯緩解出院。
案2 趙某,女,66歲。間斷性左膝關節疼痛1年,加重伴活動受限20 d。患者1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間斷性左膝關節疼痛,上、下樓梯時左膝關節疼痛加重,左膝關節有摩擦感,勞累后加重,臥床休息后可稍緩解,未做特殊治療。近20 d無明顯誘因出現上、下樓梯時左膝關節疼痛難忍,呈持續性,不能行走,嚴重影響日常生活。患者自發病來神志清楚,夜間雙小腿酸困、抽筋,以左小腿為甚,納可眠可,二便常,舌淡苔薄白,脈沉細。查體:左膝關節腫大畸形,局部壓痛(+),左膝關節研磨試驗(+),左膝關節屈伸活動不利,側方加壓試驗(+),左膝關節髕骨兩側凹陷存在,左膝關節皮膚溫度正常,左膝關節皮膚顏色正常,左膝關節抽屜試驗(-)。膝關節CT檢查示:膝關節對位尚可,左膝內側關節間隙變窄,關節面硬化,西醫診斷為左膝骨性關節炎。中醫證屬腎虛寒侵,經脈痹阻。治以溫針灸溫陽散寒,補腎通絡。取穴:左內膝眼、左外膝眼、左足三里、左陽陵泉、雙側腎俞穴,溫針灸,留針30 min,日1次。內膝眼、外膝眼在屈膝位時髕韌帶兩側的凹陷處取穴。其中內膝眼向外針刺,外膝眼向內針刺,刺入膝關節囊。針刺輔以艾灸,利用艾葉燃燒產生的熱量,通過針灸針傳導至關節囊,直達病所,起到溫陽散寒、祛濕通絡、通利關節的作用,達到“通則不痛”的目的。此為治膝痛之標,經治療8次后,上、下樓梯時左膝疼痛緩解,左膝活動好轉出院。
按:上述2則驗案,患者骨痹日久,腎臟虛弱,津液輸布失常,筋脈失養,導致濕結于內,聚為腫痛。當此之時,加強腎臟臟腑氣化,使水液代謝正常,津液正常輸布,方可恢復膝關節正常功能。臨床上,艾灸治療膝骨性關節炎療效尚佳,被廣泛應用于臨床。有學者研究發現, 艾灸腎俞、足三里對類風濕關節炎模型大鼠滑膜組織中EPK1/2、Ras、和Raf蛋白表達有影響,能減輕滑膜炎性反應[5]。因此針刺結合艾灸,可緩解所在病位的組織粘連、瘢痕等,改善微循環,加速血流速度,增加穴位血流灌注量[6],消除無菌炎性物質,減輕水腫,緩解疼痛,恢復膝關節功能。故溫針灸腎俞、足三里、陽陵泉,補腎舒筋通絡,調動氣血生化,加強臟腑氣化,腎氣足則氣化足,氣化足則筋柔,筋柔則膝健[7],此為治膝痛之本。如此標本兼治,補腎通絡,加強機體臟腑氣化狀態,使氣血津液正常代謝,膝關節得以濡養,膝關節活動功能得以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得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