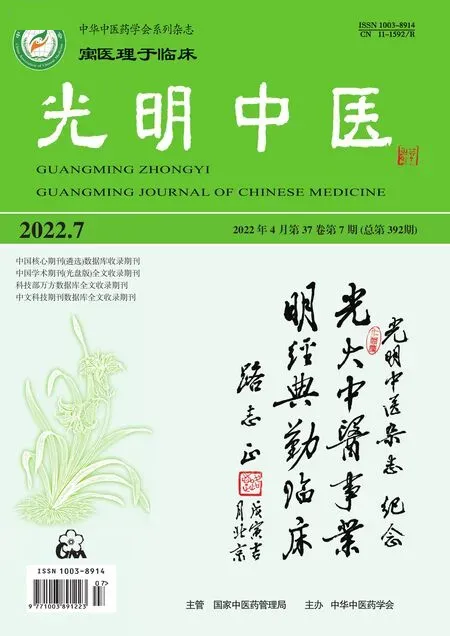基于五行思維模式辨治肺系疾病*
李 剛 韓 雪
陰陽五行是古代哲學的重要思想,自古以來根深蒂固的尚五文化及古代先民以象隱喻為主導的認知世界的思維方式成就了五行學說的發生發展[1]。五行學說作為中醫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描述了特定系統內部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早期五行學說主要體現在五行的單一對應性和五行生克的有序性,生克關系模式過于簡單,不能夠全面反映復雜事物的復雜聯系,為此,中醫學在應用五行學說時一直不斷地對其進行調整[2]。中醫五行思維模式是建立在中醫五行學說基礎上的一種辨證思維體系,依據臟腑五行生克制化規律,依據臟腑之間關系及臨床表現推求疾病的病因病機為臟腑辨證的一種延伸,并為臨床提供一種新的診療思路。
1 理論依據
1.1 中醫五行思維模式的理論來源及內涵五行學說最早見于《尚書》,作為一種認識世界、探索宇宙規律的思維方式,而被應用到各個領域。五行思維模式是基于陰陽五行學說及人體五臟特點而產生的一種思維方式,重視及強調臟腑特性為其主要特點。《黃帝內經》將五行理論與藏象理論結合起來,實則是將五行的系統思維方式引入藏象理論的構建中,用五行類比五臟的生理、病理,形成了中醫五行思維模式[3]。在普遍哲學意義上的五行學說中五行生克是單向的、不可逆的,相對較為機械,五行學說應用于中醫學后,對其系統性做了進一步分析,生中有克、克中有生,處于一個不斷往復循環之中。中醫五行思維重在描述臟腑間的關系,也是對臟腑辨證的進一步完善。中醫的五行不僅僅著眼于人體自身,結合四時、四方、六氣的變化,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因此中醫的五行思維是囊括天、地、人為一體的綜合辨證體系。鄧鐵濤說:“中醫的五行生克,不應簡單地把它視為循環論、機械論。它包含著許多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關系,實質是臟腑之間、人與環境之間、體內各個調節系統促進和抑制之間的關系”[4]。
1.2 臟腑不均衡是中醫五行思維模式構建的基礎中醫是以五臟為中心的整體觀,然而各臟腑并不可等量齊觀,各有自身的特點,取類比象是中醫學認識自然與人體的一個重要方法。臟腑地位不均衡思想可追溯到《黃帝內經》,通過將五臟在人體中的作用與不同的官職相類比,如心者,君主之官;肺者,相傅之官……首次明確提出不同臟腑在人體所處不同的地位及作用。其中“貴賤”言主從關系,體現五臟的不平衡性;明代兒科醫家萬全提出“二有余三不足”理論,即“五臟之中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腎常虛,心熱為火同肝論,嬌肺易傷不易愈”,進一步補充完善臟腑不均衡的觀點。臟腑不均衡的產生,除了臟腑自身的特性外,個體間差異也是臟腑不均衡的重要方面,就某一個體而言,體質不同單一臟腑在機體所處的生克乘侮地位也不同,如木旺體質則易克金,木虛則金侮之。體質學將人劃分為五體人,利用五行相互之間生克制化的聯系和規律,可以有效地預測疾病的發生發展方向[5]。
1.3 中醫五行思維模式的本質是一種動態平衡觀五行,《尚書·洪范》指五種不同的運動狀態,這種運動狀態在人體則體現在臟腑的運動趨向,中醫的五行亦是各臟腑氣機升降出入的一種描述。任何疾病的發生都是機體失衡的表現,《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其治療最終目的使其歸于“平”的狀態。陰陽平衡是人體最佳的一種狀態,五行間通過生克制化最終使機體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即五行系統內部的自穩動態協調機制。臟腑五行間相互制衡,貫穿到生命發展的始終,在生理狀態下表現為五行相生相克,在病理狀態下則表現為五行相乘相侮。乘侮傳變是指臟腑疾病發生相克太過或反克關系的病變,并在這種不斷的生克制化關系中實現自我調適。世界是一個聯系的整體,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在不斷制衡中達到自身與外界的平衡。五臟要維持機體的平衡,臟腑亦需不斷地通過相互制衡,并通過臟腑間不斷生克制化而達到一種動態平衡。
2 肺與四臟的關系
五臟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五行生克傳變雖有其特定的規律,臟腑的不均衡性,決定臟腑五行生克乘侮非等次性,肺為嬌臟,因其特性而易受其余四臟之凌侮,清代程國彭在《醫學心悟·第三卷·咳嗽》中說:“肺為嬌臟,攻擊之劑,即不任受,而外主皮毛,最易受邪”。臨床中肺系疾病的發生要明顯高于其他臟腑。以下從五臟生理病理特點,闡述肺與四臟的生克乘侮關系。
2.1 相生關系
2.1.1 肺與脾中醫對于肺、脾關系的認識:肺屬金,脾屬土,在五行中為子母關系。脾胃為后天之本,肺的生成和發育皆賴后天之本以濡養,《素問·經脈別論》 曰:“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于脈。脈氣流經,經氣歸于肺”。肺氣的肅降的正常與否,不僅關乎肺臟本身,亦與中焦氣機的調暢有密切關系,圓運動理論認為:中焦為樞,四肢為軸,人身之氣機全賴中焦脾胃氣機之斡旋,降胃即降肺,臨證治療以通腑理氣為法。肺受脾胃運化之精微以養之,中焦之濁氣,亦可以氣血為媒介而上侵于肺,脾健則血自清、濁自去。中醫認為肺與大腸相表里,腑通亦有利于肺之肅降,大腸則構成肺與脾胃連接溝通的橋梁,肺氣不降影響大腸之氣的下降而導致土壅,瀉土亦可安肺金,腑氣通而肺氣通降有路,正如《素問·五常政大論》:“病在上,取之下”,為肺病治腸提供了理論依據。《雜病源流犀燭·咳嗽哮喘源流》云:“蓋肺不傷不咳,脾不傷不久咳”,指出脾傷是久咳的一個重要病因,宜“培土生金”之法,可予六君子湯、二陳湯加減以絕生痰之源。研究表明:培補后天之本,不僅可以提高機體免疫力,還能改善肺部血液循環,有利于炎癥吸收和治愈[6]。
2.1.2 肺與腎中醫對于肺、腎關系的認識:肺屬金,腎屬水,二者為相生關系。腎為先天之本,內涵元陰元陽,為五臟陰陽之本,五臟之陽非此不能發,五臟之陰非此不能滋;雖曰金能生水,然肺金亦有賴于腎水的滋養,《醫醫偶錄》中有云:“肺氣之衰旺,全恃腎水之充足”。肺衛為人一身之藩籬,其根源于下焦之元陽,《靈樞·營衛生會》云:“營出于中焦,衛出于下焦”。衛氣的生成、循行、發揮功能皆不離腎,衛氣功能的強弱取決于腎氣的盛衰[7],而肺金的斂降有利于陽氣及陰津下歸于腎水之中,二者相互滋生,互相為用。腎者主水,凡痰飲之生成亦不離腎,李用粹在《證治匯補》中說:“痰之源,出于腎,故勞損之人,腎中火衰,不能收攝,邪水、冷痰上泛”,補腎調腎乃為治療痰飲的治本澄源之法[8],方以濟生腎氣丸溫腎化氣、利水化飲。經言“五臟之傷,窮必及腎”,久病及腎,腎氣不足,失于攝納,不能引肺氣下行以歸元,從而導致氣機上逆于肺而致咳嗽,或腎陽不足,易出現水寒金寒,肺寒則易感寒而咳[9]。
2.2 相克關系
2.2.1 肺與心中醫對于肺、心關系的認識:肺屬金,心屬火,二臟為相克關系。心主血,肺主氣,氣與血可分而不可離,《靈樞·邪客》曰:“宗氣積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宗氣乃溝通心肺之橋梁。心主火,其性炎上;肺屬金,居身之高位,以肅降為順;火能克金,心火多夾肺氣上逆,而為咳為喘,《陳平伯外感溫病》王孟英按:“溫熱為陽邪,火必克金,故先犯肺,火性炎上,難得下行”,指出火性上炎,克伐肺金的機制。正如王肯堂曰:“火乘肺者,咳嗽上壅,涕唾出血,甚者七竅出血”。其治當急以苦寒降其心火,《素問·藏氣法時論》有:“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根據五行理論,火、苦均與心相對應[10],方以葶藶大棗瀉肺湯為代表。倘心陽不足,無以克制肺金,肺飲凌心,亦可見咳喘上氣,輕者甘草干姜湯以溫心肺之陽,重者可用麻黃細辛附子湯加葶藶子以強心利水,臨床中重癥肺炎的發生與轉歸多伴有心功能的異常,心不強則肺難愈,應重視心肺二臟關系。
2.2.2 肺與肝中醫對于肺、肝關系的認識:肺為金,肝為木,二臟為相克關系。肝為剛臟,將軍之官,性暴急;肺者相傅之官,比之臨床則多木火刑金之證。五臟之氣機調暢皆賴于肝,氣機不暢則百病生,誠如朱丹溪所言:“氣機調暢,百病不生,氣機一郁,諸病生焉”;肝咳多呈陣發性、痙攣性咳,甚則涕淚俱出;肝體陰而用陽,陰不斂陽,則肝陽上亢,肝氣通于目,肝氣上迫,肝液上涌則為淚;肝血上逆則面赤而頸脈怒張;肝火傷及目絡則目睛充血;肝火灼傷肺絡則咯血、鼻衄;咳引兩脅作痛為肝咳之征[11]。清代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云:“人身氣機合乎天地自然,肺氣從右而降,肝氣由左而升,肺病主降日遲,肝橫司升日速,嗆咳未已,乃肝膽木反而刑金之兆”。指出陣發性嗆咳為木火刑金之兆的病機,治宜疏肝柔肝斂肝為法,方以四逆散加減,若肝氣上逆較甚,佐以鎮肝之法;若陣咳較甚,佐以地龍、全蝎、蜈蚣等解痙之藥。
3 典型醫案
劉某,男,2歲6個月。主訴:反復咳嗽半個月,加重伴咳憋1周。現病史:患兒半個月前出現咳嗽,有痰,以輕咳為主,無發熱、喘息等,予對癥治療效欠佳;1周前患者咳嗽加重,呈痙攣性咳,伴咳憋,無流涕,痰少,無喘息,自行服清熱化痰藥,咳嗽逐日加重,遂來就診。刻下癥:咳嗽,夜間咳頻,以凌晨及2~3時咳嗽尤重,呈陣發性,時伴干嘔,無喘息,納減,脾氣急躁,二便可,舌質淡紅,苔白,指紋紫。診斷:咳嗽。辨證:肝郁氣滯,木火刑金。治療:疏肝柔肝,降逆止咳。方藥:四逆散合瀉白散加減:柴胡6 g,枳殼10 g,白芍10 g,甘草3 g,桑白皮10 g,地骨皮10 g,紫蘇子10 g,葶藶子10 g,蟬蛻6 g,僵蠶10 g,生姜3 g。4劑,日1劑,水煎服。服上藥1劑,咳嗽大減,繼服3劑基本痊愈,后以沙參麥冬湯養陰清肺收功。
按語:古人云:“咳不離乎肺,亦不止于肺”。《素問·咳論》曰:“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說明咳嗽病位雖在肺,但咳嗽之病因卻紛繁復雜,臨證當詳辨之。《靈樞·經脈》有云:“肝足厥陰之脈……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小兒稟少陽升發之性,體陰而用陽,五臟之氣機調暢皆賴于肝;五行方面,肝屬木,肺屬金,肝常有余,肺常不足,臨床中肝木常侮肺金,致木火刑金之證。肝者,將軍之官,性暴急,故以陣發性、痙攣性咳為主要表現;子午流注方面,1~3點為肝經之主時,故夜咳多集中在此時,咳雖在肺,病因在肝,當治其肝,肝平則咳自愈,以四逆散疏肝、斂肝,瀉白散清肺肅肺,肝肺同調,升降同施,諸藥相投則病愈。
4 結語
中醫五行思維模式是將經典五行理論與中醫學辨證論治的特點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新的思維模式,也是對藏象學說的進一步延伸與發展,它將天地人融合在一起,體現了天人合一的觀念,采用運動的、變化的、聯系的、辨證的思維方式去看待問題,然而具體問題當具體分析,不可機械性套用,觀其脈證,知犯何逆,知常達變才符合中醫個體化的發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