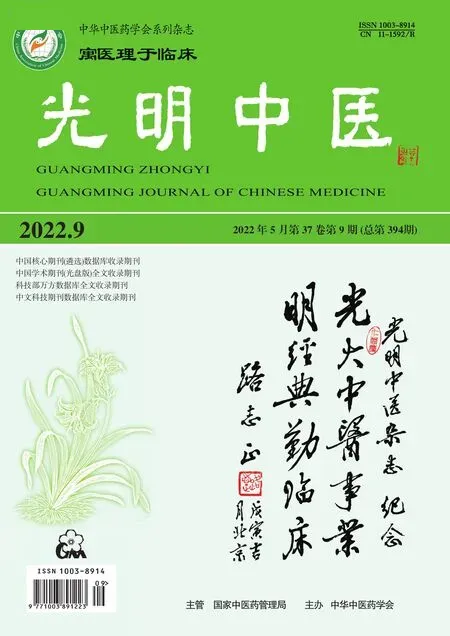從《神農本草經》看《金匱要略》濕熱黃疸四方證之用藥*
肖肽平 王曼菲 艾碧琛
《金匱要略》是一部論治雜病辨證論治的經典之作,其中《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并治》較全面地論述了黃疸病病因病機及辨證論治,對后世辨治黃疸病有很強的指導意義。論及黃疸病辨證論治時,張仲景把黃疸分為谷疸、酒疸、女勞疸3類闡述其辨證論治,盡管此分類法在后世醫家的臨床中逐漸不被延用,但后世醫家仍根據以方測證原則掌握了各方證的證治精髓,將該篇中的方劑用于臨床黃疸病的治療當中,繼承與發展了張仲景論治黃疸病的理法方藥。以方測證來分析《金匱要略》黃疸的辨證論治,可以清晰地看到《金匱要略》的黃疸方證中,除硝石礬石丸證外(因其論治的是女勞疸兼證而非本證,故并非是黃疸方證),其余四方證(茵陳蒿湯證、梔子大黃湯證、大黃硝石湯證、茵陳五苓散證)均為濕熱黃疸方證,再結合《傷寒論》中發黃三證(茵陳蒿湯證、麻黃連軺赤小豆湯證、梔子柏皮湯證)亦均是濕熱黃疸方證,可以看到盡管張仲景在論述中提到發黃有濕熱、寒濕、火逆、瘀血等多種原因,但是其臨證時接觸最多、論述最多的證型毫無疑問是濕熱黃疸。從今天臨床來說,濕熱黃疸確實也是最常見的黃疸證型。本文擬對《金匱要略》濕熱黃疸四方證證候特點及組方用藥進行一次整理回顧,并結合《神農本草經》分析張仲景治療黃疸的用藥規律,或可為更有效地運用四方于臨床治療黃疸提供新思路。
1 《金匱要略》黃疸濕熱四方證證候特點辨析
1.1 茵陳蒿湯證茵陳蒿湯證見于《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并治第十五》第13條。篇中論及茵陳蒿湯證的癥狀均為濕熱內蘊的常見臨床癥狀,如濕熱內蘊致營衛不和所致的發熱惡寒(“寒熱”)、濕熱內困脾胃所致的食欲不振(“不食”)及食后易生濕濁內阻(“食即頭眩”“心胸不安”)等[1],結合服藥后提及的藥后反應“小便當利”“一宿腹減”以及與《傷寒論》260條互參,可知患者還有因濕熱內阻所致的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及腹滿等癥。治療本證時,仲景用藥僅三味,茵陳、梔子清利濕熱,大黃通腑泄熱,三藥合用既可利小便,也可通導大便,使得內蘊之濕熱之邪從二便而出,濕熱得出,諸癥得除。從方藥劑量來看,方中用六兩茵陳、十四枚梔子,清利濕熱的力量頗強,可見本證濕熱之邪較重,同時大黃用二兩,弱于方中清利濕熱之力,可知本證病位偏于中焦。
1.2 梔子大黃湯證篇中第15條論述了梔子大黃湯證。本條原文敘證較茵陳蒿湯證簡單,僅提及“心中懊憹或熱痛”,需要結合以方測證來分析梔子大黃湯證。“心中懊憹”是濕熱內蘊的重要表現,方中用藥四味,梔子、大黃、枳實、淡豆豉,沒有用茵陳,僅梔子清利濕熱,輔以大黃通腑泄熱;方中還用苦、辛、微寒的枳實,破氣消痞,結合原文所說“心中熱痛”,故知此證當有濕熱內阻所致的氣機阻滯不通,不通則痛。此外,方中有一味淡豆豉,和方中梔子相伍即成梔子豉湯,用以治療邪熱內郁胸中的心中懊憹。綜合全方,梔子大黃湯清熱之力較強,利濕之力較弱,可知本證應是熱重于濕,且有較明顯的氣機阻滯不通。從該方劑量來看,梔子十四枚,同茵陳蒿湯,但是通腑泄熱的大黃僅用一兩,且方中還合用了主治胸中煩悶的梔子豉湯,不難看出梔子大黃湯證病位偏于上焦。
1.3 茵陳五苓散證茵陳五苓散證是濕熱黃疸四證中原文最簡單的一證,原文18條只言“黃疸病,茵陳五苓散主之”,并未提及任何脈證。以方測證來看,茵陳五苓散組方思路清晰明了,茵陳加通陽化氣利水滲濕的五苓散,雖五苓散中有性溫的桂枝、白術,然而茵陳五苓散中茵陳用量10分,五苓散僅5分,所以此方還是主治濕熱黃疸,且利濕之力明顯大于清熱之力,故其病機特點是濕重于熱。
1.4 大黃硝石湯證篇中第19條原文論述了大黃硝石湯證。原文直接點明了其病機的一大特點——“里實”,并且強調了治法以“下”為主,這與方中用四兩大黃通腑瀉下相印證,同時方中另用黃柏,黃柏苦寒沉降,善于清瀉下焦濕熱,結合用四兩大黃通腑瀉下,可知大黃硝石湯證病位當偏于下焦。除大黃、黃柏之外,方中還配以梔子清利三焦濕熱,輔佐黃柏除濕熱;用硝石消瘀活血,配合大黃攻除瘀熱。綜合全方來看,通腑泄熱除濕力量較強,然而大黃硝石湯如同梔子大黃湯一樣沒有用茵陳,全方清熱力量強于利濕力量,故原文除了提到“腹滿”“小便不利而赤”等濕熱內阻之證外,還強調了因熱盛于里導致的“自汗出”。綜上可見大黃硝石湯證有別于前述三方證的病機特點是熱重于濕、且兼里實,病位重在下焦。
2 從《神農本草經》看仲景治療濕熱黃疸的用藥經驗
2.1 喜用大黃活血祛瘀《金匱要略》黃疸病第1條原文中論述黃疸病病機時提出“脾色必黃,瘀熱以行”,不少學者將“瘀”字注釋為“郁”,但是筆者認為仲景的“瘀”“郁”是有明確區分的。《傷寒論》及《金匱要略》中多次用到“郁”字,如《傷寒論》48條的“陽氣怫郁”,103、123條“郁郁微煩”,380條“外氣怫郁”,《金匱要略》中的“郁冒”等等,然而一旦論述發黃時,仲景則會用“瘀熱”而不用“郁熱”,除了前述的“瘀熱”外,在《傷寒論》中也有兩處發黃證提到“瘀熱”一詞,分別是236條的茵陳蒿湯證、262條的麻黃連軺赤小豆湯證。此外還有124條的抵當湯證提到“瘀熱”,抵當湯證是明確的蓄血證,太陽之邪與瘀血相結于里,綜上來看其論述發黃病機所言“瘀熱”一詞,更能確定仲景原意為黃疸的發生與血分有關,濕熱入血分、周行于身方致發黃。
方從法出,法由證立,仲景對發黃病機與血分有關的思想體現在其治法用藥中就是大黃的應用了。《金匱要略》濕熱四方當中,茵陳蒿湯、梔子大黃湯、大黃硝石湯三方均有大黃,而其原文敘證時僅有大黃硝石湯證原文有“里實”,方中用大黃四兩,與大承氣湯、小承氣湯及調胃承氣湯中的大黃用量相同,所以大黃硝石湯證的里實證是非常明顯的;但茵陳蒿湯證及梔子大黃湯證原文并未提及里實便秘,且二方的大黃用量均較大黃硝石湯為輕(分別為二兩及一兩)。此外,如前所述,梔子大黃湯證病位在心胸中,病位偏上,從因勢利導治則來看,亦是不適合以攻下法來治療的,故可以明確茵陳蒿湯證及梔子大黃湯證的病機中僅有輕微里實、或者沒有里實,而仲景仍用大黃的原因,除了通腑泄熱之用外應該還別有深意。雖然仲景在《傷寒雜病論》的自序中并沒有提到《神農本草經》,但全書共用藥170余種,絕大多數可見于《神農本草經》,從仲景對眾多藥物的用藥情況來看,其藥物理論也主要來源于《神農本草經》。再看《神農本草經》中記載大黃主“下瘀血,血閉,寒熱,破癥瘕,積聚……”[2],結合仲景 “瘀熱以行”之論,不難看出仲景喜用大黃治療濕熱黃疸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活血祛瘀。實際上活血祛瘀法治療濕熱黃疸已被后世眾多醫家驗之于臨床,確為有效治法,如現代著名的中醫肝膽病大家關幼波就非常肯定黃疸系濕熱入于血分的思想,且重視解毒活血化瘀治法治療黃疸[3],活血化瘀治法貫穿慢性肝病治療的始終[4],眾多國醫大師治療黃疸的文獻研究也證實了行氣活血法的重要性[5]。
2.2 濕重用茵陳蒿 熱重用梔子 黃柏《金匱要略》濕熱四方證當中,茵陳蒿湯、梔子大黃湯及大黃硝石湯三方均用梔子,其中梔子大黃湯、大黃硝石湯中有梔子但未用茵陳蒿,另外茵陳五苓散中有茵陳無梔子,結合前文分析的四方證病機,可見仲景治濕熱黃疸時,濕重者用茵陳蒿,若熱重而濕不重則僅用梔子而不用茵陳蒿,或加黃柏(如大黃硝石湯、《傷寒雜病論》中的梔子柏皮湯)。《神農本草經》中記載茵陳蒿“主風寒濕熱邪氣,熱結黃疸”[2],梔子“主五內邪氣,胃中熱氣……”[2],柏木(黃柏)“主五臟腸胃中結熱,黃疸,腸痔,止泄利,女子漏白赤下,陰傷蝕瘡”[2],其中茵陳蒿、黃柏主治中明確有“黃疸”之病名,這可以解釋仲景為何喜用茵陳蒿、黃柏治療黃疸,尤其是茵陳,《傷寒雜病論》全書中僅在茵陳蒿湯與茵陳五苓散中用過茵陳蒿,皆與治黃有關,頗有專病專藥之意。另一方面,《神農本草經》中并未提及梔子主黃疸,只言“主五內邪氣,胃中熱氣”,而黃柏主治也只提“熱”而未言“濕”,故而仲景用梔子、黃柏的主要用意應是除熱,這也印證了梔子大黃湯證、大黃硝石湯證及《傷寒論》中的梔子柏皮湯證熱盛的病機特點。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神農本草經》未提梔子、黃柏除濕,鑒于仲景在黃疸病篇曾說“然黃家所得,從濕得之”,強調發黃者必有濕邪,所以即便梔子大黃湯證、大黃硝石湯證熱勢較盛,仲景亦定會在方中加入除濕之力,但二方中僅梔子、大黃、黃柏、枳實、豆豉、硝石諸藥,由此推知仲景當時對梔子、黃柏的功效認識中或許已超出《神農本草經》記載,知其兼有除濕之力。
3 結語
仲景論治黃疸時,雖在《金匱要略》中論及過多種發黃原因,然而其論述的黃疸方證絕大部分都是濕熱黃疸,加之現今臨床中黃疸證型的觀察,可以看到濕熱黃疸從古到今都是臨床中最常見的證型。而在論治濕熱黃疸時,仲景非常重視對每個具體病證濕邪與熱邪孰重孰輕的鑒別,以及其病位在上、在中或在下的分析,從而調整用藥。筆者在知網中查閱2001—2021年之間的文獻,以“茵陳蒿湯+黃疸”為檢索關鍵詞查閱到的相關文獻有283篇;以“茵陳五苓散+黃疸”為檢索關鍵詞查閱到的相關文獻55篇;然而以“梔子大黃湯+黃疸”為檢索關鍵詞查閱到的相關文獻僅10篇;以“大黃硝石湯+黃疸”為檢索關鍵詞查閱到的文獻則更少,僅有4篇。這一數據側面說明了茵陳蒿湯、茵陳五苓散是臨床治療黃疸常選用方劑,而梔子大黃湯及大黃硝石湯的臨證運用較少,也提示臨床當中濕熱并重和濕重于熱的黃疸證型更為多見。
在用藥方面,仲景治療濕熱黃疸的藥物選擇依據源自《神農本草經》,茵陳蒿是仲景治療濕熱黃疸時濕邪較盛時的首選用藥,且仲景將茵陳蒿僅用于黃疸的治療;若病證熱邪偏盛,喜用梔子、黃柏;仲景認為黃疸的發生均是邪入血分所致,故其治療濕熱黃疸還常針對血分用大黃瀉熱逐瘀而不論是否有里實。值得一提的是,仲景在繼承《神農本草經》時也有創新,如對梔子、黃柏的認識,《神農本草經》中僅言主“熱”,但是通過分析仲景對黃疸病因病機的認識再結合其用藥,還能看到仲景不僅用梔子、黃柏清熱,且有除濕之意,由此不得不感嘆仲景用藥經驗之豐富,師古而不泥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