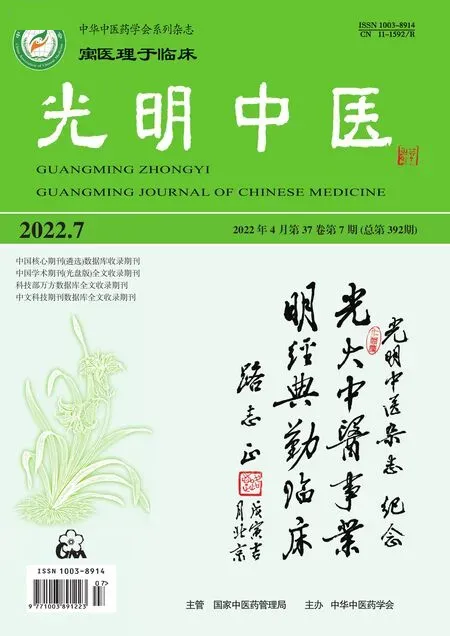王誠喜教授加味溫脾湯治療復發性口腔潰瘍經驗
何相紅 王誠喜
復發性口腔潰瘍是臨床上最常見的口腔黏膜疾病之一,其表現為出現在口腔黏膜上的圓形或者橢圓形的局限性潰瘍,以潰瘍反復發作,潰瘍局部表現為紅、腫、凹、痛為主要特征,具有自限性、復發性、周期性等發病特點。俗稱復發性口瘡、復發性阿弗他口炎[1]。其患病率10%~25%, 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2]。復發性口瘡因發作的復發性,病程的遷延性,致使患者飽受苦痛。
目前,復發性潰瘍的病因及發病機制尚不明確,現代醫學認為此病可能由局部創傷、食物、藥物、情志、激素水平改變等因素誘發[3],與機體免疫功能降低、口腔菌群失調、微循環障礙、維生素或微量元素缺乏等機制有關[4]。此病病因復雜, 反復發作, 纏綿難愈, 目前現代醫學無針對復發性口腔潰瘍的特效藥。中醫根據其臨床表現將此病歸屬于“口瘡”“口瘍”“口糜”等范疇,從口腔潰瘍發病證候、患者體質學說等方面綜合考慮,中醫辨證論治,在治療復發性口腔潰瘍,減輕潰瘍面積、減少潰瘍復發率等方面具有顯著療效。
王誠喜教授,湖南中醫藥大學博士后指導老師、碩士研究生導師,衡陽市中醫醫院肺病科學科帶頭人,曾任衡陽市中醫醫院院長,先后被聘為湖南省名中醫、湖南省抗疫先進個人,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中醫診斷學專業理事會理事,湖南省中醫藥和中西醫結合學會副會長。王誠喜教授從醫、從教50余載,學驗俱豐,尤在中醫藥防治呼吸系統疾病領域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善用古方,又不拘于原方,根據患者情況靈活化裁,每獲奇效。王誠喜教授對復發性口腔潰瘍的診療有其獨特的見解和治療思路。筆者有幸師從王教授,現將其臨證經驗介紹如下。
1 病因病機
口瘡之名首見于《黃帝內經》。其中《素問·氣交變大論》曰:“歲金不及, 炎火上行……民病口瘡, 甚則心痛”。《素問·至真要大論》:“火氣內發, 上為口糜”。口瘡病因主要與外感六淫、飲食不節、內傷七情、勞倦過度、先天不足等因素有關,促使臟腑功能紊亂、氣血失調,導致邪熱灼絡,繼而引起病變。王金海等[5]經廣閱讀醫籍,得出口瘡的病因病機與火熱邪氣、內寒、心脾等密切相關的結論。口瘡雖為局部黏膜病變,病位在口,但與五臟六腑、氣血經絡密切相關,臟腑功能紊亂、氣血失和、陰陽失調均可誘發此病。正如《醫學入門·口舌唇》所載:“心之本脈,系于舌根;脾之絡,系于舌兩旁;肝脈循陰器,絡于舌本;腎于津液,出于舌端。分布五臟,心實主之,故曰:諸經皆會于口”。本病病位在口,與脾胃、心、腎、肝膽等臟腑密切相關。本病病機為臟腑陰陽氣血失調,火熱循經上炎、熏蒸口舌。辨證當分虛實,虛為脾胃氣虛、或氣陰兩虛、或脾腎陽虛、虛火上炎而致病;實為濕熱困脾、或心脾積熱、火毒上攻而發病;久病則虛實兼夾, 本虛標實。
王誠喜教授在學習經典、總結前人經驗和臨床遣方用藥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復發性口腔潰瘍發病以脾胃虛寒為本,治之當溫陽。趙獻可有言:“蓋用胃虛谷少, 則所勝者腎水之氣, 逆而乘之, 反為中寒, 脾胃衰微之火, 被迫炎上, 作為口瘡”。復發性口瘡多因素體虛寒,陽氣不足;飲食不節,過食寒涼;起居失常、勞累過度;過用寒涼清熱之劑(包括用抗生素)損傷陽氣而致臟腑失調,脾胃虛寒,中陽虛衰,土不攝火,相火上越,發為口瘡。《口齒類要》謂:“口瘡上焦實熱,中焦虛寒,下焦陰火,各經傳變所致,當分別而治之”。口瘡初期,多為心脾有熱,氣沖上焦,熏蒸口舌,發作口瘡,古今醫家多以實證論治,以苦寒直折之品清熱瀉火,如瀉心湯、清胃散一類,驗之臨床, 則顯效者約半數,日久則脾胃中陽被克伐,致使陽氣不振,升降失司,格陽于上, 熏于口腔, 故口瘡久而不愈或反復發作。即《丹溪心法》所云:“口瘡服涼藥不愈者,因中焦土虛,不能食,相火上沖無制”。口瘡反復遷延, 陰病及陽, 易致脾腎陽虛[6]。張麗娜[7]醫家使用扶陽法治療復發性口腔潰瘍療效顯著。
2 臨證特色
根據病因病機,王誠喜教授以溫陽為此病治療大法。補益脾胃陽氣,使中陽得復,陰寒得消,攝納浮陽,引火歸元,陰陽平衡,臟腑協調則口瘡得愈。王誠喜教授臨證運用溫脾湯化裁作為復發性口腔潰瘍的治療基礎方。溫脾湯原方出自唐代著名醫家孫思邈所著《千金備急方》:“溫脾湯,治腹痛臍下繞結繞臍不止方”。原文闡述了溫脾湯為治療陽虛寒積證的溫下方劑,原方由大黃、當歸、干姜、附片、人參、芒硝、甘草等藥物組成。方中用附片與干姜溫陽祛寒;人參合甘草益氣補脾;大黃蕩滌積滯,諸藥協力,使寒邪去,積滯行,脾陽復。加味溫脾湯為溫脾湯化裁而成,原方去瀉下之芒硝加牛膝、黃連、沙參、麥冬等寒性藥物。附片配伍大黃為君藥,以大辛大溫之附片溫脾陽、散中寒。大黃清泄火熱之邪,附片引上行之虛火歸于中下焦,具有溫養下元、攝納浮陽、引火歸元的功效。干姜溫中助陽,助附片溫中散寒,為臣藥。黨參、白術、當歸益氣健脾養血,使下不傷正為佐;牛膝補肝腎、導熱下行,引上行之火下歸中焦,以降上炎之火;麥冬、北沙參微苦甘寒配伍少許苦寒之黃連,清上焦之浮火,共為佐藥。炙甘草既助黨參益氣,又可調和諸藥,為使藥。諸藥協力,使積滯之寒邪去,脾陽復,元火歸,則口瘡得愈。溫陽、補益、清火三法兼備,溫陽以祛寒不傷正。此外,現代藥理研究證明:黨參、白術、干姜等藥物能夠增強機體免疫功能,調節機體免疫,其治療口腔潰瘍具有增強療效,減少復發的作用[8]。
3 驗案
王某某,女,58歲。2020年5月19日初診。主訴:反復口腔黏膜潰瘍2年余。現病史:患者自訴2年前因過食辛辣食物后出現口唇及舌體黏膜潰瘍,面有少量白色分泌物,伴疼痛灼熱,于當地衛生院就診,考慮診斷為“口腔潰瘍”,予“西瓜霜”“牛黃解毒片”等藥物治療后癥狀改善。此后口腔潰瘍反復發作,遷延不愈,自服“抗生素類藥物”療效欠佳,曾于私人中醫館用清咽利喉、養陰清肺之法治療口腔黏膜潰瘍可暫時減輕,但藥停后或食用辛辣食物多加重。現今為求中西醫結合系統治療,特來衡陽市中醫醫院呼吸內科門診就診。刻下癥見:口唇黏膜及舌體有數個黃豆樣大小不等的潰瘍散在分布,潰瘍表明凹陷,表面可見少量白色分泌物,周圍皮膚稍紅,伴疼痛,口干、口淡無味,四肢不溫,食納欠佳,納呆,夜寐安,小便清,大便干結。體格檢查:舌淡,苔薄白,脈沉細。四診合參,辨病為口瘡;辨證為脾胃虛寒,虛火上炎。治宜溫補脾陽,方用加味溫脾湯加減。具體方藥如下:附片(先煎)20 g,大黃10 g,干姜10 g,黨參20 g,白術10 g,炙甘草6 g,北沙參15 g,麥冬10 g,黃連3 g,牛膝10 g,當歸20 g,茯苓20 g,山藥20 g。上方7劑,水煎服,每日1劑,分2次溫服。囑患者保持樂觀豁達的心情, 改變飲食習慣, 多食蔬菜水果, 忌食辛辣刺激之品, 保持二便暢通。服藥7劑后, 二診患者潰瘍癥狀明顯改善,大便較前通暢,予原方去黃連繼服鞏固治療, 口唇黏膜潰瘍基本消失,諸癥改善, 后隨訪約1年;病無復發。
按:在中醫學理論體系中,口瘡之為病,其病位雖在口舌,病機則與人體內在臟腑、氣血、陰陽的失調密切相關。因此,口瘡治療中應治病求本,遵循臟腑整體觀的治療原則,辨證而論治。此病患者為典型的復發性口腔潰瘍:反復發作性口舌生瘡,伴口瘡部位疼痛、紅腫,故辨病為口瘡。此案患者為中老年女性,多次運用清熱類藥物及抗生素效果一般,致病情反復發作2年余,每每延醫治而不得其法,治則多投寒涼,更傷中陽,致使病情反復不愈。現癥見:口舌生瘡,納呆,四肢不溫,小便清長,大便干結。舌淡,苔薄白,脈沉細。患者年高,臟腑氣血陰陽漸虧虛,過往用藥寒涼,損傷脾胃陽氣,故見納呆;臟腑陰陽失調,脾胃陽氣虧虛,陰寒內盛,積聚于中焦,寒積腹中,故見大便干結;臟腑陰陽失調,脾胃陽氣虧虛,不能濡養皮毛肌膚,故見四肢不溫;虛寒內盛,格陽于上,虛火上炎,熏于口腔,發為口瘡。朱丹溪所著《丹溪心法·口齒》中有言:“口瘡久服涼藥不愈者, 因中焦土虛, 且不能食,相火沖上無制”。《景岳全書》亦有“口舌生瘡, 因多由上焦之熱, 治宜清火, 然有酒色勞倦過度, 脈虛而中氣不足者, 又非寒涼可治, 故雖久用清涼終不見效。此當察其所由, 或補心脾, 或滋腎水, 或以理中湯, 或以蜜附子之類反而治之”的論述。“邪之所湊, 其氣必虛”,此病患者久病復發發作, 體質虛弱, 因此用藥當忌苦寒直折, 宜用溫熱藥治之,扶正去邪,收斂在外之浮陽, 溫煦在里之陰寒, 迎陽歸舍, 使異常的“內陰外陽”結構回歸到“內陽外陰”, 以達陰陽和合、疾病自愈之目的[9]。另外,在治療過程中,應注意患者及潰瘍創口的護理調護,應囑患者注意口腔衛生、注意保護口腔黏膜;飲食宜清淡,宜多食蔬菜瓜果,多飲水,少食辛辣、油膩、生冷食物;調情志,避免勞思過度、情緒焦慮。
4 結語
正如清代醫家齊秉惠在著書《齊氏醫案·口瘡》中所說:“口瘡上焦實熱, 中焦虛寒, 下焦陰火, 各經傳變所致, 當分辨陰陽虛實寒熱而治之”。復發性口腔潰瘍病情多纏綿難愈,反復發作,患者身心受苦,病機上多虛實夾雜,寒熱并見,治療上非用一法而盡解。目前復發性口腔潰瘍現代醫學沒有特效治療方案,而中醫學因其獨特而精深的理論體系,以整體觀念、辨證論治及陰陽等理論體系,從陰陽臟腑角度著手,探尋復發性潰瘍治療方案,以求得更好的近期療愈及遠期防之復發的療效。中醫辨證論治、整體調理,在預防復發方面有西醫無可比擬的優勢[10]。王誠喜教授認為,臨床上復發性口腔潰瘍病機有虛、有實,亦有虛實夾雜者;治療當辨證論治,分清標本虛實。對于病程長久者,虛實夾雜多見,遣方用藥應當虛實兼顧, 切忌純補純清, 故宜于溫熱藥處方中少佐黃連、黃柏、知母, 麥冬、生地黃等清熱養陰之品,以防陰傷邪留, 但主次需明,清熱養陰之品用量一定要小。 孟澍江[11]曾說:“治此類病證, 苦寒之品不可不用, 又不可多用”。除此之外,應多參加集體活動,增強身體免疫力,從而加快口腔潰瘍的消失,縮短療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