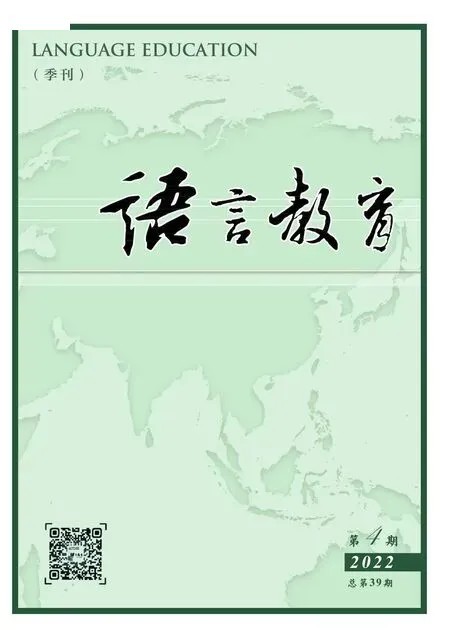翻譯活動家蔡元培:成就及影響
劉洋 文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學院, 北京)
1.引言
蔡元培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民主革命家和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毛澤東曾贊譽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①參見重慶《新華日報》1940年3月8日。。他一生在教育、科學和文化領域不遺余力,為中國現代科學研究和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在學術研究方面,蔡元培興趣廣泛,涉及哲學、倫理學、美學、民族學、人類學以及中西藝術史等諸多領域。其學術成就除了大量的學術著述、譯著以外,還更突出地表現在對教育學術、社會活動的組織領導以及人才的培養等方面。在譯學領域,蔡元培的建樹同樣是多方面的,其成就與貢獻不僅在于多部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外學術專著的譯介與譯學思想的提出,還在于他以領導者和組織者的身份直接參與并推動了一系列與翻譯緊密相關的活動,這些活動成效卓著,對近代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關于蔡元培的翻譯實踐與翻譯思想,已有相關學者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如對蔡元培譯學觀點的分析(陳福康,1997;黃勤,2006),對蔡元培翻譯理論、思想和實踐等的梳理(陳向科,2008;高文芳,2012;胡新蓮,2013;吳彩霞,2021)以及其譯學思想對當代翻譯人才培養的啟示(廖冬芳,2013)等。與此同時,針對由其創導、組織和提議的相關翻譯活動,至今未見專文論述。事實上,蔡元培曾憑借其淵博的學養與高遠的眼界,運用其特殊的社會政治地位以及廣泛的社會影響力組織開展了大量相關工作,在引領促進近代中國編譯事業發展、相關學科譯名確定與本土化、對外交流與宣傳以及提議翻譯作品結集等方面居功至偉,在近代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通過考察和梳理由其促成的一系列翻譯活動來進一步探究其成就及影響,在完善和豐富相關史料的同時,力求更為全面地呈現蔡元培為近代中國翻譯事業所做出的貢獻。
2.蔡元培的翻譯活動及其成就
作為其翻譯事業的重要一維,蔡元培在創導、組織和提議相關翻譯活動中貢獻突出,這些活動連同其翻譯實踐和翻譯思想一起,不僅推動了近代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并與其他的學術事業同步進行、互為促進,成就顯著。總體來看,這些翻譯活動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引領推進近代中國編譯事業發展;確定民族學學科譯名以及學科本土化嘗試;發起組織英文中國年鑒社以及編印英文版《中國年鑒》;提議編輯五四時期翻譯作品結集。
2.1 引領推進近代中國編譯事業發展
從20世紀初期直至晚年,蔡元培一直對近代中國編譯事業的發展殫竭心力。他主持參與編譯新式教科書、設立編譯處、關愛編譯人才、推介譯著及編譯叢書,提議擴大編譯館。
2.1.1 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主持并參與編譯新式教科書
“中國教科書的近代化是由西方教科書的傳入而引發的”(王建軍,1996:3),“但是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只是停留在被動接受西方傳教士帶來的教科書的層面上;甲午戰爭之后才轉為主動編譯,進而有了民間自編教科書的嘗試”(董麗敏,2017:333-334)。為滿足時代的現實需求,商務印書館于1902年設立編譯所,時任商務印書館經理的夏瑞芳請張元濟主持,因未脫離南洋公學,張元濟最初并沒有親自領職,便商請蔡元培去兼任該館的編譯所所長(高平叔,1985)。由此,蔡元培受聘商務印書館,出任編譯所所長,并開始主持相關工作。他與館內同仁商定改變此前的經營方針,轉為從事編輯教科書,由他擬定計劃和編輯體例,并進行編輯,“此商務印書館編輯教科書之發端也”(張靜廬,2003:140)。在編稿辦法上,蔡元培統籌布局,“首先訂定國文、歷史、地理三種教科書編纂體例,采取承包辦法”(高平叔,1985:75),后來逐步完善,代之以合議制的方法,同時根據“學堂章程”頒訂,規定整個編輯計劃,率先按照學期制度編輯教科書(盧仁龍,2017)。這一時期,商務印書館先后出版了《最新國文教科書》《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等多套“最新教科書”系列叢書,“它開我國現代教科書之先河,具有重大教育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價值”(石鷗 張斯妮,2009:5)。
除了負責主持和指導工作,蔡元培還躬行實踐,參與到具體的編譯工作之中。在《最新國文教科書》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以后,蔡元培和張元濟開始聯手推出了《中學修身教科書》。“蔡元培眼高一景,最早提倡基礎教育中的修身——即人格的養成”(盧仁龍,2017:31),因此,把《中學修身教科書》作為最主要的門類來編纂,并親自編纂中學五冊。此外,從這一時期開始一直到留學德國、法國期間,蔡元培應商務印書館的約定和要求先后編譯了多部國外哲學和倫理學方面的著作,包括《哲學要領》《倫理學原理》《哲學大綱》等,這些譯著有很多被列為當時的師范教科書,影響廣泛,為國內師范教研以及教科書的編纂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參考。
2.1.2 于北京大學設立編譯處、批準成立“新知編譯社”
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蔡元培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教育改革。在他的倡議下,學校設立研究所,組織學術團體,出版學術刊物,鼓勵并培養學生的思辨力,這些舉措開創了北大學術自由之風氣,促進了新思潮的傳播。這一期間,蔡元培對編譯工作及相關學術社團活動同樣給予了高度重視,主要包括設立編譯處以及批準成立“新知編譯社”。
據《北京大學大事記》記載:“七年一月(指公元1918年,筆者注)……研究所附設編譯處,每月加經費二千元”(中國蔡元培研究會,1998c:257)。根據《北京大學編譯處簡章》規定,“本處以擴充本大學學生參考資料,及對于一般社會灌輸知識為宗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1998c:257),所辦事務包括征集編譯員、商定應行編譯各項書籍、審定編譯各稿以及與特約印刷發行所接洽等事宜。出版書籍分為編、譯兩種。在集稿辦法上,分為本人自行編譯、聘人編譯和特約編譯三類,版權一律歸編譯者自有。在隨后的1918年到1920年間,北大編譯處與商務印書館開展了《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大綱》《歐洲文學史》和《二十世紀叢書》(隨即改名《世界叢書》)等編譯書稿和叢書排印事宜的多項合作。在訂定編印《世界叢書》的條例中附有如下要點:“本叢書的目的在于輸入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關系的學術思想,先從譯書下手;若某項學術無適當的書可譯,則延聘學者另編專書。無論是譯是編,皆以白話為主,……一律用新式標點符號,以求明白精確……”(高平叔,1996:289)。通過編譯和引進國外名著以及有意識地規范譯著中的文字表達,這一時期,北大編譯處在譯介西方先進思想文化以及向國內民眾普及白話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此外,由于校長蔡元培的提倡和鼓勵,這一時期北大校園里的學術社團活動也十分活躍。1920年初,北大中文系學生成舍我邀集一批同學“在校內組織‘新知編譯社’,專以翻譯外文名著為旨,由校長蔡元培批準成立”(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1998:286)。該社分文學、哲學、政法、理化四部開展編譯。根據一年后的《新知編譯社報告書》稱,該社已經完成的譯著有兩種,正在編譯的有11種。后來,“新知編譯社”又改組成“新知書社”,其營業項目除了延續編譯社時期的翻譯外文著作的工作,又做了適度的調整。這一時期,編譯社翻譯并出版了相當數量的國外著作,對研究學術、傳播思潮等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后來,成舍我又涉足新聞事業,最終成為“一代報人”,而他“從北京《世界報系》,到南京《民生報》,再到上海《立報》,都顯示北京大學時期所留下的深刻影響”(唐志宏 李明哲,2013:47)。
2.1.3 愛惜編譯人才、竭力助推編譯事業發展
20世紀30年代,國內時局動蕩,原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眾多學者遭遇失業。此時,蔡元培先后致函多家出版社,為眾多失業的學者和編譯人才尋求一份工作。1932年2月,蔡元培致函胡適,他于信中寫道:“……但日人破壞一切,毫無顧忌,平民生命財產,固已損失不貲,而對于文化機關,尤肆摧毀,如東方圖書館所搜集之方志,不少孤本,盡付一炬矣!商務印書館有多數受訓練之人物,有三十年之信用,復興非無望,但短時期內當然停頓,編譯所中學者多患失業。……可否請先生于編譯委員會中,酌量擴張,吸收一部分學者,……謹以貢獻于左右。如荷采納,曷勝欣幸……”(中國蔡元培研究會,1998a:24)。在隨后的幾年間,他更是多次撰函舉薦相關學者和編譯人才擔任叢書編譯會譯務、編輯以及承擔譯書工作等。在風云突變、戰亂不斷的艱難時期,蔡元培仍惦念著眾多學者和編譯人才的生計處境,可謂愛才惜才、關懷備至。
此外,在推廣譯著、編譯叢書以及審查提議擴大國立編譯館事宜等諸多方面,蔡元培同樣給予了鼎力支持。據相關資料統計,從1910年至1936年間,蔡元培曾先后為《攝生論》《政治經濟學》《畫法幾何學》《懺悔錄》《西洋科學史》《政治思想史大綱》《自由哲學》《近代教育學說》等百余部譯著撰寫序文、跋語并題署書名等。1935年,鄭振鐸組織眾多著名作家、翻譯家以及學者主編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蔡元培同意列名于該編譯委員會(中國蔡元培研究會,1998b:391),并親自撰寫序文,為這部大型的文學叢刊進行廣泛的推介。同年,在相應時機提出:“(甲)擴大編譯館組織,慎選富有學識及確有經驗之人才,統制編譯全國中小學教科書,并編譯及審核青年兒童讀物,……由各省市主管教育機關,審核各地出版青年兒童讀物,并搜集各地史實及有價值之材料,送國立編譯館采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1997c:192)。
2.2 確定民族學學科譯名以及學科本土化嘗試
19世紀中葉以后,民族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式產生,西方一些國家相繼建立了專門從事民族學研究的學術組織,隨后民族學得到迅速發展。直到20世紀初葉,民族學作為一門學科開始被引進中國,西方民族學的著作也通過翻譯陸續被介紹到國內,但當時對這門學科名稱的譯名卻很不統一。“有的譯作‘民種學’,有的譯作‘人種學’,也有的譯作‘人類學’等等。而正式稱為‘民族學’的,實開始于蔡元培”(胡起望,1981:251)。
1926年12月,蔡元培在《一般》雜志第1卷第12號發表《說民族學》一文。該文首先定義:“民族學是一種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從事于記錄或比較的學問”(中國蔡元培研究會,1997b: 441),隨后對西方“民族學”一詞的詞源和內涵進行了考證,并從詞義方面對比了其他語言與德語之間的差別,最后得出結論:“……也唯有德國人用他的民族學多數作為考察各民族文化的學問的總名(英文Folklore一字,并無多數字),而又可加以記錄、比較等語詞。今此篇用民族學為總名,而加以記錄的與比較的等詞,是依傍德國語法的”(中國蔡元培研究會,1997b:442)。隨后,該文又對我國古籍中有關民族學的史料記載以及民族學與人類學、人種學、考古學和時代的關系等諸多問題做了詳細的梳理和闡釋。由此,蔡元培正式提出并確定“民族學”學科的譯名。此后,盡管還有“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等各種不同的稱呼,學科的定義與內涵也不斷發生著變化,但“民族學”這一名稱也從那時起一直沿用至今(胡起望,1981)。
與此同時,蔡元培大力倡導在中國開展民族學研究,他不僅撰寫了大量學術研究論文,還組織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1928年至1940年期間,蔡元培身體力行,既自承一些專題研究,又指導研究專家的各項工作(蘇敏,2013)。在機構設置上,蔡元培于社會科學研究所之下分設法制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民族學四個組,這是我國最早設立的專門研究民族學的科研機構(王穎吉 陳遠,2005)。蔡元培親自兼任民族學組的主任,在組里開展了多項關于少數民族情況的調查研究,其中便包含了“外國民族名稱的漢譯”一項。由于蔡元培的大力倡導,中國近代民族學的研究得以迅速發展。在西方民族學的引介以及我國近代民族學學科的初創和發展的過程中,蔡元培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2.3 發起組織英文中國年鑒社以及編印英文版《中國年鑒》
1928年開始,蔡元培與李石曾、史量才、陳立廷等發起組織英文中國年鑒社,同時擬定編印一部完全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英文版《中國年鑒》。這是他繼革新北京大學之后對我國文化科學事業的又一重要貢獻(中國蔡元培研究會,1997a:5)。蔡元培、李石曾、俞佐庭、陳立廷等12位人員組成編委會,蔡元培同時擔任英文中國年鑒社名譽理事長。
該社“編輯緣起”中寫道:“……其他屬于專門性質者,如……《經濟年鑒》,……《教育年鑒》,亦行將問世矣。以上諸作,都為漢文,國人參考,誠稱便利。而異國人士,欲研討中國問題者,則徒以文字迥異,無從參閱。試觀東鄰日本,每年不惜巨資,編印英文年鑒,宣達國情于世界,以為國際宣傳之利器,刊行英文年鑒意義之重大,概可想見。不謂此項重要工作,我國人一向放棄,竟由英人伍特海氏代庖至十余年之久,此不僅為我國文化出版界之缺憾,抑為國家之恥辱也。去歲滬上著作家十余人,曾聯合發表宣言,希望全國各機關勿供給伍書材料,唯此舉事屬消極,積極工作當在國人自編英文年鑒,以為替代,同仁等愛本此旨,特發起組織一英文中國年鑒社,尚希國人予以援手,共襄是舉,幸甚幸甚”(王世儒,2019:1152)。與此同時,對擬刊行的英文版《中國年鑒》也作了如下說明:“全書約一百四十萬字,采用各國年鑒最新編制方法,內容務求扼要完備,各項章目,均請專家撰稿,擬委托商務印書館出版,預定今年底出書”(王世儒,2019:1152)。
1935年,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5—1936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第一本完全由中國人編寫的英文版《中國年鑒》,譜寫了《中國年鑒》編撰史最初的華麗篇章(閆浩 杜小軍,2016),蔡元培親自為其撰寫前言并大力推廣。該年鑒全面地反映了1935年至1936年中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情況,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宗教等45個章節,共1966頁。它內容翔實、資料完整、數據權威,不僅是當時海內外各界人士了解中國、研究中國的參考刊物和權威工具書,而且在編撰體例、方法、規模、范圍和原則等諸多方面對日后開展中、英文年鑒的編寫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參考。后來,因抗戰爆發,中國人編寫英文版《中國年鑒》一度中斷。直到1945年,曹文彥、錢鐘書等依據1935年英文版《中國年鑒》的結構體例編寫了The Chinese Year Book 1944—1945,并由上海的中國日報論壇出版公司出版(閆浩 杜小軍,2016)。
2.4 提議編輯五四時期翻譯作品結集
20世紀30年代,出版家趙家璧主編了《中國新文學大系》這部中國最早的大型現代文學選集,蔡元培為其撰寫了萬余言的總序。該書出版后社會反響強烈,有人評價其與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并稱為出版界的“兩大工程”(蘆珊珊,2016:147)。與此同時,趙家璧還組織編譯了一部“系統介紹近百年間的各國短篇小說,分國整理五四以來的文學翻譯作品”的結集,而“這樣一部成套書的倡議者是蔡元培先生”(趙家璧,1984:158)。
1935年,當趙家璧手持《中國新文學大系》樣書謁見蔡元培之時,“他(指蔡元培,筆者注)一邊撫摩著這幾本書,一邊用沉重的語氣,向我表達了如下的心愿。他說:‘假如這套書出版后銷路不壞,你們很可以續編第二輯。但我個人認為比這更重要的是翻譯作品的結集。五四時代如果沒有西洋優秀文學作品被大量介紹到中國來,新文學的創作事業是不可能獲得如此成就的。當時從事翻譯工作的人,他們所留下的種子是同樣值得后人珍視的。困難的是這些作品散佚的情形,比這套書更難著手整理了’”(趙家璧,1984:159)。
蔡元培關于編輯五四時期翻譯作品結集的提議為趙家璧“提出了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出版任務,指出了又一條值得為之奮斗的道路”(趙家璧,1984:159)。在蔡元培的引導下,趙家璧深受啟發,“五四新文學運動之蓬勃發展,當然是受到世界各國近二三百年文藝思潮沖擊的影響。當反對舊傳統的文學家渴望有所新成就時,他們的目光勢必投向國外,去探索和發現我國文學傳統中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和新的藝術形式;而這方面也是前人所沒有匯集和總結的新天地。在完成一部五四以來創作文學的結集后,再編一部翻譯文學的結集,那對將來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發展史的人,不是一份同樣有用的參考史料嗎?而且我自己對外國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工作素感興趣,因此,聽了蔡先生的建議,更躍躍欲試”(趙家璧,1984:159)。趙家璧隨后向許多朋友和翻譯家們請教,最后決定把編選范圍局限于短篇小說,出版一套《世界短篇小說大系》,編輯方法與出版形式均與《中國新文學大系》保持一致,并稱“姊妹篇”,并邀請了郭沫若、黎烈文、曹靖華、郁達夫、巴金等十人分別編譯不同的卷別,“書前由編選者寫二萬字左右的導言,包括三個內容:首敘該國或該地區短篇小說發展的歷史和藝術特點;次談五四以來被翻譯或介紹到中國來的經過;最后分析這些作品對中國作家和他創作的小說的影響,并舉例說明”(趙家璧,1984:160)。該書不僅囊括了英國、美國、德國、法國等國家的翻譯作品,同時還編譯了“北歐”“南歐”“新興國”短篇小說集,包括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國家的翻譯作品,書中的“導言”部分更是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該書于1937年春完成全部組稿,并擬于當年正式出版發行。但由于戰亂等各種歷史的原因最終未能成書行世。否則它無疑是現代翻譯理論、比較文學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貴學術史料(趙敬立,1998)。
3.蔡元培翻譯活動的影響
蔡元培所領導和組織的一系列翻譯活動與其翻譯思想和翻譯實踐齊頭并進,與其他的學術事業和活動相得益彰,為近代中國翻譯事業以及社會的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他積極創導、組織和提議一系列與翻譯緊密相關的活動,不僅為近代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添磚加瓦,而且在學術界以及社會中均引起了一連串的積極效應。
3.1 極力推動近代中國翻譯事業發展
蔡元培對近代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肩負一個譯者的使命,譯介西學專著的同時闡述翻譯之于國家存亡和民族發展的重要性,旨在喚醒國民陳舊的思想意識,以教育救國的信念響應時代的訴求。同時,他以一個領導者和組織者的責任和擔當,對翻譯事業孜孜以求,為近代中國的翻譯事業盡其所能。
蔡元培譯介國外學術專著以自己的學術志趣為基礎,同時重點關注社會和民眾的現實所需,其譯作主題廣泛地涵蓋了哲學、倫理學以及教育文化等重要的專業領域,對填補當時國內相關學科知識的空白、促進相關學科的創立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此外,他依托商務印書館、北京大學等出版機構和學術平臺,極大地推動了新式教材的編譯以及編譯機構的蓬勃發展,使得編譯從較為零散的民間自發性活動發展成為一項重要的學術事業,并在傳遞知識、普及教育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在推介、宣傳譯著和編譯叢書等方面,蔡元培盡心盡力。經由他撰序并推薦的譯著和編譯叢書,往往認可度更高,社會影響也會持續擴大。此外,他多次列名一系列大型叢書的編委會,承擔部分工作并為其撰寫序言,在推動知識的普及和傳播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不僅如此,蔡元培還極力地幫助了眾多學者和編譯人才,尤其是在動亂的戰爭年代,他依舊不忘舉薦失業的人才,向出版社推薦相關譯著,并為其尋求工作,可謂博施眾濟、無微不至。蔡元培殫精竭慮,從多個方面、多個層次引領并促進了近代中國翻譯事業的向前發展。
3.2 同步促進其他各項學術事業發展
“對于不少翻譯家而言,翻譯活動只是整個活動的一部分,還需參照別的活動比照研究”(方夢之 莊智象,2016:5)。科學研究和教育文化既是蔡元培學術生涯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其翻譯事業和活動因浸潤于科學研究和教育文化事業之中而得到有效的實施,反過來,翻譯活動也同樣極大地助力了其他各項科學研究和學術事業的發展。
20世紀初期,我國中小學教育發展滯后,教材的匱乏使得知識的傳播停滯不前。此時,蔡元培于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倡導編纂、編譯新式教科書,通過學習和對比外國教材,并針對我國中小學生的特點進行合理的改編和規范,最終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最新教科書。三十年代,我國大學教育發展遲緩,缺乏本國編寫的相應教材,蔡元培于此時號召開展“國化教科書”運動,提倡從編譯教科書到自編教科書,從而有效推動了我國高等教育的健康有序發展。這種翻譯活動與教育發展的相互促進使得學術研究與事業發展形成了良性的互動,加快了科學研究和學術事業的不斷進步。此外,在國外相關學科知識的引介及本土化的過程中,蔡元培貢獻突出。通過其對國外學術專著的大量譯介,使得哲學、倫理學、民族學等眾多學科在中國創立并持續發展。與此同時,得益于其在確定學科譯名、規范學科專業核心術語等方面所做出的大量實質性的貢獻,國內相關學科領域的研究得以深入有效地開展。不僅如此,蔡元培還積極組織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并隨之涌現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在進一步完善和豐富相關學科領域建設的同時也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近代教育、科學和文化事業的發展。
3.3 深刻影響中國近代化進程
作為一位同時在學界和政界具有重要影響的領袖人物,蔡元培的翻譯活動無疑極富感召力和廣泛的影響力,因而鼓舞了一眾志士仁人在各自的行業領域和事業活動中奮勇爭先并取得不俗成績,這一切最終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蔡元培翻譯活動的重要影響之一在于引領的力量。從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到北京大學校長等科研機構領導職務的每個事業階段,蔡元培都留下了他為近代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傾注心力的足跡。在這一過程中,蔡元培始終引領著一批又一批的有識之士加入翻譯以及其他各項事業的建設之中,其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后來均成為各個行業領域的核心人物和中堅力量,他們在各自專業領域的突出成就和貢獻對于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其重要影響還在于啟發的力量。究其根本,蔡元培具有一個學者深厚廣博的學識和遠闊的眼界,其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和開闊的視野啟發并指引著后人的思想、追求、選擇和方向。在這類活動中,雖其本人未直接參與,但正是由于他的號召和倡議,才使得后人予以大力踐行,相關研究才得以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這些成就同樣是中國近代化歷史上一筆筆珍貴的遺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
4.結語
蔡元培肩負家國使命和責任,傾全身心致力于中國現代科學研究和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引領了一個時代。而由其創導、組織和提議的一系列翻譯活動也因其個人非凡的膽識以及身體力行而大放異彩。“翻譯家個體的翻譯活動一方面具有時代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有他個人的特點”(方夢之 莊智象,2016:5)。蔡元培吸收舊學的菁華,融中西之所學,喚醒翻譯之于時代發展的意義。他登高一呼,以一個領導者和組織者的擔當,不僅以一己之力多方推動了近代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進程,同時還以其遠見卓識和寬廣的胸懷引領、啟發、鼓舞并影響了一眾仁人志士紛紛投入翻譯事業的建設中來,將近代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推向了新的高度,也為教育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貢獻了非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