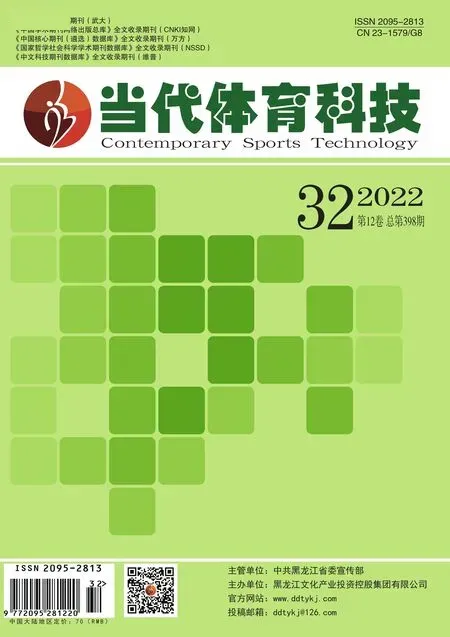貴州省級體育非遺“畬族武術”文化闡釋及傳承對策研究
向宇宏 巴義名
(1.貴州財經大學體育學院 貴州貴陽 550025;2.貴州民族大學體育學院 貴州貴陽 550001)
畬族武術是畬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一門技藝,主要流傳于黔東南麻江縣金竹街道六堡村、仙壩村;凱里市下司鎮的長江村、碧波鎮的償班村、爐山鎮的六個雞村等畬族村寨,傳承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具有保家護衛、防身健體的作用,于2019年被正式列入貴州省第五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該武術盛行于清代、民國和解放初期,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習練之人眾多,習武之風日漸濃烈,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的生活水平日漸提高,社會和諧,治安穩定,該武術逐漸脫離了人們的生活實踐,瀕臨失傳的危機。
1 尋根溯源——黔東南畬族起源及其發展
畬族作為我國南方重要的游耕民族之一,是我國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員。在我國多民族歷史發展進程中,有著獨特、濃墨重彩的一筆。畬族作為我國人口較少的民族之一,經過多年的發展及不斷遷徙,分布范圍從僅限于原始居住地擴散至閩、浙、贛、皖、湘等多個省份,并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點[1]。據2021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畬族總人口74萬余人,其中九成以上聚居在我國的福建省及浙江省,并主要從事農業生產。而在貴州境內,畬族屬于人口較少的民族之一,人口僅4.4 萬余人,主要分布在黔東南、黔南兩自治州的麻江、凱里、福泉、都勻等地,其中尤以黔東南麻江縣畬族人口最多,共3.8 萬余人,約占全省畬族總人口數的86%。畬族在貴州史稱“東家人”,自稱“嘎孟”,有自己的語言但無文字,語言屬于漢藏語系苗瑤語苗語西部方言惠水次方言[2]。基于歷史遺留問題,“東家人”一度被作為未識別民族,直到20世紀90年代,經麻江、福泉、凱里一帶的“東家人”代表前往福建、浙江等地考察,發現與當地畬族同胞較為相似,后經族人同意,貴州省政府于1996年發文批準并認定黔東南凱里市、麻江縣以及黔南都勻市、福泉縣共4個縣(市)的“東家人”為畬族,但從民間習俗、建筑、服飾等方面來看,黔東南畬族與東部沿海地區畬族同胞依然存在較為明顯的區別[3]。
2 黔東南畬族武術文化整體風貌
黔東南畬族武術可分為套路、對練和集體表演3種形式,根據內容不同可分為拳術和器械兩類。據六堡畬族民間武師趙文華家藏的拳譜介紹,畬拳有108套,以硬功為主,有沖、劈、削等特點,動作剛勁有力,利于實戰,無花架子。習練不受時間和場地的限制,利用農閑和晚上時間均可練習,練拳的場地可在堂屋、院壩、田間等。一般以學會一套為一個學段,全部學完需要3~5年。器械除了棍、刀、槍、斧外,就連鋤頭、扁擔、板凳等生產生活用具都被作為用以習練武術的器械。
2.1 套路
套路是以格、沖、摟、扣、壓、砸、劈、撩、頂、靠等技擊動作為基本素材,按照進退攻防、剛柔虛實等矛盾運動的變化規律編成的整套習練形式。主要內容有拳術、器械、對練和集體表演[4]。
2.1.1 拳術
(1)四門開
四門開是黔東南畬族武術的入門套路,以基本的格、摟、沖拳和上步、環繞步格手沖拳為主要進攻防守方法進行演練,它以東南西北為整套拳術的演練方向,每個方向演練一次,有的在演練完畢后還要向四方揖拜,具有強烈的民族色彩。拳術特點是發力短促,姿勢低矮,以格摟手和沖拳為主。技法清晰,動作干凈利落,練用一體,勁力內外結合、勇猛快速、剛柔相濟、快慢相間、節奏分明。拳打4 個方位,分別攻擊前、后、左、右四面,因而得名為四門開。
(2)門第拳
門弟拳是黔東南畬族武術入門拳術之一,流傳于貴州省麻江縣六堡村。行進路線以前后為主,兼顧左右,在四門開的基礎上增加動作,逐漸變化。手形有拳、掌、勾;步形有弓步、馬步、虛步、環繞步。整套拳共分兩段,結構嚴謹,剛柔相濟,簡練樸實,易學易用,適于初學者習練。
(3)大手拳
大手拳傳承歷史久遠,具有拳勢威猛、剛勁有力、樸實無華、腳步扎實、功架渾厚、結構嚴謹、協調整齊、內外兼修、技擊實用等特點。集氣、功、拳、架于一體,練、用于一身。它重在實戰應用,以掛、撩手為本,以順風拳見長,以馬步為先,以半跪步穩己,以整扣勁取勝。
(4)出神拜地
出神拜地拳是黔東南畬族武術的中級套路,拳打前、后、左、右四方,來回往返共分四段,54個動作98個分解動作。手法以沖、撩、砸、扣、壓為基本技法;步型有弓步、馬步、跪步、丁步、三七步;手型有拳、掌、勾。具有結構嚴謹、步法扎穩、拳法剛勁有力、大開大合之特點,常用以競技表演等。
2.1.2 器械
(1)棍術
棍術是黔東南畬族武術最主要的器械之一,取材方便,棍法快速勇猛,舞動如飛,練起來虎虎生風。畬棍主要技法有劈、掃、挑、撩、撥、戳、壓等。要求練習者手臂圓熱、梢把兼用,身棍合一,力透棍梢,快速勇猛,體現“棍打一大片”的特點。
(2)刀術
黔東南畬族刀術主要有單刀和雙刀兩種,常用的刀叫“大馬刀”。這種刀直背直刃,刀背較厚,刀柄呈扁圓環狀,長度1m左右,便于在騎戰中抽殺劈砍,是一種實戰性較強的短兵器。其特點是樸實無華,簡練流暢,勇猛快速,氣勢逼人,剛勁有力,如猛虎一般。主要技法有劈、砍、撩、刺、截、攔、崩、斬、抹、纏裹等刀法。
(3)凳術
板凳,同樣作為黔東南畬族武術中主要的器械之一,深受人們喜愛。其在日常生活當中突發爭斗時可就地取材,方便自衛防身,制敵取勝。凳術的步法主要有弓步、馬步、跪步、丁步、躍步等;主要技法有沖、砸、攔、掃、絞、壓、架、藏、挑、纏、裹等。板凳可用來對付刀、棍等兵器,具有獨當一面的作用,體現了樁法穩固、樸實無華、勁力分明的畬族武術特點。
(4)鏜
鏜,黔東南畬族武術的主要器械之一,是從農具演變而來的一種兵器,長七尺六寸,重5 斤左右,形似三股叉,上有利刃稱“正峰”,長約50cm,橫有月牙,牙朝上,上下均有一定間隔的利刃。鋒與橫刃互鑲并嵌于柄,尾端有一三棱鐵鉆叫蹲。其技法有為拍、拿、滑、壓、橫、挑、扎用法。套路中多采用扎捻勢、中平勢、騎龍勢、架上勢、閘下勢等基本姿勢。代表性套路有鎦金銳、燕尾翅等,廣泛流傳于黔東南麻江縣畬族地區。
2.2 對練
對練是兩人或兩人以上按照編制的套路進行假設性攻防格斗練習,它包括了徒手對練套路和器械對練套路。黔東南畬族武術對練套路有對打拳、擒拿與反擒拿、棍對棍、棍對凳子、刀對鏜等。
2.3 集體表演
集體表演是6 人或6 人以上的徒手或器械的集體演練。可以編排成圖案,使隊形變化忽聚忽散,攻守有度,同時可以采用音樂伴奏,使隊形整齊,動作劃一。
3 黔東南畬族武術文化傳承價值
3.1 歷史價值
流傳于黔東南麻江縣六堡村等地畬族村寨的畬族武術是一種特色鮮明的民族武術文化,該武術作為畬族人民共同的族群記憶和身體實踐,是畬族先民創造的珍貴文化財富,生動地呈現了畬族人民的生活風貌、生產習俗以及宗教信仰等,同時也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文化遺存,承載和存留了該區域內畬族的許多歷史文化信息,蘊含著厚重的歷史文化價值,同時該武術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構成,其存續豐富了民族武術文化的多樣性。
3.2 健身價值
黔東南畬族武術講究精、氣、神的和諧統一,可以達到強身健體和修身養性之目的,體現了畬族人民質樸、敦厚和堅忍不拔的民族性格。經常習練畬族武術的人,通常可以達到利關節、便手足、強筋骨、壯體魄的作用。特別是該武術基本功中的跌、撲、翻以及一些對抗性的拍打、撞擊訓練能有效提高抗擊打能力,增強體質,從而和順氣血,改善身體機能和精神狀態。另外,畬族武術在習練過程中融入了當代健康養生的理念,通過呼吸、吐納等練習方法,重塑了練習者的精、氣、神,提高了練習者的體質健康水平[5]。
3.3 教育價值
黔東南畬族武術尊師重道,注重師徒傳承,強調習武先修身,該武術的教習過程不僅是技術的傳授,更重要的是人的培育,其中蘊含著豐富的道德倫理和人生哲理,具有深厚的教育價值和教育理念。例如,畬族武術前輩們常以崇高武德諄諄告誡弟子“學拳宜以德行為先”,尚有“三打三不打”的行為規范。三打是指路見不平、欺辱婦女兒童、對方先動手者可以出手制服;三不打是指父母不能打、兄弟姐妹及親朋好友不能打、老弱病殘不能打。同時,畬族武術的用途主要在于強身和自衛,推而廣之在于增強民族體質,而炫耀武技、好勇斗狠向來為武界所切戒,其武術形態能夠呈現出東方文明的氣質,爭斗而有禮讓,有勁而不粗野,藝純熟而不懸浮,情飽滿而含蓄內向,具有富于觀賞且追求高尚的精神氣質。
4 非遺保護視域下黔東南畬族武術文化的傳承對策
4.1 提升文化認同
為有效提升黔東南畬族武術的保護、傳承與發展工作,首先要從思想上充分認同黔東南畬族武術多元的價值取向和深邃的文化內涵。它是黔東南畬族人民在長期勞動生產活動中創造的精神財富,是黔東南畬族人民勤勞與智慧的結晶,是黔東南畬族文化的代名詞,也是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6]。300 年來,黔東南畬族武術在教育和陶冶人的思想情操、道德品格,提升人們的文化修養和促進社會生產等方面有著重大的功用。它所具有的歷史文化價值、藝術審美價值、科學研究價值、旅游經濟價值與教育傳承價值等都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挖掘黔東南畬族武術的深層內涵,充分展示其多元價值,進一步拓展和豐富畬族武術的文化意蘊,是人們保護與傳承好黔東南畬族武術的思想保證[7]。
4.2 強化政府職能
政府是我國權力機關的執行機構,是有效幫扶黔東南畬族武術傳承工作的決定性力量。政府的鼓勵能夠帶動黔東南畬族武術文化在建設上獲得更多的經濟資助,用以改變保護資金嚴重缺乏的經濟局面,為黔東南畬族武術的傳承打好堅實的基礎。黔東南畬族武術屬于特定區域文化,其興衰存亡完全依賴于地域的文化生態,因此對于當地生態的保護至關重要[8]。首先,政府部門應依據實際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規或出臺相關的保護條例,以保障保護傳承工作的順利開展。其次,政府還可以通過組織比賽、公開匯報、交流演出等活動,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此同時,政府應攜手屬地企業做好黔東南畬族武術文化宣傳及推介工作。最后,鼓勵并支持建立黔東南畬族武術協會,重點向特色民族村寨傾斜,鼓勵其承接賽事活動、節慶展演活動的組織策劃與管理,不斷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技能水平。
4.3 加強人才培養,健全傳承機制
加強人才培養是保護、傳承與發展好黔東南畬族武術的關鍵環節。通過田野調查顯示,黔東南畬族武術的傳承主體老齡化趨向越發地嚴重,面臨著后繼傳承人斷層的困境,這顯然不利于該武術文化的持續、健康發展。因此,保護好健在的傳承人,建立健全傳承人培養機制,是目前最重要也是最艱巨的任務。相關職能部門應加強對“活態”傳承人的保護,給予他們相應的優惠政策和經濟資助,創設環境,積極鼓勵他們參加各類演出,引導他們做好傳習工作,增強他們的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9]。同時,也要積極組織老一輩武師定期進行交流,以提高自身素養。還要支持他們到地方社區、學校舉辦講座,將黔東南畬族武術文化與社區、校園文化結合起來,在社區、學校中培養起合格的傳承人。
4.4 持續推進教育傳承
學校對于傳承文化、多元文化的交流來說,都是最好的場所。作為一種有效傳播人類文明成果的載體,黔東南畬族武術進校園對該武術文化的傳承、創新以及校園文化的建設、學生的思想解放、價值觀的完善都是十分有利的。目前,麻江縣六堡村等畬族村寨學校不斷加強畬族武術進校園的力度,一方面,通過建設民族、民俗文化館全力傳承和弘揚畬族武術文化,把畬族武術文化進校園活動作為學校教育的必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各級中小學校中組建畬族武術興趣班,通過組織各學校骨干教師先集中統一培訓,再回學校推廣的形式,讓畬族武術融入學校的大課間。可見,持續推進黔東南畬族武術文化的教育傳承,既可以有效提升該武術文化的賡續傳承,也可以使學生在掌握常規知識之余了解、學習本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提升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興趣,進而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10]。
4.5 創新傳承模式
黔東南畬族武術的保護與傳承,要堅持傳承發展與弘揚創新的結合,通過融合現代元素、時代的特點給予黔東南畬族武術新的文化內涵,賦予它與時俱進的時代特征[11]。并在此基礎之上,開展富有時代性的民族、民間文化演出、賽事等實踐活動,使黔東南畬族武術在傳承中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需要。具體而言,在保留傳統文化魅力的同時,尋覓市場開發和滿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的契合點,用時代的符號傳承黔東南畬族武術。內容上,視角應對準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展現其精神風貌,做到觀賞性、實用性的有機整合,擴大受眾群體;形式上,應使建立在民族基礎之上的風格體系橫向借鑒、融合、吸收新元素和新思維,不斷注入新的時代精神和內涵,使黔東南畬族武術能以豐厚的底蘊和強烈的時代感持續發展。
4.6 加大普及宣傳力度
黔東南畬族武術的保護、傳承和發展必須把推廣、普及工作做好。不僅要走進學校,同時也應該在社區、政府單位、企業進行推廣。充分借助數字化媒體如電視臺、電臺、網絡、微博、微信等各類媒體平臺對黔東南畬族武術文化進行專題報道,開設畬族武術門戶網站,開發微信公眾平臺,把珍貴的歷史文獻數字化,并建立數據庫,形成一個集黔東南畬族武術文化保護、價值挖掘、文化弘揚、文化展示、文化創意、文化研究等于一體的綜合、全面的數字化平臺,將黔東南畬族武術文化從文物式平面保護向交互立體化傳播,主動式傳承創新轉化,不斷促進該文化資源條理化、結構化和系統化的加工和整理。同時,舉辦研習會,加強與其他地方武術文化形態的交流,擴大黔東南畬族武術的輻射力、影響力,提高知名度。
5 結語
對于長期生活在黔東南麻江地區的畬族同胞而言,畬族武術承載著該族群的生命記憶和文化傳統,是一個融合族群歷史、價值觀念、技術技藝為一體的宏大敘事體系。數百年來,該武術形態在特殊地理環境、文化氛圍、風俗習慣等的共同作用下,在自給自足的地域經濟和外來民族的相互交融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內容。如今用縱向的歷史眼光來看,黔東南畬族武術文化已具有很高的文明程度。因此,保護和傳承好黔東南畬族武術文化,有利于喚醒民眾復興民族文化的意識,提升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實現文化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