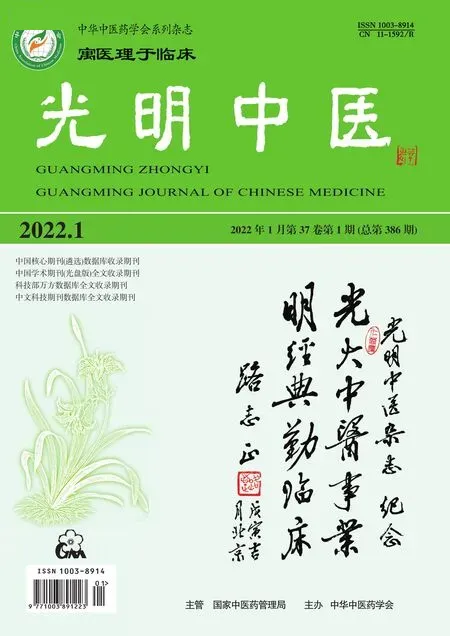經方辨治小兒情志病臨證體會
賈 慧 鈔建峰
情志致病是中醫學內傷致病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七情致損,五志內傷,情志刺激超過了一定的強度、時長和性質從而導致情志疾病的發生[1]。隨著社會的發展,獨生子女、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增加,社會競爭愈加激烈,父母管教缺失以及過早接觸影視媒體等問題,使小兒所處的社會環境因素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兼之小兒在心理上表現為神氣怯弱、心神不足,在受刺激后情志波動遠較正常人顯著,故小兒情志病發病率不斷增加,重視小兒情志病的防治日趨迫切。
經方或曰仲景之方,配伍嚴謹,用藥精簡,選藥精當,用之臨床,效如桴鼓。經方辨證謹嚴,全在隨證立法治方,寒溫并用者多,最利于兒科。因小兒生理上“稚陰稚陽”,病理上“易寒易熱”,故在小兒用方中,溫熱之劑,多佐苦寒、寒涼之劑,多佐辛溫。臨床上經方治療情志疾病的研究頗多,用于治療小兒情志異常類病證也具有明顯療效,且有不良反應少、無藥物依賴性等優勢。今以仲景之方,臨證加減化裁,分治小兒多例情志病證,現舉驗案及分析體會淺述如下。
1 小兒厭食癥
李某,男,5歲。2019年5月16日初診。主訴:不欲飲食1周。家屬訴患兒每因感冒后出現食納不香,常于每餐進食則心煩,躁擾不安,時有惡心,口苦咽干,口渴思飲,大便干結。曾多次在外院診治,效果不理想,遂到北京市西城區廣外醫院兒科求治于中醫治療。查體:患兒神情焦慮,默默不言,頭發枯萎,脘腹脹滿,按之柔軟, 舌淡紅,苔薄白,脈弦有力。診斷:小兒厭食癥,證屬少陽肝經郁熱,脾胃失和。治以和解少陽,理脾和胃。處方:柴胡6 g,黃芩5 g,法半夏5 g,黨參9 g,焦麥芽、焦神曲、焦山楂各6 g,香附6 g,薄荷(后下)3 g,炙甘草3 g。3劑,每天1劑,水煎服,每日3次。
2019年5月19日二診:患兒納食增加,大便正常,但仍時有脘腹脹,煩躁等,上方加青皮、夜交藤各6 g,繼服3劑后癥狀減輕,食欲正常。繼后1年余,本癥再發1次,仍投本方而收效,后未再復發。
按:小兒厭食癥是指小兒非疾病因素而出現較長時間的見食不貪、食欲不振、食量減少、甚則拒食的一種常見病[2],歸屬于中醫“不食”“食不下”“不欲食”等范疇。近年來小兒厭食癥的發病率呈上升趨勢,尤其以1~6歲的兒童為多見。其病因較多,病機的關鍵在肝疏泄失司,脾失健運,胃不受納而成本癥。
本例患兒厭食癥反復出現于感冒之后,當屬于《傷寒論》中少陽病的厭食[3]。正如《傷寒論》第266條言:“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脅下硬滿,干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及《金匱要略》所言:“大便堅,嘔不能食者,用小柴胡湯”。故取仲景小柴胡湯和解少陽,方中柴胡氣質輕清,透達少陽之邪,配苦寒之黃芩清泄肝膽郁熱;法半夏和中止嘔;因甘能增滿,故去方中人參、大棗,用黨參、甘草平補中氣;焦三仙健脾和胃消食;加香附、青皮理氣解郁;薄荷宣郁升清;夜交藤除煩安神。諸藥寒溫共用,疏中寓補,共奏瀉肝補脾之效,使脾胃升降和調而愈。
2 小兒抽動障礙
王某,男,10歲。2019年6月20日初診。主訴:不自主眨眼1個月余。患兒于1個月余前因患眼病后出現眨眼、翻眼睛,初期家長未予重視,并訓斥之,但患兒不但未見好轉,且眨眼、翻眼睛日漸頻繁,有時搖頭,自訴心煩眼癢,食欲不振,睡眠較差,發病以來無大叫,無肢體抽搐,無發熱咳嗽等,二便調。患兒平素情緒易于緊張。體查:神清,精神緊張,發育正常,心肺、腹部、神經系統體查無異常,有不自主的、快速重復的眨眼動作。舌淡紅,苔白略膩,脈弦。外院曾查腦電圖示:兒童界限性腦電圖。診斷:抽動障礙,證屬脾虛肝旺。治以溫膽化痰,平肝健脾。處方:清半夏10 g,茯苓15 g,陳皮6 g,枳實6 g,竹茹9 g,全蝎5 g,蜈蚣5 g,烏梢蛇10 g,鉤藤10 g,白芍10 g,夜交藤12 g,炙甘草6 g。5劑,每天1劑,水煎服。并囑咐家長不可訓斥小兒以及提示其眨眼和翻眼睛的問題,盡量緩解小兒的緊張情緒。
2019年6月25日二診:患兒癥狀明顯減輕,無翻眼睛,有時不自主眨眼,偶有搖頭,睡眠可,二便調。效不更方,繼服5劑以鞏固療效。后隨診1個月,仍以此方加減,癥狀消失,無復發。
按:抽動障礙又稱為多發性抽動癥,臨床表現不自覺的眨眼、皺眉、喉中怪聲或口中穢語等為特征,該病目前發病率和復發率都逐年增加。中醫藥在治療抽動障礙方面有一定的優勢[4]。該病以肝風內動為病機之核心,脾土虛而肝木乘之,風動則上干頭目,諸癥遂生。
本例患兒平素易緊張,受訓斥或驚嚇則癥狀加重,素體膽氣虛寒。不自主眨眼、翻眼睛乃肝風之象,如《小兒藥證直訣》曰:“風動則上干頭目,目屬肝,風入于目……故目連扎也”。食欲不振,舌淡苔白略膩乃脾虛之象,心煩乃痰熱內擾所致。故選用溫膽湯加減化裁治療,該方系從《金匱要略》之橘皮竹茹湯合半夏加茯苓湯增減而成,方中二陳湯之半夏、陳皮、茯苓健脾祛痰和胃,枳實、竹茹化痰清熱,全蝎、蜈蚣、鉤藤、烏梢蛇以平肝熄風、祛風止痙,白芍養血柔肝,夜交藤養心安神,甘草調和諸藥。全方組方嚴謹,共奏健脾疏肝、安神祛風之功,故臨證獲效。
3 小兒睡眠障礙
劉某,男,2歲半。2019年11月22日初診。主訴:夜間易驚醒3周,家人訴患兒3周前受驚后出現夜寐不安,有時啼哭不止,伴有煩躁好動,汗多,大便干,尿頻色黃,無嘔吐,無發熱咳嗽,胃納可,白天睡眠尚可。查體:精神可,發育正常,唇干紅,咽無充血,雙側扁桃體無腫大,心肺未見異常,腹脹,神經系統查體無異常。舌尖紅苔薄白,脈弦滑。診斷為:夜啼(睡眠障礙),證屬少陽樞機不利,郁熱化火。治以疏肝解郁,鎮驚安神,予以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加減。處方:柴胡 6 g,黃芩6 g,清半夏6 g,黨參6 g,茯苓12 g,桂枝6 g,制大黃5 g,生龍骨(先煎)10 g,生牡蠣(先煎)10 g,干姜3 g,珍珠母(先煎)10 g,炙甘草6 g。5劑,每天1劑,水煎服為100 ml,每日2次。
2019年11月27日二診:服藥后患兒癥狀減輕,夜寐有好轉,大便偏稀,守前方改制大黃3 g,加夜交藤6 g,繼服7劑而告愈。
按:兒童睡眠是一個重要且動態的過程,影響著健康和發展的許多方面[5]。睡眠障礙是指在睡眠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影響睡眠的異常表現,兒童睡眠障礙包括入睡相關障礙、睡眠晝夜節律紊亂、異態睡眠(睡驚癥、夢魘、睡行癥、遺尿癥、磨牙)等,近年來已引起重視,調查研究發現兒童睡眠障礙的發生率有增高趨勢[6]。中醫辨證論治兒童睡眠障礙,有較好的臨床療效。
本例患兒年幼,臟腑嬌嫩,屬于小兒睡眠障礙中的睡驚癥,其病位主要在膽,基本病機是膽氣虛弱,易受驚恐,驚則傷神,致心神不守,出現易驚夜啼之癥,少陽樞機不利,肝經熱盛、熱擾心神,則見煩躁好動、多汗的表現,大便干、舌尖紅等表現亦為郁熱化火之象。故本案治療以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以平肝潛陽、寧心安神,使肝氣不致升發太過,調理臟腑陰陽。方以和解少陽樞機之小柴胡湯為基礎方,助樞機運轉,加桂枝、半夏辛散透達,行郁結之氣,輔以大黃以通腑泄熱,根據“心驚必鎮,神離需安”的原則,予龍骨、牡蠣、珍珠母以鎮驚安神,夜交藤、茯苓以健脾安神,黨參扶助正氣,使邪不內傳,甘草調和諸藥。諸藥配伍,使氣機暢通,邪熱得以宣泄,共奏疏肝解郁、通調三焦和鎮驚安神之功,病機相合,故疾病得愈。
4 考前緊張綜合征
陳某,女,12歲。2019年11月2日初診。主訴:考試前經常情緒緊張伴頭痛反復3年余。患者現為初中一年級學生,自訴從小學起每遇考試即出現情緒緊張,初期時僅僅是頭暈心慌等,經過放松和休息可以緩解,家人也未予重視,升入初中后,學習壓力較前增加,考試前一段時間就擔心學習成績不佳,出現情緒高度緊張,甚至頭痛頭昏,煩躁不安,食欲不振,食少,有時腹瀉腹痛,失眠多夢,思維反應遲鈍,記憶力下降,患者月經初來,近2個月來月經量少,伴有痛經,手腳涼。本次又因臨近期中考試,出現上述癥狀。現癥見:情緒低落,心煩,頭痛,入睡困難,甚至整夜難眠,難以安心備考,食欲差,大便偏稀,手腳涼,經期紊亂量少,時有下腹痛,舌淡紅,苔薄白,脈沉細。心理社會因素:患者平素性格內向,學習努力上進,交際少,父母要求嚴格。診斷為:考前緊張綜合征,證屬脾虛肝郁。治以健脾益氣,疏肝解郁,予以小建中湯、甘麥大棗湯和四逆散加減。處方:桂枝6g,白芍12g,柴胡6 g,枳殼6 g,茯神12g,炒白術10g,炙甘草6g,飴糖15g,生姜5 g,浮小麥15 g,大棗15 g。7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溫服。并囑其父母對患兒進行了言語疏導,給予適當的安慰和鼓勵,使其思想放松,幫助克服考前過分緊張的狀況。
2019年11月9日復診,患者服藥后緊張狀況減輕,頭暈、心煩及失眠等癥狀好轉,諸癥改善,效不更方,再進7劑。后隨訪一段時間,患兒心理素質也有了一定的改善,考前緊張情況已不明顯,臨床痊愈。
按:考前緊張綜合征是指考生在考試前一段時間內因過度疲勞、緊張、壓力過重等原因而出現的一系列病癥,嚴重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7]。西醫將該病歸入廣泛性焦慮范疇,常給予口服小劑量抗焦慮藥,雖有一定療效,但不良反應諸多。中醫學可將該病歸屬于“郁證”“百合病”“不寐”等范疇[8],中醫認為“思出于心,而脾應之”,考生在考試應激狀態下出現焦慮、思慮太過,“思傷脾”,使脾主運化、升清的功能失職,導致氣滯或氣結,從而出現食欲不振、納差食少、頭暈等癥狀。謀慮傷肝則木失條達,肝郁則氣滯,陽氣被遏,失于溫煦,于是出現手足冰涼。《普濟本事方》:“久視傷血,血主肝,故勤書則傷肝”,而女子以血為本,以血為用,肝血傷則月經紊亂量少、痛經,虛火上炎則見心煩、頭痛、失眠等癥。該案以小建中湯溫中補虛,調治脾胃,四逆散疏肝解郁,調和肝脾,并合用甘麥大棗湯以補心養肝,益陰除煩,寧心安神。三方合用,則肝氣得疏,中氣得健,氣血生化有源,陰陽通調,則精神乃治。
5 小結
小兒情志病也歸屬于心身疾病,與情志心理及社會因素等密切相關,情志因素在小兒疾病的發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且受刺激后情志波動遠較成人顯著,更易導致相關疾病的發生,正如萬全在《育嬰家秘》中所說:“小兒神氣怯弱,心藏神,驚則傷神,腎藏志,恐則失志,大人皆然,小兒為甚也”。
經方治療情志病具有悠久的歷史。張仲景《傷寒雜病論》所創六經辨證雖為外感熱病而作,但有許多經方被運用于內傷雜病的治療,而且還記載了許多情志疾病,如“梅核氣”“百合病”“不眠”“臟躁”等。經方辨證重視審因論治,創立情志疾病的辨證論治,許多經方如柴胡劑、酸棗仁湯等至今在治療情志疾病時仍被廣泛運用[9]。對于治療小兒情志疾病,經方隨證立法,寒溫并用,尤其適宜于小兒“稚陰稚陽”和“易寒易熱”的生理病理特點,且其藥少而精,辨證處方常能取得較好的療效。以上小兒情志疾病驗案雖不能與《傷寒雜病論》中情志或精神異常的條文中所述病癥直接對應或等同,但按照經方辨證,有是證用是藥,靈活運用經方,可以緩解甚至治愈小兒情志病。因此,臨床應用經方治療小兒情志病,既要按照“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又要能“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靈活運用經方,師古而不泥古,抓其主癥,切中病機,對經方辨治小兒情志病會有更深的認識和更好的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