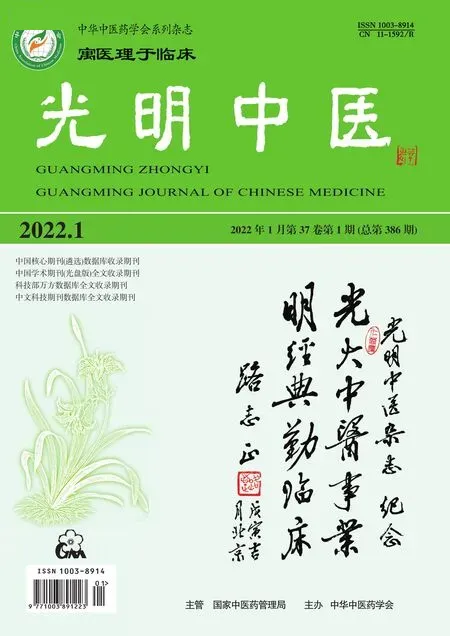中藥炮制對精準用藥的作用機制
王懷興
中藥炮制是根據中醫藥理論,按照辨證施治用藥需要和藥物自身性質,對藥物進行加工的技術。中藥材經過炮制以后,通過一系列的作用機制使藥物的性能、功效發生改變,消除藥物和人體之間的不適應性,就可以滿足個體化精準用藥的需要,達到最佳的治療效果。多成分、多靶點、一藥多效是中藥的重要特征,但也為臨床精準用藥帶來了很大的困惑。了解中藥炮制對精準用藥的作用機制,對于正確炮制加工中藥材,準確應用中藥飲片,提高臨床療效,減少資源浪費,避免不良反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 氣味調和
氣味是中藥的基本性質和特點,是其發揮效能的物質和功能基礎。正如徐靈胎所言:“凡藥之用,或取其氣,或取其味…… 各以其所偏勝,而即資之療疾,故能補偏救弊,調和臟腑……”。中藥氣味秉承于自然造化,并且各有所偏,偏則利害相隨,因而產生各種治療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通過炮制來調節其固有的氣味,滿足臨床精準用藥的需要。例如梔子,具有統瀉三焦之火的作用,多用于溫熱病氣分熱盛、臟腑實熱證。但由于氣味過于寒苦,容易損傷脾胃陽氣,導致嘔吐、便溏。在使用梔子治療溫熱病氣分熱盛證、臟腑實熱證兼有脾胃虛弱患者時,使用辛溫的姜汁炮制苦寒的梔子,就可以通過“以熱制寒”的機制降低其不良反應。鐘瑞等[1]研究證實姜的辛溫之性可以抑制梔子的寒性,增強其和胃止嘔的作用。再例如天南星,善于燥濕化痰、祛風止痙,長于治療濕痰咳嗽、肝風挾痰阻滯經絡之證。生品溫躁毒烈之性強,對于中風、破傷風、癇證兼有熱痰的患者就不適用。若用苦寒之性的膽汁炮制天南星,則可緩和其燥烈之性,使其藥性由溫轉涼,味由辛轉苦,功能由溫化寒痰轉為清化熱痰。唐照琦等[2]研究發現膽南星具有清熱、抗驚厥、抗氧化等藥理作用。除去“以熱制寒”“以寒制熱”這種“反制”方法調和藥物氣味的炮制方法外,也可以通過“以寒制寒”“以熱制熱”的“從制”方法調節藥物的氣味,如使用膽汁制黃連,酒制仙茅等。
2 輔料增效
中藥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輔料炮制后,可以通過不同的途徑,不同的方式,實現趨利避害,提高療效,滿足患者個體化治療的需要。陳嘉謨在《本草蒙筌》中將輔料炮制的原則概括為:“酒制升提,姜汁發散,入鹽走腎臟仍仗軟堅,用醋注入肝經且資住痛……”。例如大黃,生品苦寒沉降,氣味重濁,走而不守,直達下焦,瀉下作用峻烈,只適用于實熱便秘、高熱、譫語、發狂、血瘀經閉等病灶位于下焦的病癥,對于目赤咽痛、齒齦腫痛等上焦有熱的病癥則無法使用。在炮制過程中,借助酒的升提之性,引藥上行,清上焦血分熱毒,滿足使用大黃治療目赤咽痛、齒齦腫痛等病癥的臨床需求。周珊珊等[3]在研究中證實酒大黃煎煮液中具有瀉下作用的結合型蒽醌含量比生大黃低,所含抑菌成分和生品相近。紫菀生品味辛、苦,性溫,散寒、降氣化痰之力勝,能瀉肺氣之壅滯。但肺氣不足的患者服用后,可導致小便失禁,小兒更易如此。使用煉蜜進行炮制,增加紫菀增益元陽、潤肺止咳之功效,還可避免肺氣中虛患者服用紫菀導致的小便失禁之弊。淫羊藿生品祛風濕、堅筋骨力勝,羊脂油炙后溫腎助陽作用增強。侯健[4]研究過程中,通過宏觀動物系統藥效學評價及微觀內源性生物標志物2個方面的指標,證實淫羊藿通過炮制中“加熱”和“羊脂油”2個關鍵環節增強其溫腎助陽的作用。
3 生熟異治
明代眼科醫家傅仁宇《審視瑤函》中稱:“藥之生熟,補瀉在焉。劑之補瀉,利害存焉。蓋生者性悍而味重, 其攻也急, 其性也剛,主乎瀉。熟者性淳而味輕,其攻也緩,其性也柔,主乎補……”。可見生飲片和熟飲片在功效方面還是存在很大差異的。科學的使用生、熟飲片對于增強臨床療效,規避不良反應,提高用藥的精準性是非常必要的。如生地黃味苦,性寒,歸心、肝、腎經,具有清熱涼血、養陰生津之功效,多用于血熱出血及陰虛發熱證。加入黃酒蒸制成熟地黃后,藥性由寒轉溫,味由苦轉甜,功能由清轉補,具有滋陰補血、益精填髓的功效,可以應用于肝腎陰虛導致的目昏耳鳴、腰膝酸軟、須發早白等癥,免除了久病體虛病者服用生品易致腹瀉、腹痛之弊。何首烏生品苦泄性平兼有發散的作用,具有解毒消腫、潤腸通便、截瘧之功效,適用于瘰疬瘡癰、腸燥便秘、瘧疾等癥。經黑豆汁伴蒸后,味轉甘厚而性轉溫,增強了補肝腎、益精血、烏須發、強筋骨之作用,可用于血虛萎黃、眩暈耳鳴、須發早白等癥,還可消除生首烏滑腸致瀉的不良作用。王麗[5]在研究中發現,何首烏中瀉下成分結合蒽醌的含量隨炮制時間的延長逐漸下降。生、熟中藥飲片功效方面的差異除去“生瀉熟補”之外,類似的還有萊菔子“生升熟降”, 木香“生用理氣, 煨熟止瀉”, 柴胡“生用解表, 醋制清肝”,生黨參“補中益氣”, 米炒黨參“健脾止瀉”,生石膏“清熱瀉火”, 煅石膏“收濕生肌”等。這種由炮制引發的中藥飲片生熟之間差異和變化,被歷代醫家在臨床實踐中廣泛應用,對于提升治療的精準性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4 歸經導引
歸經、升降浮沉是藥物的固有屬性,是指藥物作用于機體的部位和趨向。但由于人體所患疾病各不相同,在選擇藥物時就會因藥物固有作用趨勢、作用部位的局限導致選藥的困難。例如當患者熱壅上焦、熱在氣分時會出現目赤、咽喉腫痛、口舌生瘡之癥,在選擇黃柏進行治療時,就出現藥物性味對癥,而作用趨勢和歸經不對癥的情況。生品黃柏味苦,性寒,主沉降,歸腎、膀胱經,使用酒炙的方法,則可以借酒的升騰之力,引藥上行,使黃柏具有清上焦血分濕熱之功效。有的中藥存在一藥歸多經的情況,而患者所患疾病可能只損害一經或者一個臟腑。這個時候就可以選擇適當的炮制方法,使藥物的作用重點發生改變,強化藥物對患病經絡、臟腑的作用,弱化對其他經絡、臟腑的作用,使其治療作用更加專一、準確。例如青皮入肝、膽、胃經,用醋炒后,可增加專入肝經的作用。閔行銓[6]研究證實醋青皮可以降低辛燥之性,引藥入肝,增加舒肝止痛的作用。補骨脂生品味辛、苦,性溫,通過鹽炙炒香后,得到咸味之扶助,可引藥入腎,溫腎助陽、納氣、止瀉作用增強,適用于脾腎虛弱、脾腎虛寒者服用。
5 變形改效
中藥多來源于自然界的天然植物、動物和礦物,受生環境及自身構造的影響,形態大小各不相同。即便是同一基源,不同部位功效也有很大差異。正如《本草蒙筌》所云:“跟梢各治,尤勿混淆”。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改變藥物的外觀形態和分開藥用部位,已到達趨利避害的用藥目的。例如麻黃,莖具有發汗作用,而根具有斂汗作用;遠志具有祛痰的作用,遠志心則沒有祛痰作用;蓮子心清心熱、除煩,蓮子肉補脾澀精;另外種子類藥材的種皮細胞排列比較緊密,常有不同程度的木化增厚,質地比較堅硬, 在浸漬、煎煮或服用后,水分、消化液等難以滲入到藥材內部組織細胞中,導致有效成分溶出率很低。因而就需要采用炒或者搗碎的方法,破壞堅硬的種皮,改變其原有的形態。水分子或者消化液就能順利通過裂隙進入到藥物內部,通過一系列的滲透、溶解、置換、擴散等過程,實現藥物有效成分的溶出,到達理想的溶出和治療濃度。如萊菔子生品能升能散,長于涌吐風痰,適用于痰壅咳嗽。經過炒制后,變升為降,消除了涌吐痰涎的不良作用,即緩和了藥性,又有利于粉碎和煎出。礦物類中藥也需要借助于搗碎或者煅淬、水飛的方法改變其固有的形態,實現增加溶解度、降低毒性、提高臨床療效的作用。如朱砂的主要成分為硫化汞,經過水飛處理可以去除游離汞和可溶性汞鹽等有毒性成分,便于制劑及內服,從而發揮內服治療心悸易醒、失眠多夢的作用。
6 生物催化
生物催化的炮制方法是指在一定的溫度、濕度、空氣、水分的條件下,借助于微生物和酶的作用,促進藥物發酵或者發芽,改變其原有的性能,增強或者產生新功效,擴大藥物使用的范圍,以適應各種臨床治療的需求。例如紅曲,就是將霉菌科真菌紫色紅曲的菌絲及孢子,經過人工培養,使菌絲在粳米內部生長,使整個米粒變成紅色的制品。粳米經過生物催化變成紅曲后,味甘性溫,具有活血化瘀、健胃消食的作用,可適用于產后惡露不凈,瘀滯腹痛、食積飽脹等癥。淡豆豉是由黑豆和青蒿、桑葉等中藥經炮制發酵而制成。黑豆味甘性平,具有烏發、祛風除熱、調中下氣、解毒利尿、補腎養血之功能。制成淡豆豉后,味辛、甘、微苦,性寒。歸肺,腎經。具有解表、除煩的作用,適用于傷風感冒、發熱惡寒或胸中煩悶,虛煩不得眠。陳怡等[7]研究發現,淡豆豉和黑豆比較,功能活性物質大豆異黃酮與γ-氨基丁酸類成分增加,其中γ-氨基丁酸具有良好鎮靜安神、抗焦慮等作用,這也是淡豆豉發揮解表、除煩作用的物質基礎。
7 陳化轉換
所謂的陳化中藥是指在一定的貯存條件下,通過長時間放置使藥物由新藥變為陳藥, 使其性味、功效發生有益變化, 增加中藥的適應性,從而進一步符合復雜臨床治療的需要。“六陳歌”中提到的枳殼、陳皮、半夏、麻黃、狼毒、吳茱萸就是這類中藥的代表。陳皮“陳久者良”的觀點由來已久,《湯液本草》稱:“色紅故名紅皮,日久者佳,故名陳皮”。陳嘉謨《本草蒙筌》言:“久藏者名陳皮, 氣味辛烈, 痰實氣壅服妙”。陳皮來源于蕓香科植物橘及其栽培變種的成熟干燥果皮,新鮮時味較辛辣,氣較燥烈,經放置陳久后,氣味緩和,行而不峻,溫而不燥,具有行氣健脾、降逆止嘔、調中開胃、燥濕化痰的功效,適合于濕熱困脾胃、濕阻中焦、痰濕壅滯等證。嚴寒靜[8]研究表明,不同貯存時間的廣陳皮藥材揮發油的成分和含量都發生了變化,總體上呈現出分子量小的成分減少,分子量較大成分增加的趨勢。而小分子量成分是橘皮燥烈之性的物質基礎。再例如枳殼,來源于蕓香科酸橙及其栽培變種的干燥未成熟果實,鮮果時含有較多不飽和醇、烯和萜類揮發油類成分,對溫度和日曬較為敏感,采用陳放的辦法使其辛散之性即刺激性明顯下降。
8 討論
精準用藥是基于患者體質、疾病、生活環境特異性制定精準診斷、精準預防、精準治療方案基礎上的個體化給藥模式,對于緩解傳統以群體為診療對象形成的標準化給藥模式造成的患者損害、資源浪費、醫患矛盾具有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在臨床實踐中,按照精準治療方案的要求,采用傳統的炮制技術,對中藥材進行加工,通過氣味調和、輔料增效、生熟異治、歸經導引、變形改效、生物催化、陳化轉換等炮制機制,對藥物形質、性味、歸經、功效進行有目的改造,對于提升治療效果,避免毒副作用,規避治療風險,降低資源浪費,提高群眾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