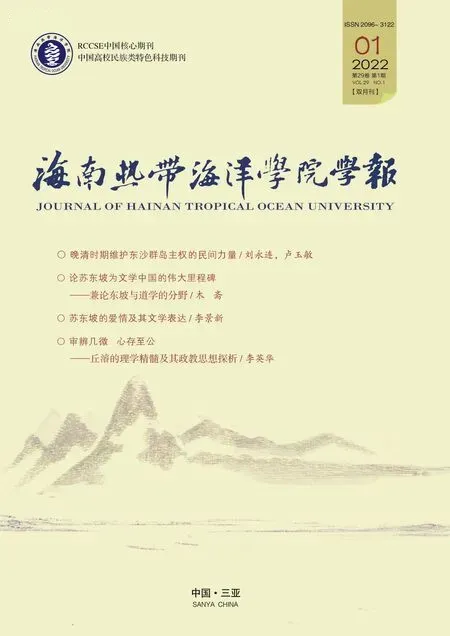丘濬詩歌的生命本體觀
智宇暉
(海南熱帶海洋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海南 三亞 572022)
丘濬以理學家、經世思想家而聞名,其實他還創作了大量的詩歌,這些詩歌雖然被文學史家忽略了,卻為后人提供了認識作者的另一個視角。詩歌中呈現的丘濬,不再有理學名臣的刻板乏味,也少有經世士大夫的壯懷激烈,少見明前期臺閣體的典雅頌美,關注社會現實的篇章也不多,拋開100多首應制酬贈之作,他的詩歌總體上圍繞著個人的生命體驗展開抒寫,并表現出真實的特征,是個體生命流程的自然流露,是對生命形式的復雜體認。
生命本體觀,是指對于生命本質的認識觀念。本文借用此概念來討論丘濬在詩歌中以感性意象透露出的個人的內在生命意識。“生命哲學或生死哲學是基于對生命的理性思考而構建的形而上的理論體系,而生命意識則是人對生命的感性認識,具體說,就是對于生命的感受、體驗與感悟。無論是對個體生命本質的把握,還是對生命目的、生命價值、生命狀態的認識,都建立在自我經驗與感知的基礎之上,甚至就出自自我的生命狀態、自我內心生命脈搏的節律,出自內心的激動、情感的不安,如同身體感受疼痛一樣直接、感性而又具體。”[1]丘濬詩歌中所表現出的生命直覺感知,應屬于此種形式。他一方面秉承儒家重生之傳統觀念,對于人的生命的消失表現了深切的悼惋與痛惜之情,一方面哀嘆著自身生命形式的不確定性,表現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某種疑慮,最終到歷史中尋求生命不朽的典范。
一、 對他人生命的確證
丘濬在詩歌中對于肉體生命的根本性肯定,是在對親友的悼念和對歷史中女性悲劇命運的詠嘆中實現的。對親友,他主要是出于倫理的情感表達本能;對后者,則是其秉承儒家重生觀使然。
對死者的悼挽之作在丘濬的詩歌創作中占有一定比例,絕大多數純屬應酬之作。其中有30多首悼念親友的詩歌,涉及母子、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師弟等人倫關系,感情真摯,形式多樣。
(一)血肉親情,生死一體
由于與逝者具有血緣上的直接的生命關系,因此,從丘濬所寫的以母親、兄長、兒子為哀悼對象的詩歌可以看出,他對于此種死亡的意識,既是對個體生命的本能反應,也受到儒家家庭倫理觀念的影響。丘濬7歲的時候,其父去世,母親含辛茹苦把兄弟二人撫養成人,在丘濬49歲那年,母親去世。守喪結束返京途中,他寫下《望云思親》:
白云在天不可呼,仰天望望增煩吁。蒼茫四顧宇宙闊,去住彼此無寧居。昔人望云憶親舍,親舍依稀白云下。君今望親不可留,何處荒臺閟長夜。長夜漫漫無復晨,舉頭見云不見親。誰展白云書楚些,臨風為爾賦招魂。魂兮去去招不返,沒齒白云長在眼。(1)本文所引丘濬的詩歌作品皆出自丘濬《丘濬集》(周偉民等點校),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此詩借用唐代狄仁杰的典故,狄仁杰望云之時,雙親健在,情有寄托;而彼時的丘濬惟見白云,不見雙親,其痛何如!他只有效法屈原作招魂之詞,為母親招魂,然而母親的魂魄一去不復返,只能留住那白云。父母與子女之關系,在眾多倫理關系中具有優先地位,是由自然血親決定的。儒家倫理賦予了這種天然關系以恩孝的色彩,強化了此種關系。丘濬在個別文章中表達了關于此種倫理之情的思考。他在《永思堂記》中說:
夫人子有此身也,合父之氣、母之血以成形,形具而理寓乎其中,其主宰者謂之心,心之官,則思也。父母之于子,其初本一人之身,繼而分焉,分則離,離則漸以遠,于是乎有思,思而不可復見,于是乎永思,永思云者,終其身之謂也。吾之身,親之遺也,凡吾之身,形自一孔以上,氣自一息以上,理自一念以上,皆親之余也。[2]4302-4303
正因如此,當子女去世,其生命消逝給父母帶來的痛苦就更深。丘濬58歲那年,他的未滿10歲的幼子丘昆夭亡,他作《哭子昆》4首述懷。丘昆聰穎,“至性奇姿迥異常”“汗血漫夸千里驥,與玄亦似九齡烏”;幼子的夭亡令老父不能釋懷,如同自己生命的消逝:“喪汝分明是喪予”;他甚至發出悔不當初的啼號:“早知今日會有死,何似當初莫要生”;還寧愿以兒子的愚笨換取其生命的長度:“養兒何用太聰明”;甚至訴諸于幻想,希望幼子來年轉世丘家:“安得感通如顧況,非熊還有再來時”;最終是對生命不可復返的絕望:“老鶴倚巢空叫月,飛雛應是不歸來。”
丘濬所作懷念兄長的詩篇《閑中懷伯兄》,也是對親情生死分離的感喟。此詩充滿了靈異色彩。據詩序,詩作于成化十二年(1476)五月十七日夜,同一天,丘源在海南病逝,似乎兄弟之間冥冥中有生命的感應。丘濬之兄丘源,長丘濬3歲,于成化十二年去世,時年59歲。詩云:
看看白發滿頭顱,心志蹉跎歲月徂。半世多違同被約,九原未遂首丘圖。孔懷此日歸心切,想見他年有命無。最是不堪聞感處,霜天鴻雁夜相呼。
“半世多違同被約”,寫兄弟二人分居南北近30年,當年希望兄弟怡怡,同床共被以終老,而如今卻仕宦牽連,天各一方。丘濬有《祭先兄文》表達他與兄長之間的親密關系,正可以作為本詩的注腳:
兄弟二人,一氣分形。死者非死,生者非生。宗祀所系,在我二人。如鳥兩翼,如車兩輪。相依相成,缺一不可。我不可無兄,亦如兄之不可無我。[2]4564-4565
(二)夫婦之愛,刻骨之思
丘濬悼念妻子金氏的詩歌最多,且感情深摯,在他的倫理情感中是異乎尋常的,在親情之外,還有愛情的因素。愛情,是儒家侈言的。儒家倡導的夫婦之愛,諱言愛情的存在。由于丘濬是一位事功派的理學家,而非一般道德心性的講學者,這使他的觀念能夠擺脫道德至上主義式的嚴苛。如果從儒家關于家庭倫理的論述看,他對妻子的深情似乎超過了對于母親的思念,起碼從詩歌看是如此。他是一位經世派的理學家,在儒學史上是一位崇尚實學的人物。“丘濬將‘四書五經’與‘近世諸儒之書’都當作是‘窮理之具’,這是對經書作為道德價值載體的消解,事實上將朱學的主導方向從價值理性轉向工具理性”[3],因此,他不是謹守儒家教條的俗儒,經世之志使他的胸懷更為闊達,見解更為宏通。他編錄《朱子學的》共20篇,在篇目次序的安排上就勇于突破儒家倫理規范,他說:
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后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遠也。[2]4564-4565
他的宏通的見識使得他的悼亡詩在中國詩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2)這里采用尚永亮的觀點,用悼亡詩狹義的概念:“自晉代潘岳以《悼亡》為題寫了三首追悼亡妻的詩作之后,‘悼亡’二字似已約定俗成地成為丈夫哀悼亡妻詩作的專稱,以致后人一見‘悼亡’字眼,便自然聯想到這是悼妻之作,而每逢喪妻,也都習慣地以‘悼亡’為題。”參見尚永亮《血泊哀歌生死戀情——中國古代悼亡詩初探》,《江漢論壇》1989年第4期,第75頁。。
丘濬25歲時,娶崖州金百戶之女為妻。結婚一年半之后,丘濬即進京參加禮部會試,此后幾年中滯留北方未歸。景泰二年(1451),31歲的丘濬落第回鄉省親。此時,妻子金氏已經重病在床,垂危之際,夫妻有幸相見最后一面,不久金氏即去世。新婚未久即為了追求仕途拋妻而去,數年之中,兩次科考均失敗,卻付出了妻子逝世的巨大代價,這使得丘濬充滿了自責與內疚,很長時間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因此創作了一系列詩歌寄托哀思。其中五古組詩10首、五律組詩3首,詩歌之中表達的感情痛切,藝術水平堪為上乘;另外還有題為《悼亡》的集句詩5首,當亦為悼金氏所作,藝術性不高(3)丘濬先后娶金、吳兩位夫人,金氏早逝。胡旭據詩句中有“芙蓉肌骨綠云鬟”之句,認為此集句詩應為金氏所作,有理。參見胡旭《悼亡詩史》,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248頁。。其中五言古詩以敘事為主,回顧了妻子從與他新婚到死亡的生命歷程。在丘濬的記憶之中,二人的關系是“一見如宿昔,友之如琴瑟”。他感念妻子在家中的勤儉操勞:“我行逾四載,之子苦幽闃。登堂事老母,燈下事蠶績”。感念她的體貼:“亹亹用甘言,慰我不得意”。回想金氏去世前的種種細節:“臨終嚙我指,與作終天訣。雙淚住不流,戀戀不忍別。氣促發言遲,奄奄殆垂絕。勉我赴功名,努我立名節。事我不盡年,命薄將奚說?死生皆其天,無用過哀切。”丘濬的3首五律悼亡詩則純以抒情為主,更為凝練地表現了悲痛的情懷。“物在人何在,情深痛始深”(《悼亡》),自潘岳以來,物在人亡的反襯是哀念逝者的一種方式,也是最真切自然的方式。詩云:
萬里歸來日,移燈照別離。會稀疑是夢,歡極反成悲。生別已堪恨,死傷應可知。平生湖海氣,為爾重凄其。
二聯以悲歡巨變凸顯生命的無常,三聯以生離死別之情的比較表現感情的深度。《詩經·綠衣》中“綠兮絲矣,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4]的句子以妻子做的衣服作為悼亡的線索;晉代潘岳悼亡妻子的詩中有“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5];唐代元稹《遣悲懷》有“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6]的詩句;丘濬則說“刀尺存余澤,衣箱閉故封”。詩人不許別人移動妻子的故物,是在感情上還有幻想:“情知是死別,猶冀或生逢。”10年之后,他尚在《夢亡妻》一詩中寫到夢中與亡妻相會:
越南冀北路紛紛,死別生離愁殺人。誰信十年泉下骨,分明猶有夢中身。
丘濬的悼亡詩在明代詩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胡旭在《悼亡詩史》中有準確的剖析定位,他認為丘濬悼亡詩的最大特色,是注重對亡妻的道德評價。這一特點與他的理學家身份相關。但是也不能因為他的理學家身份,就懷疑他的詩歌情感的真實性[7]248。這一論斷大致不差。如前文所述,丘濬是一位重實學的理學家,而非討論道德心性的道學先生,這就使他的悼亡詩中的理學色彩與內在情感融合在一起,具有生命的溫度,而非枯燥的道德說教。當然,夫妻“恩愛”中“愛”的因素是不能忽略的。這是對于夫妻之“情”的張揚,而這與明代前期理學濃厚的氛圍是不協調的。如何解釋此種現象?除前文所述丘濬的思想氣質的獨特性以外,恐怕還有其他內在的原因。明前期悼亡詩的優秀作者丘濬并非孤例,與他同時代年長于他的于謙,也有悼亡組詩,藝術成就也高。于謙也是“理學思想培養出來的標準儒者”[7]236,在他的思想中,國大于家,君大于妻子。胡旭由此認為,關于宋明理學對于文學的負面影響的判斷,還需要重新考量[7]236。
(三)友朋夭逝,才華可期
丘濬關對于那些奔波在科舉之路上的年輕朋友的死亡,也給予真誠的哀悼,痛惜于生命價值的不得實現。如《哭劉文燦》《哭唐珊》《哭張書紳大尹弟紀》等篇皆是。劉文燦是詩人早年結交的一位舉子,蜚聲科場,才華突出,然蹭蹬多年,不得一官而去世。丘濬作詩10首悼念他,后來詩稿遺失,再補作以示紀念:
搜索終千古,勤劬老一經。夜來翹首望,天上失文星。
唐珊是丘濬的弟子,在進京趕考的路上不幸去世,丘濬作詩遺憾痛失英才:
洗耳沿途聽捷音,捷音未到訃先臨。苗生南畝初成秀,云出西郊未作霖。天上遽傳宣李詔,世間空有鑄顏金。青年妙質歸冥漠,負我平生望汝心。
在生命的面前,丘濬開始懷疑科舉功名的意義:
畢竟十年成底事,等閑一第是何人?燈窗枉費平生力,旅櫬空歸既死身。
(四)悲劇女性,真摯同情
依儒家的倫理生命價值觀,歷史上許多悲劇女性如王昭君、虞姬、綠珠等人的價值都無法被明確衡量,而她們都曾進入丘濬筆下。對于她們的命運,丘濬賦予無限的同情,并進一步反思他們的生命價值。重生尊生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周易·系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8]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9]梁漱溟認為:“這一個生字是最重要的觀念,知道這個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話,孔家沒有別的,就是要順著自然道理,頂活潑頂流暢的去生發。他以為宇宙總是向前生發的,萬物欲生,即任其生。”[10]有學者認為:“儒家這種生命價值觀是以道德為本位的。其理性精神表現在,它一方面肯定人的生命價值,主張重生珍生,反對輕生賤生;另一方面也反對茍且偷生,將生命價值與道德理性結合在一起。”[11]丘濬對于歷史中悲劇女性的吟詠屬于前一個方面的傳統,他明確地批判統治者對女性生命的戕害。
在丘濬所作關于王昭君的詩歌中,突出表現了他的這種生命意識。丘濬共有9首詩反復吟唱王昭君,似乎在他心中有一種昭君情結。唐代的杜甫、宋代的王安石和歐陽修等著名詩人都有詩寄情于這位漢代的悲劇女性,丘濬承襲了這一傳統。他在詩中強烈批判漢元帝以犧牲女性幸福換取政治和平的屈辱行徑。他說:
堂堂中國仗天威,雷令風行孰敢違。卻把蛾眉為虜餌,不羞巾幗代戎衣。知心只計恩深淺,論事都忘理是非。豈是漢家生女子,桑弧蓬矢掛宮闈。
在明代前期北方游牧民族長期威脅王朝邊境的背景下,丘濬的詩歌具有現實指向。他甚至以嘲諷的口吻反問當朝統治者:“嬌態能傾國,蛾眉解殺人。妾身亦何幸,為國靖邊塵。”(《明妃曲》)杜甫說昭君“環佩空歸月夜魂”[12]3849,他說:“骨已成胡土,魂猶戀漢庭”(《明妃圖》);杜甫說“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12]3849,他說“千年遺恨在,孤冢草青青”(《明妃圖》);王安石說“人生樂在相知心”[13],丘濬說“當時不遇毛延壽,老死深宮誰得知”。在《明妃圖》中,丘濬構思了一個昭君寄語的情節:“使回煩寄語,莫殺毛延壽。君王或夢思,留畫商巖叟。”勸諫君主,用意顯豁。
二、 對自我價值的期待與生命不可把控之間的矛盾
丘濬對于生命價值的理想,有著理性而明確的定位,有著一貫而執著的追求。在現實生活中,其個體生命卻受到束縛,存在種種的不確定性,無論是歲月的流逝、身世的漂泊,還是官場中的無聊乏味,都使他的生命狀態呈現出難以調和的復雜性。
(一)科舉追求的迫切感
丘濬是儒家思想培育出來的理學家,他的人生理想無疑是儒家式的,是修齊治平的傳統。這一理想在明代的現實外化就是科舉仕途之路。只有進入仕途,才能實現士大夫的生命價值。實際上,丘濬表現進取意識的詩歌甚少,而且集中在他的青少年時期,如《夜坐和曲江感遇詩韻》表達珍惜光陰,自勵奮發的決心:
人生天地間,奮發須有為。不見東注波,逝者恒如斯。心中茍自盡,意外非所知。嗟爾亡羊者,紛紛多路岐。
丘濬的科舉路并非坦途,他卻一直保持執著的科舉信念。他第二次會試落榜,作《辛未下第還至金陵寄友》:
都門草草惜分群,把酒看花每憶君。四海弟兄同素志,百年交誼在青云。陸沉共笑安蛇足,務隱還期變豹文。鐵硯未穿心不死,文場重與策奇勛。
兩年之后,丘濬再赴京師,果然一舉中第,二甲第一名,以庶吉士身份入翰林院庶常館讀書,并參與修撰《寰宇通志》。九年之前鄉試第一,如今會試又中二甲第一,作為一名出身海外的學子能與天下英杰朝夕游處,丘濬感覺到無比的幸運。他作《初讀書中秘與修天下志書柬陳宣之》七律4首,抒發欣喜自得之情,身處書海之中,是“奪錦文章清禁里,登瀛人物玉堂中。回看人世仙凡隔,弱水浮埃迥不同”。此后的20余年間,除成化五年(1469)至成化八年(1472)間因母親去世丁憂家居,他的官階按部就班逐漸提升:36歲被授翰林院編修,44歲為侍講,47歲為侍講學士,57歲為翰林院學士,60歲升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67歲加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丘濬的仕途可謂波瀾不驚,一帆風順,他的詩中卻很少再能見到渴望建功立業的豪情。
(二)仕宦生涯的無力感
官場中的人事傾軋、爾虞我詐令丘濬厭倦不已,消磨了他的仕途之志。他讀到張九齡《秋懷》詩中“宦成名不立,志在歲已遲”的句子,聯想了自身的現實境遇。丘濬感喟自己缺乏先哲的執著理想,“血氣不覺衰,境變志亦移。終為小人歸,甘與世俗隨”,可以相信這是丘濬憤世嫉俗的過激之言。詩人甚至產生人生虛無的感慨:“人生在所處,卑卑徒而為?”現實的環境導致了詩人的頹唐情緒,他在官場中“閱人日已多,涉世日已深”(《秋懷》),所見盡是友朋間的虛偽與背叛,他說“許身徒稷契,知己卻孫劉”(《即事》),“萬事皆天豈自由,何須屑屑咎孫劉”(《丁未秋偶書》)。在名利場中,處處多是孫權、劉備似的利益之交,癡尋知己徒枉然。他說“高官世所慕,直道古所欽”(《秋懷》),秉性耿直的丘濬浸淫官場日久,身經目睹,當不為少,無奈之下,常起歸隱之念:“故山猿鶴休嘲怨,早晚乘桴海上浮”(《丁未秋偶書》),“有山不歸去,何勞憶山吟”(《秋懷》),“海上孤飛燕,沙頭決去鷗。斂將經世志,終老向菟裘”(《即事》)。官場中的無聊應酬、曲媚事人,也是丘濬意欲歸隱的另一個原因。他有詩表達此種情緒:“了無毫發負公私,苦奈年年尚欠詩。不是阿諛即啼哭,等閑償足是何時?”
在丘濬的詩文集中,祝壽詩、挽詞、贈別等應酬之作隨處皆見,碑文、銘文、序文數量不菲,許多都是應人請托的無聊之作。就連皇帝也請他代筆作詩贈諸侯、贈百官,這些與自身毫無關聯的詩文創作,令丘濬苦惱不已。隨著官階日高,年齒日增,他的內心世界愈來愈彷徨。74歲時,丘濬進封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官居一品,作《入閣謝恩表》,表達年老無力報效的生命狀態:
所慮臣年已老,臣病日加,志欲為而氣力不克,機可乘而歲月不待,有如伏櫪老驥,志雖存乎千里,而力已難馳,鎩羽倦禽,脰徒奮乎一鳴,而飛不能遠,終致困躓之失,有辜豢養之恩。[2]4008-4009
既然過著“御酒飲余黃票揭,詔書草罷紫泥封”的榮貴生活,就要“君恩代為報親恩,誓以報親心報君”(《受一品封》),而現實卻是“殘念故智余無己,圖報無能只自傷。”(《冬夜掖門待漏口占》)丘濬有時會喟嘆少年理想失落的悲哀:“可憐歲月閑中過,年少功名異所期。”(《歲丙申六月伏中雨中待朝偶成》)陷入意欲報效或歸隱相交替的煎熬:“心態時時思報國,神魂夜夜夢歸田。”(《壬子九日偶書》)國家政務都是俗事:“內閣歸來日已沉,無端世事苦縈心。”(《內閣晚歸》)。束縛住他的自由身:“身似凍翎飛不去,事如春蔓苦相纏。”(《病起寫懷》)。最終,他的心態出現了難以調和的矛盾:一方面他時刻想著歸去,一方面又有所留戀;一方面時時不忘感戴皇恩,表現忠誠,一方面又度日如年,禁受著官場空虛的煎熬;一方面是俗事纏身,一方面又感覺著才無所施。生命的矛盾時時沖擊著他的內心,各種情感交替涌現,無法釋懷。他在畫像《自贊》里有近乎禪理似的表達:
天賦汝以性,而汝不能盡。地全汝以形,而汝不能踐。謂汝全無用耶,則似乎亦有所為。謂汝了無知邪,則似乎或有所見。噫!我則汝也,尚不知汝之有無。[2]4486
這是他的自我對話,表現了其對自身生命價值歸屬的焦慮。在丘濬的高頭講章中,看到的是一位富有道統使命感的士大夫;而在其詩歌中,我們卻看到了一位彷徨在宦途中的正直知識分子的矛盾心靈。兩方面都是丘濬真實的表達,一面是理性,是責任與擔當;一面是感性,是生命的彷徨。
(三)客居京師的漂泊感
漂泊是世界范圍內文學的常見主題,中國古代詩歌之傳統尤為突出,《詩經》中的征旅詩歌無不蘊含著漂泊的意味。就作家個體而言,從屈原開始,到李白、杜甫、蘇軾,生命體驗中都充滿了漂泊意識,詩歌中的表現也非常充分,研究成果甚多,茲不贅述。屈原和蘇軾主要是政治的放逐帶來的生命的疏離,是與政治主體的疏離,其生命是被操控的,現實中的流放,也是精神的流放;李白、杜甫的漂泊更能代表古代士人漂泊生活的典型樣態,為了仕途、為了理想,為了生存,他們總是奔波在路上。日本學者松浦友久稱李白的這種意識為“客寓意識”,他認為李白是不安定的客之子,沒有土地,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固定的家鄉,任何一方都不是久居之地,所以具有“客寓意識”[14]。丘濬就屬于這一種類型的生命狀態,他對自身生命價值的疑慮常常伴隨著漂泊思鄉之感和歲月遷流之思。
從27歲進京應試,到75歲病逝皇都,在近50年的歲月里,丘濬絕大部分時間寄居京師,因而他在詩中始終把自己視作客子、一個羈旅中人。生命的漂泊感貫穿了他一生的詩歌。漂泊感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思鄉。丘濬曾作《懷鄉賦》:
朝吾登乎金門兮,夕偃蹇乎玉堂。置身非不高兮,信美非吾鄉。入結群仙之綬兮,出聯七貴之鑣。游從非不多兮,匪吾齠齔之交。[2]4465
在丘濬的作品中,以思鄉為主題的詩歌寫得最為真摯動人。特別是他的五言絕句,格調清新,感情純樸,很有藝術感染力。如“萬里思歸客,傷心對月華。愿憑今夜影,回照故園花”(《客中對月》)、“別后經三載,斯須不暫亡。殷勤問季主,報道壽元長”(《思親》)、“一自新河別,經今三月余。聞鴻即延佇,恐有帶書來”(《思兄》)、“客里逢秋景,思鄉倍愴神。依然今夜月,不是去年人”(《中秋有感》)等。客居京華的詩人,一事一物都能觸動鄉愁。每逢親友歸南海故鄉,送行的人最是愁苦,《送人歸鄉》詩云:
年年京國里,日日送行頻。又別海南客,重思堂上親。輿圖垂地盡,江海獨歸人。為報吾兒道,官居只舊貧。
京華非久居之所,漂泊仕途的人們來來往往,眼見新朋舊友一個個離京歸去,送行的詩人歸而不得,此種對比甚為強烈。享受著京城的美味佳肴,使他常想起母親:“薊北天南萬里長,欲歸無計苦思鄉。帝城品物多嘉味,每恨慈親未得嘗。”時節的變換更是常年困擾著思鄉的詩人。每到秋天,衰颯的秋風也攪動沉淀的鄉愁:“颯颯秋風聲,才生便不停。去年猶可耐,此度不堪聽”。詩人心情百無聊賴,秋聲入耳,思緒聯翩:“客里渾無賴,櫥頭俄有聲。倚窗頻側耳,無限故鄉情。”(《秋風》)氣候的變化令他想起家中的親人:“北風吹枕席,寒氣覺侵肌。況乃白頭母,高年血氣衰。”(《初寒》)秋天鳥兒的鳴叫也令他悲傷不已:“越客不識雁,聞之心輒悲。自憐長作客,不似鳥知時。”丘濬強烈的思鄉之情往往以詩題直接標示,如《思歸》《思家》《思親》《思歸偶書》《辛亥思歸偶書》等。“萬山歸路夢中家”(《秋夜偶吟》)是丘濬常見的心理狀態:“游學他鄉未得回,夢魂常繞望鄉臺。西風曾到幽閨否,寒到身邊衣未來。”(《客京師作》)果然,在一個秋夜,他夢中回到了熟悉的故園,枕上醒來,依然是羈旅他方,他作《夢起偶書》記下心靈的波動:
秋來歸夢到家園,景物分明在眼前。樹掛碧絲榕蓋密,籬攢青莿竹城堅。林梢飄葉重堆徑,澗水分流亂落田。乞得身閑便歸去,看魚聽鳥過殘年。
丘濬的思鄉念遠的詩歌如此之多,貫穿了他在京師為官的所有歲月。在儒家道德中,個人的親情在效忠封建王朝的大前提下顯得微不足道,然而這種感情又是最切身、最真實的。丘濬在戲劇《五倫全備記》《投筆記》中表現忠孝之間的矛盾和痛苦,應該也是他自己仕宦生涯的親身體驗的寫照。
(四)歲月流逝的焦慮感
對于歲月遷流、生命消逝的敏銳感覺也是丘濬詩歌中常常表現的內容。他在畫像《自贊》中曾言:
蓋人承父母之遺體,為天地之委蛇,有形而動,不可久恃。[2]4486
在送友人的詩序中也曾表達類似的感慨:
老成日以凋喪,壯者日以老,少者日以壯,今之生者,又且嶄然而起矣,人生斯世能幾何時?彼蚩蚩者,乃欲為千萬年不可拔之計,何哉?”[2]4215
人的內心是復雜的,經世之志外,丘濬也會產生生命短暫、及時行樂的感慨,如“一日生,一日落。明日不如今,今日不如昨。短歌行,聲苦惡。人生行樂須及時,腰纏何必揚州鶴”(《短歌行》)、“人生會有老,老至不自知。壯心恒未已,外貌忽已移。青青巾中發,俄然成素絲。灼灼鏡中顏,忽覺如枯梨。盛年不可恃,行樂須及時。有酒且痛飲,不醉將奚為”(《感興》),然而年歲漸老、事業無成,更是詩人生命感受中的常態:“短發忽絲絲,天公未老期。百年將及半,有志未曾施。”(《白發》)此時的丘濬為從五品的侍講學士,尚未進入政治統治的高層,他以禮學教化天下的素志還不得施展,白發盈首,時不我待。有時他又自我安慰:“與老無期遽見侵,不知不覺忽盈簪。朝來把鏡驚還笑,已到頭顱未到心。”(《覽鏡有感》)詩人沒有邀請衰老到來,它卻突然降臨,白發漸多黑發少,殊堪心驚,轉念一想,志向未衰,啞然失笑。面對衰老的臨近,豁達之中有時又夾雜著空幻、思鄉的種種情緒。成化十九年(1482)歲末,丘濬寫下《歲暮偶書》:
屈指明年六十三,人情世態飽經諳。幾多黑發不曾白,無數青衿出自藍。大半交游登鬼錄,一生功業付空談。不堪老去思歸切,清夢時時到海南。
功業無成的失落、顏容老去的無奈、客居異地的鄉思,種種情感交織在一起。他在去世前一年的生日寫下《甲寅初度》,中有“所欠是歸兼是死”的句子,對于衰老的反應直白而激烈。
詩歌中的丘濬,感傷情緒多于進取精神,個人心理感覺與現實社會地位存在錯位,詩中衰憊矛盾的官員形象與現實中為經世著述的思想家面目似乎難以兼容,如何理解這種現象?他在詩歌中對自身生命形態和生命價值充滿了不確定和猶疑的態度,應是他面對現實壓力的個體宣泄,是真實的“另一個”丘濬。
三、 在歷史中體認生命的不朽
丘濬是理學家,同時也是歷史學者。他在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參與編撰了許多史志著作,具有深厚的史學修養。在職責范圍內,他編撰歷史著作的目的是為封建國家的統治提供借鑒,他在其中持理性的態度,以一個負有責任的士大夫發出自己的聲音。在詩歌中,他對歷史人物的生命價值則作了藝術化的思考。本質上,丘濬對他自己的功業是持懷疑態度的,這在前文多有表述。然而對永恒生命價值的實現,他并不懷疑。當他把目光投向歷史,圍繞三不朽的觀念,許多歷史人物就縈繞在他的筆端。無論是功業彪炳的將相、才華卓越的文人,還是超脫自由的隱士,都進入丘濬的筆墨云煙之中。
(一)立德
丘濬身為理學家,對于歷史中的忠臣烈士,懷有特殊的崇敬之情,以詩歌表彰他們的氣節。另外,在他的眼中,不與統治者合作的隱士也是立德不朽的典型。岳飛是千古愛國英雄,他死后,封建時代的士大夫本著為君主避諱的原則,把迫害岳飛的罪責全部推到秦檜的身上,在杭州的岳王墳前,特意鐵鑄秦檜夫婦跪像以昭示后人。丘濬作為正統的理學家,能夠突破一般迂腐文人的陋見,為岳飛作詩、詞各1首,把矛頭指向最高統治者。詩云:
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草木猶知表藎臣,君王乃爾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為誰人。忠勛翻見遭殺戮,胡亥未必能亡秦。嗚呼!臣飛死,臣俊喜,臣俊無言世忠靡。檜書夜報四太子,臣構再拜從此始。
詩中說,連墳前的樹枝都南向朝廷,而昏庸的君主宋高宗卻不明真相,相信了奸臣的讒言。
丘濬另有《沁園春·寄題岳王廟》,以口語化的風格表達對歷史悲劇的憤慨之情。詞云:
為國除患,為敵報仇,可恨堪哀。顧當此乾坤,是誰境界,君親何處,幾許人才。萬死間關,十年血戰,端的孜孜為甚來?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柱石潛摧。 雖然天道恢恢,奈人眾將天拗轉回。嘆黃龍府里,未行賀酒,朱仙鎮上,先奉追牌。共戴仇天,甘投死地,天理人心安在哉!英雄恨,向萬年千載,永不沉埋。
詞中說,冤殺岳飛,親者痛,仇者快,十年抗金終成幻。當年岳飛唱起“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豪壯歌詞,到如今,卻是追其返回臨安的詔書,此情此恨,萬年難滅。
文天祥是丘濬崇尚的另一位愛國者。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在洪武九年于北京建文天祥祠以示紀念。祠廟位于國子監以西不遠處,丘濬28歲落第以后即入太學讀書數年,常去文天祥的祠廟,拈香拜祭的同時以詩紀念:
舉世紛紛拜名節,獨捐一死正綱常。英雄千古誰褒獎,自有真人出鳳陽。
綱常名教的傳承,是理學家關注的要點,帝王建祠又何嘗不是為了名教呢?丘濬熟讀文天祥詩文,曾集其詩詞為七絕1首:如此男兒鐵石腸,英雄遺恨落滄浪。人生自古誰無死,轟轟烈烈做一場。上述4句依次出自文天祥的《登樓》《蒼然亭》《過零丁洋》《沁園春·題張巡廟》。他崇拜文天祥,文天祥以《沁園春》詞牌題張巡廟,丘濬以《沁園春》詞牌題岳王廟。
丘濬認為除儒家的道德理想外,道家的隱逸人格也是不朽的,這是他的宏通卓識之處。中國古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基本內容就是追求修齊治平的儒家理想。在丘濬看來,隱逸之士求得自身的個性自由與滿足,保持人格之獨立,同樣具有不朽的價值,甚至可以超越建功立業。
嚴子陵與陶淵明是他的偶像。《嚴子陵圖》贊揚了隱士傲視富貴,但求真純自在的個性精神。詩云:
長笑劉歆頭,不及嚴陵足。厥角稽首勢若崩,況敢橫足加帝腹。嚴先生,何壯哉!釣臺豈但高云臺。清風遼邈一萬古,落日頹波挽不回。
詩中兩次用對比。一是劉歆與嚴子陵,西漢末的學者劉歆,汲汲追求利祿,依附王莽,最終死于非命,而嚴子陵面對皇帝親手送上的富貴,拒而不納;二是云臺將相與嚴子陵,在丘濬眼中,榮華易逝,精神長存。在這里,丘濬似乎是一位道家的隱士。在另一首《寄題釣臺》中又以劉秀江山與釣臺作比較,突出隱逸精神的不朽:
祚終四百已無漢,灘歷千年尚姓嚴。終古祠堂釣臺側,水光山色擁高檐。
陶淵明是隱逸詩人之宗,在《彭澤圖》中,丘濬賦予了陶淵明隱居精神以儒家忠貞的色彩。詩云:
幾年作縣山城里,只緣五斗官倉米。終朝汩沒簿書間,矮屋抬頭頭不起。可堪時事日已非,賦歸豈為鄉里兒。候門童子望我久,奮飛不得嫌舟遲。
五六句所表達的詩意,他在另一首《題淵明圖》中作了直接表述:“桓公事業晉山河,觸目傷心可奈何。”詩中說,陶淵明的曾祖陶侃為東晉大司馬,去世后謚“桓”,他為晉王朝的穩定立下汗馬功勞;而陶淵明生活的時代,已經到東晉末期,權臣干政,皇權岌岌可危,陶淵明經歷了劉宋代晉的朝代更迭,他心念故國,只有選擇“籬下菊花門外柳,時時相對醉吟哦”的隱居生活。這種見識又體現了丘濬的理學家本色。
(二)立功
有學者曾指出:“以治國平天下為儒者德業之完成,為儒者人格的最高形態,這是丘濬的特殊之處。”[15]丘濬最為仰慕的前代政治家是張九齡。明代時,海南隸屬廣東,因此,張九齡是丘濬的同鄉先輩,是丘濬一生心儀的歷史人物。在為張九齡文集作的序文中,丘濬通過與出身南方的陸贄、王安石、歐陽修和唐代的宰相們比較,認為張九齡不僅是嶺南第一流人物,而且是江南第一流人物,是唐代第一流人物[2]4021-4022。
丘濬所作關于張九齡的懷古詩有十幾首之多。《感遇詩》36首是張九齡的代表作,少年時的丘濬勤讀揣摩,認真體會,既得奇文,又得奇志,他作《夜坐和曲江感遇詩韻》4首述懷。丘濬夜坐空齋,似乎與前賢冥心感通:“空齋坐幽獨,夜氣淡以清。冥心古圣賢,悠哉怡我情。”閱讀著他的感遇遺篇,不由得再三感嘆遇合的艱難:“南極有名相,風度邈難得。鴟梟群刺天,孤鳳戢其翼。韶石佳山水,因之增秀色。班班青史間,流譽靡終極。莊誦感遇詩,臨風三嘆息。”少年的丘濬也要像前賢一樣,展翅高飛,一展大志:“鳳凰翔千仞,枳棘安足顧。一朝覽德輝,棲止梧桐樹。”他告誡自己,既然有這樣的文脈淵源,只要刻苦自勵,終將有所成就:“深源無淺流,高樹無卑枝。人生天地間,奮發須有為。”他還刊刻張九齡文集以示崇仰之情。 丘濬在《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中回憶刊刻張九齡著作的過程:
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太學,遍求之兩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群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2]4285
他的詩中有云:
兒時夢寐慕鄉賢,購訪遺編四十年。秘閣抄來郡齋刻,文章功業兩皆傳。
27歲時,丘濬赴京應考,跋涉梅嶺,路過梅關,首次拜謁張九齡祠廟,作《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平生夢想曲江公,五百年來間氣鍾。行客不知經世業,往來惟羨道傍松。
既表達自己的崇仰與興奮,又慨嘆世人的無知與漠然。晚年的丘濬,創作組詩10首寄題曲江祠廟。鄉賢的盛世功業是他一生企冀的境界,他在詩中回顧了張九齡一生的主要事跡,盛贊其功業:
嶺海千年第一人,一時功業迥無倫。江南入相從公始,袞袞諸賢繼后塵。
(三)立言
就三不朽衡量,丘濬應歸入立言不朽的人物序列。在為蕭镃的文集寫的序言中,他曾表達過立言不朽的觀點:
嗟乎!人生天地間,具形與氣,形動而為威儀,氣出而為言辭,人死則威儀隨形澌盡。惟言也者,宣于其心,發于其氣,著為辭采,載為簡冊,而常留于天地之間,千萬年而不朽。[2]4028
丘濬心中立言的偶像,不是儒家先賢,而是唐宋文豪李白、蘇軾。
蘇軾被貶謫儋州三載,為海南島留下豐厚的精神遺產。少年時期,閱讀學習蘇軾的詩文作品是丘濬的必修課業。蔣冕《瓊臺詩話》載八九歲時,丘濬在社學中曾以《東坡祠》為題吟詠,有“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敬醉翁”的句子[2]5160。他有一首《讀東坡詩》記錄下了學習的心得。在詩中,丘濬描繪了蘇軾詩歌多樣化的風格:
東坡居士真天人,文章豪邁如有神。光焰豈但長萬丈,筆端真可斡千鈞。萬斛源泉隨地滾,玉盤明珠無定準。虢國夫人控玉驄,淡掃蛾眉卻胭粉。風霆翕歘一時來,須臾雨霽煙云開。虹收電戢星斗爛,一天明月光昭回。
詩中說,蘇軾才思涌動,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涌出。其筆端變化萬千,不可捉摸,在語言上摒棄裝飾,自然灑落。其勢或雷霆萬鈞,或雨霽云開。丘濬形容得如此貼切,說明他在少年時對于蘇軾的詩心有著準確的體會。他贊揚蘇軾:
此翁落落不可得,謫仙少陵乃其匹。小兒淮海秦少游,大兒豫章黃魯直。前生自是永禪師,后學宜稱韓退之。
他稱頌蘇軾巨大的才華吸光了眉山的靈氣:“眉山至今草木枯,五百年來生一個。”蘇軾居海南三年,留下雙泉遺跡:“海南遺跡有雙泉,我家依約雙泉邊。”丘濬生為海南人,又與蘇軾之魂相伴,何其幸也!落日云煙籠罩了天空,雙泉朦朧,若有若無:“雙泉湮沒不可見,山城落日生云煙。”
丘濬心儀的另一位大詩人是李白。他在進京、歸鄉的旅途之中,數次路過金陵。李白在金陵逗留的遺跡令他流連忘返,李白在金陵創作的詩歌也令他傾慕不已。過采石磯,丘濬作七律1首吊絕世天才:
蛾眉亭下吊詩魂,千古才名世共聞。江上波濤生德色,磯頭草木帶余醺。光爭日月常如在,思入風云迥不群。岸芷汀蘭無限意,臨風三復楚騷文。
此詩一二聯交代行蹤,在黃昏時分,詩人來到峨眉亭下,這時波濤變幻了色彩,江邊的草木尚帶落日余暉的溫煦。第三聯由唐宋詩人的詩句變化而出:“光爭日月常如在”從李白的“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16]化出,“思入風云迥不群”融合杜甫“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12]107和程顥“思入風云變態中”[17]的詩句。尾聯結意,宮闕不再,文章不朽,在晚風中,丘濬默默吟誦起楚騷的篇章。李白在金陵作《登金陵鳳凰臺》,丘濬作兩首追和之,《和李太白鳳凰臺韻》《和李太白韻寄題金陵 》,同用流、丘、洲、愁,氣象與原詩頗為神似。第二首云:
昔年曾作鳳臺游,萬里長江入望流。龍虎峙形長拂闕,金銀厭氣漫成丘。眼空八表人間世,興寄三山海上洲。卻笑古人多事在,煙波云月起閑愁。
仔細考察丘濬的詩歌創作,特別是抒發個人情懷的部分,與他本人的文學思想是不盡一致的。他的文學思想還是以政治教化為中心的功利主義的觀念,所謂“達政事”“備問對”“厚人倫”“美教化”,屬于儒家的一貫主張[18]。儒家文學思想中,對于個人的生命世界的復雜性關注是薄弱的,詩歌抒情的本性,使得丘濬這樣的理學大師在創作實踐中,也會偏離他的主張,呈現個人豐富的心靈世界。丘濬有關個人生命本體的詩性表達的創作心理,與他的個別詩學觀念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他關于《詩經》作者創作心理的描述,正可用來評價他自己的抒情詩創作,他在《大學衍義補》中云:
蓋以人之生也,性情具于中,志趣見于外,必假言以發之也。言以發其心之所蘊,志有所抑揚,言不能無短長;心有所喜怒,言不能無悲歡。[2]1160
在丘濬的詩中,親情與故土在其個體生命中占有首要的位置,他的公共的士大夫面目在詩中隱退,露出本我;經世致用的生命價值,常常被無意義的歲月所消磨,特別是隨著官階遞升,此種無意義的情緒愈加強烈;個體生命的終極價值,究竟如何判斷?他把目光投向歷史,將相、隱士、文豪的形象在他的詩歌中得到了再現,是他關于生命不朽的詩性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