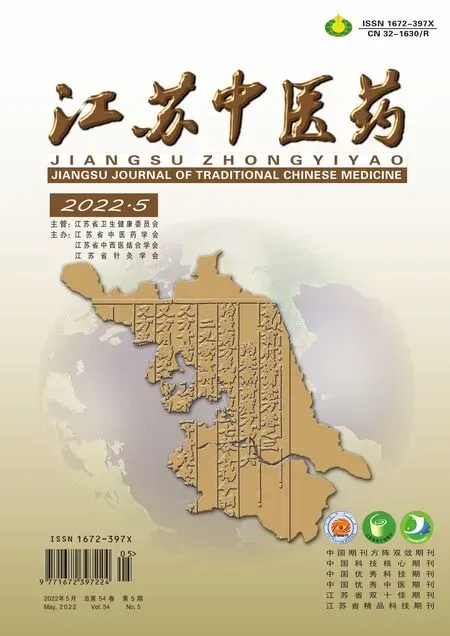桂枝茯苓丸加味辨治紫癜驗案3則
吳美達 曾秋菊 李紅毅
(1.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廣東廣州 510405;2.廣東省中醫院,廣東廣州 510120)指導:廖列輝
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牡丹皮、桃仁、芍藥)出自《金匱要略·婦人妊娠病脈證并治第二十》[1]:“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為癥痼害。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也。下血者,后斷三月衃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桂枝茯苓丸原用于治療婦科癥瘕,后世醫家拓展其應用范圍,包括冠心病、腦出血、慢性前列腺炎、痤瘡、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全國名中醫黃煌教授認為桂枝茯苓丸是全身血液循環障礙的調整劑,并將適用本方的患者體質歸納為瘀血體質[2]。
紫癜屬臨床常見病、多發病,是由紅細胞外滲引起的皮膚或黏膜顏色改變,其西醫學分類較多,治療方式不一[3]。紫癜的形態學表現為瘀點瘀斑,可將紅細胞外滲視為離經之血,病位在血分,屬中醫學“血證”范疇。廖列輝教授認為血瘀是紫癜的基本病機,活血化瘀之法應貫穿治療始終,并運用桂枝茯苓丸加味辨證施治,療效顯著。其中血熱者熱迫血出,當重視清熱涼血;血寒者寒瘀互結,應重視溫經通脈;老年者腎虛血瘀,重在益腎養血。現將其運用桂枝茯苓丸加味辨治紫癜驗案3則介紹如下。
1 血熱型紫癜,重在活血化瘀、清熱涼血
呂某,女,63歲。2019年5月11日初診。
主訴:雙下肢瘀點瘀斑反復發作4個月。患者于2019年1月無明顯誘因出現雙下肢瘀點瘀斑,顏色鮮紅,伴有瘙癢,外院診斷為過敏性紫癜,予激素及抗組胺藥等治療后癥狀緩解,停藥即復發,為減撤激素遂來就診。刻診:精神疲倦,怕熱,動則汗出,口干口苦,無咽痛,無發熱,無腹痛、關節痛,食欲旺,眠差,小便黃,大便可,舌質暗紅、苔黃膩,脈弦數。查體:雙下肢瘀點瘀斑,色暗紅,呈對稱分布。西醫診斷:過敏性紫癜;中醫診斷:紫癜(瘀熱互結證)。治以活血化瘀,清熱涼血。方選桂枝茯苓丸合犀角地黃湯加減。處方:
桂枝10 g,茯苓15 g,牡丹皮10 g,桃仁10 g,赤芍10 g,生地黃15 g,水牛角15 g(沖服)。7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飯后溫服。囑患者停用激素及抗過敏藥。
2019年5月18日二診:患者雙下肢瘀點瘀斑較前增多,疹色鮮紅,部分融合。皮疹撫之礙手,觸之稍熱,食欲旺,眠差,小便偏黃,大便偏干,舌質暗紅、苔黃膩,脈弦數有力。初診方水牛角用量增至30 g,牡丹皮用量增至15 g,加大黃5 g(后下),14劑。配合四黃消炎洗劑(廣東省中醫院院內制劑,主要成分為大黃、黃芩、黃連、黃柏)于局部皮損處外搽。
2019年6月1日三診:患者皮疹基本消退,散在暗紅色瘀點瘀斑。繼予二診方調治2個月。
隨訪半年,患者諸癥未再復發。
按:本案患者為血分伏熱,加之長期服用激素等免疫抑制劑使正氣受損,衛外不固,風濕熱邪犯于營血。血熱瘀阻,壅盛成毒,灼傷脈絡,血不能循經而走,溢于脈外,發為本病。血熱上炎,熱邪擾動膽火則見口苦、食欲旺,熱擾營衛則見怕熱汗出,熱盛傷津則見口干、小便黃,熱擾心神則難以入睡。激素等抗炎治療可短暫取效,停藥則反復,乃因有形之炎癥易除,無形之血熱難去。辨證屬瘀熱互結,治宜活血化瘀、清熱涼血,方選桂枝茯苓丸合犀角地黃湯加減。方中桂枝辛甘而溫,溫通經脈,推動血液運行,以行瘀滯;芍藥的作用和桂枝相反,酸斂之性使血回收,一通一收,對瘀血有消磨作用。《金匱要略》中并無赤白芍之分,一般野生者為赤芍,栽培者為白芍,兩者均有活血化瘀之功,赤者偏重涼血散瘀,白者偏重斂陰和營,葉天士云:“至入于血,則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本案患者血熱明顯,故選用赤芍。桃仁味苦,入心主血,且種仁類藥有柔潤滑利、降泄下行之性,故可破血分之瘀滯;牡丹皮味苦辛性微寒,苦能肅降,辛可開散,微寒之性可除熱,故牡丹皮可辛散祛除血分之郁熱;“血不利則為水”,茯苓通利三焦,利水滲濕以促進血瘀祛除;犀角(現以水牛角替代)入心、肝經,清熱涼血活血,清解血分熱毒而不留瘀;熱在血分,必傷陰津,故以生地黃清熱涼血、養陰生津。諸藥合用,熱清瘀化血行而無耗血動血之弊。二診時,患者皮損加重為戒斷激素的反跳現象,眠差、小便黃、大便干為熱入陽明、熾盛傷津,舌質暗紅、苔黃膩、脈弦數有力為血分實熱,故于初診方基礎上加大水牛角及牡丹皮用量以增清熱涼血之力,稍加大黃取釜底抽薪之意。血熱清則炎癥無以生,血瘀行則紫癜無從顯。配合四黃消炎洗劑外搽皮損,達消炎止癢、清熱解毒、活血化瘀之目的。本案患者為單純皮膚型紫癜,不伴有其他系統損害,故可大膽停用激素,但需告知停用激素后癥狀可能會加重,乃激素的戒斷反應,勿過于焦慮。
2 血寒型紫癜,重在活血化瘀、溫經通脈
潘某,女,38歲。2019年5月27日初診。
主訴:雙下肢瘀點瘀斑反復發作,進行性加劇1年余。患者1年前雙下肢出現多處鐵銹色苔蘚樣斑片,無自覺癥狀。外院曾予復方左氧氟沙星軟膏及蛇油外搽,金銀花、蒲公英煲水外敷及激素等治療,均無效。刻診:神疲乏力,惡寒,無汗,四肢涼,口干無口苦,胃納可,眠差,小便可,大便偏稀,每日一行,舌質淡紅、苔白膩,脈弦細,既往月經量少。查體:雙下肢多個鐵銹色苔蘚樣斑片,邊界清楚,大小不等。西醫診斷:色素性紫癜性皮膚病;中醫診斷:紫癜(寒瘀互結證)。治以活血化瘀,溫經通脈。方選桂枝茯苓丸合當歸四逆湯加減。處方:
桂枝10 g,茯苓15 g,牡丹皮10 g,桃仁10 g,白芍15 g,炙甘草15 g,細辛3 g(先煎),當歸10 g,大棗15 g,川木通5 g。7劑。每日1劑,水煎,分早晚溫服。
2019年6月4日二診:患者舊皮疹較前稍變暗,無新發皮疹,神疲乏力改善,大便成形,余癥同前。繼予初診方21劑。
2019年6月28日三診:患者原皮損遺留暗色色素沉著,手足偏溫,無口干、惡寒,有汗出,二便調,月經量適中,周期規律。予初診方去細辛、川木通,加薄蓋靈芝15 g,14劑。
隨訪半年,患者諸癥未再復發。
按:本案患者惡寒、四肢涼、大便偏稀、平素月經量少,皆為厥陰肝血虛寒之象。肝主藏血,肝寒則血寒。血液循經脈流注有賴陽氣的推動,寒傷陽氣,寒凝血滯,寒與血相互搏結成瘀,故皮膚瘀血反復不愈。《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陽化氣”的功能不足,機體無力輸布陰津,陽氣不能運化陰形;“陰成形”太過,則瘀血難以排泄。因此,在活血化瘀的同時,應輔以溫經通脈,方選桂枝茯苓丸合當歸四逆湯加減。木通入肝經,能通厥陰之邪,細辛則可通少陰,兩藥合用疏通厥少二陰之氣機,使寒邪有出路。當歸入肝體補肝血,合桂枝溫通經脈,使陽歸于陰;白芍養血和營,配當歸增補益陰血之功,伍桂枝增調和營衛之效;大棗補血,配歸、芍可補血,配桂、辛則通陽;甘草補中兼調和諸藥;再加茯苓治水兼治血,桃仁、牡丹皮活血化瘀以消癥,使瘀血去,新血生。三診時,患者已無口干、惡寒,皮膚有汗出為陽氣驅寒外出、血液溫通之象,故去細辛、木通,加薄蓋靈芝補益脾氣。薄蓋靈芝味甘性平,功擅補肺益腎和胃健脾、安神定志,其補益之力優于普通靈芝。新血生瘀血去,故諸癥除。
3 血虛型紫癜,重在活血化瘀、益腎養血
張某,男,83歲。2019年5月9日初診。
主訴:雙手臂瘀斑、瘀點反復發作2年。患者2年來反復出現雙手臂、前臂等多處皮膚瘀點瘀斑,皮損可緩慢消退,無痛癢等自覺癥狀,多次查血常規、凝血功能指標均顯示正常。刻診:精神疲倦,畏寒肢冷,腰膝酸軟,口干,舌淡紅、苔少,脈沉細。查體:雙上肢皮膚散在暗黑色瘀斑,皮膚干燥、松弛、變薄,似羊皮紙樣改變。西醫診斷:老年性紫癜;中醫診斷:紫癜(腎虛血瘀證)。治以活血化瘀,益腎養血。方選桂枝茯苓丸合金匱腎氣丸加減。處方:
桂枝10 g,茯苓15 g,白芍15 g,牡丹皮5 g,桃仁10 g,生地黃10 g,懷山藥15 g,山萸肉10 g,澤瀉10 g,熟附子5 g(先煎)。7劑。每日1劑,水煎,分早晚溫服。
2019年5月17日二診:患者口干較前減輕,余癥同前。初診方生地黃、山萸肉用量增至15 g,7劑。
2019年5月24日三診:患者精神尚可,已無口干,畏寒肢冷明顯減輕,脈象較前有力,皮膚未見新起瘀斑。繼予二診方7劑。
2019年5月31日四診:患者瘀斑基本消退。予二診方易桂枝為肉桂5 g(焗服)。
予四診方調治半年余,患者諸癥基本痊愈未見復發。
按:腎為人體先天之本,主藏先后天之精,決定著臟腑氣血津液的盛衰。老年性紫癜是一種慢性血管性出血性疾病,本案患者皮膚發生老年性退變,膠原和彈性蛋白減少,輕微的外傷即可引起血管破裂出血。本病核心病機為腎陰陽俱虛。腎陰虧虛,精血虛少,皮毛失于濡養,故皮膚干燥、枯槁;腎陽虧虛,火不暖土,脾胃氣血生化乏源,脾不統血,故血液失于固攝而溢于脈外。腎陽乃一身陽氣之根,腎陽虛則無力推動血液運行,血行不暢停而成瘀。治宜活血化瘀,輔以益腎補血,方選桂枝茯苓丸合金匱腎氣丸加減。方中生地黃色黑,封藏腎精,山萸肉味酸,收斂腎氣,兩者均為補腎水之要藥;山藥補脾益胃,亦能補腎,為后天給養先天之意;腎水既補,瘀血未消,濁水未去,伍以茯苓、澤瀉、桃仁利水袪瘀,以固中焦脾土;桂附溫煦腎水,推動氣機之轉輸,若瘀斑未消,宜用桂枝之溫陽發散,若瘀斑已消,宜用肉桂之溫陽收斂;白芍與牡丹皮均入肝經,一收一散,可制桂附之火。二診時,患者口干減輕,但余癥未變,故增加生地黃、山萸肉用量以增滋腎水之力,寓意陰中求陽。三診時,患者脈象搏動有力,為腎氣始足,使腎水上承,則無口干,且津液隨腎氣輸布滋養周身血脈,故畏寒肢冷減輕。四診時,患者瘀斑基本消退,故易桂枝為肉桂以溫斂腎氣。腎虛血瘀體質得以改善,則瘀斑自消。
4 結語
上述3則驗案均以血瘀為基本病機,符合桂枝茯苓丸之方證。血熱者熱迫血出,合犀角地黃湯涼血止血,選用赤芍以涼血散瘀;血寒者寒凝血滯,合當歸四逆湯溫經通脈,選用白芍以養血和營;老年者腎虛血瘀,合金匱腎氣丸益腎養血,斑消后易桂枝為肉桂以溫斂腎氣。血瘀的根本病因迥異,需隨證靈活遣方。具體用藥時,赤芍多用于熱證、實證,白芍多用于寒證、虛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