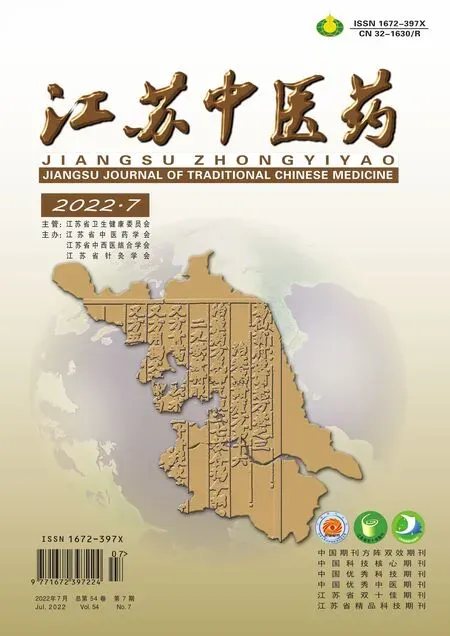國醫大師徐景藩腹診應用發揮
嚴曉雙 陸為民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蘇南京 210029)
腹診源于《靈樞·水脹》:“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東漢張仲景將腹診與辨證論治有機結合,《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曰:“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湯主之”,使腹診得到進一步完善。漢末至隋唐,腹診相關理論迅速發展,廣泛應用于各種疾病的診察,尤以《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為主要代表。然至宋金元時期,醫家只注重脈診與舌診,又受封建禮教影響,腹診漸失傳承,直至清代方被重視,但臨床運用仍較為少見。新中國成立后,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腹診幾乎與西醫腹部觸診類似。直至葉橘泉院士[1]將腹診與方證相結合,中醫“腹診”的定義才得以明確,并與脈診、舌診相參而用,對于現代醫家鑒別患者體質強弱、氣血盛衰、臟腑病位具有重要意義。
國醫大師徐景藩,衷中參西,融會新知,在長期的臨床診療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徐老在脾胃病的診治過程中,尤其強調腹診的重要性,其在明辨病因病機、病位病性、處方用藥、判斷預后等方面的腹診經驗具有重要的臨床指導價值,現將徐老臨床運用腹診辨治疾病之經驗介紹如下。
1 病位病機,腹診明晰
《靈樞·本藏》云:“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徐老認為腹診是基于“司外揣內”思維方式的一種診察方法,臨床診斷疾病時,可通過腹診明晰病位病機。
1.1 臟腑內居,以定病位 《靈樞·脹論》曰:“臟腑之在胸脅腹里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名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夫胸腹,臟腑之郭也。……故五臟六腑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由此可知,臟腑居于胸腹腔內,排列有序,各有其名,發揮著不同的功能。臟腑在胸腹的投射反映區域亦不相同,故可運用腹診診察不同部位出現的異常現象來推測相關臟腑發生的相應病變。
對于胃脘腹痛者,徐老通過腹診來確定病位。觸診時,先讓病人指點痛處,醫者先按其他部位,輕重適當,同時詢問是否有壓痛,最后按其自訴之痛點。若自覺痛點與壓痛位于中脘、梁門等穴附近,病位在胃;疼痛以上脘至鳩尾為主,病位在胃之上部近賁門處;疼痛以下脘為主,涉及水分、神闕等穴者,病位在胃之下部及脾、膽;若胃脘及心下、脅肋、背部、肩部按之均痛者,無論中脘是否疼痛,均應考慮肝膽胃同病,且以肝膽為主;若疼痛位于上腹左側、脅之下(肝經之所絡,無論左、右、脅下均為肝之分野),病位在肝;若脹痛及于臍部周圍,病位及脾與腸。形瘦之人常有“胃下(胃下垂)”,若下脘及臍部脹痛,但按之疼痛不著,仍應考慮病位在胃。中老年人若心下疼痛連及左下胸或心前區,劍突下按之無痛感,常考慮病位在心或心胃同病。除上述病證之外,胰腺疾患亦不可忽視,其臨床癥狀頗似胃脘痛,有時痛及脘之兩側,或可連及左脅肋部,腹部切診常在用力深按時覺痛,需仔細辨別。
1.2 審察病情,明析病機 俞根初在《通俗傷寒論》“按胸腹”一節中指出:“若欲知其臟腑何如,則莫如按胸腹,名曰腹診”[2],并稱腹診為“診法上第四要訣”,胸腹部為“五臟六腑之宮城,陰陽氣血之發源”。由此可知,胸腹部是氣化、氣機活動的場所,亦是經絡起止循環的部位,分布著許多募穴腧穴,腹診的運用正是建立在臟腑生理機能及氣機運轉的基礎上。故運用腹診可及時發現和分析臟腑機能與氣機失調時所致的各種病理變化,徐老臨證時亦常用腹診來審察病情、明析病機。
對于重癥肝炎患者,徐老常問其腹感、觀其腹形、按其癥塊、聞其腹音[3]。該病初起時患者常自覺腹部脹滿而腹形無明顯膨大,觸診或可觸及右脅下腫塊,癥狀常朝輕暮重、食后脹甚,此時以氣滯氣脹為主;隨著病情進展,腹形逐漸增大,輕者僅限于臍周圍,脹甚則連及脘部和小腹部,腹壁可見靜脈顯露,少數患者還可見皮膚黃染,臍周及中、下脘部位叩之空空然,此時仍以氣脹為主,并逐漸出現水脹,因脹而飲食日減、腹大日甚。由于短期內脹勢會隨黃疽等其他病癥加重而快速增長,故見腹皮繃急,可與慢性單腹脹之腹形隆起、如囊裹水狀相鑒別。此外,因氣滯水留日久則夾血瘀,還可見瘀斑、肌衄等癥,病邪及于脾胃則食欲不振、惡心、脘痞腹脹,及于肝膽則身面俱黃,失于疏泄則小便不利。因此,徐老認為本病與急黃、臌脹、血證等相關,且病證病機相兼錯雜,后期甚至可發展為關格、喘、水腫等病;其病位多在肝脾,久則及腎,病機多以本虛標實為主,本虛表現為陰虛或陽虛,標實多為濕阻、熱郁、血瘀等。
2 病證病性,腹診析微
腹診在《中醫大辭典》中的定義為以按、觸診為主,結合望、聞、問診手段來診察患者胸腹部位,以了解病情的診斷方法。其診察方法與現代醫學的“視、觸、叩、聽”相近,但手法、診察內容及理論體系卻不相同。西醫多通過腹部觸診來尋找器質性病變,而中醫腹診主要通過診察患者胸腹部脹、痛、滿、浮、痞、硬、急、結等病變征象,來判斷氣、血、食、水在人體分布的狀況,以察知臟腑寒熱虛實之病證病性等情況。
2.1 一胃三脘,可助辨證 臨床診療胃脘痛時,徐老常借助腹診,結合經絡穴位,協助辨證。徐老認為胃容量大且形態迂曲屈伸,故臨床多將胃分為上、中、下三脘來診察,上脘以胃底為主,下脘位于胃角水平線以下,中脘則位于上、下脘之間。喻嘉言在《寓意草》中提出“上脘氣多,下脘血多,中脘氣血俱多”,徐老認為此論甚為精辟,指出胃中氣體輕清而在上,故上脘多氣;中脘主磨化,為氣血生化之源,故中脘氣血俱多;下脘則存水谷及胃中津液,猶如濁陰,血亦屬“濁陰”范疇,故下脘多血[4]。以此為理論基礎,通過分區觸診可對胃脘痛進行初步辨證:如心下鳩尾至中脘部壓痛以肝胃氣滯為主;中脘、建里部壓痛,虛者多為脾胃氣虛,實者多為氣滯;下脘壓痛,如日久且固定局限,多為血瘀;上、中、下脘均有壓痛,則提示食滯不化。若自訴胃脘疼痛,但按診時痛點不明顯,常提示病情輕淺,以氣滯、肝胃不和居多;若按診時自訴不適,且有脹滿、痞塞不舒之感,提示濕邪阻滯。若用食指交替快速按壓腹部雙側梁門、天樞穴外側時,聞得內有漉漉聲響者,常為胃中有飲,或因幽門管部約而不利,導致氣血瘀結。若見患者腹部有手術疤痕,則需考慮皮肉損傷、疤痕收縮、結扎牽引等局部因素影響,有瘀血內停之可能。如胃已大部分切除,胃容量減少,飲食入于殘胃,迅達于腸,腐熟與運化過程失常,脾胃功能低下,則多為氣血虧虛。
除此以外,有胃病未愈而伴發心、肝、膽、胰等疾患者,常有上腹痛之癥,此時不可因痼疾而忽略“卒病”,當詳細診查,以免疏漏。如腸癰患者常以上腹疼痛為初發癥狀,若進行全面腹診,右下腹可見壓痛,此時應先治腸癰。
2.2 寒熱虛實,研判病性 《素問·至真要大論》言:“諸脹腹大,皆屬于熱。……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于熱。”《金匱要略》曰:“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者為實。”由此可知,腹診可用來判斷寒熱虛實等病性。徐老認為上脘壓痛多屬實證,中脘壓痛則有虛有實,或虛實兼夾,下脘壓痛多屬虛證或兼見血瘀。若患者腹部皮膚望之干枯無華,觸之硬結,多為虛實錯雜之證。當患者脈切之滑數有熱,但按腹無熱,則可知其熱在表易去;反之若按腹灼手,則知其熱深伏難去。故結合脈診有助于鑒別“真熱假寒”或“真寒假熱”之證。徐老指出,通過腹診可知患者之寒熱偏好、是否有壓痛、喜按或拒按等,從而可對疾病寒熱虛實等病性作出初步判斷,但臨證時還需結合其他診察信息,綜合判斷,切勿以偏概全。
3 方藥預后,腹診輔之
在確定了疾病病位病機、病性病證的基礎上,徐老運用腹診輔助確立治療原則和用藥,并推斷疾病的預后發展。
3.1 腹證不同,隨證治之 日本名醫奧田寬在其著作《腹證考》中提出:“仲景曰:‘隨證治之’,凡從事古疾醫者,必先明腹證,腹證明,而后藥能詳;藥能詳,而后方法正;方法正,則無病不愈矣。”[5]腹證可分為癥狀與體征兩類,痞滿、疼痛、動悸等自覺癥狀,問詢乃知;膨隆、濡硬、腫塊等他覺體征,望切乃得。故可通過腹診判定腹證,以腹證為據遣方用藥。《內經》中多有運用,如《素問·腹中論》中記載治鼓脹病心腹滿用雞矢醴方,治血枯病胸脅支滿用四烏鲗骨一藘茹丸等。
據徐老經驗,若上腹部劍突下胃脘(上、中、下脘穴)處自覺痞硬滿痛且拒按,治以和解瀉熱,方選大柴胡湯;若腹部滿痛持續、拒按,兼有痞滿燥實證,治以泄下,方選大承氣湯;若腹痛隱隱,喜熱喜按,得食可減,治以溫中補虛、緩急止痛,方選小建中湯;若自覺腹滿,而外形望之不滿,舌色紫黯時,當考慮內有瘀血,治以活血化瘀,方選膈下逐瘀湯;若胸骨后或劍突下飽脹,甚則疼痛,性質常為隱痛、脹痛或灼痛,伴噯氣、食物反流,治以理氣和胃降逆,方選四逆散加減;若脘脅脹痛或自覺抽動,伴胸悶、情志不舒,治以疏肝和胃解郁,自擬徐氏疏肝和胃湯(紫蘇梗10 g,制香附10 g,炒枳殼10 g,炒白芍15 g,陳皮6 g,川芎10 g,佛手10 g,廣郁金10 g,炙雞內金10 g,莪術10 g,生薏苡仁30 g,石見穿15 g,甘草3 g),兼脘脅痛劇者加延胡索、川楝子緩急止痛,兼胃脘自覺灼熱嘈熱者加牡丹皮、山梔、象貝清瀉肝胃郁熱;若脘腹鳴響,脹滿抽痛,叩之空空然,治以補脾斂肝祛風,藥選白術、扁豆、防風、烏梅、五味子、藿香等,甘、酸、辛相合,以肝脾同治。
3.2 腹證變化,推斷預后 《靈樞·外揣》曰:“五臟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臟腑、經脈、氣血津液等內在的變化必然在外部胸腹有所反映,隨著臟腑氣血盛衰的變化,腹證也會隨之改變,因此,徐老常借腹診來推測疾病的預后。當患者脘痛發作較劇時,若疼痛快速減輕,特別是短時間內覺疼痛如失,不可放松警惕,應當注意觀察有無黑便,謹防出血可能。若僅覺疼痛及壓痛減輕,但飲食減少,形體更瘦者,不宜過于樂觀,應警惕不良轉歸;若疼痛緩解,余癥亦隨之改善,說明病情向愈。此外,腹診還可與脈診相參,凡腹證與脈證相符者為順為生,預后佳,不符或相背者為逆,預后不良。
4 驗案舉隅
王某,女,44歲。1992年11月18日初診。
主訴:脘腹發脹1年余。患者食后上腹發脹,繼而臍下、脘腹均脹,脹甚則隱痛,得噯氣、矢氣則舒。腹脹晨起稍舒,進食后即覺脹,午后加重,晚餐后尤甚,整個腹部均感脹滿,衣褲嫌緊。因脹而妨食,食量減少約1/3,啖甜食、飲水稍多則更脹。1年之中,夏暑癥狀最輕,氣候轉冷之時,尤入秋后脹滿加重。月經基本正常,經來之時腹脹加重。大便不暢,但每日能解。既往用四磨湯、六磨飲等調治,前醫在理氣方中加用參芪,病人自訴不適,服后尤脹,夜臥不安。西藥曾用艾司奧美拉唑+克拉霉素+阿莫西林抑殺幽門螺桿菌(Hp),嗎丁啉等促進胃動力,初服有效,旬余之后效果不甚明顯,再服亦無效。起病以來無咳嗽、黑便、發熱等病史。腹診:觸之腹部脂肪層稍厚,無明顯壓痛,無振水音,叩診鼓音較著,無移動性濁音,腸鳴音低。舌脈:舌淡紅、苔薄白,脈細弦。肝功能、乙肝兩對半檢查未見異常;B超示:膽囊壁稍粗糙;胃鏡示:慢性淺表性胃炎,Hp(+)。西醫診斷: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胃炎,幽門螺桿菌感染;中醫診斷:脹病(氣脹實證)。治以理氣和中消脹。方選香蘇散合五磨飲加減。處方:
紫蘇梗10 g,制香附10 g,炒陳皮6 g,廣木香6 g,烏藥10 g,檳榔10 g,降香5 g,炒枳殼10 g,炒白芍15 g,炙甘草3 g,佛手片10 g,石見穿15 g。5劑。每日1劑,水煎,分2次服,服藥后端坐30 min。
1992年11月23日二診:患者服藥后上腹脹有明顯好轉,但臍腹仍脹,藥后噯氣較多,矢氣較少。予初診方加枸橘李10 g,5劑。
1992年11月28日三診:患者臍腹之脹亦漸改善,進食之量稍增,食后脹勢亦不加重。予二診方去降香,加谷芽30 g,10劑。
1992年12月8日四診:患者脘腹脹滿基本緩解,繼予三診方調治,改為2日服1劑,1劑分3次服(第1日服2次,次日服1次)。
半個月后患者腹脹癥狀消失,飲食正常,大便通暢,余無所苦。停藥觀察2個月,癥狀未見反復,腹部體征均正常。
按:本案患者腹診時觸之腹部脂肪層稍厚,腹力充實,叩之鼓音明顯,結合食后脘腹脹加重,噯氣、矢氣則舒等癥,可診為脹病,辨證屬氣脹實證,病位在胃,與肝相關。患者面肢不腫,腹診時腹部無振水音、無移動性濁音,可排除臌脹;脹甚覺隱痛,并無持續或較劇之疼痛故不能診斷為胃脘痛、腹痛;心下腹壁按之結實,不濡軟,無痞滿嘈雜感,可排除痞證。肝主疏泄,疏泄失常,氣機不調,胃中氣滯,故其脹先從上腹開始,繼及大腹、少腹。患者病程雖久,但其虛不著,不宜補氣,且其癥狀夏暑最輕,氣候轉冷則脹滿加重,可知病性偏寒。故徐老治以理氣消脹,方選香蘇散祛寒理氣和中、五磨飲破滯降逆順氣,共奏除脹滿、暢氣機之功。方中紫蘇梗易紫蘇葉,因紫蘇梗其性不甚溫,其味不甚辛,“能使郁滯上下宣行,凡順氣諸品惟此品純良”;沉香改降香,因降香降氣兼行瘀,入肝、脾、胃經;本案患者肝郁氣滯為因,故用香附疏肝解郁、理氣寬中,配以佛手理氣和胃,木香、枳殼行氣消積,檳榔破滯行氣;陳皮辛行溫通,有行氣止痛、健脾和中之功,因其苦溫而燥,善行偏寒之氣滯,再配以烏藥行氣散寒;因病程日久,加石見穿活血散結;白芍寓和陰養胃、剛中配柔之意,并制諸藥辛溫之性。二診時,患者臍腹仍脹兼噯氣多矢氣少,故加枸橘李加強疏肝和胃、消積化滯之力。三診時,患者上腹及臍腹脹滿均漸改善,進食亦增,因降香辛香性溫,不宜久用,故中病即止,遂去降香,加谷芽養胃兼助脾之運化。四診時,患者脘腹脹滿基本緩解,效不更方,續服以鞏固療效。
5 結語
通過腹診可直接客觀地診察臟腑經絡與氣血津液情況,且能實時掌握病情變化,具有較好的實用性與準確性。徐老運用腹診理論辨治疾病之經驗,對診斷鑒別疾病、判斷病位病性、分析病因病機、指導治療、觀察療效、判斷預后轉歸等各個方面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值得進一步學習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