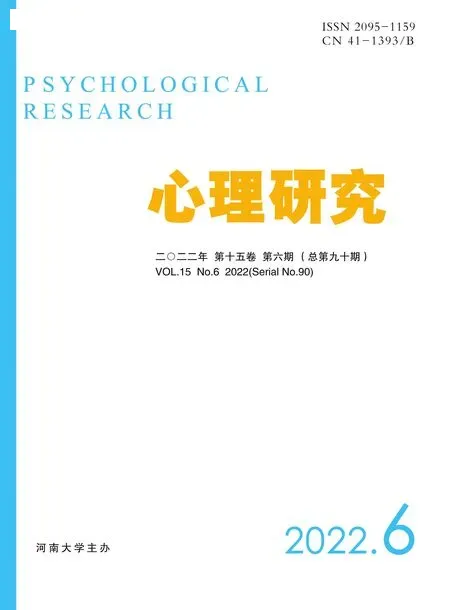說話人口音對聽者態度與行為的影響及中介機制
張姝理月 趙 峰 黃駿青 唐文清
(1 廣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桂林 541006; 2 廣西師范大學認知神經科學與應用心理廣西高校重點實驗室,桂林 541006;3 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廣西民族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桂林 541006)
1 引言
隨著“藍瘦香菇”(難受想哭)、“大噶好我系渣渣輝”(大家好,我是張家輝)、“短褲穿太高”(膽固醇太高)等一系列帶有地方口音特色的普通話爆紅網絡,讓我們看見了口音帶來的娛樂效果。但現實生活中,人們會如何評價一個說話帶口音的人呢? 口音是受母語影響而形成的發音規則,是涉及語調、音韻的一種發音方式或風格(Giles, 1973),雖然不同口音的說話人可以分享相同的語法、句法和詞匯,但聽起來卻有很大的不同(Giles, 1973; Gluszek & Dovidio,2010a,b)。一項元分析研究發現,非標準口音持有者比標準口音持有者得到的人際評價更消極(Fuertes et al., 2012)。 可見,口音會影響聽者對說話人的評價,且這種評價不利于非標準口音者。如相比標準英式英語說話的人,人們對荷蘭、越南口音說話人的態度更消極(Kraaijeveld, 2017);英語、法語、德語或西班牙語中帶有濃重荷蘭口音的人被認為不如標準口音說話人稱職、 友好和有能力 (Hendriks et al.,2017)。
雖然國外的相關研究證實口音的消極影響是廣泛存在的, 但語音材料大多是各種口音的英語(Fuertes, et al., 2012)。 而國內的研究主要用調查法或語言配對技術(matched-guise technique)研究人們對方言、 外語與漢語等不同語言的態度 (張積家, 1990; 林泳海 等, 2010; 王佳佳 等, 2019;高一虹 等, 2019)。 如張積家(1990)發現講普通話的教師比講蓬萊話的教師在人格特征、 講課效率和人際吸引等方面都獲得了更為積極的評價, 但語言態度與口音態度并不完全相同。 語言態度主要是指聽者對不同語言說話人的態度, 如對英語說話人的態度、對德語說話人的態度。而口音態度是人們對同一語言的不同口音說話人的態度,如對川味、粵調普通話說話人的態度。 中國幅員遼闊,方言眾多,各民族、 各地區人民在幾千年的交往融合中既一體又多元, 很多人在說普通話時不可避免地受方言的影響而帶有口音,是口音研究的天然土壤。那么在普通話的語境下,相比非標準口音說話人,聽者對標準口音說話人的態度評價是否也會更積極? 為探究這一問題, 我們選取了南方某一城市的口音作為地方口音代表,考察普通話不同口音(地方口音、標準口音)對聽者評價說話人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 傳統語言態度研究隱含了這樣一個假設:說話人的語言首先被聽者感知,引發了對這種語言的態度,然后再形成對說話人的評價。不區分對語言態度和對說話人的態度, 就無法確定對說話人較消極的評價是因為純粹不喜歡這種語言, 還是因為不喜歡說話人(Cargile & Bradac, 2001)。所以語言態度應分為對語言的態度和對說話人的態度(Schoel et al., 2012)。 同理,口音態度與語言態度一樣,也涉及了對“說話人”和“口音”兩者的態度,也應分為對口音的態度和對說話人的態度。 社會認知領域對人臉的研究表明, 印象激活過程包括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對面孔知覺的社會類別信息 (如性別、種族等)進行提取,第二階段是激活所提取社會類別信息的刻板印象(張曉斌, 佐斌, 2012)。 所以在根據人臉信息形成總體印象評價時, 知覺面孔并提取面孔基本信息是第一步。同理可以推測,在評價帶口音的說話人時, 首先得到加工的應該是聲音本身的信息, 然后再根據這些信息形成一個對說話人的評價。且有研究表明,人們在聽時所經歷的不適程度會影響其對說話者的評價 (Sebastian et al.,1980),因此口音本身聽起來是否悅耳、舒適可能是影響聽者評價說話人的一個因素。 另有研究表明,5個月大的嬰兒就能注意到口音變化并做出反應(Kinzler et al., 2007)。 因此從發展進程來看,在聽口音評價說話人時,個體首先知覺口音,形成對口音本身的態度,再涉及對說話人的評價。 所以,聽者對口音本身的感知和態度會影響其對說話人的評價,且知覺和評價口音信息可能是聽者評價說話人的基礎。基于此,本研究對口音態度和說話人的態度進行了區分,用“聽者態度”指代聽者對說話人的態度評價, 并嘗試把對口音本身的評價作為人們評價口音說話人的中介變量, 探討口音態度在口音影響聽者態度的路徑中的中介作用。 區分口音態度和聽者態度,有助于深入理解口音的社會影響,而探討口音態度在口音影響聽者態度的路徑中的中介作用, 能為我們解釋口音如何影響聽者態度提供新的視角。
研究態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預測行為,研究發現標準美國口音的求職者被認為比法語口音的求職者更有就業前景 (Deprez-Sims & Morris,2013),漢語、墨西哥語和印度語口音的求職者會受到歧視(Timming, 2017),非標準口音說話人比標準口音說話人被雇傭的可能性低 (Hosoda et al.,2012; Roessel et al., 2017)。 即在只有聲音線索的情況下,人們不僅會對標準口音者的評價更好,也更愿意錄用他們。但求職面試是相對正式的職場情境,在日常的人際交往中, 說話人的口音會不會影響他人對其的人際選擇呢?基于此,探討口音對行為的影響,本研究關注更加生活化的情境,考察聽者對不同口音說話人的人際選擇,并探討口音態度、聽者態度和對說話人的人際選擇之間的關系。
2 研究一
研究一采用口音態度問卷與說話人態度量表,考察被試對地普(地方口音普通話)和標普(標準口音普通話)說話人的評價以及口音態度的中介作用。我們預測:相比標普說話人,人們對地普說話人的評價更消極(假設1);口音態度在“口音→聽者態度”的路徑中起到中介作用(假設2)。
2.1 方法
2.1.1 被試
選擇用G*power3.1 重復測驗方差分析, 設定顯著性水平為 0.05, 效應量為 0.25, 統計檢驗力為0.95,組數為 1,重復測定為 2 時,計算得樣本量為106。在廣西某大學的圖書館內隨機招募被試參與實驗,141 名在校學生同意并參與實驗, 女生107 名,男生 34 名, 年齡范圍為 19~32 歲,M年齡=22.45 歲。其中20%的被試為少數民族,36%的被試為城鎮人口,69%的被試會說方言。所有被試的聽力和言語能力均正常。
2.1.2 設計
研究采用單因素被試內設計。自變量為口音,分為地普和標普兩個水平, 因變量為聽者對說話人的評價得分。
2.1.3 材料
為了減少群體或地域刻板印象對本研究結果的影響,作者選取了流傳度不高、相對小眾的南普①南普是指含有南寧白話口音的普通話,翹舌發音不明顯,音腔不圓,句尾有加重語氣的語氣詞或直接加重句尾詞語氣,口音特點突出,使用地區主要為南寧城區。(南寧口音)作為地方普通話的代表,盡量避免聽者通過錄音推斷出口音所對應的群體或地區。然后,讓兩位錄音者分別用地方普通話和標準普通話朗讀 《桂林山水》第一自然段并錄音。 錄音者均為年輕女性,年齡、音色相近,朗讀時語速適中、語氣自然。 《桂林山水》為小學語文課文,文字通俗易懂,主要描寫桂林的山水風景。 錄音經過聲音處理軟件GoldenWave進行降噪、調音、剪輯后,形成兩段17 秒的錄音材料。為避免地域或身份相關的刻板印象的影響,分別以人名拼音Xiejing 和Lidan 對錄音進行命名,對應地普和標普。29 名大學生聽錄音后對兩段錄音材料進行1~7 分口音嚴重程度評分,1=完全沒有口音,7=口音非常嚴重。結果為地普(M=6.10±0.82)的口音嚴重程度顯著高于標普 (M=2.24±0.95),t (28)=17.98,p<0.001,d=3.34。 29 名大學生均能明確回答此錄音在描寫桂林的山水,口音操控成功。之后把兩段口音不同的錄音嵌入一頁PowerPoint(如圖1),被試每次可隨意聽取其中的一段錄音,再填寫問卷,直至聽完兩段錄音。 錄音在頁面中的位置是隨機變化的。

圖1 研究一錄音播放界面
2.1.4 測量工具
(1)口音態度問卷
在社會語言學領域有關語言態度研究的文獻(陳松岑, 1999; 單韻鳴, 李勝, 2018; 尹小榮,李國芳, 2019) 中選定了6 道題測量對說話人口音的態度,分別為:好聽的、有趣的、有用的、交流方便的、社會影響力大的,以及對這種口音的喜歡程度。題目采用 7 點計分,例如:1 代表“非常不好聽”,7 代表“非常好聽”。在問卷指導語中表明,此問卷僅對三段錄音中的口音進行評價。 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82(地普)、0.81(標普)。
(2)說話人態度量表
說話人態度量表選自 Zahn 和 Hopper(1985)編制的言語態度量表 (Speech Evaluation Instrument,SEI),分為優勢(superiority)、吸引力(attractiveness)和活力(dynamism)三個維度,共30 對反義形容詞。問卷經過雙語華人修改、專業翻譯人員校正、心理學教授審閱。 題目采用7 點計分,例如:“邪惡的—善良的, 選擇1 則表示你認為錄音說話人非常邪惡,選擇7 表示你認為錄音說話人非常善良。 ”SEI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94(地普)和 0.96(標普), 三個分維度的信度 α 系數范圍為 0.79~0.92。
2.1.5 程序
首先,指導被試仔細閱讀指導語,在完全理解實驗要求和錄音播放設置的情況下佩戴耳機, 播放錄音進行實驗。 要求被試聽一段錄音,填一次問卷,依次聽完兩段錄音,完成問卷。被試可根據自身需要隨機、反復播放錄音。
2.1.6 數據分析與統計
使用SPSS20.0 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考察被試對不同口音、說話人評價的差異;采用兩水平被試內設計的中介效應分析方法 (王陽, 溫忠麟,2018),利用Mplus 數據分析軟件考察口音態度在口音影響聽者態度路徑中的中介效應。
2.2 結果
2.2.1 對口音的評價差異
在口音態度問卷上, 被試對地普的評價 (M=3.15±1.01)顯著低于對標普的評價(M=5.13±0.96),F(1,138)=393.99,p<0.001,ηp2=0.74,差異值為-1.98,95%置信區間為[-2.18,-1.79]。
2.2.2 對說話人的評價差異
在說話人態度量表上, 被試對地普說話人的評價(M=3.78±0.74)顯著低于對標普說話人的評價(M=5.21±0.80),F (1,132)=240.77,p<0.001,ηp2=0.65,差異值為-1.43,95%置信區間為[-1.61,-1.24]。
2.2.3 口音評價的中介效應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在地普條件下,口音評價與說話人評價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r=0.42,p<0.001;在標普條件下,口音評價與說話人評價之間也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r=0.46,p<0.001。
中介分析結果表明(圖2),普通話是否帶有口音對口音評價(B=1.79,SE=0.13,p<0.001)有顯著影響, 口音評價對說話人評價 (B=0.46,SE=0.09,p<0.001)也有顯著影響,且普通話是否有口音對說話人評價的直接影響也顯著 (B=0.47,SE=0.17,p=0.005)。 采用 bootstrap 檢驗估計口音對說話人評價的間接影響的顯著性,結果顯示(表1),是否有口音→口音評價→說話人評價的中介效應估計值為0.82,其 95%置信區間為[0.49,1.10],置信區間不包括0,說明口音評價的中介效應顯著,即對口音的評價越積極,對說話人的評價也越積極。 同時,是否有口音對說話人評價的直接效應也顯著, 說明在排除口音評價的效應后, 口音仍可正向影響對說話人的評價。 總效應=0.47(直接效應)+0.82(間接效應)=1.29, 中介作用的效應量 PM=0.82 (間接效應)/1.29(總效應)=0.64,所以在口音影響說話人評價的效應中有64%是通過對口音評價起作用的。

圖2 中介模型圖

表1 是否有口音對說話人評價的間接效應
2.3 討論
研究一結果發現, 不論是在口音評價上還是說話人評價上,對標普的評價顯著高于地普。這與前人的研究一致, 即標準口音說話人比其他口音說話人得到的評價更積極 (Fuertes et al, 2012; Chan,2016; Hendriks et al., 2017; Roessel et al.,2017; Dragojevic et al., 2017)。中介分析進一步表明,口音對說話人評價的影響有64%是由口音評價介導的, 聽者對口音本身的消極態度會進一步影響其對口音說話人的態度, 人們部分地通過消極評價口音來消極評價說話人。
盡管研究一驗證了研究假設,但仍有局限性。首先, 沒有考慮口音熟悉性的影響。 在Huang 等人(2016)研究中,大多被試自我報告說,他們對熟悉口音的演講者更加寬容。 但也有研究證明當聽者熟悉某種非母語的英語口音時, 往往對這種口音的評價較低(Nejjari et al., 2012)。 因此,如果被試對研究中的口音較熟悉,并能識別出口音的來源,可能會對研究結果造成干擾。 雖然使用小眾口音作為研究材料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口音熟悉性的影響, 但是缺乏自我報告檢驗。 其次, 沒有考慮到口音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的影響。 研究表明可理解性會影響聽者對說話人的評價(Fuse et al., 2018),且可理解性在口音影響聽者態度評價的路徑中起中介作用(Kraaijeveld, 2017)。 因此,需要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排除可理解性可能存在的影響。最后,本研究結果還可能受到內-外群體的影響。 高一虹等人(1998,2019) 在香港回歸前和回歸20 年后研究了北京、廣州、香港三地的人對英語、普通話、粵語和粵調普通話的態度, 兩次研究都發現香港人對粵調普通話的評價高于內地人(北京、廣州),但也可能存在替代恥辱 效 應 (Vicarious Shame Effect et al., 2006)。Hendriks 等人(2018)研究發現,對于都帶有中度口音的說話人, 德國聽眾和荷蘭聽眾都更喜歡荷蘭口音說話人而不是德語口音說話人, 說明德國聽眾對帶口音的同胞感到了替代性的羞恥, 而荷蘭聽眾則表現出對帶口音同胞的內群體偏好。因此,如果被試自身帶有嚴重口音,在面對口音說話者時,既可能會把其視為內群體而給予不那么消極的評價, 也可能會因為替代性羞恥而給予更消極的評價。綜上,基于研究一的這些局限性, 研究二不僅要進一步揭示口音對人際選擇的影響,而且還需控制口音的熟悉性、可理解性以及內-外群體的影響,重復驗證研究一,增加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3 研究二
研究二試圖在控制熟悉性、 理解性和內-外群體對研究結果的干擾后,重復驗證研究一的結果,并考察人們對不同口音說話人的人際選擇。 此外也將進一步探討口音態度、 說話人態度和人際選擇三者間的關系。我們預測:首先,在控制了熟悉性、理解性和內-外群體的影響后,研究一的假設仍然成立;其次,聽者對說話人的人際選擇會受到其口音的影響,即相比地普說話人, 更多被試選擇標普說話人作為游戲搭檔(假設3);最后,人們會因為積極評價說話人而選擇其作為游戲搭檔, 即說話人態度在口音影響人際選擇的路徑中起中介作用(假設4)。
3.1 方法
3.1.1 被試
用G*power3.1 計算所得樣本量同研究一,最終在廣西某大學招募得168 名大一新生參與實驗。女生 143 名,男生 25 名,年齡范圍為 16~20 歲,M年齡=18.53 歲。 其中 72%的被試來自廣西,36%的被試為城鎮人口,25%的被試為少數民族,79%的被試都會說方言, 被試對自我口音嚴重程度評分M=2.92±1.25(1=沒有口音,7=口音非常嚴重),且 18%的被試能識別地普。所有被試都報告自己的聽力、視覺和言語能力正常。
3.1.2 設計
同研究一。
3.1.3 材料
同研究一,但在PowerPoint 上呈現《桂林山水》的文字內容(圖3)。 錄音配備文字是為了消除口音可理解性對說話人評價的影響。 實驗結束后詢問被試是否理解語音內容,所有被試均表示理解。

圖3 研究二錄音播放界面
3.1.4 測量工具
(1)口音態度問卷
同研究一。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83(地普)和 0.86(標普)。
(2)說話人態度量表
同研究一。 SEI 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94(地普)和 0.93(標普),三個分維度的信度 α 系數范圍為 0.70~0.92。
(3)干擾變量的測量
為了控制和考察口音熟悉度和內-外群體對說話人評價的影響, 在問卷后面考察了被試是否會說方言(1=會,2=不會)、自我口音評價(1~7 評分:1=完全沒有口音,7=口音非常嚴重)、 是否熟悉該口音(1=熟悉,2=不熟悉), 以及口音識別 (讓被試寫下Xiejing 的口音為何種口音,1=能識別,2=不能識別)。
(4)游戲搭檔選擇
這實際上是一個假任務, 要求被試對說話人形成一個印象評價后(即完成問卷后),根據自己的主觀意愿, 從兩位說話人中挑選一位作為接下來的游戲搭檔。但其實并沒有接下來的游戲,此設計的目的在于考察被試在只有聲音線索的條件下對不同口音說話人的人際選擇。
3.1.5 程序
實驗在安靜的機房進行,其他同研究一。在被試填完問卷后,告知其還有游戲任務,在做游戲之前請在兩位錄音說話人中挑選一位作為自己的游戲搭檔,但是不具體說明游戲詳情。 在被試選完搭檔后,宣告實驗結束。
3.1.6 數據分析與統計
采用卡方檢驗考察被試的人際選擇差異; 采用兩水平被試內設計的中介效應分析方法(王陽,溫忠麟, 2018),利用Mplus 數據分析軟件考察說話人態度在口音影響人際選擇路徑中的中介效應; 其他同研究一。
3.2 結果
3.2.1 對口音及說話人的評價差異
把自我口音評價作為協變量, 方差分析結果表明,被試對地普的評價(M=2.99±1.21)顯著低于對標普的評價(M=5.16±1.27),F(1,126)=24.77,p<0.001,ηp2=0.16,差異值為-2.67,95%置信區間為[-3.31,-2.03]。此外,被試性別、口音識別、是否熟悉該口音和是否會說方言的主效應均不顯著,ps>0.05, 與口音類型的交互效應也均不顯著,ps>0.05。
把自我口音評價作為協變量, 方差分析結果表明,被試對地普說話人的評價(M=3.48±0.89)顯著低于對標普說話人的評價(M=5.40±0.68),F(1,127)=24.19,p<0.001,ηp2=0.16, 差異值為-2.10,95%置信區間為[-2.55,-1.65]。 此外,被試性別、口音識別、是否熟悉該口音和是否會說方言的主效應均不顯著,ps>0.05,與說話人類型的交互效應也均不顯著,ps>0.05。
3.2.2 對說話人的人際選擇
選擇地普和標普說話人做游戲搭檔的人數分別為24,144。 在只有聲音線索的條件下,如果被試對口音在行為上沒有偏好, 選擇地普和標普說話人的人數比率理論上為1∶1。 卡方擬合度檢驗結果顯示,選擇地普、 標普說話人所占比例分別為14.29%,85.71%,與隨機選擇比例 1∶1 有顯著差異,χ2(1,N=168)=85.71,p<0.001, 絕大多數被試選擇了標普說話人作游戲搭檔。
3.2.3 口音評價、 說話人評價和人際選擇的相關分析
鑒于本研究為兩水平的被試內實驗設計, 在考察人際選擇與口音評價、說話人評價時,首先把人際選擇轉化為二分變量, 即把選擇標普說話人做游戲搭檔記為1,選擇地普說話人做游戲搭檔記為0。 考察人際選擇與口音評價、 說話人評價在不同口音條件下的差值相關。
相關分析結果表明, 不同口音條件下說話人評價的差值與人際選擇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r=0.28,p<0.001;不同口音條件下口音評價的差值與人際選擇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r=0.34,p<0.001;不同口音條件下口音評價的差值與說話人評價的差值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r=0.46,p<0.001。
3.2.4 說話人評價的中介效應分析
把地普說話人記為1,標普說話人記為2,形成一個兩水平的人際選擇變量。中介分析結果表明(圖4), 普通話是否帶有口音對說話人評價 (B=1.89,SE=0.10,p<0.001)有顯著影響,說話人評價對人際選擇(B=0.07,SE=0.02,p=0.002)也有顯著影響,且普通話是否有口音對人際選擇的直接影響也顯著(B=1.72,SE=0.06,p<0.001)。 采用 bootstrap 檢驗估計口音對人際選擇的間接影響顯著性,結果顯示(表2), 是否有口音→說話人評價→人際選擇的中介效應估計值為 0.14, 其 95%置信區間為[0.06,0.23],置信區間不包括0, 說明說話人評價的中介效應顯著,對說話人的評價越積極,則越會選擇其作為游戲搭檔。同時,是否有口音對人際選擇的直接效應也顯著,說明在排除說話人評價的效應后,口音仍可正向影響被試的人際選擇。 總效應=1.72 (直接效應)+0.14(間接效應)=1.86,中介作用的效應量 PM=0.14(間接效應)/1.86(總效應)=0.08,所以在口音影響人際選擇的效應中有8%是通過對說話人評價起作用的。

圖4 中介模型圖

表2 是否有口音對人際選擇的間接效應
3.2.4 口音評價和說話人評價的鏈式多重中介效應分析
鑒于在研究一中, 口音→口音評價→說話人評價的中介效應都顯著, 以及研究二中口音→說話人評價→人際選擇的中介效應也顯著, 此處對口音→口音評價→說話人評價→人際選擇的鏈式中介效應進行探索性的考察。 兩水平被試內鏈式多重中介效應分析的結果表明, 是否有口音對人際選擇的間接影響和直接影響均顯著,如圖5 所示。采用bootstrap檢驗估計是否有口音對人際選擇間接影響的顯著性(表3),結果顯示,是否有口音→口音評價→人際選擇的中介效應顯著, 在口音影響聽者人際選擇的效應中有5%可單獨通過口音評價起作用。 是否有口音→說話人評價→行為選擇的中介效應顯著,在口音影響聽者人際選擇的效應中有4%可單獨通過說話人評價起作用。 是否有口音→口音評價→說話人評價→行為選擇的鏈式中介效應也顯著,在口音影響聽者人際選擇的效應中有2%可鏈式通過口音評價和說話人的評價起作用。 同時,是否有口音對人際選擇的直接效應也顯著, 說明在排除中介效應后, 口音仍可正向影響人們對說話人的選擇。

圖5 鏈式中介模型圖

表3 是否有口音對人際選擇的間接效應
3.3 討論
研究二在控制了口音熟悉度、理解性和內-外群體可能造成的影響后,與研究一的結果一致,不論是對口音還是對說話人, 標普獲得的積極評價仍然顯著高于地普。 此外,研究二增加了“游戲搭檔選擇”,絕大多數被試(85.71%)選擇了標普說話人作為游戲搭檔,說明在人際選擇上,人們也更傾向于選擇標普說話人。此外,說話人評價在口音影響人際選擇的路徑上存在中介效應, 即人們傾向于選擇標普說話人作為游戲搭檔的部分原因在于對其有更積極的評價。最后,口音評價和說話人評價在口音影響聽者人際選擇的路徑上存在鏈式中介效應:人們聽帶口音的錄音,會依次通過對口音本身的評價和對說話人的評價, 進而影響對說話人的人際選擇。
4 總討論
兩個研究結果均表明, 不論在態度評價上還是人際選擇上,非標準口音說話人均處于不利地位。具體而言,相比標普說話人,人們對地普說話人的評價更為負面,也更少選擇其作為游戲搭檔。其中的中介機制在于, 人們會消極評價口音進而消極評價口音說話人, 甚至還會因為消極評價口音說話人而不選擇其作為游戲搭檔。
4.1 口音對聽者態度的影響
兩個研究都發現標普說話人比地普說話人得到的評價更積極,這與前人的研究一致,即標準口音持有者會得到更積極的評價 (Chan, 2016; Dragojevic, et al., 2017; Fuertes, et al., 2012; Hendriks, et al., 2017)。 為何聽者對標準口音持有者有更積極的態度? 有研究把對口音說話人的消極評價歸于刻板印象(Giles & Watson, 2013)。 Ryan 和Bulik(1982)認為,中產階級聽者對西班牙口音說話人的消極評價,是因為他們有一個“西班牙口音的人是下層階級”的原型概念。聽者會根據口音推斷說話人的社會群體成員身份, 對口音說話人的消極評價部分反映了他們對口音群體的成見。 我國推廣普通話已有60 多年, 學校不僅有相應的普通話課程,而且使用普通話進行教學。 因此聽者可能會推斷重口音者有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社會經濟地位, 從而導致較消極的評價。 再者,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如果說話人的口音有異于自己的口音, 意味著說話人屬于外群體, 因此會被消極評價 (Gluszek & Dovidio,2010)。 本研究中被試大多認為自己只有輕微口音,因此當聽到帶有較嚴重口音的地普時, 可能會視其為外群體而給予較消極的評價。最后,口音干擾了聽者的加工流暢性(processing fluency),即帶口音的語言更難被認知加工,進而引起了消極的情感反應。聽者會因為較難加工口音說話人的說話內容而消極評價說話人,口音越強,評價越消極(Dragojevic et al., 2017)。因此,雖然聽者都能理解語音內容,但相比標普, 地普引起的認知加工困難可能也是聽者消極評價說話人的原因。
4.2 口音態度的中介作用
Ryan 和 Bulik(1982)的研究發現,無論社會階層如何,聽眾還是會較消極評價德語口音者。對此他們的解釋是: 口音刻板印象似乎并不是聽者態度的主要預測因素, 德語口音更難理解, 聽起來更不舒服, 可能是聽者消極評價德語口音者的一個重要原因。本研究區分了口音態度和聽者態度,并把口音態度作為口音影響聽者態度的中介變量, 探究聽者是否會通過消極評價口音本身而消極評價口音說話人。 本研究發現相比地普, 人們對標普的評價更積極, 且口音態度在口音影響聽者態度的路徑中起中介作用,這就印證了Ryan 和Bulik 的觀點。
標準普通話為什么會得到更積極的評價?首先,標準普通話是官方用語, 相比地普具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力,交流起來也更方便;其次,口音普通話趣味性的體現需要一定的情境, 并不是所有口音普通話都具有娛樂效果;最后,對口音的評價也會受節奏韻律的影響(Prafianto, et al., 2017),說話人言語的韻律特征越好, 聽者感知到的口音水平越低 (李景娜, 王遙, 2015), 聽者之所以會評價地普不好聽,很可能是口音的腔調影響了普通話該有的韻律和節奏。 而對于口音態度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結果與Schoel 等人(2012)的觀點契合,他們認為對語言本身的評價以及對說話人的社會知識(如年齡、刻板印象等)會影響聽者對說話人的評價,而對語言本身的態度是評價過程的基礎。與語言態度類似,人們對口音本身的態度也會影響聽者對說話人的態度評價。這為我們解釋口音如何影響聽者態度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同時也表明,對口音本身的態度是口音研究中不應忽視的一個因素。
4.3 口音對人際選擇的影響
相比標準口音說話人, 口音攜帶者不僅會獲得消極的態度評價,也會受到不平等對待。如非標準口音代言人被認為可信度更低 (Reinares-Lara et al.,2016),管理者不愿雇傭墨西哥或西班牙口音求職者(Hosoda et al., 2012)。 本研究結果與前人研究一致, 在人際選擇上,85.71%的被試選擇了標普說話人做游戲搭檔, 說明非標準口音說話人不僅在求職方面可能處于不利地位,在交友、合作方面也會受到不利影響。 在 Roessel 等人(2017)的研究中,被試需要通過競選錄音評估一個候選人是否適合擔任助教職位,因為助教的課程將用德語授課,候選人的英語技能不會影響未來的教學,教學資格才是評價核心。盡管強調候選人的英語能力不會影響未來的教學,但口音仍然會使候選人的能力降級, 甚至不管候選人說什么,重口音候選人的可雇傭性得分都很低。因此,口音會使說話人的能力降級。 在本研究“選擇游戲搭檔”的任務中,聽者傾向于選擇標普說話人做游戲搭檔, 可能是認為標普說話人會更有能力一起完成游戲。
4.4 說話人態度的中介作用
研究還發現, 說話人評價在口音影響人際選擇的路徑中起中介作用, 人們會選擇標普說話人做搭檔的部分原因是對標普說話人的評價更好。 這說明被試對口音說話人的態度可以預測其接下來對說話人的行為。根據第一印象效應,如果一個人在初次見面時給人印象良好,那么人們就愿意接近他。 反之,對于一個初次見面就產生了反感的人, 即使無法避免與之接觸, 人們也會對之很冷淡, 在極端的情況下, 甚至會在心理上和實際行為中與之產生對抗狀態(時蓉華, 1988)。在本研究中,被試根據聲音對口音說話人產生了消極的第一印象, 從而影響了其后來對說話人的行為表現,不選擇說話人為游戲搭檔。
前人有關口音的研究, 大多集中在 “口音-態度”或“口音-行為”,本研究不僅探討了“口音-態度”和“口音-行為”的關系,還進一步探討了“口音-態度-行為”的關系,結果表明,口音評價和說話人評價不僅能各自獨立介導口音與人際選擇的關系,而且它們還能形成鏈式中介, 介導口音對人際選擇的影響。 雖然口音對人際選擇的影響的間接效應較小,僅有8%通過口音評價和說話人評價起作用,但也說明了口音對行為的影響并不僅是簡單的 “刺激-反應”,存在較復雜的影響機制,這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口音的社會影響。
4.5 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對普通話推廣、日常交友、工作求職等方面有一定的啟示作用,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在研究材料上,本研究選取了小眾口音作為研究材料,這是為了避免聽者根據口音推測說話人的身份信息, 例如聽到粵調普通話推測是廣東人、 聽到京味普通話推測是北京人,盡量排除地域刻板印象影響。但這也限制了本研究結果的推廣性。 未來的研究可以考察口音和說話人社會信息(如社會階層)對聽者態度的交互作用,以及使用常見口音作為研究材料。 此外,本研究的被試群體缺乏多樣性,主要是在校大學生,且男女比例不均衡, 因此未來研究需豐富被試群體進一步驗證本研究結果。再者,口音的影響不總是消極的,在某些情況下也有積極的效果,如口音也會帶來親切感。而本研究的設定主要是介紹桂林山水,沒有考察不同情境下口音對聽者態度的影響, 未來研究需要增設口音情境以更全面地了解口音的社會影響。
5 結論
(1)口音影響聽者對說話人的態度評價,相比地方口音說話人, 人們對標準普通話說話人的評價更積極;
(2)口音影響聽者對說話人的人際選擇,人們更愿意選擇標準口音說話人做游戲搭檔;
(3) 口音態度在口音影響聽者態度的路徑中起中介作用, 人們對口音說話人的評價部分通過口音評價起作用, 而聽者態度又可以部分介導口音對人際選擇的影響;
(4) 口音態度和聽者態度可鏈式介導口音與人際選擇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