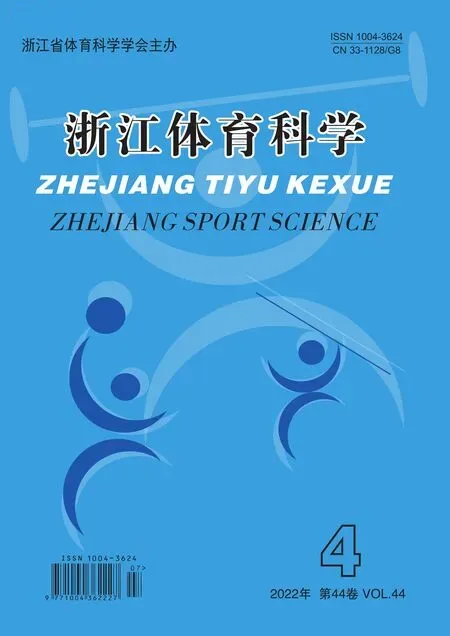嘉興“摜牛”文化符號闡釋
朱家歡,孫德朝,程 馨
(寧波大學(xué) 體育學(xué)院,浙江 寧波 315211)
在浙江嘉興南湖地區(qū)發(fā)展起來的嘉興摜牛,起源于回族的宰牲節(jié),是回族的一項(xiàng)傳統(tǒng)體育活動,屬于節(jié)日禮儀的一部分。2011年5月, 正式列入第3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由于“非遺熱”以及摜牛的獨(dú)特性、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文化價(jià)值,使其成為重要的文化資源,但是現(xiàn)有的文章從符號學(xué)解析嘉興摜牛的文化意涵尚未涉足,因此將嘉興摜牛文化延伸到學(xué)術(shù)交流層面,具有理論和實(shí)踐意義,從而實(shí)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共享。
嘉興摜牛承載回族的民族歷史文化記憶和嘉興人深厚的人文主義情懷,在時(shí)代變遷過程中與摜牛相關(guān)的一些有形物質(zhì)文化和無形物質(zhì)文化內(nèi)容延展開來,形成了一種高度融合的文化符號。對嘉興摜牛進(jìn)行研究,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回族的獨(dú)特文化,促進(jìn)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格局形成,尤其是在當(dāng)今符號消費(fèi)這樣的背景之下,深入挖掘整理民族傳統(tǒng)體育項(xiàng)目的文化符號價(jià)值,這無論是在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傳承方面,還是在國際化發(fā)展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視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1 摜牛文化符號闡釋
1.1 牛的文化符號及其象征意義
在畜牧農(nóng)耕文化時(shí)代,牛是重要的畜牧對象,從畜牧的“牧”字可見牛與畜牧的密切聯(lián)系,在那個(gè)時(shí)代出現(xiàn)了與牛有關(guān)的牛耕、牛市、牛車、牛制具和牛器物。牛文化也滲透在人生禮儀習(xí)俗中,十二屬相習(xí)俗就有以牛為生肖,有以牛為參照物衡量姑娘的身價(jià),他們的聘禮往往就是牛,還有把牛作為隨葬品的喪葬習(xí)俗。慢慢地也把牛文化滲透在紀(jì)念牛的專門性節(jié)日里,比如,牛王節(jié)、斗牛節(jié)等,尤其是到現(xiàn)代斗牛也依舊十分盛行,有日本和我國金華的牛牛相斗,西班牙和我國回族的人牛相斗,說明了現(xiàn)代人們對牛的興致依然不減,是具有象征意義的典型性符號標(biāo)識。
馬、牛、羊、雞、犬、豕是我國公認(rèn)的六牲,是所有奉獻(xiàn)給神靈的禮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祭品,而在六牲中最重要的又是牛牲。在我國處于農(nóng)業(yè)社會或前農(nóng)業(yè)社會,牛是部落的圖騰,被看做是五谷之神,能給人帶來吉祥,同時(shí)還有財(cái)富的象征。對牛的圖騰崇拜到后來演變成其他形式,有牛王、牛頭馬面、仙牛三種崇拜,并出現(xiàn)了像老子騎青牛出關(guān)、莊子不愿作牲牛、洗耳之水不飲牛等傳說。牛是一種體壯有力的動物,牛的神力具有威懾作用,因此牛除了象征財(cái)富以外,在初民的觀念中,牛還是男性和力量的象征。民間與牛有關(guān)的習(xí)俗有斗牛(人牛相斗)、角力(摔跤),這些游藝活動的主角都是男性,追其根源,都與人們視牛為力神,視牛為男性力量象征這一心理意識有關(guān)。正因?yàn)榕>哂刑厥獾姆栆饬x,又無時(shí)無刻出現(xiàn)在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娛樂當(dāng)中,與文化有著不可分離的關(guān)系,所以從“牛”文化符號衍生的“摜牛”文化符號有著巨大研究價(jià)值。
1.2 摜牛運(yùn)動的文化符號屬性
根據(jù)美國人類學(xué)家克利福德·格爾茲的觀點(diǎn),文化概念實(shí)質(zhì)上是一個(gè)符號學(xué)的概念。他在其《文化的解釋》一書中對文化定義為:“文化是一種通過符號在歷史上代代相傳的意義模式, 它將傳承的觀念表現(xiàn)于象征形式之中。通過文化的符號體系, 人人得以相互溝通、綿延傳續(xù),并發(fā)展出對人生的知識及對生命的態(tài)度”[1]。基于此文化的詮釋,“認(rèn)為文化是自然人進(jìn)化為人類(智慧人)進(jìn)程中勞動與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cái)富、精神成果和生活方式,具備三重屬性”[2]。進(jìn)一步對文化符號進(jìn)行剖析認(rèn)為“文化是借助于符號所進(jìn)行的能動性創(chuàng)造行為;符號是人類約定成俗的對象指稱,符號是人類表達(dá)思想的工具,符號是以人為主體的創(chuàng)造成果”[3],這被進(jìn)一步論證“文化與符號的關(guān)系是立體滲透與融合的關(guān)系”[4]。符號是文化的載體,它以物質(zhì)性的實(shí)體承載著文化精神性的內(nèi)涵,“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賴于符號。正是使用符號的能力使文化得以產(chǎn)生,也正是對符號的運(yùn)用使文化延續(xù)成為可能。沒有符號就不會有文化”[5]。符號是人類獨(dú)創(chuàng)的信息載體, 是文化的體現(xiàn),是人們之間傳遞信息的工具,“文化從形式上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可見或可感覺到的載體,另一部分是無法看到的載體所承載、蘊(yùn)含的背后意義,也即隱藏的或隱喻的意義”[6],因此發(fā)現(xiàn)文化背后的意義就是發(fā)現(xiàn)符號背后的文化意涵。
嘉興摜牛作為民族傳統(tǒng)體育類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具備文體性、娛樂性、民族性,是回漢民族歷史文化、傳統(tǒng)文化的集中體現(xiàn)。它與西班牙斗牛、金華斗牛等最大的區(qū)別就是嘉興的摜牛是人與牛身體的直接碰撞,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嘉興身體文化符號。尤其是在休閑娛樂時(shí)代,作為獨(dú)特的文化資源在進(jìn)行復(fù)制、改造、升華后成為休閑娛樂的核心文化因子,這為民族文化資源保護(hù)與傳承找到了新的發(fā)展路徑。到了現(xiàn)代,依據(jù)大眾審美需求和心理訴求進(jìn)行大幅度改良,創(chuàng)作出集合摜牛、武術(shù)、舞臺文藝等綜合元素的情景劇,形成屬于嘉興地區(qū)獨(dú)有的摜牛文化。符號學(xué)是意義學(xué),是人類歷史上有關(guān)意義與理解的所有思緒的綜合提升,因此運(yùn)用文化符號學(xué)闡釋民族文化具有前瞻性意義[7]。引入符號學(xué)研究嘉興摜牛其價(jià)值在于:第一,在西方體育的影響下,摜牛傳承中存在“外在形式展演,內(nèi)在紋理消融”的現(xiàn)狀,符號學(xué)的闡釋功能與摜牛現(xiàn)狀具有高度吻合性,借助符號學(xué)功能,闡釋摜牛文化符號的能指與所指,闡釋其文化意涵;第二,嘉興摜牛的符號化加深了人們對嘉興的印象,成為人們心中重要的城市文化標(biāo)識。
2 摜牛文化分層闡釋
文化是承載“意義”的符號系統(tǒng),因此文化研究的第一性就是發(fā)現(xiàn)意義。在意指過程中,我們不僅要理解符號“載體”,更要理解 “編碼”,在研究涵義時(shí)破解“編碼”,進(jìn)行符義還原,在文化闡釋時(shí)探討“文本”內(nèi)涵,聚焦隱喻。文化分層理論來源于西方文化研究領(lǐng)域,為理解多樣性的文化現(xiàn)象提供了一種較為系統(tǒng)與客觀的方法[8],對于闡釋摜牛文化意涵,體現(xiàn)文化價(jià)值找到可操作性中介。中國大陸學(xué)者馮天瑜把文化構(gòu)建為四層面:物質(zhì)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觀念文化或稱意識形態(tài),格爾茨發(fā)展出一種田野研究策略,把具有文化意義的事件或社會戲劇作為“深度游戲”層層剝開來觀察分析,達(dá)到對意義事件的“深描”,這兩者的結(jié)合對研究傳統(tǒng)體育項(xiàng)目頗具參考性和借鑒價(jià)值。因此,采借文化符號學(xué)理論,選取馮天瑜文化分層的可操作性中介,格爾茲茨的“深描”,闡釋嘉興摜牛運(yùn)動文化內(nèi)涵,實(shí)現(xiàn)對嘉興摜牛的挖掘整理。
2.1 物質(zhì)層面
韓海華被列入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xiàng)目代表性傳承人,被稱為“中國式斗牛第一人”,嘉興摜牛就從他這里發(fā)揚(yáng)光大。摜牛運(yùn)動是身懷絕技的“摜牛勇士”與野性雄壯的公牛之間的對抗,也就是人的身體和牛的身體直接對抗,是原始社會與野獸搏斗的真實(shí)寫照。嘉興摜牛讓人回到最原始的自然之中,是人與牛的本能對抗,此時(shí)的人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是永恒自然規(guī)律的對象,一切的活動都要建立在對牛的敬畏和尊重之上。摜牛的整個(gè)比賽過程都充分展現(xiàn)了人與自然萬物斗爭的觀念,遵照著“自然”的規(guī)律去對待自然,順應(yīng)生物天性,尊重萬物生存的權(quán)利,回歸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狀態(tài),構(gòu)成了一個(gè)完整的有機(jī)系統(tǒng)。
摜牛的場地最初是不固定的,隨處空地上就可進(jìn)行。現(xiàn)在,為了保持原生性,在嘉興市政府的支持下嘉興摜牛有了專業(yè)的斗牛場。在場地選址上,無論是“爭霸賽”、“表演賽”等賽事,還是宗教祭祀一般為戶外場地;在場地材質(zhì)上,一般為紅褐色干燥土壤(本地的紅色山泥與黏土混合,并壓實(shí))或青褐色地磚;在場地形式上,摜牛空間為圓形,觀眾空間為扇形。其場地選址的“天人和諧性”,場地設(shè)計(jì)理念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參與者對“自然的親近和親和”高愉悅體驗(yàn)和感悟,觀賞者禮儀文化的熏陶感染和自我壓抑心境聚集能量的輕松釋放,正闡釋著人類既是符號的“生產(chǎn)者”,又是符號的“消費(fèi)者”[2]。尤其場地形式——圓,是穆斯林信仰圖騰,是伊斯蘭教的符號標(biāo)識,是真主的形態(tài)表征。圓的無始無終、無限循環(huán)的形態(tài)表征著真主——安拉在宇宙中“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的主宰地位。
摜牛士的服飾要求:絳紅色風(fēng)髦和上衣、黑色寬松功夫褲、白色回族禮拜帽、系寬牛皮皮帶、足蹬黑褐色短筒牛皮靴、手腕系靠牛皮制護(hù)腕、手套為黑色羊皮露指半截。白色圓形禮拜帽是穆斯林外部特征的一個(gè)重要標(biāo)志,王岱輿在《正教真診·正命》中寫道:“五色之中,唯白最吉,因其本來清潔,并無造作因由,皆非諸色可及者也。”白色是“本然正色”,象征回族由內(nèi)而外純潔的氣質(zhì)以及對真主安拉的純潔信奉[9]。黑色符合波斯民族審美觀念,象征高雅、莊嚴(yán)。外表的莊嚴(yán)肅穆,內(nèi)心的純潔樸素,表述穆斯林對真主信奉的“身心合一”特征。絳紅色風(fēng)髦和上衣為了激起牛“斗”的本性。牛皮靴、護(hù)腕、手套是為了保護(hù)摜牛士的安全。摜牛士的服飾是回族文化的歷史標(biāo)記,是伊斯蘭教義物化,承載著不同代際回族人民的歷史文化記憶,敘述著回族集體意識的“原始印象”。
2.2 制度層面
韓海華運(yùn)用形意六合拳、排打功等武術(shù)手法、技法以及體育元素,把摜牛運(yùn)動由原來祭祀活動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逐漸演變?yōu)橐粋€(gè)傳統(tǒng)體育項(xiàng)目,更是在時(shí)代的變遷下,融入更多時(shí)代元素和體育元素,豐富了比賽內(nèi)容,增加了比賽程序,還有了像競技體育一樣的訓(xùn)練內(nèi)容、規(guī)則,將嘉興“摜牛”發(fā)展到一個(gè)較完整的體系。在表演前先要營造氣氛,參加摜牛的運(yùn)動員整隊(duì),聽師傅教導(dǎo),隨后按照口令進(jìn)行集體武術(shù)表演,以此來喚起摜牛士的搏斗的熱情。摜牛運(yùn)動開展的秩序與規(guī)定:首先選牛,一般選擇成年的、體格壯實(shí)的水牛和黃牛,且牛犄角豐滿、姿態(tài)雄壯、有斗志,因考慮到水牛斗性相對較差,所以現(xiàn)在基本上選用成年黃牛進(jìn)行比賽。其次,摜牛士開始摜牛之前,助手先牽牛上場,由武術(shù)功底扎實(shí)、體態(tài)輕巧的“逗牛士”將牛“逗”得性起,等牛完全被激怒后,助手等人退場,摜牛士登場,摜牛正式開始,此時(shí)整個(gè)運(yùn)動達(dá)到高潮部分,摜牛士用足力氣,讓牛失去平衡,以此來獲取勝利。有比賽就有規(guī)則,在體育動作規(guī)則上,嘉興的摜牛有著嚴(yán)格的分級評判規(guī)則,初段(雙臂單腿別摔)、二段(雙臂側(cè)摔)、三段(肩扛摔)、四段(頂摔)動作有嚴(yán)格的分界線,比如二段中不能出現(xiàn)一段的動作,以此類推。在成績評定上,“摜牛士”及“牛”均可獲勝,在規(guī)定時(shí)間內(nèi)牛倒地為“摜牛士”勝,牛不倒地,則為牛勝。莊子說過“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在與動物的公平直接對抗中,“摜牛士”并沒有把自己放在主宰者的地位,而是把自己也作為一個(gè)普通的自然之物,用同等條件進(jìn)行競爭,體現(xiàn)了人與自然、與其他物種的和諧平等的價(jià)值觀,展現(xiàn)了中國人素來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
摜牛折射出的制度文化還體現(xiàn)在禮儀方面,開始前向作為競爭對手的牛行抱拳禮,在比賽過程中,不打牛、不傷牛、不辱罵牛;若摜牛對抗中,牛贏得勝利,還將為牛披上摜牛勇士的披風(fēng),并向牛再行一個(gè)抱拳禮,以示對牛的尊重,這樣的大會不光是人的自我展現(xiàn),也是牛的盛會。自古以來,牛為中國幾千年的農(nóng)業(yè)社會發(fā)展進(jìn)程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在人類的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都占有重要位置[10],它更是一種具有圖騰意義和神性的動物,有著風(fēng)調(diào)雨順、國泰民安的象征。
2.3 行為層面
哈維蘭在《文化人類學(xué)-人類的挑戰(zhàn)》中提到文化是基于符號的,很多人類的行為中包含了符號,并以有意義的方式代表著某樣事物。俗語講:“言為心聲,行為心表。”美國人類學(xué)家格爾茲借用馬克斯·韋伯有關(guān)文化是“意義之網(wǎng)”的理論, 提出:“人是生活在由自己編織的意義網(wǎng)絡(luò)里的動物,人的行動是一種傳達(dá)價(jià)值意義的最直接的行為表現(xiàn)”[11]。行為是意義的外在表現(xiàn),而意義又是行為的內(nèi)在反映。摜牛最初的形式是斗牛。斗牛作為一種游藝活動在中國已經(jīng)有著相當(dāng)長的歷史了,嘉興的摜牛就是從回族的斗牛演變發(fā)展過來的,它是兩種文化的交融,一種是馬家浜文化孕育了嘉興先民擒牛抓牛的技術(shù),另一種是嘉興的回族人民將馬家浜抓牛技藝運(yùn)用到傳統(tǒng)節(jié)日“宰牲節(jié)”中,在這樣兩種文化的交融下延伸出了摜牛的雛形,最后逐步形成摜牛運(yùn)動。在慢慢演變發(fā)展中嘉興人開始把斗字改成了摜,這個(gè)字可以說用的非常妙,“摜牛”的“摜”字,意味“摔”、“使跌”、“握住東西的一端而摔另一端”,也有“摜交”一說,是嘉興的方言,指摔倒在地上,兩人相抱,用力用技,以摔倒對方為勝,這和斗是不同的。據(jù)嘉興市志記載,在回族同胞歡慶穆斯林“宰牲節(jié)”傳統(tǒng)節(jié)日時(shí),有一套固定的回族宗教儀式,摜牛常常被作為儀式的一部分。在宰牛時(shí),一般由阿訇手捧《古蘭經(jīng)》主持誦經(jīng),完畢后,由幾名壯漢將牛摜倒捆住,然后由阿訇主刀“開宰”,此固定的儀式程序,得到世界各地的伊斯蘭教的認(rèn)可并仿照執(zhí)行。元代時(shí),嘉興的回族人民從河南、山東回族聚居地遷移到嘉興南湖區(qū)甪里街一帶聚居,在繁忙的勞動之余,回族人民以斗牛為樂,進(jìn)而演變?yōu)楣?jié)慶、喜事中的助興節(jié)目,每逢開齋節(jié)、古爾邦節(jié)都要表演這一項(xiàng)目[12]。隨后,聚居嘉興的回民,逐漸開始用習(xí)武之力單人或雙人將牛摜倒,慢慢地形成區(qū)別于其他回族地區(qū)的摔牛,富有它獨(dú)有的特點(diǎn)。隨著時(shí)間的演變,嘉興摜牛開始轉(zhuǎn)化為一項(xiàng)藝術(shù)表演和競賽項(xiàng)目,成為集體育、游藝、雜技于一體的運(yùn)動,這項(xiàng)運(yùn)動因韓海華而名揚(yáng),也因他而發(fā)展,他結(jié)合自身摸索出“擰”、“壓”“扛”等技術(shù)動作,“雙臂單腿別摔”、“雙臂側(cè)摔”、“肩扛摔”和“頂摔”四大摔法,這四種摔法看似是摔跤里的普通動作,但在摜牛中它們是段位或者說是身份級別的象征,每種摔法對應(yīng)不同的級別,如同運(yùn)動員等級,有標(biāo)志性的符號特點(diǎn),級別越高,挑戰(zhàn)的難度系數(shù)越大。初級的摔法動作看則容易,用其則難,它對摜牛士有很高的身體綜合素質(zhì)要求,特別是對手臂力量和腰部力量,在摜牛過程中,摜牛士要雙手緊緊抱住牛頭,用右肩頂住牛下巴,以壓、扛、擰等多種絕技使牛失去重心將其摔倒在地,這一系列的動作都需要摜牛勇士極強(qiáng)的身體素質(zhì)而且還必須經(jīng)過多年的武術(shù)、硬氣功等訓(xùn)練[13]。
“摜牛”運(yùn)動是人與大型動物同場競技的項(xiàng)目,競技方式獨(dú)一無二,它類似于摔跤,卻又不是平常所見到的摔跤,類似于其他斗牛,卻又有著自身獨(dú)有的特點(diǎn)。回族獨(dú)特的摜牛運(yùn)動,體現(xiàn)的是人與動物和諧共存之美,展現(xiàn)出了摜牛士英勇無畏的精神。除了作為一項(xiàng)體育競技運(yùn)動,摜牛貫穿著娛樂與武術(shù)的成分,在韓海華等傳承人的創(chuàng)編下,融合了江南船拳、形意拳、心意六合拳、查拳等武術(shù)內(nèi)容,達(dá)到內(nèi)外兼修,增加觀眾的觀賞性并激起摜牛士的搏斗激情;在斗爭過程中,摜牛士需要斗智斗勇,將技術(shù)和體力、柔美和勇猛完美地結(jié)合到一起,還要結(jié)合摔跤的靈活性和硬氣功的爆發(fā)力,用最快的速度將牛摜倒,這體現(xiàn)了智和力之美、柔與剛之美。摜牛運(yùn)動中的美和精神是嘉興文化的精髓所在,它展現(xiàn)著嘉興人勇敢無畏、智善并存、積極進(jìn)取的品質(zhì)。
2.4 精神層面
郭學(xué)松研究指出, 民間體育文化歷經(jīng)中國農(nóng)耕文化的洗禮, 已經(jīng)成為這種農(nóng)耕文化的重要記憶, 這種文化記憶的主體是身體運(yùn)動[14]。文化記憶并不是單一地附著在文本上,而是還可以附著在舞蹈、競賽、儀式、面具、圖像、韻律、樂曲、飲食、空間和地點(diǎn)、服飾裝扮、文身、飾物、武器等之上。這些形式以更密集的方式出現(xiàn)在了群體對自我認(rèn)知進(jìn)行現(xiàn)實(shí)化和確認(rèn)時(shí)所舉行的儀式慶典中[15]。這些祭祀儀式慶典又通過身體運(yùn)動的展演,來反映人們心中的文化記憶。郭學(xué)松在研究“三公下水操”中還指出,身體運(yùn)動中歷史記憶的建構(gòu),通過身體運(yùn)動的展演使民族精神得到重新展示,通過傳說記憶中陸秀夫與元軍在海中搏斗的歷史場景的再現(xiàn),升華了陸秀夫浩然正氣的民族氣節(jié),凸顯了這種民族精神在普通大眾心目中的反響[16]。“宰牲節(jié)”儀式中的摜牛運(yùn)動,同樣是身體運(yùn)動的展演,通過一種人的身體與牛的身體搏斗情境的再現(xiàn),不僅是歷史事件的再現(xiàn)與記憶,是社會記憶或歷史記憶的保存與傳遞,更是民族精神的展現(xiàn)。
摜牛不是普通的人與人之間的摔跤,它較量的是重達(dá)500kg以上的公牛,面對如此倔強(qiáng)的動物,難免會有心理的壓力,摜牛士克服壓力和牛進(jìn)行比拼,無不展現(xiàn)著摜牛勇士高雅、勇敢獨(dú)特的靈魂和形象,這讓摜牛勇士的高大形象深入人心,使得更多家長將孩子送到摜牛文化園進(jìn)行鍛煉,塑造和培養(yǎng)他們崇尚和諧、勇敢無畏、公平競爭的品格和精神。在參加摜牛演出或者比賽之前,練習(xí)者會相互切磋,相互學(xué)習(xí),相互鼓勵,共同成長。在人與牛體重不對等的情況下,摜牛士要戰(zhàn)勝“對手”,就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臺下的技巧力量訓(xùn)練就顯得如此重要,可謂是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臺下艱苦的訓(xùn)練不光是動作技能學(xué)習(xí)的過程,也是競爭意識和意志力培養(yǎng)的過程,更是把牛勤勞、務(wù)實(shí)、勇敢奮進(jìn)的精神發(fā)揚(yáng)光大的一個(gè)過程。
中華傳統(tǒng)文化是各族人民團(tuán)結(jié)友好、發(fā)奮圖強(qiáng)、共同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為整個(gè)中華民族的壯大提供了無比強(qiáng)大的物質(zhì)基礎(chǔ)、制度保證、精神動力。而摜牛的出現(xiàn),正是嘉興人民對異文化的接納和包容,才為穆斯林文化的融入提供了空間。嘉興摜牛承載著獨(dú)特的民族精神與民族記憶,是回族人民長期以來創(chuàng)造并積累的重要財(cái)富,摜牛的發(fā)展凝聚了嘉興人民的智慧與創(chuàng)新,同時(shí)也是嘉興地區(qū)漢族人民與回族同胞友好相處的美好象征,團(tuán)結(jié)奮進(jìn)的重要媒介,透露著嘉興“勤善和美,勇猛精進(jìn)”的新時(shí)代嘉興人文精神,體現(xiàn)著嘉興人水一樣的包容,海納百川。
3 結(jié) 語
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是人們對歷史與世界的認(rèn)知,是日常生活的真實(shí)寫照。嘉興摜牛是回漢民族交融重要的地方性身體文化符號標(biāo)識。對其分層闡釋表述了穆斯林對真主質(zhì)樸崇拜,也表達(dá)了對祖先和歷史的追憶,同時(shí)蘊(yùn)含了回族人民無窮的智慧以及對生活的熱情,進(jìn)一步豐富對嘉興摜牛文化的認(rèn)知,為今后探索摜牛傳承和發(fā)展的符號化路徑提供相應(yīng)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