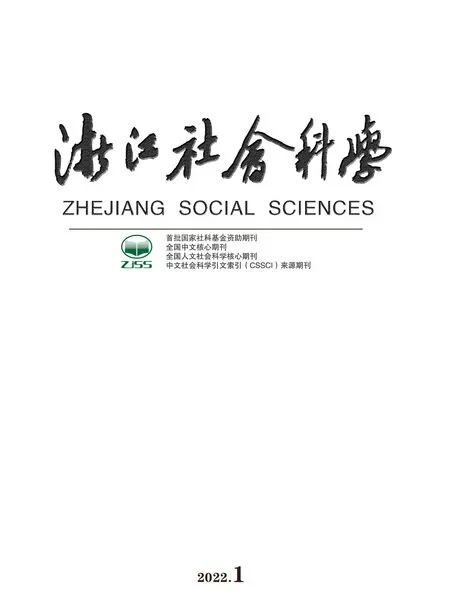“權力—權利”視野中的數字賦能雙螺旋結構*
郭春鎮
(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廈門大學黨內法規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在數字化、智能化加速融合的今天,國家、企業和個人通過數字技術實現了數字賦能,由此帶來了三方關系結構的新變化,并引發了網絡安全與個人信息保護、 智慧法治與數字人權等數字時代國家治理的新問題。這些新變化、新問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但仍在“權力—權利”這一經典命題的問題域之中。
一、前沿問題蘊含于經典論題之中
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人類社會加速從工業社會邁進數字社會、智能社會,加速變遷的信息時代正向身處其中的思想者提出各種現實、真切、緊迫的問題。其中一部分問題在呈現鮮明時代性的同時,也被時代賦予先進性、 科學性、 技術性的五彩光環。在五彩光環的映射與反照下,問題的前沿性日益凸顯,數字技術、數字化以及與之伴隨的數字賦能問題便是其中之一。
從字面來看,賦能是指賦予某個主體能力,使其從無能力變為有能力、 從弱能力變為強能力的行為、 過程或結果。該能力包括但不限于生存能力、發展能力及完成某項任務、實現某種價值的能力。而數字賦能,則是通過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提升相關主體的分析能力、 聯結能力和實現目標與價值能力的行為、過程和結果。
從現實生活來看,數字技術無疑是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方式與路徑,也是企業和個人提高自身適應社會與市場需求能力的技術保障。一方面,數字技術不僅可以提升公權力機構和市場主體整合資源的能力,而且還可以提升其治理、服務、生產以及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從而更有效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也提升了個人獲取公共資源或服務、 參與公共事務,以及在國家與社會服務、市場經濟中獲得更多有效信息的“實質能力”,進而增強自己的適應性,由此過上“有理由珍視”的生活。
數字賦能在促使國家、 企業和個人的能力得到不同程度提升的同時,還催生出一些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企業生產樣態和個人生活方式。盡管這一過程和結果與日新月異的高科技直接相關,但透過精彩而復雜的表象,將它們的運行方式類型化之后,我們仍可以借助“權力—權利”框架對其邏輯進行詮釋。通過將其置于經典理論框架中進行審視,能夠對它們未來發展的邊界與路徑提出規范性意見與建議。
二、“權力—權利”框架中的數字賦能
事物在發展變遷的過程中可能會呈現跨時代的外觀,但“萬變不離其宗”。在紛繁復雜的表象下,其仍是某個或某些經典命題的本質性主線的延伸。“權力—權利”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就是一個經典的、 可以用于闡釋很多嶄新事物與問題的分析框架。
數字技術已經為國家、 企業與個人進行了有效賦能。無論是從無到有,還是從弱到強,三方主體的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均得到提升,其中又以平臺企業尤為突出。具體而言,國家能力的核心是實現國家目標的能力,即通過調整其與個人、 與社會、與他國的關系來實現其目標的能力。數字賦能之后,以強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認證能力、規管能力、統領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納和整合能力等為代表的國家能力得到顯著提升,并且該能力促使國家實現目標的方式更為便捷。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在我國應對與治理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過程中,政府通過對包括個人信息在內的數據資源進行統合,運用數據技術實現對基層動員與核酸檢查近乎全方位的覆蓋,推動實現對確診病例“動態清零”,有效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維護社會穩定。企業被數字賦能的結果是: 它能夠在市場競爭過程中通過數字技術全方位融合生產和管理,使其在原材料、生產方式、產品、市場等方面更高效地組織或組合各種要素,發現并創造潛在客戶,提供個性化服務,進而有效降低運行成本、提升運行效率。隨著技術的發展和新經濟模式的產生,個人不僅可以通過數字平臺更便利地向公權力機關表達自己的意見、 提出自己的訴求,并能夠獲得較之以往更迅速的回應,而且還可以利用數字技術更便捷地行使控告檢舉權,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更全面、直接、高效的監督。同時,個人還可以借助企業數字平臺,以更便利的方式、更優惠的價格購買更優質的產品、享受更優質的服務。
在國家、 企業和個人均獲得數字技術賦能之后,它們之間的關系結構雖然呈現出一些新變化、新特征,但本質上仍處在傳統的“權力—權利”軌道上。首先,國家在數字賦能之后,所掌握的權力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如果說之前國家權力可以滲透至整個國家的肌體中,那么經過數字技術的加持,國家權力能夠延伸至各個毛細血管,甚至更加精細微末之處。比如,在應對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時,流行病學調查更加精準,各類信息收集和研判更加精細全面。較之以往,這種精準治理所花費的邊際人力資源、經濟資源成本幾近于無。這也以實例表明,權力擴張和延伸的邊際成本可以被數字科技降低到近乎為零,給其擴張沖動帶來極大的便利。其次,企業在數字賦能之后,不僅可以優化生產和銷售,還可以利用消費者個人信息進行大數據挖潛,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精準營銷甚至精準價格歧視,“大數據殺熟”就是典型表現。除此之外,作為“互聯網大廠”的平臺企業還可以對入駐平臺的小微企業進行精準管控,利用其壟斷地位進行排他式經營,并結合其掌握的小微企業經營數據進行“精準壓榨”,由此生成廣泛支配的社會權力。支配力和控制力,無論是源自國家還是企業,都是一種權力,都有尋租的空間與可能性。權力在運作的過程中傾向于達到極致,直至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等,而數字技術則將權力運作的邊際成本降低到趨近于零,為權力的無限延伸提供了沖動欲和便利路徑。最后,個人在數字賦能之后,其行使公民權利的能力在意想不到的方面獲得了提升,如借助數字提供的便利進行濫訴,以極低的成本消耗司法資源,又如與資本配合通過“刷單”“飯圈”等方式濫用消費者權利,甚至變相壓制其他個人表達權的實現、妨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現。
數字技術使得源自國家或大型企業的權力有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數字政體”,其運行邏輯與以往政體的“權力—支配”邏輯并無本質上不同。因此,傳統的“權力—權利”框架仍然適用于數字賦能后的個人、企業與國家的新型關系結構。
三、數字賦能后的“權力—權利”結構新變化
在古典自由主義理論中,“權力—權利”主要是限制與制約關系。在法定范圍內,權力經過法定程序,可以限制權利;通過法律程序和規范確認和保護的權利,可以監督制約權力。當然,隨著社會變遷與公法學理論的發展,也要求權力積極作為,承認某些權利的存在并保障這些權利的落實,而非將兩者設定為此消彼長的關系。數字賦能只是賦予了主體一種運用技術能力的可能性,最終掌握這一能力需要多方主體參與并通過制定相應的制度規范來助力。能賦多少能、賦哪些形式與內容的能,不僅受個人實質能力、數字能力的約束,還受權力執掌者合法、有效運用數字技術能力的限制。可見,數字賦能具有螺旋式上升的特征,可以通過數字賦能螺旋的形態融入到“權力-權利”結構關系之中。而數字螺旋的啟動,不僅需要個體技術能力、實質能力的提升,還需要政府、企業積極作為,消除“數字鴻溝”、絕對貧困等。
權力和權利之間不僅是“零和博弈”關系,還包含互相促進的關系。這種“權力—權利”之間的關系,不僅適用于公權力與個人權利之間,也延伸至社會權力與個人權利之間。尤其是,企業在數字賦能中獲得更多的社會權力,有著較之過去更強的信息資源控制力和支配力,使其主體地位不斷凸顯。換言之,從“權力—權利”結構呈現為國家、企業、個人之間的復雜關系,形成“權力—權利”雙螺旋結構。這一結構有相互制約的一面,即雙螺旋結構中的兩個“主鏈”在具體的權利義務等“堿基對”加持下始終保持著相對穩定的距離。這意味著一方在另一方的制約下很難單獨改變形狀,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權力—權利”關系形成對照。這一結構也有權利與權力、 公權力與社會權力互相聯動的一面,“權力—權利” 既可以互相促進而螺旋式上升,也可以互相掣肘而螺旋式下降,甚至可以說二者數量上有正相關關系。一方面,國家或企業在數字賦能后,有了更強、成本更低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如果在尊重個人尊嚴與基本權利的基礎上善加運用,在遵守憲法和法律的基礎上提供質量更好的公共產品或消費品,并有效防范權力的尋租行為,就可以使個人享有更真實、充分的權利,進而能夠更好地把控自己的生活,實現個人尊嚴和價值。另一方面,當個人有了更強的數字技術運用能力,能夠通過數字技術、數字平臺有效表達自己的觀點,對公權力和社會權力進行更有效監督時,既有助于防范權力對權利的擠壓,也有助于監督公權力和社會權力并促使其各守其分,避免公權力對社會權力的過分壓制,防范社會權力對公權力的“俘獲”,從而讓權力更有效地服務于權利。如果權利與權力在數字賦能的基礎上各守其位并互相促進,那么二者就容易進入雙螺旋的上升通道; 如果兩者中一方越位而另一方未能利用數字賦能后所獲得的能力進行有效的制約,例如將數據治理變為全景式監控或濫用數字技術賦予的權利,那么二者可能進入下降通道,在“能力越大、危害越大” 的軌道上不斷下滑,最終破壞二者的平衡,導致雙螺旋系統的崩潰或重啟,給各方帶來難以承受之重。
四、新時代需要數字賦能新結構螺旋式上升
新時代既是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時代,也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和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的時代,還是國家、企業和個人實現數字賦能的時代。在這個新時代,國家和企業在借助數字技術大幅度提升數字能力的同時,需要慎用善用賦能后擁有的權力,在法治框架內用好云計算、 大數據等技術提升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也要約束這種數字強化后的能力,避免把公民當作抽象后的一組數字乃至字節對待,而忽視一個個具體的、有人格尊嚴、有理性和溫度的個體的存在意義。企業在得到賦能之后,也要遵守法律,做好內部合規審查,避免形成壟斷,尊重消費者的主體性和人格尊嚴,提供更公平、優質的產品和服務,而非讓資本的邏輯主宰自己的一切行為,僅把公眾視為利潤來源。與此同時,個人也應該尊重自己的現實人格與數字人格,通過有效利用數字技術、數字平臺積極行使自己的權利、監督公權力和社會權力的運行,進而實現個人價值,成就更好的自己。
總之,在數字賦能之后,數字技術帶來的各種新現象、新問題仍可以在經典框架中得到解釋,由此引出的權力和權利、 公權力和社會權力關系問題同樣需要進行平衡。在“權力—權利”框架之下,既要使權力受到內外約束進而謙抑地運行,不侵犯個人或企業的權利,也要使其高效、 精準地運行,保障公民、企業權利與合法利益的實現;還要令企業在追逐利益的同時履行社會責任,讓數字賦能后的企業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發展、 幫助實現社會公平與消費者福利; 還要使個人能夠用好數字技術,提升實質自由和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的能力,并基于此有效地監督公權力與社會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