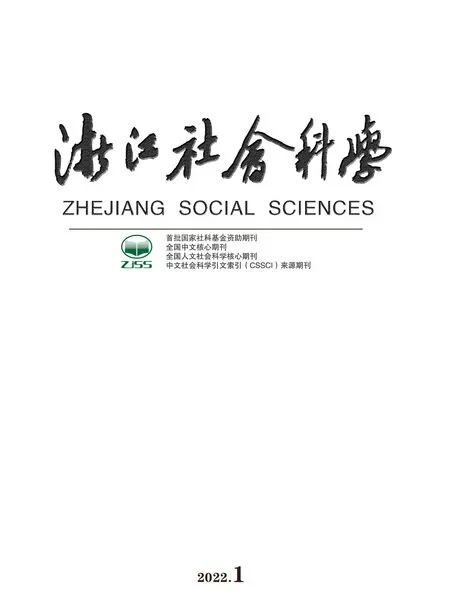羅馬法中的遺產(chǎn)買賣制度
——兼論我國(guó)民法對(duì)四大制度之借鑒
□ 徐國(guó)棟
內(nèi)容提要 羅馬法中的遺產(chǎn)買賣制度包含遺產(chǎn)買賣、射幸買賣、債權(quán)買賣、訴權(quán)買賣等方面,被大陸法系國(guó)家的民法典以不同的方式繼受。主要有《法國(guó)民法典》采用的買賣法為中心繼受模式,《奧地利普通民法典》采用的射幸合同繼受模式,《德國(guó)民法典》采用的繼承法繼受模式。我國(guó)在清末繼受德國(guó)民法時(shí),斬掉了其中的遺產(chǎn)買賣內(nèi)容,導(dǎo)致大陸地區(qū)和臺(tái)灣地區(qū)的學(xué)界皆對(duì)該制度無(wú)知,幸好《澳門民法典》對(duì)此有規(guī)定。就中國(guó)大陸而言,不知遺產(chǎn)買賣制度的不利結(jié)果是否認(rèn)權(quán)利是買賣合同的客體、不承認(rèn)浮動(dòng)客體的買賣、雖承認(rèn)具體的射幸合同卻不抽象承認(rèn)射幸買賣制度、分不清訴權(quán)買賣與強(qiáng)制執(zhí)行請(qǐng)求權(quán)買賣的界限等。通過(guò)研究羅馬法中的遺產(chǎn)買賣制度及其在現(xiàn)代各國(guó)的流變,可在我國(guó)民法中確立遺產(chǎn)買賣、射幸買賣、債權(quán)買賣、訴權(quán)買賣等制度,并改善對(duì)我國(guó)買賣合同客體的解釋,厘清訴權(quán)買賣與強(qiáng)制執(zhí)行請(qǐng)求權(quán)買賣的界限。
一、 羅馬法中的遺產(chǎn)買賣制度的有關(guān)原始文獻(xiàn)和核心問(wèn)題
蓋尤斯《法學(xué)階梯》第2 卷34、第3 卷85、86、87 規(guī)定遺產(chǎn)買賣。①《學(xué)說(shuō)匯纂》第18 卷第4 題的標(biāo)題是“對(duì)遺產(chǎn)或訴權(quán)的出售”,包括46 個(gè)法言,絕大部分關(guān)于遺產(chǎn)買賣,但有4 個(gè)法言講買賣訴權(quán),兩個(gè)講買賣債權(quán)。②《法典》第4 卷第39 題的標(biāo)題是“關(guān)于遺產(chǎn)或訴權(quán)的出售”,包含9 個(gè)法言。③把遺產(chǎn)買賣和訴權(quán)買賣放在一起的原因,《法國(guó)民法典》的解釋是:兩者都屬于無(wú)體物的轉(zhuǎn)讓,因?yàn)樵撁穹ǖ湓?“債權(quán)及其他無(wú)形權(quán)利的轉(zhuǎn)讓” 的標(biāo)題下規(guī)定兩者。④《法國(guó)民法典》的這種解釋未錯(cuò),但不排斥其他的解釋,因?yàn)橐部烧业絻烧叨际巧湫屹I賣、聚合物買賣的共性以及其他共性。
看來(lái),羅馬人對(duì)遺產(chǎn)買賣制度很重視,無(wú)論是優(yōu)士丁尼之前還是之后的立法,都關(guān)注該制度。但如果研究?jī)?yōu)士丁尼羅馬法關(guān)于遺產(chǎn)買賣的55 個(gè)法言以及相關(guān)的法言,需要一本書的篇幅。本文容量有限,只打算研究這些法言涉及的如下問(wèn)題。
(一)遺產(chǎn)買賣合同面面觀
1. 買賣的客體應(yīng)是遺產(chǎn)。對(duì)此,彭波尼在其《薩賓評(píng)注》第9 卷中說(shuō):如果出售的是尚生存的人的或不存在的人的“遺產(chǎn)”,行為無(wú)效,因?yàn)榻灰卓腕w不合事理之性質(zhì)(D.18,4,1)。⑤確實(shí),尚生存的人的財(cái)產(chǎn)并非遺產(chǎn),因?yàn)檫z產(chǎn)是已死之人遺留下的財(cái)產(chǎn)集合。如果允許這種交易,會(huì)導(dǎo)致出賣人促成遺產(chǎn)主人死亡的可能。當(dāng)然,“已死之人”必須存在過(guò),如果虛構(gòu)一個(gè)人并出售其遺產(chǎn),盡管“遺產(chǎn)”是存在的并且能讓買受人得益,但這是一個(gè)普通的集合物買賣而非遺產(chǎn)買賣,應(yīng)以普通買賣法的規(guī)則處理之。
那么,遺產(chǎn)的本質(zhì)是什么?羅馬法學(xué)家對(duì)此有深刻認(rèn)識(shí)。首先,蓋尤斯認(rèn)為,遺產(chǎn)的本質(zhì)是權(quán)利。他說(shuō),遺產(chǎn)不過(guò)是對(duì)死者權(quán)利的概括承受(Universum ius)(D.50,16,24.《行省告示評(píng)注》第6 卷)。⑥盡管遺產(chǎn)由一定的有體物構(gòu)成,但遺產(chǎn)本身是無(wú)體物(Gai. 2,14)。⑦所以,遺產(chǎn)買賣是權(quán)利的買賣。其次,阿富里坎把遺產(chǎn)看作聚合物(Universitas)。他認(rèn)為遺產(chǎn)指一定的聚合物和繼承權(quán)而非指單個(gè)的物(D.50,16,208. 《問(wèn)題集》第4 卷)。⑧所謂聚合物,指在物理上可分開,但在一個(gè)目的下被看作一個(gè)整體的數(shù)物,例如一群羊、一個(gè)圖書館等。⑨
2. 買賣的客體具有量的不確定性。所有人死后,他遺留的積極財(cái)產(chǎn)和消極財(cái)產(chǎn)的整體構(gòu)成遺產(chǎn),在它被繼承人接受前,構(gòu)成一個(gè)財(cái)團(tuán),其本身有財(cái)產(chǎn)的進(jìn)出和消耗,數(shù)量不確,價(jià)值不定,甚至不排除清算后出現(xiàn)赤字的可能,那時(shí)將發(fā)生所謂的繼承破產(chǎn)。⑩當(dāng)然,清理遺產(chǎn)的結(jié)果也可能得出積極財(cái)產(chǎn)遠(yuǎn)遠(yuǎn)大于消極財(cái)產(chǎn)的結(jié)論。由于有這樣的兩種可能,遺產(chǎn)買賣具有射幸性。對(duì)此,保羅在其《告示評(píng)注》第33 卷中說(shuō):如果某人出賣了一份遺產(chǎn),他只需交付遺產(chǎn)中所有之物,至于遺產(chǎn)的價(jià)值為多少,則無(wú)關(guān)緊要,但聲明了遺產(chǎn)總額的除外,如果有這種具體說(shuō)明,將發(fā)生待繼承財(cái)產(chǎn)的出售而不是遺產(chǎn)的出售(D.18,4,14,1)。?此語(yǔ)中的“待繼承財(cái)產(chǎn)的出售”應(yīng)指經(jīng)過(guò)清算的積極財(cái)產(chǎn)的整體,買賣此等整體,其客體不具有不確定性,相應(yīng)的交易也不具有射幸性。相反,遺產(chǎn)的出售具有射幸性。
正因?yàn)檫z產(chǎn)像月亮一樣變化不已,需要采用一個(gè)時(shí)間點(diǎn)固化它的量,以此作為確定出賣人應(yīng)交付什么,買受人可要求什么的依據(jù)。對(duì)此,烏爾比安在其《薩賓評(píng)注》第49 卷中提出了三個(gè)時(shí)間坐標(biāo)點(diǎn):在確定遺產(chǎn)的數(shù)量時(shí),人們可以選擇死亡的時(shí)間、 接受繼承的時(shí)間或出售遺產(chǎn)的時(shí)間作為基準(zhǔn),通常采用最后一個(gè)時(shí)間(D.18,4,2,1)。?第一個(gè)時(shí)間使一個(gè)人的財(cái)產(chǎn)集合成為遺產(chǎn); 第二個(gè)時(shí)間使出賣人的繼承人身份成立,這種身份的擁有是遺產(chǎn)買賣合同有效的條件; 第三個(gè)時(shí)間來(lái)得較晚,卻是“遺產(chǎn)”的身份與“繼承人”的身份都得到確定之時(shí),所以被烏爾比安說(shuō)成是人們通常采用的時(shí)間。
一旦確定了遺產(chǎn)買賣的基準(zhǔn)時(shí)間,該時(shí)間點(diǎn)面向過(guò)去和未來(lái)發(fā)生效力。就前者而言,出賣人已經(jīng)收受的孳息和出產(chǎn)也要移轉(zhuǎn)(烏爾比安:《薩賓評(píng)注》第49 卷,D.18,4,2,4)。?就后者而言,遺產(chǎn)依據(jù)其慣性將來(lái)要取得的物要?dú)w買受人。當(dāng)然,基準(zhǔn)時(shí)間后遺產(chǎn)遭受的所有損失也由買受人承擔(dān)(烏爾比安:《薩賓評(píng)注》第49 卷,D.18,4,2,9)。?
然后,遺產(chǎn)的負(fù)擔(dān)即使在基準(zhǔn)時(shí)間后呈現(xiàn),也歸出賣人承擔(dān)。對(duì)此,安東尼努斯皇帝在一個(gè)敕令中規(guī)定(C.4,39,2):遺產(chǎn)的遺贈(zèng)受益人或信托受益人訴追買受人時(shí),買受人須應(yīng)訴,然后再訴出賣人。?盡管訴訟先由買受人承接,但最終的訴訟后果歸屬于出賣人。
3. 遺產(chǎn)出賣人可以保留特定物件給自己而出賣其他。?這意味著遺產(chǎn)買賣可以不針對(duì)全部遺產(chǎn),由此有全部遺產(chǎn)的買賣與部分遺產(chǎn)的買賣之分。
4. 皇庫(kù)也可出售遺產(chǎn)。塞維魯斯·安東尼努斯皇帝在一個(gè)敕答中(C.4,39,1)做了如此規(guī)定。?我們知道,皇庫(kù)是法人,可以繼承無(wú)人繼承的遺產(chǎn)。?一旦遺產(chǎn)到手,皇庫(kù)不能利用此等遺產(chǎn)的使用價(jià)值而只能利用其價(jià)值,所以,出售是皇庫(kù)手中的遺產(chǎn)的必然走向。但出售可以是分件的或“打包”的,在合適的情形,“打包”出售的效益更好,這樣的出售體現(xiàn)為遺產(chǎn)出售。所以,出售遺產(chǎn)的主體有自然人和法人兩種。
(二)買希望
在《學(xué)說(shuō)匯纂》第18 卷關(guān)于遺產(chǎn)買賣的題中,還規(guī)定了超出遺產(chǎn)買賣的問(wèn)題,買希望是其中之一。
對(duì)此,烏爾比安《告示評(píng)注》第32 卷(D.18,4,11)中表明,事實(shí)上,允許以以下方式進(jìn)行出售:“如果你要賣給我的確實(shí)是一份遺產(chǎn),則我從你這里購(gòu)買它。”此時(shí)出賣的是對(duì)存在遺產(chǎn)的期望,因?yàn)槌鲑u的是不確定性本身,就如同出賣一次撒網(wǎng)可能捕獲的魚一樣。?這一法言把遺產(chǎn)買賣中的射幸成分單挑出來(lái)說(shuō)明,強(qiáng)調(diào)其中的買希望成分。其中提到的賣一次撒網(wǎng)可能捕獲的魚有如下案例佐證:有幾個(gè)科安斯的漁人正要拉起漁網(wǎng),幾個(gè)從米利都來(lái)的外地人向他們預(yù)買網(wǎng)里尚未看得到的捕獲。起網(wǎng)之后,發(fā)現(xiàn)撈到的是一只黃金的三角寶座,相傳是海倫在離開特洛伊的時(shí)候拋下去的。于是,這些外地人與漁人為這只寶座是否屬于射幸合同的標(biāo)的發(fā)生了爭(zhēng)執(zhí),后又引起雙方的城邦為此爭(zhēng)執(zhí),最后訴諸戰(zhàn)爭(zhēng)。?此案證實(shí)了預(yù)買可能捕獲的一網(wǎng)魚的交易。雙方合意的對(duì)象是魚,結(jié)果出水的是國(guó)之重器,發(fā)生爭(zhēng)執(zhí)是必然的。
彭波尼在其《薩賓評(píng)注》第9 卷(D.18,1,8,1)中報(bào)道的預(yù)買對(duì)象更廣。“……有時(shí)無(wú)實(shí)物的買賣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機(jī)會(huì)買賣,這方面的例子包括對(duì)可能捕捉到的魚或鳥或者在節(jié)日集會(huì)上可能得到的拋灑物的買賣。事實(shí)上,即使出賣人什么也沒有得到,買賣仍成立,因?yàn)檫@是一種對(duì)希望的買賣。如果所獲得的拋灑物被追奪,出賣人也不對(duì)此負(fù)責(zé),因?yàn)檫@正是雙方商定的契約內(nèi)容。”
對(duì)希望的買賣(Emptio spei)又稱機(jī)遇購(gòu)買,指在貨物買賣合同中,買方購(gòu)買的是取得標(biāo)的物的機(jī)會(huì)。無(wú)論買方是否取得標(biāo)的物,他都必須支付固定的價(jià)款。通常的例子如購(gòu)買彩票,彩票即為買主提供了獲得獎(jiǎng)品的機(jī)會(huì)。與買希望類似的是買希望之物(Emptio rei speratae),又稱預(yù)約購(gòu)買,指為將來(lái)可獲得的不特定的收益而購(gòu)買,以及在要購(gòu)買的物品還不存在,或出賣人還不占有該物品的情況下進(jìn)行的購(gòu)買。至于應(yīng)付價(jià)款,則應(yīng)視實(shí)際收獲數(shù)量而定。實(shí)際上,如果預(yù)購(gòu)一個(gè)活人的“遺產(chǎn)”,就是買希望之物。但前文已述,羅馬法禁止這種交易,理由之一是減少繼承中的投機(jī)。
(三)買賣債權(quán)
在《學(xué)說(shuō)匯纂》第18 卷關(guān)于遺產(chǎn)買賣的題中,超出遺產(chǎn)買賣規(guī)定的問(wèn)題還有債權(quán)買賣,而此等買賣構(gòu)成債權(quán)讓與的方式之一。后人沿著這條路線,發(fā)展出債權(quán)讓與制度。
亞歷山大·塞維魯皇帝在其于223年發(fā)布的一個(gè)敕答中規(guī)定: 債權(quán)買賣合同通常在被訴還債的人不同意的情況下締結(jié)(C.4,39,3)。這一敕答肯認(rèn)了債權(quán)的自由流通,自由到不經(jīng)債務(wù)人同意甚至違背其意志進(jìn)行。該敕答的發(fā)布可能有輔佐亞歷山大·塞維魯皇帝的羅馬法學(xué)家烏爾比安的參與。就這一主題,他在其《薩賓評(píng)注》第43 卷(D.18,4,17)中說(shuō):我們經(jīng)常買賣附條件和附期限的債權(quán),因?yàn)檫@里有我們可以買賣的東西。附條件的債權(quán)中的“條件”有成就與不成就兩種可能,非常適合成為射幸的對(duì)象。例如買賣這樣的債權(quán):如果蒂丘斯將來(lái)?yè)?dān)任了執(zhí)政官,債務(wù)人每年給債權(quán)人10 個(gè)幣(D.45,1,64. 阿富里坎:《問(wèn)題集》第7卷)。在這個(gè)交易中,蒂丘斯能否選上執(zhí)政官,是不確定的,由此使交易具有射幸性。附期限的債權(quán)往往由急需現(xiàn)金的債權(quán)人打折(扣除剩余期限中的利息)賣給他人(可能是銀行),完成貼現(xiàn)。可見,這種交易能夠滿足經(jīng)濟(jì)生活的要求,不排除附條件債權(quán)的買賣也能滿足這方面的要求。
(四)買賣訴權(quán)
訴權(quán)是債權(quán)的請(qǐng)求國(guó)家保護(hù)權(quán),既然債權(quán)可以買賣,訴權(quán)也是可以買賣的。就此,保羅在其《告示評(píng)注》第33 卷中說(shuō):凡是可以為人所擁有、占有或可通過(guò)訴訟提出要求的物,均可買賣。此語(yǔ)中的“可通過(guò)訴訟提出要求的物”,即后世所稱之“訟體物”(Chose in action)。優(yōu)士丁尼在531年致大區(qū)長(zhǎng)官約翰的一個(gè)敕答中指出:不僅對(duì)人之訴,而且對(duì)物之訴皆可出售,買受人可以自己的名義起訴(C.4,39,9)。這樣的制度安排的結(jié)果是,一些為了獲得他人錢財(cái)?shù)娜耍院艿偷膬r(jià)格向參加訴訟的債權(quán)人購(gòu)買訴權(quán),然后千方百計(jì)采用欺壓的方式讓債務(wù)人還債之全額,由此,取得債權(quán)成了一種職業(yè)。對(duì)此,阿納斯塔修斯(430—518)皇帝在給大區(qū)長(zhǎng)官Eustathius 的敕答(C.4,35,22)中予以限制。其辭曰:朕從諸多對(duì)朕提出的上訴得知,一些貪求他人財(cái)產(chǎn)和財(cái)富的人,催促他人把他們自己享有的訴權(quán)轉(zhuǎn)讓給自己,然后以訴訟的痛苦折磨相對(duì)人,因債無(wú)可爭(zhēng)議,人們總是傾向于自己行權(quán)而不是轉(zhuǎn)讓給他人。因此,朕首先以此法禁止將來(lái)再有這種交易,無(wú)疑,應(yīng)把希望訴權(quán)讓與給自己的人看作他人訴權(quán)的買受人,所以,如果此等人付錢達(dá)成讓與訴權(quán)交易,只許他就購(gòu)買訴權(quán)的價(jià)金及其利息起訴,雖然在讓與文書上說(shuō)的是買賣訴權(quán)。其次,如果讓與發(fā)生在繼承一個(gè)遺產(chǎn)訴權(quán)的數(shù)個(gè)繼承人間,或數(shù)個(gè)債權(quán)人之間或占有他人質(zhì)物的人之間,或發(fā)生在受遺贈(zèng)人和信托受益人之間,以留給他們的債務(wù)、訴權(quán)或其他財(cái)產(chǎn)為標(biāo)的,這些常常是他們的特留份,則另當(dāng)別論。第三,如果讓與是無(wú)償進(jìn)行的,大家皆知,對(duì)此無(wú)法律調(diào)整,但可遵守古法。所以,不僅訴權(quán)的讓與被作為如上列舉規(guī)則的例外,而且已經(jīng)做出的或?qū)?lái)要做出的這樣的讓與,會(huì)不打折地獲得被讓與訴權(quán)的效力(506年發(fā)布于君士坦丁堡)。以上為著名的阿納斯塔修斯法(Lex Anastasiana),許多法律辭書都為之設(shè)有專條,但通常將其內(nèi)容簡(jiǎn)化為對(duì)訴權(quán)受讓人請(qǐng)求權(quán)的限制:“如果第三人低于其名義價(jià)值購(gòu)得債權(quán)或請(qǐng)求權(quán),就不得再向債務(wù)人要求獲得高于買價(jià)外加法定利息的補(bǔ)償。”阿納斯塔修斯的上述敕答誠(chéng)然包括這一內(nèi)容,但遠(yuǎn)遠(yuǎn)不止于此。首先,對(duì)于共同請(qǐng)求權(quán)人之間的訴權(quán)讓與,例如,三人為共同受害人,都對(duì)于一個(gè)加害人享有訴權(quán),其中兩人由于事務(wù)繁巨或身體不佳,承受不了復(fù)雜的訴訟,愿意把自己的訴權(quán)讓與給三人中的堅(jiān)持訴訟意愿者,則此人可訴追全額債務(wù),因?yàn)榇说仁茏屓瞬o(wú)纏訟的意圖。其次,對(duì)于無(wú)償做出的訴權(quán)讓與,也允許受讓人全額追訴,理由也在于此等讓與并無(wú)纏訟的目的。
與出賣訴權(quán)相近的是預(yù)售判決結(jié)果。烏爾比安在其《告示評(píng)注》第77 卷(D.47,10,15,30)中提到古羅馬有這種實(shí)踐以及相應(yīng)的處理: ……出售判決結(jié)果的人,或收了購(gòu)買判決之金錢的人,要為此由總督判處鞭打,顯然,此等人被認(rèn)為是因施加侵辱受判處的,確實(shí),他被認(rèn)為冒犯了被出售的判決書的接受人。這個(gè)法言說(shuō)的是:某人對(duì)一方訴訟當(dāng)事人說(shuō),我可以左右法官的判決,為此你要付錢給我。該人的行為類似于現(xiàn)代法上的招搖撞騙罪,它損害了國(guó)家機(jī)關(guān)的威信,必然伴隨腐敗行為,因?yàn)樵手Z人肯定要向他聲言要左右的法官行賄,同時(shí)侵辱了訴訟相對(duì)人,因?yàn)樗麑?duì)有關(guān)訴訟的參與完全是無(wú)效操作,故為羅馬法禁止。盡管如此,這種交易也有射幸性,因?yàn)槌鍪叟袥Q結(jié)果的人是否能左右法官,具有不確定性,此等風(fēng)險(xiǎn)由買受人承擔(dān)。這個(gè)橋段也告訴我們,射幸交易得到法律承認(rèn)的條件是不得踏過(guò)法律的底線。
二、現(xiàn)代民法典對(duì)遺產(chǎn)買賣制度的廣泛繼受
(一)買賣法為主繼受模式
像羅馬法一樣,在買賣契約法中規(guī)定遺產(chǎn)買賣的至少有《法國(guó)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馬耳他民法典》《阿根廷民法典》《西班牙民法典》《菲律賓民法典》《荷蘭民法典》,本文僅以1804年版的《法國(guó)民法典》為例說(shuō)明這種模式。要指出的是,羅馬法傳下來(lái)的遺產(chǎn)買賣制度包含多項(xiàng)內(nèi)容,《法國(guó)民法典》 在其買賣契約法中主要規(guī)定該制度的債權(quán)買賣的內(nèi)容,并采取債權(quán)讓與的規(guī)定視角。
第1692—1694 條是關(guān)于債權(quán)讓與內(nèi)容性的規(guī)定。第1692 條采用從隨主原則,規(guī)定債權(quán)的買賣或讓與,其標(biāo)的包括保證、優(yōu)先權(quán)及抵押權(quán)等從屬于債權(quán)的權(quán)利。第1693 條規(guī)定債權(quán)出賣人的擔(dān)保責(zé)任。其辭曰:債權(quán)或其他無(wú)形權(quán)利的出賣人,雖無(wú)擔(dān)保的特別約定,對(duì)于轉(zhuǎn)讓時(shí)此等權(quán)利的存在,應(yīng)負(fù)擔(dān)保的責(zé)任。此條規(guī)定的是法定擔(dān)保,出賣人只擔(dān)保權(quán)利的存在,不擔(dān)保買受人實(shí)現(xiàn)其獲得的權(quán)利,因?yàn)榻灰妆旧砭哂猩湫倚浴5?694 條是對(duì)第1693 條規(guī)定的擔(dān)保責(zé)任的展開。其辭曰:出賣人僅在有特別約定的情形,始對(duì)于債務(wù)人的清償能力負(fù)擔(dān)保責(zé)任,且此種擔(dān)保責(zé)任以其出讓權(quán)利所得的價(jià)金為限。此條是對(duì)出賣人不擔(dān)保買受人獲得的權(quán)利實(shí)現(xiàn)的展開規(guī)定,這樣的擔(dān)保只有在有特別規(guī)定時(shí)才成立,但因其是有限的,只負(fù)責(zé)賠償買受人從原債權(quán)人買得這項(xiàng)債權(quán)所支付的價(jià)金。本條顯然體現(xiàn)了前述的阿納斯塔修斯法。
第1689—1691 條是關(guān)于債權(quán)讓與形式性的規(guī)定。第1689 條規(guī)定了債權(quán)交付完成的認(rèn)定:以讓與人向受讓人交付權(quán)利證書作為認(rèn)定交付完成的依據(jù)。第1690 條規(guī)定債權(quán)讓與的外部性事項(xiàng)。要求受讓人在獲得債權(quán)后通知債務(wù)人,如此才對(duì)第三人發(fā)生權(quán)利占有的效力。當(dāng)然,以公證書記載了債務(wù)人對(duì)于出讓的承諾的,也發(fā)生權(quán)利占有的效力。第1691 條規(guī)定債務(wù)人在收到通知前的履行的效果。其辭曰:債務(wù)人如在收到讓與人或受讓人關(guān)于轉(zhuǎn)讓的通知前,已向讓與人清償其債務(wù)者,其所負(fù)義務(wù)即有效免除。
規(guī)定完債權(quán)讓與后,以下兩條規(guī)定遺產(chǎn)買賣。第1696 條規(guī)定遺產(chǎn)買賣的射幸性。其辭曰:繼承人未列舉繼承財(cái)產(chǎn)的細(xì)目而出讓其應(yīng)繼份時(shí),僅對(duì)于其繼承人資格負(fù)擔(dān)保的責(zé)任。此條把遺產(chǎn)買賣分為列出遺產(chǎn)清單的和不列出遺產(chǎn)清單的兩種,前者不具有射幸性,后者則具有射幸性。在后者之情形,出賣人不對(duì)買受人獲得超過(guò)價(jià)金的收益承擔(dān)責(zé)任,只對(duì)繼承人身份的真實(shí)性負(fù)擔(dān)保責(zé)任。第1697—1698 條規(guī)定出賣遺產(chǎn)的效力。前者規(guī)定對(duì)于出賣人的效力,其辭曰:除在買賣當(dāng)時(shí)訂有保留的明白規(guī)定外,前條的出賣人如于出賣前已自應(yīng)繼份中的土地收取果實(shí),或受領(lǐng)屬于應(yīng)繼份的某項(xiàng)債權(quán)的清償,或出賣應(yīng)繼份中的某些動(dòng)產(chǎn),應(yīng)將此等利益返還于買受人。按照此條,買賣合同的訂立日為確定遺產(chǎn)范圍的基準(zhǔn)時(shí)間,此前出賣人已經(jīng)從遺產(chǎn)中有所得的,應(yīng)將此等所得返還給買受人。后者規(guī)定對(duì)于買受人的效力。其辭曰:如無(wú)相反的約定,買受人應(yīng)以出賣人為清償遺產(chǎn)的債務(wù)及負(fù)擔(dān)而支出的款項(xiàng)以及出賣人以遺產(chǎn)的債權(quán)人資格應(yīng)取得一切款項(xiàng)返還于出賣人。按照此條,在基準(zhǔn)時(shí)間以前出賣人已償還的遺產(chǎn)債務(wù),買受人應(yīng)返還于出賣人,因?yàn)榇说葌鶆?wù)應(yīng)屬于遺產(chǎn)的債務(wù),應(yīng)由遺產(chǎn)承擔(dān),換言之,由買得遺產(chǎn)的人承擔(dān)。
最后有兩條規(guī)定訴權(quán)買賣,首先是第1699條,其辭曰:受追訴的債務(wù)人,對(duì)于訟爭(zhēng)權(quán)利的受讓人,得償還其受讓的實(shí)際價(jià)金,受讓費(fèi)用及正常手續(xù)費(fèi)用以及自支付價(jià)金之日起的利息,以消滅此項(xiàng)訴訟。顯然,此條為對(duì)阿納斯塔修斯法核心內(nèi)容的宣示。其次是第1597 條:審判員、代理審判員、行使檢察職務(wù)的司法官、書記員、執(zhí)達(dá)員、律師、 公設(shè)辯護(hù)人及公證人在其任職法院管轄范圍內(nèi)不得為已發(fā)生的訴訟,或?qū)⑸嬖A的權(quán)利或訴權(quán)的受讓人,違反時(shí),其受讓無(wú)效,并應(yīng)負(fù)擔(dān)費(fèi)用和損失。此條規(guī)定了對(duì)訴權(quán)買受主體資格的限制,基本的精神是參加訴訟的公務(wù)人員不得買受有關(guān)訴權(quán),以免“裁判員”與“運(yùn)動(dòng)員”的身份發(fā)生混淆。其來(lái)源是烏爾比安關(guān)于出售判決結(jié)果的法言。
另外,非處于買賣合同語(yǔ)境的以下三條也來(lái)源于羅馬法中的遺產(chǎn)買賣制度。首先是第841 條(繼承法語(yǔ)境):不論何人,即使是死者的血親,其本人并無(wú)繼承權(quán)而受讓某一共同繼承人的繼承權(quán)利時(shí),得由其他共同繼承人全體或一人償還其所支出受讓的價(jià)額而排除其參與分割。本條講某一繼承人出售自己的繼承份額時(shí)把它賣給了共同繼承人以外的人,由此影響一份遺產(chǎn)的整體利用,為此,本條確立共同繼承人的贖回權(quán),允許他們利用此等權(quán)利買回已到非繼承人手里的份額。如此安排,有利于保持遺產(chǎn)的完整性。其次是第1104 條(合同法總則語(yǔ)境):“……如契約以當(dāng)事人各方依據(jù)某種不確定的事實(shí)而獲得利益或遭受損失的偶然性為代價(jià),此種契約為賭博性契約。”此條把遺產(chǎn)買賣中的射幸因素提升為關(guān)于射幸的一般性規(guī)定,此等規(guī)定亦適用于遺產(chǎn)買賣以外的射幸交易,例如保險(xiǎn)合同。再次是第1130 條(合同法總則語(yǔ)境): 1.未來(lái)的物件得為債之標(biāo)的物;2.人們不得放棄尚未開始的繼承,或就尚未開始的繼承訂立任何契約,即使取得被繼承人同意時(shí)亦如此。此條原則上承認(rèn)了未來(lái)物買賣的合法性,但不許把遺產(chǎn)買賣搞成未來(lái)物買賣交易。
總之,《法國(guó)民法典》 把來(lái)自羅馬法的遺產(chǎn)買賣制度的諸多規(guī)則打散了。主要安排在買賣法中,其他的民法分支也有零星安排。遺產(chǎn)買賣制度如此的輻射力,證明了它是許多現(xiàn)代民法制度的根源或根源之一,由此也證明了該制度的重要以及對(duì)該制度進(jìn)行研究的必要。
(二)射幸合同繼受模式
在我見到的外國(guó)民法典中,似乎只有《奧地利普通民法典》在射幸合同(賭博、終身定期金、保險(xiǎn)、船舶抵押借款等)的大類中規(guī)定遺產(chǎn)買賣。
第1278 條規(guī)定:1.出賣人已接受的遺產(chǎn)的買受人或者至少是繼承開始后出賣人可以繼承的遺產(chǎn)的買受人,不僅取得出賣人作為繼承人所享有的權(quán)利,而且取得其負(fù)擔(dān)的義務(wù),但具有人身專屬性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除外。在購(gòu)買遺產(chǎn)時(shí),如果不是以遺產(chǎn)清冊(cè)為基礎(chǔ),則該遺產(chǎn)買賣合同也是獲利機(jī)會(huì)的買賣合同; 2. 遺產(chǎn)買賣合同的生效要求辦理公證或者通過(guò)法院的記錄予以證明。此條把遺產(chǎn)買賣分為以遺產(chǎn)清冊(cè)為基礎(chǔ)的和不以遺產(chǎn)清冊(cè)為基礎(chǔ)的買賣,只認(rèn)后者是射幸買賣。此點(diǎn)與《法國(guó)民法典》第1696 條同。我已說(shuō)明《法國(guó)民法典》的這一規(guī)定,這里不再重復(fù)。
第1279 條規(guī)定:如果出賣人并非作為繼承人而是基于其他原因,如先取遺贈(zèng)、后位繼承、候補(bǔ)繼承或債權(quán),而應(yīng)從遺產(chǎn)中取得財(cái)產(chǎn),而且即使出賣人不享有繼承權(quán)也應(yīng)當(dāng)取得該財(cái)產(chǎn),則遺產(chǎn)買賣合同中的買受人不得對(duì)這些財(cái)產(chǎn)享有請(qǐng)求權(quán)。相反,對(duì)于因受遺贈(zèng)人或共同繼承人不能或不愿繼承而導(dǎo)致的遺產(chǎn)繼承份額的增加,或者通過(guò)其他方式而使得遺產(chǎn)繼承份額的增加,只要是出賣人已經(jīng)對(duì)其享有請(qǐng)求權(quán)的財(cái)產(chǎn),遺產(chǎn)買賣合同中的買受人都可以取得。此條區(qū)分了可以賣的和不可以賣的遺產(chǎn),可以賣的,主要是共同繼承人中一人或數(shù)人把自己不要的份額賣給其他繼承人,湊零成整。不可以賣的,則原因多樣,總起來(lái)說(shuō),是遺產(chǎn)第一手接受人的權(quán)利不完整,由于信托或其他原因,還有第二順位的繼承人等著繼承這份遺產(chǎn)。
第1280 條規(guī)定:在遺產(chǎn)買賣的情形,繼承人基于其繼承權(quán)而得到的所有財(cái)產(chǎn),如已收取的天然孳息和債權(quán),都應(yīng)作為遺產(chǎn);相反,為了接受繼承或者為了遺產(chǎn)本身而使用的繼承人的自有財(cái)產(chǎn),則應(yīng)從遺產(chǎn)中扣除。已經(jīng)清償?shù)膫鶆?wù)、已交付的遺贈(zèng)財(cái)產(chǎn)、 已繳納的捐稅和訴訟費(fèi)用都屬于應(yīng)從遺產(chǎn)中扣除的部分;如果沒有明確的另行約定,喪葬費(fèi)用也應(yīng)當(dāng)從遺產(chǎn)中扣除。此條規(guī)定遺產(chǎn)買賣的標(biāo)的物的范圍,剔除不屬于遺產(chǎn)的項(xiàng)目后,剩下來(lái)的即為遺產(chǎn)買賣的標(biāo)的物。喪葬費(fèi)用被此條明確由遺產(chǎn)負(fù)擔(dān),買受人享受不到遺產(chǎn)中的這一部分。
第1281 條規(guī)定了出賣人在達(dá)成買賣至交付標(biāo)的物之前的看管責(zé)任。其辭曰:在遺產(chǎn)買賣中,出賣人在交付之前已管理遺產(chǎn)的,其對(duì)此應(yīng)當(dāng)如同其他受托人一樣對(duì)買受人負(fù)責(zé)。按照此條,交付遺產(chǎn)前發(fā)生的風(fēng)險(xiǎn),由出賣人承擔(dān)。
第1282 條規(guī)定:為了實(shí)現(xiàn)其權(quán)利,遺產(chǎn)的債權(quán)人和受遺贈(zèng)人可以向遺產(chǎn)的買受人以及繼承人本人提出請(qǐng)求。他們的權(quán)利以及遺產(chǎn)債務(wù)人的權(quán)利都不因遺產(chǎn)的買賣而被改變,而且,遺產(chǎn)買賣中的買受人和出賣人中任何一人提起的遺產(chǎn)訴訟,也對(duì)另一人發(fā)生效力。本條規(guī)定出賣人和買受人的關(guān)系,遺產(chǎn)的債權(quán)人和受遺贈(zèng)人可以向他們中的任一人提出請(qǐng)求,所以他們被看作一個(gè)共同體。反過(guò)來(lái)講,他們中的任一人提起遺產(chǎn)訴訟時(shí),另一人當(dāng)然地是共同原告。
第1283 條規(guī)定:如果出賣遺產(chǎn)時(shí)是以遺產(chǎn)清冊(cè)為基礎(chǔ)的,則出賣人應(yīng)當(dāng)對(duì)該遺產(chǎn)清冊(cè)的正確性負(fù)責(zé)。如果遺產(chǎn)買賣并非以遺產(chǎn)清冊(cè)為基礎(chǔ),則出賣人應(yīng)對(duì)其繼承權(quán)和相關(guān)陳述負(fù)責(zé),并應(yīng)當(dāng)就所有因其過(guò)錯(cuò)造成的損害對(duì)買受人負(fù)責(zé)。此條也把遺產(chǎn)買賣分為以遺產(chǎn)清冊(cè)為基礎(chǔ)和不以遺產(chǎn)清冊(cè)為基礎(chǔ),兩種情形中,交易的性質(zhì)不同,出賣人的擔(dān)保責(zé)任也不同。
(三)繼承法繼受模式
在繼承法的語(yǔ)境中繼受羅馬法的遺產(chǎn)買賣制度的至少有 《德國(guó)民法典》《埃塞俄比亞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澳門民法典》。篇幅所限,本文僅以《德國(guó)民法典》為例說(shuō)明這種模式。
第2371 條規(guī)定:繼承人據(jù)以出賣已歸屬于自己的遺產(chǎn)的合同,必須做成公證證書。這是對(duì)買賣遺產(chǎn)合同的形式上的要式要求。
第2372 條規(guī)定:因遺贈(zèng)或負(fù)擔(dān)的消滅或因共同繼承人之一的均衡義務(wù)(Ausgleichungspflicht)而發(fā)生的利益,屬于買受人。此條是對(duì)被買賣的遺產(chǎn)的范圍的界定。受遺贈(zèng)人放棄遺贈(zèng)或負(fù)擔(dān)的受益人失去要求履行負(fù)擔(dān)的理由(例如,負(fù)擔(dān)的內(nèi)容是翻修房子,而此等房子因火災(zāi)滅失),以及出賣人應(yīng)得的特留份遺囑中未給足,其他共同繼承人要從自己的繼承份額中勻出部分財(cái)產(chǎn)補(bǔ)足這個(gè)特留份(此謂之均衡義務(wù)),兩種情形帶來(lái)的利益,都被認(rèn)為是遺產(chǎn),因此歸買受人。
第2373 條規(guī)定:在買賣合同訂立后因后位繼承或因共同繼承人之一的出缺而歸屬于出賣人的應(yīng)繼份,以及向出賣人給予的先取遺贈(zèng),有疑義時(shí),不得看作被一并出賣。家庭文書和家庭肖像,亦同。此條是對(duì)被買賣的遺產(chǎn)的范圍的界定,不過(guò)與前條采用“歸入”的角度不同,此條采用了“排除”的角度。首先,按照《德國(guó)民法典》第2376 條的規(guī)定,有后位繼承人的遺產(chǎn)不得出售,如果出售,構(gòu)成權(quán)利瑕疵,但出賣人違規(guī)出賣了這樣的遺產(chǎn)后,如果后位繼承人亡故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繼承遺產(chǎn),由此帶來(lái)的利好應(yīng)歸于出賣人,當(dāng)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共同繼承人之一死亡,在他無(wú)代位繼承人時(shí),其份額增加給其他共同繼承人,由此帶來(lái)的利好也歸出賣人。遺囑人給予出賣人的先取遺贈(zèng),往往為了滿足收受人的特殊需要(例如給彈鋼琴的繼承人一架鋼琴),此等遺贈(zèng)也不列為被出賣的遺產(chǎn)。其次,此條把人格財(cái)產(chǎn)排除在遺產(chǎn)之外,因?yàn)榧彝ノ臅图彝バは袢烁駜r(jià)值多而財(cái)產(chǎn)價(jià)值少,且涉及隱私,不宜進(jìn)入財(cái)產(chǎn)流通渠道。
第2374 條規(guī)定:出賣人有義務(wù)向買受人交付在出賣時(shí)存在的遺產(chǎn)標(biāo)的,包括出賣人在出賣前因?qū)儆谶z產(chǎn)的權(quán)利或作為對(duì)遺產(chǎn)標(biāo)的的毀壞、損壞或侵奪的賠償,或以涉及遺產(chǎn)的法律行為取得的利益。此條把確定遺產(chǎn)范圍的基準(zhǔn)時(shí)間定為“出賣時(shí)”,此前歸屬于出賣人的屬于遺產(chǎn)的權(quán)利、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和此前締結(jié)的法律行為在此后帶來(lái)的利益,都屬于被出賣的遺產(chǎn)。
第2381 條規(guī)定:1.買受人必須向出賣人償還出賣人已在出賣前就遺產(chǎn)所支出的必要費(fèi)用;2.對(duì)于其他在出賣前所做出的支出,買受人必須在遺產(chǎn)價(jià)額在出賣時(shí)因它們而提高的限度內(nèi)予以返還。此條規(guī)定出賣人在基準(zhǔn)時(shí)間前為遺產(chǎn)支出的必要費(fèi)用由買受人承擔(dān),如果是其他支出,買受人在遺產(chǎn)因此增益的限度內(nèi)承擔(dān)。
第2376 條規(guī)定:1.出賣人對(duì)權(quán)利瑕疵所負(fù)的責(zé)任,限于對(duì)如下情形所負(fù)的責(zé)任:出賣人享有繼承權(quán),繼承權(quán)不受后位繼承人的權(quán)利或遺囑執(zhí)行人的任命的限制,不存在遺贈(zèng)、負(fù)擔(dān)、特留份負(fù)擔(dān)、均衡義務(wù)或分割的指示,且未發(fā)生過(guò)對(duì)遺產(chǎn)債權(quán)人或其中的個(gè)別人的無(wú)限責(zé)任。2.出賣人無(wú)須對(duì)屬于遺產(chǎn)的標(biāo)的之物的瑕疵負(fù)責(zé)任,但出賣人惡意地不告知瑕疵,或已承擔(dān)對(duì)該標(biāo)的的性質(zhì)的擔(dān)保的除外。此條規(guī)定出賣人的擔(dān)保責(zé)任。首先是權(quán)利瑕疵擔(dān)保責(zé)任,由于遺產(chǎn)買賣具有射幸性,出賣人只擔(dān)保自己享有繼承權(quán)且對(duì)遺產(chǎn)的處分權(quán)完整,不擔(dān)保其他,換言之,如果買受人從遺產(chǎn)中得不到期待的利益,出賣人不承擔(dān)責(zé)任。其次是物的瑕疵擔(dān)保,出賣人原則上不承擔(dān)這方面的責(zé)任,有惡意的情形除外。所以,標(biāo)的物有無(wú)瑕疵,是遺產(chǎn)買賣合同射幸對(duì)象的一部分。
第2380 條規(guī)定:自買賣訂立時(shí)起,買受人承擔(dān)遺產(chǎn)標(biāo)的意外滅失和意外毀損的風(fēng)險(xiǎn)。自此時(shí)起,用益屬于買受人,且買受人承擔(dān)負(fù)擔(dān)。此條規(guī)定基準(zhǔn)時(shí)間前后遺產(chǎn)的風(fēng)險(xiǎn)和利好的分配,兩者的承受者都是買受人。比《奧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281 條只規(guī)定風(fēng)險(xiǎn)的承擔(dān)更全面。
第2385 條規(guī)定:1.關(guān)于遺產(chǎn)買賣的規(guī)定,準(zhǔn)用于出賣人以合同取得的遺產(chǎn)買賣,以及其他以讓與已歸屬于讓與人或以其他方式被讓與人取得的遺產(chǎn)為標(biāo)的的合同。2.在贈(zèng)與的情形下,對(duì)于在贈(zèng)與前被消費(fèi)或無(wú)償?shù)刈屌c的遺產(chǎn)標(biāo)的,或?qū)τ谠谫?zèng)與前無(wú)償?shù)貙?duì)這些遺產(chǎn)標(biāo)的進(jìn)行的負(fù)擔(dān)設(shè)定,贈(zèng)與人沒有義務(wù)給予補(bǔ)償。贈(zèng)與人不負(fù)第2376 條所規(guī)定的因權(quán)利瑕疵而提供擔(dān)保的義務(wù); 贈(zèng)與人惡意地不告知瑕疵的,有義務(wù)向受贈(zèng)人賠償因此而發(fā)生的損害。此條第1 款規(guī)定遺產(chǎn)的買受人或其他原因的受讓人可以再賣遺產(chǎn),如此可能發(fā)生同一份遺產(chǎn)有第一手、第二手、第三手甚至X 手買受人的情況,由此,這份遺產(chǎn)可以進(jìn)入全面流通狀態(tài);第2 款規(guī)定可以贈(zèng)與一份遺產(chǎn),對(duì)此準(zhǔn)用關(guān)于遺產(chǎn)買賣的規(guī)則,權(quán)利瑕疵擔(dān)保規(guī)則除外。由此,一份遺產(chǎn)的移轉(zhuǎn)不僅可有償實(shí)施,而且可無(wú)償實(shí)施。后種方式至少便于學(xué)者去世后其家人將其學(xué)術(shù)藏書捐獻(xiàn)給某個(gè)圖書館,如此既可留存該學(xué)者的學(xué)術(shù)人格于特定庫(kù)藏,也便于后人研究該學(xué)者以及他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
總之,在本文考察立法例的范圍內(nèi),《德國(guó)民法典》對(duì)遺產(chǎn)買賣制度做了最全面的規(guī)定。尤其是其關(guān)于出賣人可以再出售一份遺產(chǎn)以及贈(zèng)與一份遺產(chǎn)比照遺產(chǎn)買賣處理的規(guī)定,未見于其他民法典。
三、我國(guó)民法對(duì)遺產(chǎn)買賣制度之借鏡
前文已述,《德國(guó)民法典》 在其繼承編非常系統(tǒng)地規(guī)定了遺產(chǎn)買賣制度,遺憾的是,我國(guó)清末繼受德國(guó)民法時(shí),主事者看不到該制度的意義,完整剔除之,導(dǎo)致從《大清民律草案》到《民國(guó)民律草案》再到《中華民國(guó)民法典》,都對(duì)這一制度沒有規(guī)定。1949年后的中國(guó)歷次民法典草案,直到2020年的我國(guó)《民法典》,概不規(guī)定該制度,造成海峽兩岸的學(xué)者皆對(duì)該制度陌生。在臺(tái)灣地區(qū)方面,黃茂榮的專著《買賣法》也不研究遺產(chǎn)買賣。在大陸方面,更無(wú)一本書、一篇論文研究遺產(chǎn)買賣。聊作補(bǔ)償?shù)氖牵瑢儆诖笾腥A法律文化區(qū)的《澳門民法典》從第1964 條到第1970 條規(guī)定了這一制度,為中文讀者了解這一制度提供了方便。
然而,不規(guī)定不意味著不存在該制度調(diào)整的四大問(wèn)題,即遺產(chǎn)買賣、希望買賣、債權(quán)買賣、訴權(quán)買賣問(wèn)題,甚至強(qiáng)制執(zhí)行請(qǐng)求權(quán)買賣問(wèn)題,以下分述。
(一)遺產(chǎn)買賣
遺產(chǎn)買賣的前提是承認(rèn)繼承權(quán)可以轉(zhuǎn)讓,但我國(guó)的通說(shuō)是繼承權(quán)可以放棄,但不可以轉(zhuǎn)讓。對(duì)于實(shí)踐中某個(gè)共同繼承人把自己的份額移轉(zhuǎn)給其他共同繼承人的情形,例如父親死后母親、兄弟倆共同繼承,母親愿意將其繼承份額轉(zhuǎn)讓給弟弟的情形,法律人的解答是母親可以將她應(yīng)繼承的份額贈(zèng)與給弟弟,但這不是繼承權(quán)轉(zhuǎn)移,此權(quán)不能轉(zhuǎn)移,因?yàn)槔^承權(quán)作為法定權(quán)利,與身份緊密相關(guān),有別于一般的民事權(quán)利,不可轉(zhuǎn)讓。
但根據(jù)本文研究的立法例,繼承權(quán)顯然可以轉(zhuǎn)讓,盡管繼承人的身份不可轉(zhuǎn)讓。所以,繼承權(quán)不可轉(zhuǎn)讓論顯然是自清末以來(lái)的我國(guó)學(xué)界對(duì)羅馬法開創(chuàng)并廣泛流傳于大陸法系各國(guó)的遺產(chǎn)買賣制度了解不夠的結(jié)果。一旦克服了這一認(rèn)識(shí)障礙,遺產(chǎn)買賣制度馬上可以顯示出其不小的用途。其一,可用來(lái)滿足不愿花時(shí)間處理遺產(chǎn)事宜,只想把遺產(chǎn)迅速變現(xiàn)的繼承人的需要。我們知道,從被繼承人死亡到遺產(chǎn)到手,過(guò)程冗長(zhǎng),要清理遺產(chǎn)、納稅等等,非常費(fèi)事。其二,可以解決遺產(chǎn)的聚零為整問(wèn)題。例如,一套公寓平均遺留給三個(gè)共同繼承人,肯定只有其中之一未來(lái)住在此公寓中,其他兩位共同繼承人可通過(guò)出售(或贈(zèng)與)自己的繼承份額達(dá)成此等效果。其三,可用來(lái)解決學(xué)者身故后其專業(yè)藏書的接手問(wèn)題。從事某一專業(yè)的學(xué)者在自己的學(xué)術(shù)生涯中收藏了許多專業(yè)書籍,形成一個(gè)目的(例如羅馬法學(xué)科)性財(cái)產(chǎn)集,該學(xué)者身故后,其兒女從事完全不同的行業(yè),對(duì)其尊親的藏書毫無(wú)興趣,此時(shí),他們可出售這部分藏書給識(shí)家。類似的還有收藏家的藏品移轉(zhuǎn)問(wèn)題及其處理等。其五,承認(rèn)遺產(chǎn)買賣,可把浮動(dòng)綜合客體的概念引進(jìn)到買賣合同客體的類別中。這樣的客體消消長(zhǎng)長(zhǎng),變動(dòng)不居。該概念存在于擔(dān)保法中,尚不存在于我國(guó)買賣法中。
關(guān)于遺產(chǎn)買賣問(wèn)題,我國(guó)《民法典》有兩條“擦邊”的稀薄規(guī)定,首先是第1124 條,其辭曰:1.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放棄繼承的,應(yīng)當(dāng)在遺產(chǎn)處理前,以書面形式作出放棄繼承的表示; 沒有表示的,視為接受繼承。2.受遺贈(zèng)人應(yīng)當(dāng)在知道受遺贈(zèng)后60日內(nèi),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zèng)的表示;到期沒有表示的,視為放棄受遺贈(zèng)。此條中的“放棄繼承”“放棄受遺贈(zèng)”可以解釋為包含轉(zhuǎn)讓繼承權(quán)、受遺贈(zèng)權(quán)的意思。其次是第1160 條,其辭曰:無(wú)人繼承又無(wú)人受遺贈(zèng)的遺產(chǎn),歸國(guó)家所有,用于公益事業(yè);死者生前是集體所有制組織成員的,歸所在集體所有制組織所有。此條講城市的無(wú)人繼承遺產(chǎn)歸國(guó)家(實(shí)際上是國(guó)庫(kù))繼承,農(nóng)村的無(wú)人繼承遺產(chǎn)歸集體所有制組織繼承。這兩個(gè)法人繼承人得到遺產(chǎn)后都有把使用價(jià)值轉(zhuǎn)化為價(jià)值的問(wèn)題。轉(zhuǎn)化的方式之一是整體出售一份遺產(chǎn),這時(shí)候就發(fā)生遺產(chǎn)買賣了。
由于遺產(chǎn)買賣的本質(zhì)是權(quán)利買賣,一旦承認(rèn)了這種交易,我國(guó)《民法典》規(guī)定的買賣合同標(biāo)的物只包括有體物的缺陷可得到改善,可解釋為也包括權(quán)利。
(二)希望買賣
買希望被經(jīng)濟(jì)史學(xué)者視為人類早期的一種衍生品交易。在我國(guó),黃風(fēng)最早把羅馬法中的買希望作為現(xiàn)代法中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起源。繼而,張舫和任紅也做了類似的勾連。衍生品交易的標(biāo)的物并非商品本身,而是其某種關(guān)聯(lián)屬性,例如行情。行情有漲有落,買家都買漲的希望。如果漲了,則購(gòu)買希望成功。如果落了,則購(gòu)買希望失敗。所以,衍生品交易具有射幸性。
盡管《民法典》沒有規(guī)定衍生品交易和射幸合同,但我國(guó)早就有衍生品交易和射幸性質(zhì)的合同。就前者而言,國(guó)家外匯管理局早在1993年就發(fā)布了《外匯期貨業(yè)務(wù)管理試行辦法》,承認(rèn)外匯衍生品交易。2007年,國(guó)務(wù)院發(fā)布了《期貨交易管理?xiàng)l例》,擴(kuò)大了買希望的客體的范圍。2021年4月29日,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期貨法(草案)》,向社會(huì)公眾征集修改、完善的意見和建議。《草案》相比于《期貨交易管理?xiàng)l例》,增加規(guī)定了其他衍生品交易。其第3 條規(guī)定:……本法所稱其他衍生品,是指價(jià)值依賴于標(biāo)的物價(jià)值變動(dòng)的、非標(biāo)準(zhǔn)化的遠(yuǎn)期交割合約,包括非標(biāo)準(zhǔn)化的期權(quán)合約、互換合約和遠(yuǎn)期合約。所以,我國(guó)在一些次級(jí)立法上承認(rèn)了希望的買賣,但《民法典》對(duì)此無(wú)規(guī)定,形成不協(xié)調(diào)格局。《民法典》受商品經(jīng)濟(jì)的民法觀影響,把買賣合同的客體單純理解為商品,這未免與當(dāng)代生活現(xiàn)實(shí)的萬(wàn)千氣象不符。
(三)債權(quán)買賣
我國(guó)通說(shuō)認(rèn)為買賣合同的客體是有體物,所以,很難承認(rèn)債權(quán)買賣,但在我國(guó)《民法典》中,又埋伏著關(guān)于或可用于解釋債權(quán)買賣的規(guī)定。前者有第545 條第1 款: 債權(quán)人可以將債權(quán)的全部或者部分轉(zhuǎn)讓給第三人,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此款中的債權(quán)轉(zhuǎn)讓可以是有償?shù)幕驘o(wú)償?shù)模谟袃數(shù)那樾危褪莻鶛?quán)買賣。后者有第646條:法律對(duì)其他有償合同有規(guī)定的,依照其規(guī)定;沒有規(guī)定的,參照適用買賣合同的有關(guān)規(guī)定。此條中的可以準(zhǔn)用買賣合同規(guī)定的“其他有償合同”,可以解釋為包括債權(quán)買賣合同。所以,相比派生于遺產(chǎn)買賣制度的其他子制度,債權(quán)買賣在我國(guó)的規(guī)范基礎(chǔ)較好。
(四)訴權(quán)買賣與強(qiáng)制執(zhí)行請(qǐng)求權(quán)買賣
承認(rèn)了債權(quán)買賣后,對(duì)訴權(quán)買賣之承認(rèn)是自然而然的,因?yàn)樵V權(quán)就是為了保護(hù)包括債權(quán)在內(nèi)的實(shí)體權(quán)利而求助司法之權(quán)。訴權(quán)買賣在我國(guó)以訴權(quán)轉(zhuǎn)讓的名義被納入在任意的訴訟擔(dān)當(dāng)?shù)姆懂犞校鄶?shù)學(xué)者反對(duì)這樣的交易,認(rèn)為會(huì)造成對(duì)實(shí)體權(quán)利擁有者利益的侵害。在中國(guó)古代,包攬?jiān)~訟的人被稱為“訟棍”,名聲不好,學(xué)者們可能受此等傳統(tǒng)觀念影響。但也有學(xué)者主張,在消費(fèi)者群體訴訟中,有訴權(quán)者眾多,但不見得人人都擅長(zhǎng)訴訟,所以,不妨把訴權(quán)集中到最佳訴訟當(dāng)事人之手,即消費(fèi)者協(xié)會(huì)之手,后者代理眾多原告訴訟。此論講到的交易不構(gòu)成訴權(quán)買賣,而構(gòu)成訴訟代理,但此論開放了訴權(quán)買賣的可能性:因?yàn)橄M(fèi)者協(xié)會(huì)也可購(gòu)買眾多原告的訴權(quán)而承擔(dān)訴訟失敗的風(fēng)險(xiǎn)。
相比于承認(rèn)訴權(quán)轉(zhuǎn)讓(談不上買賣)的“小眾”,判決書買賣在我國(guó)十分大眾。盡管有爭(zhēng)議,最高人民法院允許判決書買賣。在2020年5月舉行的十三屆全國(guó)人大三次會(huì)議上,有人大代表提出了《關(guān)于禁止人民法院強(qiáng)制執(zhí)行階段變相買賣判決書行為的建議》(第5510 號(hào)),最高人民法院對(duì)其做出回應(yīng),除了為這種交易的正當(dāng)性進(jìn)行辯護(hù)外,還認(rèn)定強(qiáng)制執(zhí)行階段買賣判決書的交易為債權(quán)轉(zhuǎn)讓。我對(duì)此不敢茍同,因?yàn)榇苏撐纯紤]債權(quán)轉(zhuǎn)讓、訴權(quán)轉(zhuǎn)讓、 執(zhí)行請(qǐng)求權(quán)轉(zhuǎn)讓三種轉(zhuǎn)讓的客體處在不同的權(quán)利實(shí)現(xiàn)階段的事實(shí),把三者“一鍋煮”了。我認(rèn)為,判決書的買賣是“執(zhí)行難”催生出來(lái)的一種交易,而“執(zhí)行難”又與我國(guó)無(wú)個(gè)人破產(chǎn)制度的立法大漏洞相關(guān)。按周強(qiáng)院長(zhǎng)的說(shuō)法,約43%案件面臨執(zhí)行不能,并非法院執(zhí)行不力所致,亟需建立個(gè)人破產(chǎn)制度。確實(shí)執(zhí)行不能的,被執(zhí)行人可以申請(qǐng)個(gè)人破產(chǎn)。按2020年的《深圳經(jīng)濟(jì)特區(qū)個(gè)人破產(chǎn)條例》(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第3 條的規(guī)定:債務(wù)人經(jīng)過(guò)3年的免責(zé)考察期后,免除其剩余債務(wù)。顯然,該條例采用的是破產(chǎn)免責(zé)主義,意在給予破產(chǎn)人重新開始的機(jī)會(huì)。該條例可理解為全國(guó)性立法的試點(diǎn),代表未來(lái)全國(guó)性個(gè)人破產(chǎn)立法的方向。遵循這個(gè)方向,一旦免除判決書確認(rèn)的債務(wù),買賣判決書的做法就維持不下去了。所以,盡管通常按判決書確定債權(quán)額10%的價(jià)格購(gòu)買判決書的做法依然普遍,有的判決書甚至賣到了第四手,但在深圳,這種交易恐怕已不可行,除非買受人對(duì)被執(zhí)行人也享有債權(quán),可以行使抵銷權(quán)。我認(rèn)為,買賣判決書的本質(zhì)是強(qiáng)制執(zhí)行請(qǐng)求權(quán)的轉(zhuǎn)讓。執(zhí)行成功,誠(chéng)然幸運(yùn),不過(guò)這樣的可能性不大,因?yàn)闆]有第一手判決書取得人面臨的“執(zhí)行難”,就不會(huì)有“第二手”的買得判決書。如果執(zhí)行不成功再加上被執(zhí)行人提出申請(qǐng),則進(jìn)入個(gè)人破產(chǎn)程序,再發(fā)生“第三手”買得判決書的可能性很小。強(qiáng)制執(zhí)行請(qǐng)求權(quán)的轉(zhuǎn)讓的理解要求,判決書的受讓人不得再起訴判決書的被執(zhí)行人,以貫徹既判力的要求。如果不這樣處理,我國(guó)法院就陷入了怪圈:在明知許多被執(zhí)行人“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的情況下允許連續(xù)轉(zhuǎn)讓判決書甚至達(dá)到四手,讓相同或不同的法院承擔(dān)另外三個(gè)“訟累”,讓已在“訴訟爆炸” 中累壞的法官們承擔(dān)無(wú)謂的工作負(fù)擔(dān);而且,讓明明已經(jīng)破產(chǎn)的被執(zhí)行人承受從第二手到第四手判決書買受人的反復(fù)折磨,有何意義? 所以,當(dāng)務(wù)之急是盡快在深圳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出臺(tái)全國(guó)性的個(gè)人破產(chǎn)法,叫停執(zhí)行不能情況下的判決書買賣。
注釋:
①⑦[古羅馬]蓋尤斯:《法學(xué)階梯》,黃風(fēng)譯,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88、224、82頁(yè)。
③Codex Iustinianus,Weidmann,Berlin,1954,p.XXIII.
④李浩培等譯:《拿破侖法典》,商務(wù)印書館1979年版,第236頁(yè)。
⑥[意]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chǎn)繼承》,費(fèi)安玲譯,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頁(yè)。譯文有改動(dòng)。值得注意的是,尤里安的D.50,17,62(《學(xué)說(shuō)匯纂》第6 卷)的譯者把該法言中的Universum ius 翻譯為“法律關(guān)系的整體”。尤里安在該法言中說(shuō):遺產(chǎn)不過(guò)是對(duì)已故者的法律關(guān)系整體的繼承。參見[意]馬西姆·布魯?shù)伲骸读_馬法上關(guān)于遺產(chǎn)的若干問(wèn)題研究》,阮輝玲譯,載《羅馬法與共同法》第六輯,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8頁(yè)。
⑧The Digest of Justinian,Vol.IV,edited by Mommsen and Alan Wats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hiladelphia,1985,p.952.
⑨La voce di universitas,Su http://www.treccani.it/vocabolario/universitas/,2018年11月29日訪問(wèn)。
⑩我國(guó)繼制定《企業(yè)破產(chǎn)法》(1986)后,正在深圳試點(diǎn)《個(gè)人破產(chǎn)法》(下文詳述),但尚無(wú)制定《繼承破產(chǎn)法》的提議。
?徐國(guó)棟:《優(yōu)士丁尼法學(xué)階梯評(píng)注》,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9年版,第233頁(yè)。
?[古羅馬]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梭倫傳》上冊(cè)(黃宏熙主編),陸永庭、吳彭鵬等譯,商務(wù)印書館1990年版,第169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