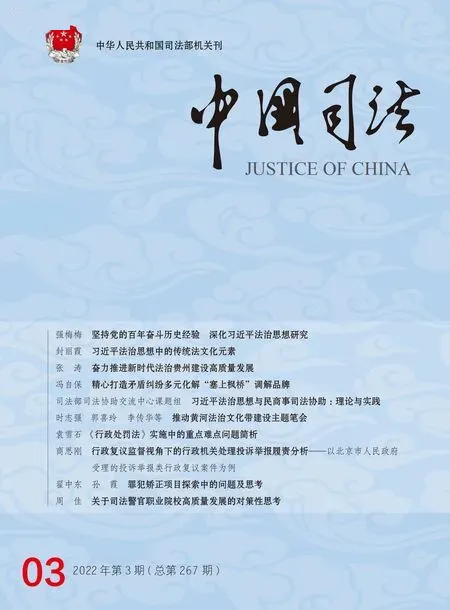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傳統法文化元素
封麗霞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和法律部副主任、教授]
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法治文明深深植根于特定的社會土壤與文化傳統之中,回應著不同形態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的規制需要,承載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記憶。中華文明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形成了源遠流長、獨樹一幟的中華傳統法文化。它衍生于中國古代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和農耕文明生產方式,具有不同于其他法文化形態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特質。它是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頑強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為當代中國國家治理和法治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文化滋養和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破除傳統法文化的虛無主義
關于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就中華傳統法文化談到,我國古代法制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智慧和資源,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等不同,中華法系是在我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和中華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蘊。中華法系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優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們傳承。
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和“歐風美雨”之下,中華法系的影響日漸衰微。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國家治理經驗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反思和質疑。中國法治現代化道路一定程度上是在對中國傳統法文化失去自信和不斷忘卻的狀況下進行的。近代以后,不少人試圖在中國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但最終都歸于失敗。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只有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摸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時借鑒國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夯實法治基礎。
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人類法治文明發展的規律也啟示我們,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法治體系和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傳統法文化是一種歷史的客觀存在,其潛移默化甚至有時是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對傳統文化的尊崇與敬重,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傳統法文化虛無主義的誤解和曲解,扭轉了近代以來法治建設言必稱西方、中國古代法治文明不足為道的偏見。這就促使我們努力摒棄近代以來關于法治建設古今對立、禮法不容、中西割裂的思維慣式,以一種深深的溫情與敬意去學習和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和傳承中華法文化的元素和精華,汲取營養、擇善而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和中國人自身實際的法治發展道路。
二、奉法者強與法治國家
習近平法治思想深深扎根于中華法文化的歷史土壤之中,建立在對中國傳統法文化的深度考察基礎之上,實現了對中國“本土法治資源”的深層汲取和批判繼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①習近平:《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 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4日01版。習近平總書記對于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予以高度評價。他說:“先秦時代管仲、李悝、商鞅、韓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就影響深遠。我們的先人留下了豐富的法制思想,‘奉法者強則國強’、‘法約而易行’、‘法不阿貴’、‘刑無等級’、‘執法如山’、‘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等名言膾炙人口。”②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177頁。
國家治理為什么需要法治呢?早在兩千多年前,先秦法家就提出“事斷于法,是國之大道也”。言下之意,即通過法治的手段來判斷是非和處理事務乃國家治理之術。“法者,治之端也”,強調國家治理的起點就是制定和執行法律。習近平總書記在論及法治對于國家治理的必要性問題時,曾引用先秦法家著名代表人物管子的名言,“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之規矩繩墨也”。就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法律是什么?最形象的說法就是準繩。用法律的準繩去衡量、規范、引導社會生活,這就是法治。”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8頁。他還強調,“法律是治國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規矩”④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頁。“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⑤《〈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2頁。“人類社會發展的事實證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穩定的治理”。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頁。
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國家治理的過程中,以中華法系作為主要制度形式,逐漸形成了中央集權、君臣共治、三省六部、郡縣制、科舉制、御史監察等行之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這套法律制度體系保障了國家統一、民族融合和社會穩定,體現出“大一統”國家法治的獨特優勢。中華法系的演進史表明,成文法典是國家統一和穩定秩序的象征。凡是中央集中統一的法律制度適用全國、運行暢通,則天下大治、國泰民安;但凡中央集中統一的法律制度形同虛設、有法難行、執法不公,則必然導致國家貧弱、社會動亂和政權崩潰。這就是古人所言“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治強生于法,弱亂生于阿”的治國道理。
在借鑒中華傳統治國理政經驗的基礎之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闡述了法治與國家興衰的關系,“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什么時候重視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時候就國泰民安;什么時候忽視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時候就國亂民怨”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8頁。。習近平總書記引用法家“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這句話,強調我們必須把依法治國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黨和國家工作納入法治化軌道,堅持在法治軌道上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依靠法治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
三、善法治國與良法善治
從我國古代來看,凡屬盛世都是大規模法典編纂和法制相對健全的時期。傳統國家治理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⑧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強調“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頁。。在中華傳統法文化中,大規模國家立法通常被視為國家統一、社會穩定與良好秩序的象征,還常常被看作是政權建立和朝代遞嬗的標志。故此,又有“律者歷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故自昔國家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律”⑩蘇天爵:《滋溪文稿》,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34頁。的說法。在法律的正義性要求上,古人主張“法不仁,不可以為法”。在法律與社會的關系上,主張“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注重通過順應時代變化的立法來推動制度革新、解決社會矛盾、推動社會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就有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法家主張“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國踐而行之,商鞅為取信于民“徙木立信”,強調“法必明、令必行”,這使得秦國迅速富國強兵、統一六國。漢高祖劉邦與百姓“約法三章”,為其贏得民心、統一天下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在漢唐時期就已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法典,漢武帝時期漢律已有60篇,兩漢沿用近400年。唐太宗奉法為治國重器,一部《貞觀律》成就了“貞觀之治”。《唐律疏議》是中國古代代表性的法典,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
在新時代的法治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立法質量和法典編纂工作,提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11]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285頁。,強調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民法典編纂工作,親自主持3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分別審議民法總則、民法典各分編、民法典3個草案。民法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制定和編纂時間最長的法律,是唯一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第一部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的法律。習近平總書記專門指出,民法典是一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
良法善治的前提是“良法”,關鍵是法律實施,即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我們的古人除了強調立“善法”,還要求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12]《〈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頁。這句話,指出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實施、束之高閣,或者實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的法律也無濟于事。他還引用管子“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13]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46頁。這段話,進一步對法律實施的公正性要求作出解釋。即法度必須公正,不公正則判案不公平。判案不公平,治理就不合理,事情就不應時。治理不合理,老百姓就無法伸冤。老百姓無法伸冤,民間就會騷亂;事情不應時,功利實業就不能興辦。功利實業不能興辦,國家就會貧窮。因此,首先要通過科學立法制定出“良法”,然后做到對“良法”的嚴格執行、公正適用與普遍遵守,唯此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的“善治”。
四、民惟邦本與“以人民為中心”
在中國傳統的治國理政實踐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占據著重要的指導地位。其核心要義就是,尊民愛民是國家治理之大道,統治者要施愛民之仁政、重視人民力量,執政者“德莫過于愛民”,鞏固政權關鍵在于“得民心”“順民心”,國家的興衰成敗取決于民心向背。在君民關系上,儒家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把君主比作“舟”,把人民比作“水”,并且深刻闡述二者之間“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依存關系。在社會生活中,注重對民眾的道德教化和告誡,強調對民眾“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主張“以法為教”,反對“不教而誅”。在司法過程中,主張“寬宥慎刑”“慎重人命”,主張對法律條文和律典從天理、人情、國法相互結合和觀照的層面予以解釋和適用,注重運用儒家倫理來對社會成員的行為與價值理念進行引領和整合。
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源于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但又實現了對其的歷史性超越和升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等等,都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值得我們傳承。“以人民為中心”涵蓋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本質屬性與基本立場。它強調法治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在依法治國的過程中,我們要通過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通過全面依法治國增添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獲得感,通過法治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增進人民福祉。
五、禮法結合、德法并濟與法德共治
西漢之后,在借鑒秦朝“專任刑法”“用刑太極”以至于失天下的教訓基礎之上,封建統治者開始既重視法律的懲戒作用又強調德禮的主導作用。禮法結合、德刑兼施、經律互用逐漸成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唐朝將“禮法結合”“德主刑輔”轉化為國家治理的基本原則,主張“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唐律疏議》就是一部“出禮入刑”“明刑弼教”的中國古代法典的典范。縱觀中國古代封建國家治理的歷史,“德”與“刑”相輔相成,德法互補、綜合為治的法文化傳統綿延不絕、相沿不改、歷久不衰。這是中華傳統法文化獨具特色的思想內核,反映了中國傳統法律觀、道德觀的鮮明特點。
習近平法治思想實現了對中華“德法互補”“共同為治”文化傳統的揚棄與升華,強調在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過程中“法治與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這既是對中國傳統治國理政經驗的總結,也是對國家治理現代化規律的深刻把握。習近平總書記專門指出,我國歷史上有十分豐富的禮法并重、德法合治的思想,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值得傳承。周公主張“明德慎罰”“敬德”“保民”;孔子提出“為政以德”,強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荀子主張“化性起偽”,提出“隆禮重法”;西漢董仲舒提出“陽為德,陰為刑”,主張治國要“大德而小刑”。盡管古人對德法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盡相同,但絕大多數都主張德法并用。
結合新時代國家治理與法治建設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了法治與德治二者的辯證關系,提出“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必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法律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基礎,只有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礎的法律才能為更多人自覺遵守。因此,要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通過國家法律強制性規范社會行為、懲罰違法行為,能夠引領社會道德風尚、確保人們的道德底線。
六、為政在人與依法治國的“關鍵少數”
中國傳統法文化注重治國者的道德品質與從政能力對于法律執行的重要意義,主張“為政在人”“為政以德”“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在為政者的道德自律與社會示范方面,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具體到法治實踐,荀子提出“有治人、無治法”的觀點,強調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離不開“人”的因素,要求為官者、執法者要清正廉潔、光明正大,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民以吏為師”的帶頭示范作用。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強調法律要發生效力和發揮作用必須仰仗于執法者的品德修養與行動能力。
關于執政者在法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與社會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14]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54頁。這句話,強調依法治國必須有一支德才兼備的高素質人才隊伍。他指出,領導干部尊不尊法、學不學法、用不用法,人民群眾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并且在自己的行動中效法。領導干部尊法學法守法用法,老百姓就會去尊法學法守法用法。領導干部裝腔作勢、裝模作樣,當面是人、背后是鬼,老百姓就不可能信你那一套。因此,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他們對法治建設既可以起關鍵推動作用,也可能起到致命破壞作用。他們的法治思維水平與依法辦事能力如何,直接影響了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領導干部只有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以上率下、厲行法治,才能推動在社會上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和氛圍,人民群眾才會在耳濡目染中養成遵紀守法的行為習慣。
人類法治文明的發展進程啟示我們,文化傳統是法治發展的“根基”與“靈魂”。只有從自身文化傳統中汲取有益的養料和強大的精神底蘊,法治才能更好轉化為現代國家治理的智慧和動力,才能獲得全體社會成員源自內心的支持與呵護。傳統是每個時代前行與發展的基礎與資本。現代法治發展不能與過去決然割裂,而是要實現在批判繼承、轉化發展基礎之上的連接和傳承。
在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我們需要盤活古人留下的有益的本土法治資源,推動中國傳統法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提升,尋求法治發展的歷史力量,凸顯中國人的法文化自信,在不忘本來、接續古今之中,賦予中國傳統法文化新的時代內涵,使中華法治文明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為21世紀人類法治文明的進步貢獻新的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