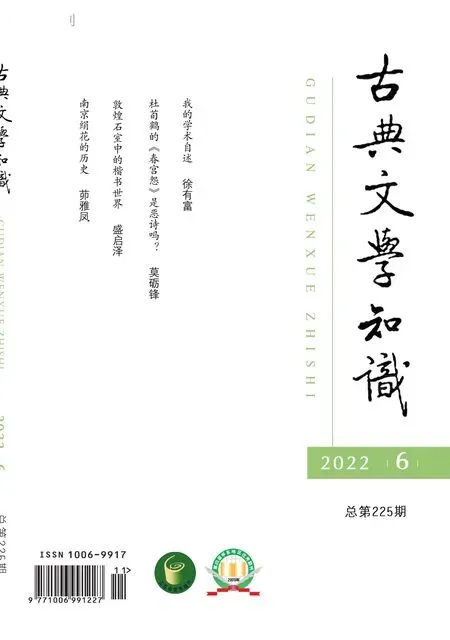我的學術自述
徐有富
我從未慶祝過生日,諸位賢弟多次表示想出一本論文集,以慶祝我八十歲生日,我都堅決反對,認為此舉勞民傷財,有害無益。后來我發(fā)現(xiàn)有人在群里組織先后畢業(yè)的同學寫論文,即嚴加制止。此后就聽不到什么動靜了。誰知最近有人告訴我,論文集已經(jīng)二校,還要我寫一篇談治學經(jīng)歷的文章,編一個論著簡目。事已至此,考慮到諸位出于尊師重教的美意,又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我若一味堅持己見,鬧得大家不愉快,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結果,也就聽之任之了。
我是南京八卦洲初中首屆畢業(yè)生。當時農(nóng)村學生參加中考首選中專,因為上學不要錢,還能早點參加工作,轉(zhuǎn)為城鎮(zhèn)居民戶口。誰知我的一位好友偏要考南師附中,還要我作陪,我頭腦一熱就答應了。幸好我倆都僥幸地被錄取了。
我是1959年秋季進入南師附中的,自然信奉“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金言,不料碰到了“三年自然災害”,食堂伙食越來越差,經(jīng)常用鹽、醬油、白開水和在一起的“三鮮湯”下飯。為了減少體能消耗,體育課就是曬太陽。因為饑餓難熬,又缺乏理想,我課余時間便坐在閱覽室里看閑書。看來理工科肯定是考不取了,有個朋友想當文學家,于是我便陪他報考了南大中文系,不過我內(nèi)心已做好了回鄉(xiāng)務農(nóng)的準備。那年我們的運氣真好,班上五位報考文科的同學,居然三位考上了南大,兩位考上了南師。
我們是1962年9月入學的,匡亞明1963年就調(diào)到南大來當黨委書記兼校長。他在我們中文系樹了兩個標兵,一個是青年教師葉子銘,他的副博士論文《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1959年就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影響很大。還有一個是青年教師黃景欣,他的學士論文《秦漢以前古漢語中的否定詞“弗”“不”研究》發(fā)表于《語言研究》1958年第3期,受到一致好評。匡校長言必稱葉、黃,點燃了我們的夢想,于是便各選一個畢業(yè)論文題目忙碌起來。我選的題目是《聞捷研究》,雖然囊中羞澀,也將他的詩集收齊了,而且還在南京古舊書店淘到一本聞捷寫的陜北革命史劇《翻天覆地的人》,是東北新華書店1949年出版的。此外,我也讀了不少詩歌理論著作。遺憾的是接下來,我們?nèi)昙壪聦W期到海安搞“四清”,四年級到溧陽勞動建校,接著又返校參加“文革”,直到1968年夏天,我們又幾乎都被分到邊疆、農(nóng)村、基層、工礦,各人的文學夢便隨之化成了泡影。
我被分配到湖北省陽新縣赤馬山銅礦,先當井下工人,后調(diào)到礦山子弟學校教書。別無他求,于是結婚生子,準備終老于此。誰想到1978年竟恢復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可惜我身邊只有幾本《中國文學史》《古代漢語》教材,別無選擇,我還是硬著頭皮報考了母校古代文學專業(yè)研究生,遺憾的是礦山偏僻,連英語復習資料都找不到,結果自然名落孫山。后來我妹妹在家中翻到了一本我當年在南大學習英語的教材,寄給了我,于是我次年又鼓起勇氣再戰(zhàn),竟然被錄取為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真是喜出望外。
我1979年秋重返母校,算是踏上了治學之路。程先生1980年4月3日與我們談畢業(yè)論文問題,一共出了九個選題。我一眼就看中了《唐詩中的婦女形象》,為此我將《全唐詩》通讀了一遍,還編了分類索引,其中有可能用到的詩都用卡片抄了下來。程先生為研究生開過校讎學、杜詩研究課,為本科生開過歷代詩選、古詩選講課,我都聽過,這對我分析唐詩中的婦女形象當然大有幫助。由于前期工作做得充分,所以論文寫得比較順利,程先生又仔細改過兩遍。后來論文經(jīng)過修改與補充,依據(jù)程先生的建議將題目改為《唐代婦女生活與詩》由中華書局于2005年出版了。如何推動唐代文學研究的深入發(fā)展,將唐代文學與社會背景研究結合起來,無疑是一個重要方面,程先生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拙著顯然也是一例。
論文寫完后離答辯還有一段時間,程先生怕我將這段時間浪費掉了,便提出來與我合寫中國古代名人傳中的《李清照》,并借給我一本《李清照資料匯編》。因為只要寫三萬字,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該書于1982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后,程先生放棄了該書的著作權。后來該書被列入“《中國思想家評傳》簡明讀本”,于2010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字數(shù)增加到六萬四千字。我也寫過幾篇有關李清照的文章,其中《李清照泛舟詞之比較》發(fā)表于《名作欣賞》2019年第11期,被江蘇電視臺城市頻道的一位編輯看到了,她認定我對李清照研究有素,便邀請我去做了一檔節(jié)目,電視節(jié)目播出后,居然被我們高中班主任,已94歲高齡的教語文的夏雁平老師看到了,她非常高興,常與去看望她的學生們提起。
我研究生畢業(yè)后,原先是要分配到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的,記得我在答辯時,該系還特派一位老先生來旁聽。但我還是想留在南京,因為我們兄弟姐妹,一個遠在遼寧丹東,一個遠在新疆塔城,一個遠在云南昆明。當我考取研究生第一次回家看望母親時,臥病在床的母親非常高興,立刻起身為我做飯,還說了句:“冷鍋里蹦出顆熱豆子。”我也很激動,并且寫了首題為《重返南大》的詩,第一段為:“母校,這個詞真好!投奔你,我撲向母親的懷抱。”我如再回湖北,年邁的父母親一定會非常失望。正好當時南大圖書館施廷鏞先生的一位研究生家在武漢,卻被分在南大圖書館,于是我們申請對調(diào)一下,并且獲得了批準,可謂兩全其美。
我在礦山工作了十年,因為讀了研究生,就能回到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而且愛人受到當年的班主任王兆衡老師的關心,很快就調(diào)到了南大財務處,還是挺慶幸的,遂決心努力做好本職工作,安然度日。而程先生還一直在關心著我,先是讓我參與整理《汪辟疆文集》,接著讓我替他為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yè)研究生開校讎學課,并且還推薦我到南師為古文獻專業(yè)本科生上版本學。后來又提出讓我與他合著《校讎廣義》。齊魯書社1988年出版了該書《目錄編》,1991年出版了該書《版本編》,1998年出齊了《校讎廣義》版本、校勘、目錄、典藏四編。該書被專家陶敏譽為“校讎學重建的奠基之作”,王紹曾稱其“為我國傳統(tǒng)的治書之學建立了一個清晰而完整的學科體系”。該書得過不少獎,如《版本編》1995年被國家教委評為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1997年被國務院評為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校讎廣義》1999年獲得第四屆國家圖書獎等。《校讎廣義》還于2020年由中華書局出了修訂本,對原書做了不少正誤與增補工作,質(zhì)量又有所提高。
南京大學于1978年恢復了圖書館學專修科,復于1985年恢復了圖書館學系,后更名為信息管理系,我自然也就成了專職教師,并于1987年被評為副教授。我于1988年申請到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古典文學史料學》,該項目完成后于1992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為我國古典文學領域第一部史料學著作。正如專家曹培根在書評中所說:“該書除了像通常的史料學著作那樣詳盡介紹重要史料外,還將史料學研究拓展到了史料搜集、鑒別、整理和檢索利用的新領域。”該書修訂本還作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guī)劃教材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于2008年再版,并且重印過。
我在教目錄學的過程中,覺得鄭樵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他不參加科舉考試,畢生從事學術研究,不僅努力讀盡天下之書,而且重視社會調(diào)查,主張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并且身體力行。如“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相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他知識廣博,在經(jīng)學、語言學、史學、自然科學、文獻學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他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往往能提出獨到見解,頗能給人以啟發(fā)。于是,我對他作了個案研究,撰寫了《鄭樵評傳》,該書在吳新雷教授的支持下,被列入“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南京大學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這一時間段寫的論文,后來匯編成《文獻學研究》(與徐昕合著)于2002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我在信息管理系多年擔任副系主任,教學、科研、行政工作都很賣力,但職稱就是上不去,當時該系說話起作用的某教授要求嚴格,《校讎廣義》之《目錄編》與《版本編》因為我排名第二都不能算科研成果。我好不容易申請到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他還寫信舉報,說老師偏袒自己的學生,評審不公。實在混不下去了,我只好找時任中文系主任的胡若定教授,請求調(diào)入中文系,想不到他一口答應,并于1995年5月很快就辦成了調(diào)動手續(xù),我還于次年春天評上了教授。不久,中文系要我擔任教學副系主任,自不便拒絕。
回到中文系,我不能影響其他老師的工作,所以想為研究生開一門新的專業(yè)基礎課。南大中文系素有注重研究方法的傳統(tǒng),打開《汪辟疆文集》,我們首先看到的就是《讀書舉要》《工具書之類別及其解題》《讀書說示中文系諸生》等一組文章。程千帆先生的《治學小言》當然是專門談治學方法的。周勛初先生承擔過一個課題,題為“現(xiàn)代學者治學方法研究”,并形成了一本專著《當代學術研究思辨》。于是我于1995年秋季開了“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課,旨在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新意識與科研能力,讓學生了解學術研究與論文寫作的規(guī)范,使他們在選題、查資料、社會調(diào)查,以及讀書、寫讀書筆記、鑒別資料、寫論文等方面得到初步訓練。其教材于2003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印過數(shù)次。后來經(jīng)過修訂,更名為《學術論文寫作十講》,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于2019年再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nèi)就印了3次,可見還是很受歡迎的。
我1998年3月被評為博士生導師,莫礪鋒隨即分一位博士生讓我指導,并提出與我合帶博士生,要我側(cè)重于宋詞研究。我雖然寫過通俗讀物《李清照》,但是哪敢指導古代文學專業(yè)博士生。考慮到我對古典文獻學熟悉一點,于是與俞為民教授、蔣廣學教授一起申請了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點,并于1999年獲得了批準。我為該專業(yè)博士生上的課程是“中國目錄學史”,并且以之申請了一個高校古委會項目。我覺得目錄實際上是記錄人類精神財富的數(shù)據(jù)庫,中國歷代目錄實際上就是中國學術史的縮影。目錄的分類、著錄項目及其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書目的序,以及按語等,都能客觀而集中地反映各時期學術的發(fā)展變化。我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講這門課的,所以該書200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時名為《目錄學與學術史》。
我還想為中文系本科生開一門課。程先生為南大中文系本科生上過兩次《古詩今選》,受到熱烈歡迎。之后似乎就沒有人上過類似的課程。我一直喜歡詩歌,早在赤馬山礦子弟學校任教時就寫過六萬字的《詩歌泛談》,讀研究生學的又是唐宋詩專業(yè),畢業(yè)論文名為《唐詩中的婦女形象》,于是便為作家班與本科生開了“詩學研究”課,還挺受歡迎的。經(jīng)過多年打磨,取名為《詩學原理》,投給北京大學出版社,想不到竟于2007年出版了。該書《開頭的話》說:“本書不僅要對詩學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而且要為詩學理論的普及與通俗化貢獻一點力量。”“本書不作純理論的探討,而是通過對作品的具體分析來說明問題。所引用的詩歌作品,既包括古代的,也包括現(xiàn)代的。將我國詩歌的精華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是本書的重要任務。”北大出版社于2017年還出了《詩學原理》第二版,該版從詩的內(nèi)容說到詩的形式,從詩的創(chuàng)作說到詩的鑒賞,從而構筑了一個完整的詩歌理論體系。
《古典文學知識》從2005年第3期至2007年第7期連載了我的《中國詩學原理講座》,產(chǎn)生了較大反響,例如豆丁網(wǎng)附注道:“關于該文檔,轉(zhuǎn)帖至人人網(wǎng)、QQ空間、新浪微博、騰訊微博、開心網(wǎng)、飛信,分享到WSN、豆瓣。”有位網(wǎng)友還談了他將《詩的構思》一講發(fā)到網(wǎng)上的過程:“好冷啊,今天先打這么多吧。實在是打得有點慢,不過慢點我自己也可以多記住一些。”“打一段,發(fā)一段,天氣實在是太冷了。希望對大家有幫助,而不是無用之舉。”該講座后來輯為《詩歌十二講》由岳麓書社于2012年出版了。這些應當說,都是我為本科生上詩學研究課的產(chǎn)物。我在本科聽文學概論課時,就想寫一本詩學概論,學生時代的夢想終于實現(xiàn)了,這當然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在職期間,我還寫過一本《聞一多》,當時江蘇文藝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外名人傳記叢書”,責任編輯于奎潮聽過我的課,可能覺得我對新詩還比較熟悉,就將這個選題交給了我。我學生時代喜歡新詩,而且特別喜歡聞一多,所以就愉快地答應了。憑借南大圖書館與中文系資料室的豐富資源,我順利地完成了任務。學生時代在新詩方面所下的功夫,能偶然獲得一點收獲當然很高興。不過聞一多《紅燭》詩云“莫問收獲,但問耕耘”,境界更高,更值得尋味。
我是2008年9月退休的,程先生在一封信中說:“退休后精力未衰,可做自己想做之事,此最是人生佳境。”我首先將詩學方面的論文,編成《詩學問津錄》于201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其中《簡談宋詩中的議論》是我讀研究生時寫的,因與某權威意見相左,一位室友勸我說這篇文章如發(fā)表,你從此就沒有好日子過了。我還是將它交給了程先生,受到程先生的推薦,該文曾以首篇位置發(fā)表于《南京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81年第6期復以首篇位置全文轉(zhuǎn)載。還有一篇《古典詩歌中的“綠”字》,也是我交給程先生的一篇作業(yè),受到推薦,發(fā)表于《長江文藝》1982年第1期,程先生為我埋下了一粒種子,我在退休后寫了不少讀詩札記,即萌芽于這篇文章。我自己比較滿意的是《“望南山”與“見南山”》,也收在這本書中,可以參看。
我將論文集《文獻學研究》之外的文獻學論文匯編成《文獻學管窺》,由鳳凰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了。書中有篇《南京大學圖書館孤本方志敘錄》還有點故事。我是程先生來南京后所指導的一個年齡最大,學歷最低,自愿從事圖書館工作,喜歡安然度日的學生,但是程先生還要繼續(xù)指導我,該文的題目與體例都是程先生定的,成稿后,程先生又作了精心批改。文章改好后,前輩魏德裕先生因為與來新夏先生是中學同學,特地幫我推薦給了來先生,不過一直沒有消息。后來我聽周勛初先生說,有次他到天津開會,程先生還專門托他向來先生問過此事,我深受感動。魏先生退休多年后,我們偶然相遇,他告訴我他在整理信件時,發(fā)現(xiàn)有封來新夏先生的回信,內(nèi)容是問我是否愿意將該文發(fā)表在某刊物上,遺憾的是此事已過去了二十多年,只好作罷。2015年,我應邀參加“《南京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新書發(fā)布會暨地方文獻整理座談會”,我在發(fā)言中提到了這篇文章,想不到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先生立即為國家圖書館所創(chuàng)辦的《書志》叢刊向我約稿,該文終于得以發(fā)表。此事讓我體會到程先生會帶學生的主要原因是他愛學生。同時也讓我體會到從事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需要花功夫,而功夫決不負有心人,只要你辛勤耕耘過,就會有收獲。
我還將過去寫過的詩編成《徐有富詩鈔》,由河南文藝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我與詩的這點緣分,尋思起來,還與我姐姐有關。她畢業(yè)分配到東北后,將一本中專《語文》教材留在家中,書上有聞一多、艾青、田間、何其芳等人的不少詩作,我無事就經(jīng)常翻翻,無形中便受到了一些影響。我到城里讀高中,成績平平,一無所長,還是挺自卑的。記得有回在作文中插了一首順口溜,想不到實習老師邢道成在作文講評時,對我的順口溜大加贊揚,使我稀里糊涂地愛上了詩。這個愛好一直保持到大學,1963年3月26日,班級組織了一個主題班會,要我也發(fā)個言,我朗誦了一首詩,即詩集中的《我要怎樣做人》,當時頗獲好評。不久系里組織了詩歌創(chuàng)作朗誦欣賞晚會,班上便推薦我參加。我深受鼓舞,于是一天到晚就是寫詩、讀詩、研究詩,有時到了寢食難安的程度。集中有些詩現(xiàn)在看來已不合時宜,但當年為時代潮流裹挾所濺起的一點浪花,也許還有些史料與認識價值。因為這些詩畢竟比較真實而完整地記錄了一個普通知識分子數(shù)十年來的心路歷程。集中有《老牛》一詩或可視為我的寫照:“田間一老牛,負軛朝前走。舉步雖遲緩,就是不回頭。”
再就是為《校讎廣義》《中國古典文學史料學》《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詩學原理》等書作了修訂工作,都在原有的基礎上朝前邁進了一大步。國內(nèi)外一些著名出版社都非常重視出版修訂本,這實在是不斷提高圖書質(zhì)量的有力措施。我的做法是發(fā)現(xiàn)書中錯誤及時糾正,遇到參考資料就在書上加批。如有機會,我將繼續(xù)做所撰論著的修訂工作。
退休后我還編著了一部《程千帆沈祖棻年譜長編》,由南京大學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陶蕓老師、程麗則大姐、礪鋒兄都有意讓我編撰程先生年譜,作為學生,我自不便推辭,在編寫的過程中,程麗則將《程千帆日記》《陶蕓日記》借給了我。吳志達先生在武漢大學檔案館將沈祖棻自傳及干部履歷表等材料的復印件寄給了我,南京大學檔案館為我查閱程千帆名人全宗提供了方便,諸位同門學友及賢弟子或提供材料,或回答問題,都幫了很大的忙。我還特地到學校申請了寬帶遠程接入服務項目,在一些報刊數(shù)據(jù)庫中查到了不少新資料。在年譜寫作方面,我也作了一些探索,首先是寫了九萬多字的《前言》,對程千帆、沈祖棻的成就作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紹。其次,在年譜目錄中,為每一年都用極短的文字寫了內(nèi)容提要,還在征引文獻中,羅列了《程千帆全集》《沈祖棻全集》未收的作品目錄,此外,于書末附了《人名、字號、別稱索引》,不少人都夸贊該年譜內(nèi)容豐富,使用方便。
退休后,我還撰寫了《千家詩賞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復由中華書局于2018年再版。起初有位同事應約承擔了該書的寫作任務,當時他還沒有退休,需要為核心雜志寫文章,于是就推薦了我。考慮到我是學唐宋詩的,承當這項任務等于重新獲得一次學習唐宋詩的絕好機會,遂爽快地答應了。誰知我即將完成時,責任編輯另有任務,要我與另外一位編輯對接。但是,我聯(lián)系了兩次都未聯(lián)系上,只好作罷。于是我根據(jù)偶然獲得的一張名片,將書稿寄給了上海古籍出版社試試,想不到該書竟很快出版了。合同剛滿,中華書局的編輯即表示愿意再版。其實,《千家詩》雖然是一本通俗讀物,我在考證作者、校訂詩題、分析作品、探討詩的內(nèi)容與藝術特色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而且很難找到錯別字。看來如果選題對路,書的質(zhì)量又有保證,出版社還是愿意接受的。
退休后想做的還有一件事,就是寫《南大往事》。該書2018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當了幾十年的教師,還連續(xù)擔任過南大圖書館學系與中文系的教學副系主任,退休后還當過多年學校督導,對教學工作略有體會,遂利用學術散文的形式,通過一些老師和學生的教學與科研活動來探討與揭示南京大學人文學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這些文章陸續(xù)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報》《南大校友通訊》《南京大學報》《古典文學知識》《江蘇文史研究》等報刊上,苗懷明教授所主持的中國古代小說網(wǎng)予以重新編輯連載,被南大校友、時任江蘇人民出版社社長徐海看中,列入選題。該書出版后,南京大學宣傳部與江蘇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5月19日在南大文學院召開了新書發(fā)布會;《南京大學報》《現(xiàn)代快報》《揚子晚報》《社會科學動態(tài)》等都作了報道與評價。《光明日報》7月22日“悅讀”欄目還發(fā)表了拙作《把培養(yǎng)學生放在第一位》。江蘇人民出版社還借上海書展之機,于8月20日安排了一場學術報告會,讓我談《〈南大往事〉的現(xiàn)實意義》,報告會由徐海主持,中華書局總編輯、南大文學院校友徐俊到場,會后還舉行了簽名售書活動。可見,此書反響熱烈,頗受重視。這表明,學術研究應當關注現(xiàn)實生活的需要,而表達方式本應當豐富多彩,不必千篇一律。
我目前在編《先唐別集知見錄》,程先生說過:“每一個同志最好有機會做一做這種最艱苦,最枯燥,最沒有趣味的,像做年譜、考訂、校勘、編目這樣的工作。”我便于1996年申請了一個項目“先唐文集別錄”,三年時間一到,便勉強結了項,遠達不到出版水平。迫于教學、科研、行政工作的壓力,只好將其擱在一邊。直到2008年退休后,想起“言必信,行必果”的古訓,我又將該課題撿了起來。等該課題完成后,我將適應廣大讀者的需要,嘗試采用大家喜聞樂見的形式,寫一些具有學術含量的詩學普及讀物。下面就以我的一首詩作為結尾,題為《銀杏葉》:“金黃金黃的銀杏葉/還舍不得與大樹告別/在成排成排的大樹上/我們是千萬只黃蝴蝶/為了豐富秋天的色彩/我們作了最后的努力/即使飄落到地上/我們也是金黃金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