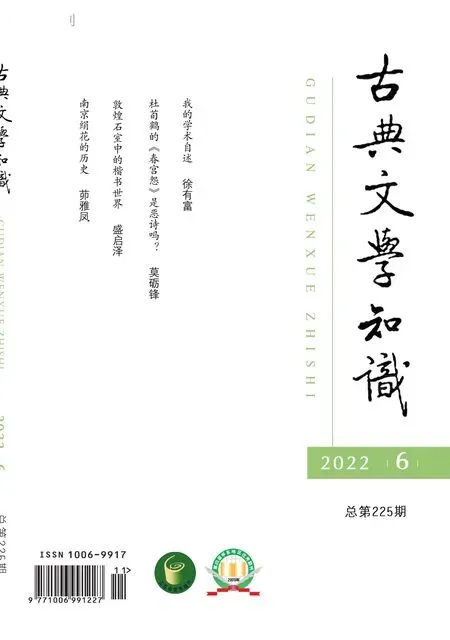杜荀鶴的《春宮怨》是惡詩嗎?
莫礪鋒
杜荀鶴的《春宮怨》是其名作,“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更是其中名聯,宋人畢仲詢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唯宮詞為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唯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幕府燕閑錄》)清人賀裳則云:“《春宮怨》,不唯杜集首冠,即在全唐亦屬佳篇。”(《載酒園詩話又編》)此詩或謂乃周樸所作(詳見歐陽修《六一詩話》),但據佟培基先生所考,此詩首見于《唐人選唐詩》中的《又玄集》《才調集》,皆署杜名,故理應歸于杜荀鶴名下。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是,有人力排眾議,稱此詩為“惡詩”,是否有理?
清人王夫之云:“晚唐饾湊,宋人支離,俱令生氣短絕。‘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醫家名為關格,死不治。”(《姜齋詩話》)又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詞相比而事不相屬,斯以為惡詩矣。”(《古詩評選》)“關格”是中醫學名詞,意即“死癥”。那么,在王夫之的眼中,《春宮怨》的中間二聯,尤其是其最負盛名的頸聯,究竟患了什么不治之癥呢?王夫之指出的病癥是“晚唐饾湊”,這是否說中了此詩的病根?
“饾湊”即堆砌雜湊之意,王夫之論詩好用此詞,比如他批評韓愈云:“若韓退之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湊之巧。巧誠巧矣,而于心情興會,一無所涉。”(《姜齋詩話》)筆者曾在拙文《論韓愈詩的平易傾向》中指出王氏對韓詩的批評僅適用于少數韓詩,且引葉燮之言為證:“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崚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獨善于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原詩》)如果說王氏對韓詩的批評是以偏概全,從而導出偏頗之論,那么他對《春宮怨》的貶斥就是只見皮毛,從而良莠不分。“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為何是“詞相比而事不相屬”呢?從此聯自身來看肯定是毫無道理,因為上、下句均是描摹風和日麗、鳥語花香之春光,渾然一氣,絕無“事不相屬”的可能。王氏所云,當是將此聯與上聯合而觀之。他可能認為上聯寫宮人失寵,意緒悲切,而此聯卻喜氣洋洋,兩者互相矛盾,故為“饾湊”,乃成“關格”。王氏也可能是將此聯與全詩合而觀之,既然整首詩是寫春日宮人之怨,而此聯卻寫春光明媚可喜,毫無怨意,故而“詞相比而事不相屬”,全篇遂成“惡詩”。如果這樣的推測屬實的話,王夫之對此詩的指責可謂無的放矢。詩題“春宮怨”,也即春日之宮怨。被幽禁在深宮里虛度光陰的宮女心懷怨恨,一年四季并無差別。正如白居易《上陽白發人》所云:“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寒風蕭瑟、陰雨連綿的秋季當然使宮女滿懷悲傷,陽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春季又何嘗能讓她們心懷喜悅?年復一年,春往秋來。宮女們既悲秋,又傷春,“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的情景又怎會與“春宮怨”的主題有所違礙,怎會“詞相比而事不相屬”?況且王夫之本人說過:“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姜齋詩話》)“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正是“以樂景寫哀”一個范例。俞陛云解曰:“五句言天寒鳥聲多噤,至風暖則細碎而多。六句言朝暉夕照之時,花多側影。至日當亭午,則駢枝疊葉,花影重重。用‘碎’字、‘重’字,固見體物之工,更見宮女無聊,借春光以自遣,故鳥聲花影體會入微。”(《詩境淺說》)況且“風暖”“日高”的明媚春光定會使宮女深切地感受到自家的青春年年空度,這是刻畫宮女內心愁怨的神來之筆!從全詩來看,首聯寫宮女的心態,由于被美貌所誤(多半是蛾眉見嫉),故無心梳妝。頷聯進一步抒寫宮女之心思:既然未能以美貌而承恩,那又教我如何修飾儀容呢?清人賀裳評此聯曰:“此千古透論。衛碩人不見容,非貌寢也。張良娣擅權,非色勝也。……讀此,覺義山之‘未央宮里三千女,但保紅顏莫保恩’,尚非至論。”(《載酒園詩話又編》)頸聯轉寫宮中春光明媚,從反面襯托宮女之苦悶無聊。尾聯宕開一筆,從眼前之春光回憶起進宮之前與女伴采蓮于越溪的樂事,如今只能年復一年地付諸空想。清人何焯評尾聯曰:“入宮見妒,豈若與采蓮者之無猜乎,落句怨之甚也。”(《瀛奎律髓匯評》)四個層次環環相扣,逐步深入,將“春宮怨”這個主題刻畫得淋漓盡致,前引畢仲詢、賀裳對此詩的高度贊譽,誠非虛言。王夫之所謂“晚唐饾湊”,真是從何說來!
況且此詩還有更深一層的意蘊。徐子擴評云:“此詩為久困名場而作,于六義屬比。士之才猶女之色也,故托以自喻,極為切至。五、六一聯,見得意之人,紛紛乘時而喜悅者眾也。末言己雖失意,年年隨計,志猶未已,亦可嘆也。故思其友之同事者為言。”(《才調集補注》)清人黃生則云:“此感士不遇之作也。才人恃才,不肯僥幸。茍得而幸獲者,皆不才之人。是反為才所誤,故為憤而自悔之詞。借入宮之女為喻,反不如溪中女伴,采蓮自適,亦喻不求聞達之士,無名場得失之累也。”(《唐詩摘抄》卷一)俞陛云亦云:“此詩雖為宮人寫怨,哀窈窕而感賢才,作者亦以自況。失意文人望君門如萬里,與寂寞宮花同其幽怨也。”(《詩境淺說》)這些意見雖然不盡準確,但指出此詩含有自況意味的結論卻是可信的。筆者完全認同劉學鍇先生對此詩的總結:“唐人的宮怨詩多數未必有寄托,但杜荀鶴的這首《春宮怨》則明顯是有寄托的。‘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正揭示出宮女與文士在命運上的相似性,以及托宮女的怨情以寄寓才士之不遇的藝術構思的合理性。但這首有托寓的宮怨詩的好處,卻主要表現在將宮女的怨情寫得非常真切細膩、婉曲含蓄,富于生活實感,毫無有些托寓之作從概念出發,用類型化的比喻,表達固定化的意旨,缺乏生活氣息的弊病。即使完全當作一首單純的宮怨詩來欣賞,也是一首優秀之作。”(《唐詩選注評鑒》)
王夫之本是一位眼光極高的詩評家,然而智者千慮或有一失,他對此詩的評價則是將璞玉看成了頑石。所以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否定王夫之的論斷,杜荀鶴的《春宮怨》是唐代宮怨詩中難得一見的佳作,根本不是“惡詩”!